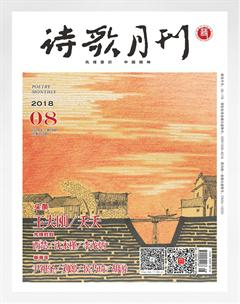主编荐语
好的或上乘的现代诗歌读起来是有气息感的:它是舒缓、澄明、幽远、有韵,可以让人低吟的,气息是一种向上升腾或攀援的物质,或是弥漫在文本里的生动,有气息的文本是有生命活跃感的。我喜欢可低吟的诗,推崇能把诗写到有气息、有韵致的纯粹之诗。
其实,这样的诗难写,写过了就是“自说白话”的“自我呢喃”或“梦呓”,写浅了就是一杯“白开水”,寡淡无味。它需要诗人在创作时心静如水,又神接八极,按下起伏的峰谷,走向微澜。
诗人王夫刚说自己“放弃了抒情功能,强化作品的理性色彩,在輕声的说。”在轻声地叙说中,他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歌美学建构。他的诗章里流动的是淡淡的忧愁。这组诗里,让我看到一个严肃且理性的知识分子在关注和凝视已逝和将逝的一切,比如“山东之东”“村庄”“桃园”“公社”,以及“纺织厂”和“青春”,当然还有祖母等亲人。向已逝的时代、岁月和人生作别或吟唱挽歌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如何写出深层次的思考和引发他人共鸣的作品,是考验作家优劣的一个标准。王夫刚有西方哲学和传统诗学打底色,加之他的独特思考和发现,使他的诗句精致、沉着、坚忍,有穿透力,同时,他的诗又不是呐喊式的,只是轻轻的诉说,这是诗歌写作的一个高的层次:“诗歌的脸应该是安静的,聪明的读者在安静的表象下可以出色地看到智性与心所有的游戏。”这好像是扎博洛茨基的话。
诗人夭夭是灵性且沉重的诗人,她的诗歌没有女性诗人的作品一般性的灵巧和艳腻,她不动声色地打量一切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细微变化本身的哲学定义,她目光里的“高速公路”“缺席者”和“梯子”以及“天黑以后”,所有的日常生活背后的东西,都有喻指,都有微言大义的表达。她也不去抒情,只是用语言魔杖,点明隐在事理深处的真相和悖论,以及事理的复杂性,残酷性和多义性。
我不知道天天是否读过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关于生命中的爱与痛,她们的诗行里跳动着一样的心声,有一种宏阔的大器。天天不是“室内抒情”,她是传统汉语的诗学表达,她写的是中国当下的事物发展和社会进程中诗人自己的发现。她的诗歌在饱含了对个体生命的体验,特别是对生命的伤痛体验,她却能够把一些沉重的话题处理得举重若轻,具有诗歌的质感和灵动。她的诗歌气息仿佛也可以说是“轻轻的”。
好的诗歌是要有气息感的,这是好诗的标准吗?当然不仅如此,也不是唯一。
——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