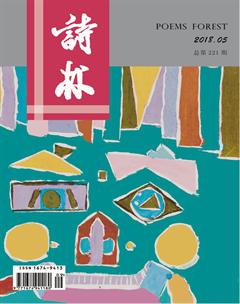吴勒诗选
相对好的方式
1
“褪雪日——”他默念。刺眼的透明
在山脊上游移,今夜依旧是寒凉之夜。
由此,他想起自身逼仄的格局:只是
行走在地面上、空气中,或作为姓名
籍贯的任意一笔,该穿上它的要义?
2
另一个他,尚不能自如行走。月台上
渐次扬起的异地口语,将他推往云层
的秩序:薄荷烟的贩卖者,最为机警
而后是窗边的骑手,唆使曼妙的冷气
将海面缚紧;他因此免于沦为坠网者
3
你收伞、下扶梯。或原谅我的晚归,
指认我们相似的境遇。“还不至太晚
指缝的琴键轻捷。”遂探向一条岔路
雾霭将歇,我们将愈加清癯,且否认
薄荷:作为幻术的一种,与季候周旋。
2018.1 一次晚归
泛 舟
我们怀着黑色的精神,鱼也如此
一个断树桩举起苍白的手告别。
——S·普拉斯
傍晚打烊前,我们匆匆把船
引向湖心;想起从前少雨的季节
我们把旗子摇上去,又摇下来
有时也只是装个模样,显然
并没有人真正看着,或停下来
交出时间,像做一次晚祷
更多时候,只是遐想一片
滑翔伞,月牙船,载我们从楼顶
安全降落。三层楼,俯视那么
稀少,一屋子绝无仅有的空气
此刻都被咽进船舱;湖水冰冷且绿
仅是看起来,周遭比任何日子
更真空,而你感到坦荡:
家在搐动,而不是你自身,这显然
不同于以往——那些好命的酒客
把词语撒在岸边,而你在湖中
并没有牵累他们的企图。间或想起
练习簿上:零散、未署名的语录
应该复写它。合上就忘了。
码头边《水手》准时奏响,而你的
父亲,你知道,他看过许多身体
不愿再看了;他看一片消退的晚景
透过玻璃隔间,他看见雨滴,并不总
在落,而是轻微地浮起。
2017.5
凫 水
事出无由,夏日。江心洲的喷泉
开始疲于重复,它们善于扯谎的汽笛
正撑开一把纸伞,等候凫水归来者。
再晚一些,浅水藻类便会张开,吞吐
气泡,在我们瞳孔立足;而赴死的行动
像每日晚餐般自然。亦栽种一些水,
柔软的搏击,走入迷途之际无一例外
成为季度的翘楚,相继接受质询,并
随弦乐队唱进夏日之夕:“泾流之大,
两诶渚崖之间,不辩牛马!”凫水者
只是不断下坠的樱桃红,测量彼此
莫须有的僭称;岸边,两只空瓶
兀自敞开,遂被暮色收割。
2017.8
宇宙滴眼液
听闻锁钥的窸窣声,我们佯装入睡
扭开滴眼液。顷刻,皈依于夜间沁凉。
远景倏然而至:一时间,簧管的合唱
透过锁孔,夜色又浸染在浓雾中。
你说:“黄公望来了。”是的
我也看见——暗语——浅绛色
警备员,将我们敞开在另一个平面
彼处,瞳孔洁净的舞蹈同履历册
是两码事。无须张口便能滑翔,向
柑橘芬芳的十一月;而一切会好起来,
宿醉只是去往银河铁道①途中的事。
于是我们架好相机,遁入沉沉雨水
——更像一对搭档,或蹑足的烟草商。
我们约好不再说丧气话,并熟稔
宇宙也可能是脚底的小小舢板:
途经桥头堡,还要渡我们过浅滩。
2017.10
①宫泽贤治童话《银河铁道之夜》。
花屋敷①
只是为了享乐,便铺张
这样的色彩。偏安一隅的
风景每时每刻更新,吐出帆板
降落在果篮:一种美好凭藉
长久隐于坊间。
反复,再俯冲——
“别尽提一些馊主意!”
像活人一样活,像恋人一样
渴望来信。对话之苦
无始亦无终;狭长甬道
沿途,隱私的奥义是伞
而我们已开始疏于
惊呼——坐下时,我们
是并置的一对,并呈现
消逝的速度。月台撤退林中
搜寻近处的猎手,缆车
可以再次触动边境
异乡之歌;片面的
乐土,却是人间乐园。
2017.10
①东京浅草,一处小型游乐场。
短 评:
我时常有种简洁印象(是错觉也未可知):比我稍年轻几岁的诗人们起笔更加恣意无焦虑,文字符号的内爆缘起于偏旋的语言决心,陌异情境让人痴爱于幻美。吴勒则从保守中取得要义,法相庄严,稳中求进,把酷炫限制在内敛却并不忸怩的刚柔相济里(他写“已确认好了/巨幅的爆破在我们身后”)。他吟唱的声线低调奢华,自带降噪功能,不至在读者既有的耳廓中侵略或者碰瓷。他诗中暗涌的生命假设轻盈化解了生活实感的艰涩,语流弹性化了现实激流的执拗,这可能跟他“莫须有的僭称”的态度合拍:他和语言的商谈终于进展到化敌为友的地步,某种程度上,这已难得地模拟出诗歌的难得的真实。
——秦三澍
(译者,巴黎高师文学博士候选人)
吴勒的语言,肌肉放松,很少展示力量,至多也只是“柔软的搏击”(《凫水》),然而质密,想要刺破其密语,是困难的。他从来只需要少量的情绪,把它们稳住在手边,“雾霭将歇,我们将愈加清癯”(《相对好的方式》)。他从来不会勉强给出他所没有的,从来不虚张声势,所以隐隐中可以感受到他的限度。在这个限度内,他可以深不可测。此外是散布语句的玲珑物件:果篮、相机、滴眼液、薄荷烟,也被赋予了玲珑感,这些“美好凭藉”(《花屋敷》)宛如开关,总是能有所触发,制造浅色调的惊喜。
——羊须(青年诗人)
吴勒的诗总是在整饬、平衡的结构中,为我们展现一种朦胧却不失细腻的氛围,我们常常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与他生活紧密相连的抒情场景,无论我们在看到这些撷取的记忆枝叶时,是回报戏谑“噗,又是薄荷烟”,还是因他赋予了我们熟悉的事物以新的清丽而不禁莞尔,他的诗歌写作都没有使他离读者越来越远,即使是他那一贯疏离又克制的语调,也从不指向冷漠;相反,他灵动的情感一直以其自身的节奏和韵律生长在诗行间,带给我们清甜却不黏腻的温柔。
——梨姜
(南京大学重唱诗社第17任社长)
“平地神仙,清凉世界,君曾知否。”吴勒诗歌叙事和抒情的主人公是一个“皈依于夜间沁凉”(《宇宙滴眼液》)之人,其诗歌也在平稳而精致的叙事中重构了通往清凉世界的“幻术”或“操纵术”。被“籍贯”和“履历册”所归驯的日常生活乏味而逼仄,诗人敏感的官能却能够捕捉沁凉,“探向一条岔路”,敞开一个异质的空间,从而使诗歌中的“我们”“免为坠网者”。一场场幻术传达的是诗人极端私人化的生命体验,而诗人也在这样的体验中得以确认自己是“绝对安全”的。
——卡珀(青年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