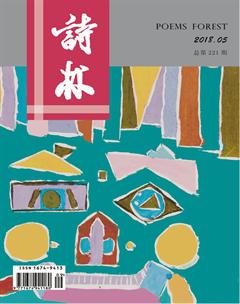任白的诗
任白,1962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曾出版诗集《耳语》、中短篇小说集《失语》。中国作协会员。现任吉林省新文化报总编辑。
一次死亡做不了什么
——纪念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
一次死亡做不了什么
就像一个冬天
扣押洪水
以奔腾的姿势一动不动
二十年过去了
更多死亡众声喧哗
你沉默不语
数不尽的诗歌
和数不尽的哭声
没有暗示溪水的流向
没有宣誓春潮的力量
我只能找到你的眼睛
在一个郊外的小酒馆里和它对视
一瓶烈酒抵得过一个时代
一场宿醉湮没所有昨天
然后呢
饮者散去
餐桌上只留下你的杯子
深得如同一眼古井
我们都错过了亚历山大的大火
错过了托勒密的谬误
历史欠我们很多场葬礼
缓慢而又庄重
足够熨干所有血泪
让活着的人感到明朗的安慰
但它总是不动声色
迅速删除死者的户籍
让屈辱成为一种燃料
坐在冬天的怀里
越烧越冷
我怀疑那些星座里的密语
是虐恋者为你留下的
残酷而又深情
而你顽皮地笑着
像死过一百次那样笑着
说未来是银子的世界
当热寂降临
大批死亡汇流成河
向着未知的海洋
奔腾歌唱
等信的人
黄昏时我在写信
长长的没办法写完的信
我感到疲倦
这个黄昏和上一个黄昏
有什么不同
这双眼睛和上一双眼睛
谁能盛得下更多泪水
这张嘴巴和上一张嘴巴
谁会用更温柔的声音轻声道别
日复一日,我越来越渴望
在这封长信的尽头
黄昏陷落成一个巨大的杯盏
火山湖,强忍心底的愤怒
整夜与我们对饮
每喝掉一杯都红着眼睛说
我们,都是
丢失了地址
也没人给写信的人
我们,都是
丢失了地址
不知把信寄到哪里的人
黑色天堂
夜晚像亲人那样阖上你的眼睛
一次短暂的死亡
多么安静
如同春水瘫倒在五月酥软的土地上
很多细细的茅草
从爱情撬开的缝隙里钻出来了
你梦见天空
云朵后面一个早年离乡的姑娘
回来了,泪水串成的项链
挂在蔷薇果般甜蜜的胸前
她回来了,像是一个信使
告訴你一些可以期待的事
一些翻过墓园就能看见的节日
你也哭了
哭得比那个姑娘还无法自持
比一个幼儿还开心
说我等到了这一天
那些来自明天的信件
每一封都藏着一个节日
而每一个信使
在这个黑色的天堂里
都是天使
一枚银币
清辉铺就的夜里,你是一枚开朗的银币
在那么多穷孩子的梦里闪闪发光
你像年轻人的爱情一样守时
总是在身体从匮乏中醒来的时候起身
去最近的市集上歌唱
你去歌唱,去找同样年轻的力量
然后待在一起,说
我们就是这样
这才是我们该记住和保持的样子
清新健朗,但又带着累世凝聚的元气
和花纹里的暗语
像银子那样从岩层里走出来
在怀里藏好宇宙秘史,轻声歌唱
有一天
有一天,你过河入林
美杜莎的发辫在深秋飒飒舞动
你知道目光总会被劫掠
总会随时间弯曲
并从背后追上自己
给垂老的肩头致命一击
但你还是想再走的远一点
就像一支箭矢
渴望在坠落之前每一个灰尘的云朵上
屏息凝神
足够找到一声最明亮的叹息
为自己送行
太阳升起来了
你挺挺脊背
看见自己的影子变得又僵又直
是的,你输得很惨
但是你的姿势很美啊
我们说再见
我听见身体在时间的槽里摩擦时发出的声音
一万面丝绸的旗子捂住嘴巴,然后撕裂
有些血肉被毫无征兆地留下来了
那些人,手指苍白地挥舞着镊子
大广口瓶像祠堂一样幽深
在神位上端坐
你呀,这么多冤死者谁能数得过来
只能互相忘记,体贴地给后来者留出胃口
明天,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而我们说再见,再见
新的血肉懵懂而又勇敢
新的旅行将串成亿万个沉默的珠串
额 头
宇宙最后的泛光地带
在夜晚遁入密林
歌声蜷缩起来
附着在云彩最靠近星光的地方
但在我的阁楼上
你的额头
苔藓一样的光芒
紧贴着我的贫困
如同爱情的包裹
藏起窘迫
藏起倔强的勇气
是的,雨天你总是昂着头走路
在去超市的路上
也像去非洲
马赛马拉,或者南美洲的合恩角
牺牲的水晶在脚下喧哗
而垃圾车在身后如影随形
但是你的脚踝像瞪羚
记住了大迁徙
跳跃和恐惧的季节
记住了桉树上的夕阳
记住了神在天上说
没有英雄
人在哪里
访谈与回应
1.各位都是写作多年,多是《诗林》的资深作者,一路走来,创作历程中的感受和体悟一定不少,有坚持,也有改变。请谈谈你们各自的诗歌追求、诗歌理念。
答:诗是一种存在方式,就像探险和旅行是一种存在方式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进入大千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许多隐秘空间,发现在日常现实中难以想象的事物,并且和它们产生奇妙的连接。大多数情况下诗歌不是一张门票,而写诗更像是一种翻墙而过私闯禁地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惶恐、绝望、迷茫和狂喜。
2.你的写作,在艺术上是否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参照系?
答:有的。那是一个驳杂和怪异的组合:屈原、但丁、古诗十九首、李白、荷尔德林、艾略特、聂鲁达、金斯堡、茨威格、索尔·贝娄和王小波。后三位是小说家,但我认为他们面对世界的基本姿态有鲜明的诗歌属性。
3.网络时代给你的诗歌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答:网络让我确认诗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没有诗歌灵魂的连接,所有字符都是海滩上的沙砾。
4.你是否注重诗歌理论和詩歌评论?
答:诗学作为所有文艺理论的核心,应该在不同年代都对“诗人何为”这个最基本的设问做出自己的回答。好的诗歌评论同样是创造,同样是对沉闷现实的突破和超越。最好的评论家应该像摩西,领着自己的族人穿红海,出埃及。
5.你怎样理解诗歌写作的先锋性?
答:真正的先锋不是一件新衣服和一个新发型,而是一种新的眼界和新的发现。先锋的标志物是创造,而不是复制和包装。
6.在你心目中,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答:初读时的陌生感和紧随其后的似曾相识,最重要的它是日常经验的重建和对有灵之物的唤醒。
7.怎样理解诗歌的传承与“断裂”?
答:所谓传承其实是对诗歌本质的坚守。在这个大前提下,断裂随时发生,每一首好作品的诞生都意味着某种断裂和逃离。
8.你认为当下中国现代诗多元格局中是否有主流?
答:不知道,所谓主流即便有也未必好。
9.你个人偏爱哪一种诗歌风格?有你心目中最推崇的诗人吗?
答:我偏爱有重量的诗歌,它必须面对人最严峻最根本的困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虚与委蛇、故作玄虚、语言杂耍随处可见,但真的和诗没什么关系。
10.你认为诗歌作为一种写作类别,其前景如何?
答:诗是所有艺术之母,是灵魂的语言,人如果还想活得像人样,诗是不能缺少的。诗歌在现实中无用,但无用为大用,人通过诗歌可以航渡到星光之海。在那里,你从一堆随时可能腐败的蛋白质中脱颖而出,做最美的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