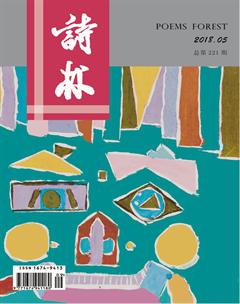空山寂(组诗)
水子
空山寂
整座山,似被长裙裹着
略显稀薄的朦胧之美,飘在一座道观的凹凸
间
为一个外乡女子设置了千百道帷帐
深山的晨景,蜿蜒而陡峭
我们拾级而上,鸟鸣堆积成若干巨石
高调占据爱情中的位置,三角梅
偶尔出现,最终接纳了它们迎风的世相
我几乎忘掉自己是来自北方的人
直到梦幻的针尖穿透绝壁,成为梵音的一个
引子
神性的鸟类,开始晨祷、沐浴、礼佛
喜欢的事,都在石径上行走
那扇我曾为之徘徊的赭红门,那条再次
隐身而去的小青蛇,带来的回声
从此消失在画板上
原路返回
听窗外鸟叫,应该是我每天
做的第一件事:偷偷释放出漫山遍野的忧伤
在绵绵细雨中一直走,并反复伸出左手
扬起微不足道谜一样的水雾
我以为这是最浪漫的上坡或下坡
所有人都不在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草木
集体跑过来,用暗香魅惑
突然而至的伤口
它们不停地发出前所未有的低吟
并真理一样原路返回
念经不知疲倦的麻雀,落在我的前方
我们对视的一瞬,窥见彼此
成为孤儿那些年,从来不懂低头的美德
弱小不过如此,在更高的台阶上
似乎我是唯一的注目者,在一个地方升起思
想
另一个地方的艾草便会发出苦涩的缠绕
令人时时为之迷路
上坡路
我为一段上坡路着迷
昨日的湮没,断开连绵不绝的矮灌木
沿一个短句下山
浮云将山体拦腰抱起,似乎低到了脚下
它们制造出阴暗,又仿佛横空出世的死结
有高调,务实之牙齿。使空山倾倒,时间成谶
细微的风在我第一句话后面停下
空中抛物一样,抛出感情的弧形线
有人用现实主义延续它
不存在的,蓝雾之城抱紧纯净的婴孩
最后,热暴力持续上升
人心偏向我们永远陌生的云朵,落下
轻柔的细雨来
西山,南山
无需知道是西山还是南山
那时,我第一次被鸟儿从梦里拉出来
看清它们的族群,置错边界
原型除外,木纹和香案的虔诚清晰可见
像游人幻化的木棉。花开无声
花谢时听到万籁静止
山中女神的长发错位了我走过的山路
佛曲向左移动诗人们的倾听,到大山深处
他们的眼中尽是消解,是圣徒归来
我仍保持红酒的姿态,高脚杯跟紧惊慌
在一个小角落,侧目奢华俗世
不愿为任何人饮下虚词
我还是醉在第二杯酒中——
偶然回忆起晚宴上独坐的人,所沉寂的
未经持刀人打破的排列
迷 失
我省略掉的——
唯有穿墙而过的缓慢古琴声
几朵扶桑花,视我为熟人,而不是
海市蜃楼中神情恍惚的游客
多情一如青苔,倚墙而望
宽广得辽阔:唇际的歧途,戛然而止的古代
百年榕树被风吹了百年,气根悬垂
指向真,也指向假。粗壮的树干绕过我,绕过
高墙
依然偶遇呢喃的琴曲,愁肠百转的轮回
我是擅自闯入,下一秒才学会失忆的人
隔世风景未变,体内早已无刺。矮如苔藓的植 物
每根刺的天真,都与我隔着一条银河的宽
只是重叠于此刻的濛濛细雨
有人轻轻抛过来古巷的寂静,再递给另一群
体内有海的人,完成一次触手可及的缓慢
琴声从未传来
——我承認,我一无所有
青石板踩在脚下,无法还原雨中的私生活
细微的沙沙声,让我与一架古风琴并肩而立
当年的老史密斯无家可归,久居在琴键上
与我共持光阴里的旧账本,向自己宣读
我们眼内都有沙子,生在孤岛
口袋里装满人间烟火、大河之波和海潮击岸
古老的味道,离岸的颤动。那些寄生在
沙粒内的脚印还给踏板一个去处。好像琴声
从未传来
实木纹理,私藏着忽左忽右的高低音
我被这种高低音推出门外,过分的安静
浮现出300年前的旷达,
空巷子总是不见一人
对面壁立石刻垂直坠下百年的孤独
依然是谜一样幽深
我真的来过吗?今人风雅,淡蓝的感伤
再大不过芭蕉叶——
侵 入
但是,没有一个事物
使老榕树旁边的一棵木棉,深邃而遥不可及
亲近它,花朵与枝干同时失去岛屿
许多礁石凸显,获得与失去的双重效应
我尝试着走下沙滩,青石如一件旧物
麻雀的蹦跳挡在前方,眼神却是我们的
那是传说的引拉,正在移向天空通过海面
远远袭来的欢愉,像花朵上掉落的古建筑遗
风
侵入归途中所有的时间
雨中轮渡
微雨安静,轮渡船按住海水
浪潮努力向上,涌起的涛声能让岛屿转身
此刻,这浪潮在白色的泡沫中
已接近沉沦。又被一双大手推向高处
再沉落。我怎么忍心回头——
站在船边淋雨
一只海鸟的鸣叫声,也湿漉漉的
黄昏已远,博大的海域在我的前方
那陌生的,低于自己的事物
正逆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