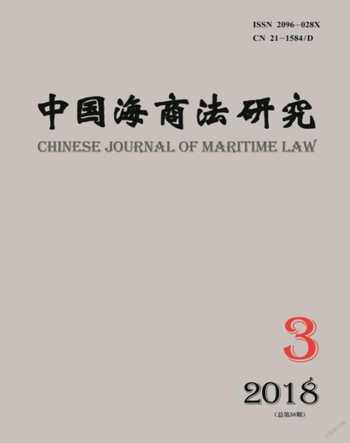《日本商法典》运输总则最新修订之评析
陈昊泽 何丽新
摘要:《日本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由于技术革新、运输方式变革等原因,其规定已落后于时代。顺应法律条文现代化趋势,2018年《日本商法典》迎来了时隔约120年的大修改。此次修法基于运输法制体系化的立法理念,使得日本运输法制由分散化而形成了从“一般法”到“特别法”的立法结构。运输总则的设置使得立法在精简的同时增加了整合性,法律适用呈现统一化,保障了人们对现代运输交易的稳定预期,促进了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原则向统一责任制发展。修改后,在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多式联运等制度修订上,体现了海商法的“上岸”趋势。
关键词:《日本商法典》;运输总则;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多式联运
中图分类号:DF961.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18)03008810
Analysis on the latest revis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ransport law in Japanese Commercial Code
CHEN Haoze,HE Lixing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Due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change in transportation mode and other reasons, the rules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maritime part of Japanese Commercial Code have been behind the times. To keep up with the trend of law modernization, the Japanese Commercial Code was amended after 120 years in 2018. Based on the idea of systematization of transport legislation,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law has changed to a new legislative structure which is from general law to special law.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ransport law makes the legislation more integrated while simplifying it.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s unified which ensures peoples stable expectation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transactions. The principle of liability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carriers is developing towards uniform liability principle. After the revi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ritime legal system presents a dual track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water transport law has been unified. This amendment reflects the trend of landing of maritime law in cargo transport,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multimodal transport.
Key words:Japanese Commercial Code;general provisions of transport law;cargo transport;passenger transport;multimodal transport
舊《日本商法典》(简称《商法典》)自1899年施行以来,其中第二编第八章“运输营业”和第三编“海商”,没有经过实质修改。2014年2月7日,日本法务大臣对运输法制的修改提出要求,至2018年5月18日,修改《商法典》运输和海商部分等规定的修正案在国会全票通过。此次修法最大的亮点是将原本只适用于陆上运输的运输营业章修改为适用于所有运输方式的总则性规定。修改后的运输营业章
①
被日本学界普遍称为运输总则。此外,海商编也顺应时代进行了现代化修订,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①
仅删去了内容与运输总则规定相同的部分,做了形式上的修改。
一、修法的动因
(一)旧有规定与实务的背离
《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立法至今经过了约120年,大部分规定已完全落后于时代,既不能反映现代运输发展趋势,也不能调整和指导实务运行,缺乏合理性与整合性。日本旧《商法典》于1899年施行,主要受到1897年《德国商法典》的影响。立法后,旧《商法典》经过了几次修改,但是运输和海商部分的内容均没有实质性的变动②
。因此,旧《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中仍体现了许多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商习惯③
,并且,由于立法时不存在航空运输方式,修法前日本调整国内航空运输的规定处于空缺状态。
如此古色苍然的法律仍能留存至今,令人不可思议,原因之一是法律完全与实务背离。[1]84举一个典型例子,旧《商法典》第805条第1款规定:“船舶所有人应支付的救助费用为,从事救助的船舶为汽船时,救助费用的三分之二;从事救助的船舶为帆船时,救助费用的二分之一。剩余救助费用的一半,由船长及船员支付。”虽然在立法时,海运船可以被分为汽船和帆船,但是现代商业航海中已不使用帆船。从这点来看,法律修改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旧《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中的许多规定是任意性规定,纠纷解决实践中并不依照,而是通过行业法和业界自律规范合同条款来调整法律关系。但合同条款的作用是有限的,与运输专门法并行,才能更好地确保现代交易的预测可能性。合同条款不能修正不合理的强行性规定,也不能认为合同条款自身总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并且,由于合同条款的制作主体是企业,即使其内容合理,也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2]例如,对于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危险品,修法前日本判例法上认为,“海上货物运输业者负有了解货物是否是危险品的义务。在运输危险品时,为确保船舶和货物的安全,海上货物运输业者应调查危险品的性质、危险程度、保存方法等注意事项,有适当装货,防范事故发生的义务”。但要求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逐一调查货物是否是危险品,过于严苛。[3]9此种情况下,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难以通过合同条款的方式维护其合理利益。
(二)立法语言的革新趋势
旧《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很少在实务中被使用的原因之一是,其文字叙述仍然保持着片假名与汉字相交的旧式法条表现方式。[4]旧《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早于1899年即已制定,其条文内容使用明治时期文体,汉字与片假名夹杂,使用古文文法,并有许多生僻词,再加上法律用语的专业性,导致一般人对法律敬而远之,也给法律从业者的找法用法带来不便。
基于对法律条文通俗化的要求,在国内立法上,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民商事基本法的现代化工作,使法律的内容与表现方式符合时代。日本于1996年修改《民事诉讼法》,2004年修改《破产法》,2005年制定《公司法》,2006年修改《信托法》,2006年制定《法律适用法》,2008年制定《保险法》。2017年完成了《日本民法典》债编的修改后,《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的修改是民商事基本法现代化的最后任务。2018年5月18日修正案被众议院通过,至此,日本民商事主干法律全部完成口语化,日本运输法制亦得以现代化。
(三)技术的演进
时代发展要求《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顺应时代潮流,创设和变更相应规范。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自1899年旧《商法典》制定以来,以文字为联络手段的通讯方式经历了从书信到短信再到移动互联网的变化,信息流量急剧增加,交流便利性大大提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商品运输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网上购物甚至可以不分地域,不问国界。基于互联网系统,货物运输上,无车承运人平台和中介服务商平台等应运而生,提供货主和承运人的对接服务。旅客运输上,定制客运和旅客联程运输成为常态,旅游产品的数量更呈现快速增长,这些都催生了对现代运输业越来越高的要求。加之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生产管理中,零库存成为可能,科技的发展要求企业拥有连贯的供销管理机制。物流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要求运输业自身进行大幅改变,旧有法规已难以满足高度专业化的现代运输,运输法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四)集装箱革命和多式联运发展
多式联运的发展要求法律对多式联运作出专门的调整和规制。多式联运的发展源于集装箱革命。1920年,美国铁路公司开发了集装箱运输方式,因其便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装箱在世界范围内普及。1956年,美国海陆通运股份公司开始了第一次集装箱海上运输。以此为开端,运输业进入集装箱时代,货物运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集装箱可以在不同运输方式中实现转运,具有通用性的特点,加之集装箱可以短时间内被大量装船,雨天装船、甲板载货成为可能,运输成本大幅降低。1966年9月,日本运输省决定了海运集装箱化政策。1968年9月,最早的日本制集装箱运输船箱根丸开航加州航路,日本开始了集装箱革命。[5]
伴随着国际多式联运的发展,出現了自身不具备运输手段而通过转包给船公司、铁路公司、航空公司等的方式来提供国际多式联运服务的从业者,称为无船公共承运人。此种情况下,合同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会发生分离。集装箱革命引发的多式联运发展,要求运输法制能够处理多式联运中合同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和货主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多式联运是日本旧有的运输法制没有考虑到的。多式联运是不同运输方式组合成的连续运输,旧有的运输法制不存在将其直接作为对象的规定,直接适用旧规定将会发生法律条文与实践的背离。虽然在多式联运专门立法前,日本实务界已有应对,通常在缔结多式联运合同时发行多式联运提单,其上记载多式联运合同条款,当事人依据条款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但是这种全凭合同条款来处理多式联运法律关系的做法存在问题,如前所述,运输法制与合同条款应当能够保持适当的平衡,故而需要新的立法方案来匹配运输实践的发展。
二、修法的特性
2014年2月7日,时任法务大臣的谷垣祯一在对法制审议会的第99号咨问中说到:“由于《商法典》制定以来,社会、经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好地调整货主和承运人及其他运输关系者间的合理利益,并且,从将海商法与世界接轨的观点出发,有必要重新考量《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的规定,应制定纲要”。[6]从此处可以看出,此次修法的范围是运输法制的现代化,要求法律更加合理地调整货主和承运人及其他运输关系者间的合理利益,也包含着顺应世界动向而进行修法的问题意识。
(一)分散化到体系化
如下表所示,日本旧有的运输法制是分散化的,对不同运输方式适用不同法律规定。在国内区域,旧《商法典》的运输营业章是陆上运输的规定,海商编是国内海上运输的规定,运输营业章的规定也准用于国内海上运输,而在航空运输领域,则没有法律调整。在国际区域,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适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国际航空运输直接适用相关国际条约。
在修法之初,日本学界有两种修改思路:其一,针对同种运输方式,在国内和国际适用同样的规定。如在《商法典》中加入《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内容,将《蒙特利尔公约》国内法化来应对国内航空运输。其二,在国内运输上设置统合所有运输方式的运输总则,而国际运输则保持原样。[1]87实际进行的修改与后一种思路更像,新《商法典》在第二编商行为的第八章设置运输总则,并设置特别规定来规制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因为运输方式不同,风险控制呈现差异化,所以旧有的分散化的运输法制具有一定价值。但随着现代运输的发展和技术革新,不同运输方式间货物毁损、灭失、迟延危险性的差异正在大幅减小,旧《商法典》运输和海商部分的立法缺乏整合性,内部法制不统一等问题已经凸显,时代要求运输法制趋向统一化。而且,由于在现今社会一般观念认识上,任何运输方式都应当是安全的,再加上通过保险风散合理风险,对于不同运输方式适用不同规定的合理性根据正在消失。重新审视运输法制,转变分散化的立法模式是有必要的。[7]事实上,日本此次修法的讨论是以陆上运输规则为出发点的,然后思考将陆上运输规则适用于海上运输和航空运输的适当性,最后得出结论,海上运输若要适用陆上运输的规则为总则,则必须设置特殊规定。[8]5
因此,新《商法典》以运输总则为“一般法”的规定,形成了“一般法”规定到“特别法”规定的层次鲜明的体系结构。运输总则是适用于所有运输方式的一般性规定。以运输内容划分,包括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以运输方式划分,包括陆上运输、海上运输和航空运输。在特别法上,对于海上货物运输,适用海商编的规定;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适用海商编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对于国际航空运输,则适用国际条约,即《蒙特利尔公约》。具体如表1、表2所示。
新《商法典》运输总则的设置使得运输法制呈现体系化编排,其体系化本身产生价值。法律体系化最原始的功能是帮助找法,找法者可以从一般法对系争法律关系作初步定位,再进一步探究是否涉及特别法。体系的效益又不以储法、找法、用法为限,必然还惠及立法和专业教育。[9]经过修改后,日本运输法制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将共同内容规定为总则,减少条文的数量,使得立法精简化,同时降低了制度理解难度。体系化带来了法律适用的统一化与整合性。在货物运输上,国内水上运输法制达到了统一化。在旅客运输上,除了国际航空运输外,统一只适用运输总则的规定,旅客运输法制也得到统一。同时通过适用总则的规定,国内航空运输的立法空缺也得以填补。这样层次分明的体系适合由浅入深地学习运输法体系,能够保障商业主体和一般消费者对现代运输法律关系的稳定预期,并能帮助一般人增加对运输的了解。
(二)水上运输的双轨制
旧《商法典》将平水运输①
纳入陆上运输范畴,受到运输营业章的规制,否定其特殊性。但司法实践中又适用船舶相关的法规如《船舶法》《船员法》《船舶安全法》《船舶职员和小型船舶操纵者法》等,故而对于平水运输的调整在旧《商法典》中落到了一种矛盾境地。日本此次运输法制的修改,将原本属于陆上运输调整范围的平水运输纳入国内海上运输范畴进行调整,适用运输总则和海商编的规定。此举统一了日本国内水上货物运输法制,无论是平水、沿海还是近海(非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都适用运输总则和海商编②
。这样,国内水上货物运输适用运输总则和海商编,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则额外适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其体制实质上形成双轨制,对国内水上货物运输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适用不同的规定。
(三)衡平承运双方利益
此次修订并非是“猛烈”的修改,而是为了使运输法制体系适应实务发展,不对实务现状造成大的影响,[10]38故而,此次修法导向上没有偏重货主和承运人任何一方,体现了商主体间利益的平衡化与对一般消费者的保护。商主体间利益的平衡,即对作为专业主体的货主方和承运人方都提出更高的要求,着力通过条文保证公平交易。新《商法典》运输总则对旧规定,基本做到实务处理轻了则加重,重了则减轻,使条文适应交易实践,力求保障现代运输交易的平稳运转。例如新《商法典》第577條加重了托运人的高价品通知义务,第581条保障了收货人对承运人的请求权,第584条调整了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期间。而修法对一般消费者则持保护的态度。由于一般消费者与承运人在对风险的认知、对交易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熟悉程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处于弱势地位,所以需要强化保护。例如新《商法典》第591条明文规定禁止免除侵害旅客人身责任的免责特别约定。
(四)海商法的“上岸”
海商法“上岸”指的是海商法中运输法律的“上岸”,与岸上运输法律相互交融,进而得到统一。其形态是岸上运输法制中吸收了海商法的内容,使得海商法原有的制度设计的适用范围扩大。[11]海商法“上岸”体现了运输法律规定的统一化趋势。统一的方式不是陆地的规定扩张到海上,而是海上的规定扩张到了陆地,对陆上运输加之更专门化的制度。海商法“上岸”源于实践的需求,现代运输的高度专业化,不同种类运输方式的风险通过保险等方式变得更加平均化,对法律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法律进行统一化。海商法“上岸”趋势在这次法律修改中有明显的体现,如运输总则第572条的危险品通知义务、第584条的承运人责任的免除、第585条的时效、第587条的承运人责任的同一化等制度,都是从国际海上运输制度中借鉴而来。这些制度能较好地解决现行运输法制运行不良的问题。海商法是运输法的起源,具有相对先进性,能够更为灵敏地反应现行运输实践的变化。故而当海商法中的一些制度运用于陆上的运输法制时,这也是一种超前的立法,能更好地指导陆上运输实践的发展。
三、修法的重点
(一)承运人损害赔偿额的参照基准
新《商法典》第576条第1款中规定:“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损害赔偿额按照应交付时间的交付地市场价格(有交易所价格的,按照交易所价格)。”此规定涵盖的范围仅有货物的毁损和灭失,没有包括单纯迟延交付的情况。单纯迟延交付造成损害的责任额,通过民法的债务不履行制度来确定。例如在汽车零件的运输合同中,如果此零件是关键零件,迟延交付会造成汽车生产者的生产线停运,而承运人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根据《日本民法典》第416条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承运人对生产线停止而造成的利益损失负赔偿责任。
旧《商法典》第580条第2款和第581条提及了迟延的情况,故而对于单纯迟延是否适用损害赔偿额参照基准,在法律修改前的解释上是有争议的。[10]34并且,将新《商法典》第576条第1款规定的承运人损害赔偿额的参照基准扩大适用于单纯迟延的情况具有合理性,因为计算货物运输迟延造成的损失额,与货物的毁损、灭失的情况一样,都是基于货物本身可能给货主带来的价值,所以其标准应当统一化。排除对单纯迟延交付的适用,可能造成依据《日本民法典》第416条计算所得的单纯迟延的赔偿额,反而高过依据新《商法典》第576条第1款计算所得的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赔偿额。举重以明轻,这是不合理的。但由于实务中普遍存在迟延损害赔偿额的特别约定,故而一般认为不适用损害赔偿额的参照基准。虽然此规定不合理,但新《商法典》基于不影响实务运行的考量,明确规定了单纯迟延不适用损害赔偿额参照基准。[12]34
(二)高价品的特殊规定
旧《商法典》第578条规定了:“货币、有价证券及其他高价品,除了托运人在委托运输时告知了种类及价格的,承运人对其毁损、灭失以及迟延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此规定的原意是为了促使货物单位价值明显高于普通货物的货主,对货物的种类和价值进行信息公开,确保承运人请求增加运费的机会。而这样的规定不见于任何国际条约,在比较法视野内也并不普遍。对于虽然没有接到高价品通知但承运人知道货物是高价品的情况,是否免除承运人责任,日本学界有不同见解。旧《商法典》采取一律不问承运人是否知情的处理方式,没有将偶然的知道与否当作问题加以考量,只要托运人没有履行高价品通知义务,承运人即免责,这隐含有督促托运人进行高价品通知的意思。学界部分观点也认为,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承运人即便在缔结运输合同时已经知道货物是高价品的,也可以免责。[12]28不过这样的情况下,与有通知的情况没有区别。所以现在多数观点认为,即使没有通知也不能免责。在此立场上,承运人在什么时间、何种程度上知道,才免除托运人的通知义务,是有争议的。故而,新《商法典》第577条第1款在继承了旧《商法典》第578条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第577条第2款予以限制,规定:“前款规定在以下情况不适用。一、在缔结货物运输合同时,承运人知道运输的是高价品的。二、承运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高价品毁损、灭失或迟延的。”第2款规定的“缔结货物运输合同时”这一时间点,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承运人在缔结合同时知道货物是高价品,即可以要求托运人履行高价品通知义务。就此而言,这条规定的主旨是恰当的。并且可以推导出,只要缔结合同时承运人不知道货物是高价品,承运人即便在接收货物时知道了货物是高价品,也不适用高价品的特殊规定。
(三)承运人责任的免除
旧《商法典》第588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责任在收货人接收货物并且运费及其他费用已被支付后免除,但是货物毁损或部分灭失的情况不能直接被發现的,收货人在货物交付之日起两周内对承运人发出通知的,不在此限。”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在承运人恶意时不适用。”新《商法典》同样有限定请求承运人承担货物毁损或部分灭失责任的期间的规定。新《商法典》第584条第1款规定:“对于货物的毁损及部分灭失的承运人责任,收货人没有异议而接收货物的,责任免除。但是货物的毁损或部分灭失的情况不能直接被发现的,收货人在交付之日起两周内对承运人发出通知的,不在此限。”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在货物交付之时承运人已经知道货物的毁损或部分灭失的,不适用。”这两款规定继承了旧《商法典》第588条的观点,但是没有采纳第588条第1款规定的“已支付运费及其他费用”的承运人责任免除条件,收货人两周内不能发现隐藏的损害的,将不能追究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有学者对新《商法典》没有加入“收货人已支付运费及其他费用”这一条件的做法持反对态度,认为旧《商法典》第588条的规定至少以支付运费等的作为要件,是只有在双方履行完基本债务后才适用的特殊规定。这是考虑到了当事人间的平衡。而按照新《商法典》的规定,可能产生货主方仍然残存着支付运费的债务,但却不能对承运人的过失追责的情况。所以这样的规定是缺乏平衡而不妥当的。[13]事实上,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2条有类似的通知义务,规定了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发现货物部分毁损、灭失的,有在收到货物的三日内通知承运人的义务,但是却不认可未履行通知义务将导致免除承运人责任的效果。
新《商法典》第584条第3款作出全新规定,规定:“承运人将运输转委托给第三人的,收货人在第1款但书的期间内对承运人发出同款但书的通知时,第三人责任相关的同款的但书期间延长至承运人接到收货人通知之日起两周。”虽然此条的立法宗旨是妥当的,但是两周期间的规定不尽合理。新《商法典》第584条第1款的但书规定的两周期间,是对于不能直接发现货物部分毁损灭失时,收货人发现的必要合理期间。而第3款的情况是从收货人处收到通知的承运人通知运输第三人的期间,这相对于要求货主在直接发现损害时即提出异议的做法来说,是有失平衡的。[3]29
(四)承运人责任时间限制制度的变化
根据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货物相关的承运人责任,自货物交付之日(全部灭失的自应交付之日)起一年内不起诉的则免除;第2款规定此期间限于损害发生后,可以通过合意延长;第3款调整的是对转包承运人求偿的情况,规定了承运人在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收到损害赔偿请求或者被起诉的,期间即使满一年,在承运人已经赔偿了损害或者应诉的三个月内,转包承运人的责任不免除。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4条的规定来源于《海牙—维斯比规则》第3条第6款,并没有明文规定此期间的性质是诉讼时效的期间还是除斥期间①
,但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是除斥期间。[14]
旧《商法典》运输部分的时效制度规定在第589条,准用了第566条的规定,规定了货物毁损、部分灭失及迟延的承运人责任,除承运人是恶意的情况外,自收货人收取货物之日起,全部灭失的自应交付之日起,经过一年,诉讼时效届满。而恶意的情况则根据旧《商法典》商行为总则第522条的规定,适用五年的诉讼时效。新《商法典》没有继承旧《商法典》的诉讼时效制度,而采用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除斥期间制度,原因如下:其一,作为商业主体的承运人反复运输不特定多数的货物,应有较高的危险预见可能性;其二,货物交付后一年后难以判断承运人的主观状态是善意或恶意;其三,货主请求赔偿的准备期间与承运人主观状态没有关系。[3]29
新《商法典》第585条第1款规定了货主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存续期间。因货物的毁损、灭失或迟延而产生的承运人责任,自货物交付之日(全部灭失的自应交付之日)起一年内不通过诉讼方式请求则免除,这也包含了使用转包承运人的情形。实际上,一年的期间对于调查货物损害发生的原因并收集证据并不必然足够。在旧《商法典》规定上,期间经过前不能通过合意而延长,为了避免期间经过致使承运人责任被免除,无论承运人主观状态是善意或恶意,货主必须在期间经过前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承运人与货主的和解,这个矛盾在此次修法中得到化解,新《商法典》第585条第2款规定了此期间在损害发生后可以通过合意延长。第3款也与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4条相同,规定的是承运人转包给第三人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期间。
(五)承运人责任的同一化
承运人造成货物的毁损、灭失、迟延的,尤其是货物的毁损和灭失的情况,直接侵害了货物的所有权,基于合同的债务不履行责任和侵权责任会同时发生。对于此种情况,日本历来的判例认可对承运人的请求权竞合,即因承运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托运人、收货人及第三人损害的,承运人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和其他侵权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减轻或免除承运人责任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原则上不适用侵权责任,货主基于合同条款或侵权责任对承运人追责,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新《商法典》改变了一情况,第587条将减轻或免除承运人债务不履行责任的各规定,即前述的损害赔偿额参照基准、高价品的通知义务、承运人责任的免除和时效制度,准用于承运人对于托运人和收货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消除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间的显著差异,[15]回应了统一承运人责任范围的要求,与世界的立法动向相符合。[16]
(六)托运人的危险品通知义务
在运输对象多样化的过程中,各种各样危险品有被运输的可能,所以在承运人看来,为了避免运输工具和其他货物因为危险品而发生损害,应有机会拒绝运输危险品,或者即使接受运输,也应有机会采取必要措施。但是,旧《商法典》中不存在针对危险品运输的特殊规定。因此,发生危险品事故的,受到损害的承运人基于合同请求损害赔偿时,在诉讼中有必要对托运人预见危险品的可能性及违反通知义务的事实立证,[12]34这给承运人的诉讼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针对此问题,新《商法典》在第572条明文对托运人课以危险品通知义务,即“货物具有引火性、爆炸性等其他危险性的,托运人在交付前应告知承运人货物的品名、性质及其他对于安全运输必要的信息”。加上《日本民法典》第415条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新法上,托运人违反通知义务对承运人造成损害的,负基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但能够立证自身不存在归责事由的,不負责任。危险品的相关的举证责任在托运人方,承运人利益得到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修法过程中讨论危险品通知义务法定化时,谈及了托运人违反危险品通知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即托运人违反通知义务而致承运人受到损害的,对托运人是课以过失责任还是无过失责任。[17]日本国内解释的通说认为是过失责任,而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第4条第6款的解释上则认为是无过失责任,近年的《鹿特丹规则》第32条更明示规定为无过失责任。无过失责任更能保障现代运输的安全性,在处理承运人与托运人间法律关系的时候也更为简单,剩下的法律问题由托运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内部求偿来处理。但是立法过程中,对此有很大争议,主要反对观点如下:其一,危险品的定义缺乏明确性;其二,制造业者、商社、无船承运人、消费者等各种托运人对危险品的认识和知识有显著差异,故而需要灵活应对;其三,实践上托运人一般不会投保赔偿责任险,因为这在保险实务上需要评价危险性;其四,认可承运人的责任限制,而对托运人课以无过失责任,有失均衡。[18]最终,新《商法典》规定托运人违反危险品通知义务时负过失责任,且没有无过失责任的特殊规定。至于危险品的内涵和外延,则留待解释加以确认。对作为运输总则的一般性规定来说,违反通知义务即课以无过失责任,未免过于严苛,故而采用过失责任是适当的。
(七)收货人权利的扩大
旧《商法典》第583条第1款规定:“货物到达后,收货人取得因运输合同而生的托运人权利。”根据此规定,收货人取得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上的权利的时间是在货物到达后。那么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则收货人不能取得任何权利,收货人只能通过要求托运人让渡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方式来追究承运人责任。在日本国内交易的实务中,由于买卖双方在标的物交付前,危险不会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故而依据旧《商法典》的规定,也不会产生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国际交易上,危险转移给买方的时间是装货时,如FOB和CIF条件,在此情况下,若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作为买方的收货人接受了危险的转移却不能取得对于货物的任何权利,而作为卖方的托运人缺乏追究承运人责任的动力,收货人从托运人处让渡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做法在实务中存在很多困难。
针对此问题,新《商法典》第581条第1款规定:“收货人在货物到达目的地时或者货物全部灭失的,取得基于货物运输合同而生的与托运人同一的权利。”该规定不仅赋予货物到达目的地时,收货人取得货物权利,而且增加了货物全部灭失情况下,收货人也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这样对收货人的保护更加周延。收货人在新规定下可以对货物在运输途中全部灭失的情况独立行使请求权,而不必要求托运人进行权利让渡。不过,该条文如此规定会造成托运人与收货人权利竞合的情况,货物全部灭失的,承运人有收到来自托运人和收货人双方损害赔偿请求的可能性。对此,新《商法典》在第581条第2款规定“收货人在请求货物的交付或损害赔偿时,托运人不能行使此权利”,在托运人和收货人的权利行使中确定了顺序,保障了收货人权利的行使,减轻了收货人的负担。而托运人的权利只是被暂时冻结了,若收货人撤回了请求,托运人仍可以行使权利。
(八)多式联运下的不完全的统一责任制
随着多式联运的广泛普及,新《商法典》新设了基于运输总则的多式联运规定。理论上,若已经创设适用于全部运输方式和区段的一般法的话,对于多式联运便无必要设置特别规定。但在实践中,多式联运常见的问题是,当损害发生的原因和区段不明确时如何适用规范。并且,海上运输的责任制度体系具有特殊性,国际运输上存在《蒙特利尔公约》《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等强行性规定,因此创设多式联运的责任规则是有必要的。
新《商法典》第578条是多式联运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以货物运输适用运输总则的规定为前提,第578条第1款规定了多式联运的定义,即将陆上运输、海上运输和航空运输中两个以上的运输约定在同一个合同中的运输。那么,比如将两个以上的水上运输约定在同一合同中的就不是多式联运。但立法者考虑到了陆上运输的特殊性,陆上运输中,有汽车、铁路等不同的运输工具及相应的不同法令,[8]9故而在第578条第2款中规定:“前款规定准用于将根据区段的不同而适用不同法令的两个以上的陆上运输约定在同一个合同中的情况。”
根据新《商法典》第578条第1款的规定,多式联运中货物发生毁损、灭失或迟延时多式联运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能确定发生的区段,则多式联运承运人根据运输合同条款规定适用的日本法或者日本缔结的国际条约规定承担责任;而若区段不能确定的,则适用《商法典》的一般性规定,即运输总则。从这里可以看出设置运输法总则的价值,体系化的运输法制能带来法律适用的同一,使得日本运输法制呈现出高度整合性,尤其使多式联运制度得益。
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统一责任制和网状责任原则的对立。前者认为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责任并非是根据运输方式的分散化法律规制,应适用统一的责任原则。而后者则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手段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制。[19]统一责任制是发展的目标,相较于适用不同的责任制度,更适合于保护承运人和货主双方的利益。网状责任制是目前多数国家采用的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原则,但均不是单纯的网状责任制。因为实践中发现,在货物毁损灭失或产生毁损灭失原因的区段不能查明的情况下,单纯的网状责任制是不能适用的。多式联运是一个连贯的运输过程,在单纯迟延的时候,判断迟延发生的区段很困难,此时不同区段的适用不同的法律,很可能达不到公平的法律追求。中国现行的多式联运责任原则采用不完全的网状责任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321条的规定,可以确定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责任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不能确定的,依照《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105条、第106条的规定,能确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责任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多式联运承运人应当依照《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负赔偿责任。那么,中国现行法律对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为:能确定损害区段时,适用该区段的规定;不能确定损害区段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有国际海上运输的情形,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从形式上看,中国现行的多式联运责任原则与日本修法后新增的制度相似。但是仔细考究就会发现,《合同法》对于多式联运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呼应实践,而《海商法》将不能确定区段的情况统一适用《海商法》,不利于货主合法权益的保护。由于《海商法》第四章采用不完全过失责任制,并且第十一章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承运人实际承担的责任可能比能够确定区段的情况轻很多。反观日本的规定,如果能确定损害发生的区段,则多式联运承运人根据运输合同条款规定,适用日本法或者日本缔结的国际条约承担责任;而若区段不能确定,则适用运输总则。运输总则的特性使得日本的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原则更接近统一责任制,可以称作不完全的统一责任制。这样,在可以确定区段时,需要适用的是运输总则的规定,在平水运输、海上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时加之特殊规定;而在不能确定区段时,则全部适用运输总则的规定。可见,适用总则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运输总则的设置是基于各种运输方式的共通性特征,故而对承运人和货主来说,责任的承担具有更好的可预测性。此外,适用运输总则的规定较之适用海商制度,更有利于保护货主。比如,以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国内航空运输中的两个以上运输方式进行多式联运,在日本法上可以明确知晓多式联运适用的责任规定为运输总则,而中国可能适用的法律为《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简称《铁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简称《民航法》)。在现行条件下,由于海上运输存在特殊性,运输法制不可能完全趋同,不完全的统一责任制是现阶段相对优越的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原则。
(九)旅客运输中特别约定的禁止
旧《商法典》中关于旅客运输的规定共有14条,缺乏航空旅客运输的规定。在现代社会下,这些条文大多失去实践意义,出现了与交易实态的背离。因而,实践中行业法和旅客运输业者拟定的运输合同条款起着很大作用。[20]新《商法典》将陆上旅客运输、海上旅客运输、航空旅客运输都适用运输总则,通过此方式改变了国内航空旅客运输规定欠缺的情况,去掉了不適应现今交易实践的规定。同时由于已经规定了适用于旅客运输中承运人责任的一般规定,故而在海商编中删去了海上旅客运输的相关规定。
新《商法典》第590条规定:“承运人对于旅客因运输受到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能证明没有怠于履行对旅客的
注意义务的,不在此限。”该规定维持了旧《商法典》第590条的对承运人责任的过失推定原则。旧《商法典》第590条第2款中“考量损害赔偿额时,法院应斟酌被害者及其家庭情况”的内容被删除,这是由于审判实践中对于旅客损害赔偿请求的赔偿额,一般通过治疗的实际费用、停业造成的利润损失、抚慰金等来算定,斟酌被害者及其家庭情况客观上很难被付诸实践。
新《商法典》重视对旅客安全的保护,着力点在承运人责任上,按照第591条的规定,除了特殊情况外,减轻或免除造成旅客人身侵害的承运人责任的合同条款是无效的。由于旧《商法典》没有这样的规定,故而这是强化了规制。有学者认为,基于实践运行中不存在减轻或免除旅客人身侵害的承运人责任的条款,并且有《消费者合同法》及行业法的规制,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此类合同条款的无效。[1]89但是没有专门的法律而全部通过准用其他领域的法律来解决问题,终究难以圆满。从专门立法的完整性和法律通俗化来看,此条立法仍有其价值。
但是,明文规定全面禁止旅客运输中承运人的免责特别约定,会导致两个问题。
其一,特别约定无效将导致不利后果。如铁路等的公共交通,一次迟延会造成承运人对大量旅客承担迟延责任的情况,若没有免责特别约定,运输业难以合理运转,也会造成运输费用的上升。其二,
难以维持真正有必要的运输。比如在灾区运输的,或运输重病患者的,或因运输通常伴随的振动造成人身重大危险的,由于运输业者没有接受运输的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没有减轻或免除责任的特别约定,运输业者为了减少风险,可能选择不进行运输。针对这两个问题,新《商法典》第591条规定了三种例外情形:其一,运输迟延是造成旅客人身侵害的主要原因的;其二,
发生大规模火灾、地震及其他灾害时,或有发生大规模火灾、地震及其他灾害的危险时运输的;其三,因运输通常伴随的振动及其他情況造成旅客生命或身体发生重大危险的。以上三种情形的特别约定虽不被禁止,但受到一般法条文的制约,如《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日本《消费者合同法》第8条禁止了免除业者损害赔偿责任的特别约定,第10条禁止了单方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特别
约定。
四、结语
如前所述,日本此次修法的主要着力点在运输总则,海商编的修改多参照《海牙—维斯比规则》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国1993年施行的《海商法》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法律,参考了《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结合中国实践,采用独特的混合模式来规制国际海上运输。然而已过去了二十余年,《海商法》需要加以修改。日本海商制度修改后的内容没有跳脱出中国1993年立法即已参考的《海牙—维斯比规则》的范围,对中国的借鉴空间是有限的,但海商法的“上岸”,即运输总则的条文内容参考《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制度设计的做法,对于运输立法是值得参考的。
中国现行的运输法制也采用一般法与特别法结合的模式,一般运输合同由《合同法》规制,铁路运输有《铁路法》作为特别法,航空运输有《民航法》作为特别法,国际海上运输有《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内河、沿海的航运现状没有特别法①
。但是《合同法》关于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和多式联运的规定过于简要,而内河和沿海领域航运特别法的缺失,也给实践带来很大的问题。虽然中国目前的运输法制存在着矛盾和空白,但是正逢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时刻,笔者认为应当抓住机会,参酌新《商法典》运输总则的修法经验,完善《合同法》运输合同的相关规定,整合不同种类运输方式的规定,朝着运输法制统一化努力。统一的运输法制能带来承运人和货主对权利义务的稳定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对现代交易带来的风险,促进运输业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
藤田友敬.日本における運送法·海商法改正の全体的構造[M]//日本法学会.海法会誌(復刊第61号).东京:劲草书房,2017.
[2]落合誠一.運送法の課題と展開[M].东京:弘文堂,1994:2.
[3]淺木愼一.新運送法:改正商法案と新民法を基に[M].东京:信山社,2018.
[4]手塚祥平.《商法(運送·海商関係)等の改正に関する要綱》が企業実務に与える影響:海商関係を中心に[J].商事法務,2016,2099:25.
[5]渡辺逸郎.コンテナ船の話[M].东京:成山堂书店,2006:6264.
[6]野村修也.運送法·海商法改正案:今回の改正案の考え方[J].法律時報,2018,90(3):4.
[7]落合誠一.複合運送契約立法の基礎的考察[J].ジュリスト,2002,1219:9.
[8]山下友信.商法(運送·海商関係)等の改正に関する要綱について[J].NBL,2016,1072.
[9]苏永钦.体系为纲,总分相宜——从民法典理论看大陆新制定的《民法总则》[J].中国法律评论,2017(3):7475.
[ZK)][10][ZK(#]池山明義.運送人の責任の実務的検討[J].法律時報,2018,90(3).
[11]陈琳.论国际运输法统一下的海商法“上岸”——以《UNCITRAL运输法草案》为起点[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6(5):534535.
[12]箱井崇史.運送人の責任の理論的検討[J].法律時報,2018,90(3).
[13]岩原紳作,上村達男,江頭憲治郎,等.「商法(運送·海商関係)等の改正に関する中間試案」に対する早稲田大学教授の意見[J].早稲田法学,2015,91(1):64.
[14]中村真澄,箱井崇史.海商法[M].2版.东京:成文堂,2013:279.
[15]松岡弘樹.商法(運送·海商関係)の改正の概要[J].東京交通短期大学研究紀要,2017,22:45.
[16]大野晃広.商法(運送·海商関係)改正をめぐる動向と展望[J].商事法務,2018,2155:39.
[17]松井秀征.物品運送契約をめぐるその他の問題[M]//日本法学会.海法会誌(復刊第61号).东京:劲草书房,2017:117.
[18]清水真希子.荷送人の義務の理論的検討[J].法律時報,2018,90(3):18.
[19]落合誠一.複合運送人の責任[M]//竹内昭夫.特別講義商法II.东京:有斐閣,1995:221.
[20]増田史子.旅客運送契約[M]//日本法学会.海法会誌(復刊第61号).东京:劲草书房,201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