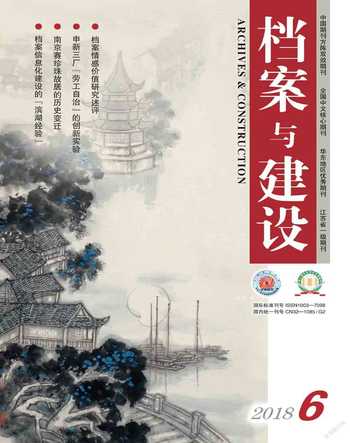申新三厂“劳工自治”的创新实验
蒋伟新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在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无锡工商企业或者相互模仿,或者与社会团体合作,分别举办带有浓厚社会实验色彩的劳工事业。凡稍有眼光的企业家无不对此倾注极大热忱和可观投资,写下了近代无锡企业文化中颇具创新特色的一页。
一、“劳工自治”的理念和设想
在大革命浪潮的激荡下,1920年代农村的农民运动和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厂罢工接连不断。如何平息工人情绪,缓和劳资关系,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荣德生等工商企业家深知潮流所趋只可疏导不可堵塞的道理,所以设想通过改革企业管理来加以疏导。劳工福利的实施,虽然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展开,旨在调节劳资关系,但又带有企业管理变革的意义,体现企业劳动组织和劳动关系的进步。在无锡,所谓“惠工”“福利”,既有企业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又有相互比较、相互竞争。其中尤以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最具特色也最有成效。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兴办实业发家后,时刻不忘父亲临终的教诲:“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1]社会义务、社会责任感是荣氏兄弟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荣德生对于劳工福利事业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实践中,荣氏兄弟深切体会到:一个企业获取良好的效益,既要依靠技术设备的改进,更要加强企业管理,协调好各部分人员的关系。所以荣德生说:“余素主实际,不尚空谈……三厂职员主教以实习,对工人主恩威并用,兼顾其自治及子女教养。”[2]所谓“恩威并用”,既严格管理,又增加员工的福利,同时加强教育,以德服人,对职员和工人注意笼络感情,调和矛盾。他们深知,只有让大家安居乐业,工人才会心甘情愿依靠工厂,为工厂出力。所以,荣家企业的管人、用人,首先在于“治理人心”。有一次,申新三厂失火,住在附近的一些职工纷纷赶到厂里救火,荣德生也赶来了,他一面吩咐人通知消防队灭火,一面叮嘱门卫不要让员工进厂,并记下这些人的名字。许多人对此大为不解,他说:“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忠臣。厂烧了,保险公司会赔偿,可以再造;忠臣烧死了,就不好找了。”事后,这些人都得到提拔和重用。
促使榮氏兄弟酝酿“劳工自治”的动机,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另有一层外部环境的原因。在荣氏兄弟兴办实业之初,国内民族工业界已形成“南张北周”两大显赫的企业集团。有“南张”之称的南通张謇,以“儒者”自居,在创办大生企业集团之后,又在家乡南通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力图以南通的社会改造作为试点,造福于一方,进而影响社会、影响全国。在他的倡导下,江苏地方士绅成立了苏社。在苏社的开幕宣言中,张謇说:“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放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荣德生出席了在南通召开的苏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观张謇在南通兴办地方自治的各种成果,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启发荣德生思考很多问题,但他更为务实,也没有更强的实力由企业来筹办本该由地方政府去办的“大社会”,于是他设想把张謇的自治理念应用到企业的治理实践之中。自1920年代末起,荣德生开始酝酿在无锡申新三厂试行“劳工自治”,并由薛明剑具体规划自治方案。
薛明剑勤奋好学、兴趣广泛,是一位热心于社会改革的年轻人,得到荣德生的器重,被热情邀请参与申新三厂的筹办,并担任工厂总管(厂长)。薛明剑进入工业界,一直有自己的理想,用他的话说:由教育界转入工业界,并“不是想发财,也不是羡慕虚荣,的确是目睹工业生产事事不如他国,并且存在种种不合理措施,急需改进和改革。”[3]以后在实际管理申新三厂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旧式管理制度的种种弊端,亲眼见到工人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下的生活待遇,因而更加坚定了倡导改革的想法。他是无锡企业管理改革的积极鼓吹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经过深入调查,并反复酝酿,与利益相关各方沟通,在荣德生主持下,薛明剑提出了申新三厂“劳工自治”方案。
二、“劳工自治”的实施
1931年,申三正式开始试办劳工自治区,拉开了“劳工自治”的序幕。正如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变革,开始总会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劳工自治”同样面临种种抵制。这要求改革者全力以赴,顽强推进,同时不断优化实施方案,在进取和迂回中谋求突破。
工厂举办劳工事业,原本着眼于提高工人福利、改善职工生活,可是令创办者意想不到的是,首先遇到的反对阻力竟来自工人。原因是“劳工自治”实施方案的第一步,是要将一部分工人宿舍划入劳工自治区。当时各工厂招收的工人来自四郊八乡,也有的来自邻近县区,甚至有来自苏北和外省的。其时交通不便,为了准时上班,工人必须就近居住。为此厂方在工厂附近建造了一些工房,或腾出一些空余不用的厂房,租给工人作为宿舍。这些工人宿舍原来没有专人管理,男工宿舍与女工宿舍混杂,单身职工集体宿舍与家属宿舍混杂,导致秩序混乱、卫生状况较差,个别品行不端者游串各室,惹事生非,欺凌弱者,引诱异性。因为工厂将整幢房屋出租,又准许承租者将剩余的房屋转租外人,由此产生了专以转租房屋牟利的二房东。为了设立劳工自治区,厂方决定将工人宿舍加以整顿,改建成男工单身宿舍区、女工单身宿舍区和家属宿舍区,并派专人实行分区管理。这剥夺了二房东的额外收入,自然遭到他们的抵制。厂方为举办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为工人工余学习提供方便,统一规定未成婚的工人住进集体宿舍,这也与工人原来的生活习惯不符。当时的工人来自农村,习惯于合家居住,方便而自在;相互之间为同乡邻里、沾亲带故,且纺织厂工人盛行“认寄亲”,方便相互依托照应,因而反对住进集体宿舍。工厂加强宿舍管理,就有人造谣生事,加以阻挠。甚至有人身穿半红半白的衣裳,半夜三更登上楼顶装神弄鬼,恐吓单身女工宿舍的女工和管理人员,致使一些女工结伴逃离宿舍。
实施“劳工自治”还遭到部分工头、职员、股东的反对。原先工厂中的一些工头都有一定的帮派势力,掌握管理工人的部分实权,他们平日欺压凌辱普通工人,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工资,乃至强迫工人按时按节送礼送物,指派女工到家中帮佣家务。工厂实行科学管理,实施“劳工自治”,他们的权力被剥夺,种种陋规随之被废除,因而不惜以激烈的手段对抗改革[4]。而工厂的一部分股东和职员只看重眼前利益,并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在他们看来,改革的实施必定多加开支,增加工人的福利就会减少自己的收益;同时也担心改革激化矛盾,引发动荡,最终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对“劳工自治”的变革畏首畏尾,主张稳重守成,反对多生枝节,本能地反对一切新生事物。
工厂内部的阻力以外,设立劳工自治区还受到来自工厂外部的压力。工厂邻近的一些商店,它们的顾客主要是工厂的工人,以向工人出售日用品而营利。建立劳工自治区后,工人自己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加上自己种菜、搞家庭副业,减少了到商店购买商品。这当然是商店店主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当申新三厂实施“劳工自治”计划时,附近一些商店就以集体请愿和匿名恐吓、造谣惑众等方式加以阻挠。有几个理发店店主还手扬香火,多次守候在申三厂门外的小木桥桥头,拦住厂主、总管及高级职员的车辆,要求厂方“发发慈悲”,停办合作社,让他们维持生意、维持生计。
对此,荣德生、薛明剑并未采取高压措施,强行推进改革,而是区别情况,运用迂回战术,分别加以化解。为了帮助股东和职员消除顾虑,厂主亲自出面进行协商,多次召开会议说明情况,争取大家的认同。为了让职工明白他们是“劳工自治”最大的受益者,厂方不强逼工人返回宿舍,而是首先在厂内兴办子弟小学和职工医院等福利设施,增强对职工的吸引力。从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入手,举办女工养成所,首先招收部分远道女工,统一住進女工宿舍,以此示范“劳工自治”的好处。注重对老工人进行宣传引导,摆事实、讲道理,让原先有抵触情绪的部分职工逐渐认识“劳工自治”的好处,从而使消极观望者变为拥护者、赞成者[5]。为了处理好与邻近商店的关系,经过协商寻求多赢的解决之道,允许他们以合办或代办相关业务的形式,进入自治区开店,统一管理,既减少厂方自办福利的麻烦,也较好地顾及当地店家的利益,消解了来自外部的阻力。至于工头闹事和二房东转租的问题,也在工厂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得到了解决。劳工自治区的创建计划,终于在百般困难中一步一步地得到实施。
三、“劳工自治”的基本内容
“劳工自治”的基本精神,是在劳资雇佣关系的范围内,让工人自己管理自己,改善劳工福利状况,提高职工素质。荣德生、薛明剑把创设劳工自治区的宗旨概括为:“改善区民生活,培养良好工友。”其施行方针大致包括这样一些要点:一是加强技术培训,让工人获得立身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二是以劳资合作的方式,举办各种合作事业和公共设施,以促进工厂增加生产,帮助工人减轻消费负担;三是注重文化教育,让进入自治区的工友人人有读书的机会,有正当的文化娱乐;四是开展社会教育,帮助工人学习农业栽培和手工工艺,即使在工厂退职也具备必要的生活技能。
“劳工自治”采用工人自行组织的方式,对工人实行积极劝导和“参与式”的激励。自治区区长一人,由厂方任命。自治区分设单身女工、单身男工、工人家属、职员家属四个宿舍分区,分区下设村,村下设室或组。宿舍每室住8-12人,其中一人为室长;14-26室为一村,设有正、副村长。分区正副区长、各村正副村长及室长、组长,均由工人自己推举产生,分别负责本室、组、村、分区有关事项的管理和矛盾的协调。区内各种生活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均由工人自己协商订立公约,大家共同维护[6]。各项惠工、福利设施的建设、维护、运行,尽量动员和组织员工共同参与。
“劳工自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为了推广应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适应科学管理制度,培养合格职工,工厂先后创设职员、女工、机工三种养成所。1932年秋季又创设工人晨校和夜校,进行在职教育。当时纺织厂工人一般是日夜两班制,所以职工业余教育只能分别进行。教育属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学习,不收学杂费、书籍簿本费。按工人原有文化程度,分识字训练班、公民训练班、技能训练班三级,每级分早夜两班。教材以自编为主,教员也大多为本厂职员。教学内容主要有:文化补习,教识字,扫盲;生产技术,讲授机械原理,培养熟练机工;家事技能,如烹饪、缝纫、医护常识等;副业生产知识,如养蜂、养兔、养鸡鸭、养鼬、刺绣、织花、园艺、种菇、种菜、酿造、打字、修理钟表等。由工人自由选修,既增加谋生的技能,也作为工余的休闲。晨、夜校也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传授中西音乐知识及乐器演奏技法,开展歌咏、舞蹈、武术、球类等活动,以充实工余生活,陶冶性格情操,提高工人的文化素养。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学校设立小导师制度,在工人宿舍内每室聘请一名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能力较强的工人为小导师,负责在课外辅助督导同室工友学习,起到互帮互学、互相促进的作用。作为教育辅助设施,厂中设有图书馆、阅报室,经费列有预算,定期添购各类图书、报刊[7]。申新三厂这方面的设施,在当时无锡私营企业中是最为完备的,因为与教学活动相辅相成,适合工人的需求,所以吸引很多工人参加到学习培训之中。
二是医疗保健。1932年8月,申新三厂在女工养成所设立职工医院,第二年5月搬至新院址,以后又增建三层楼一幢作为新医院。医院分中医和西医两个部门,设有诊察、治疗、手术、化验、调养、传染病隔离等室,购有X光机等当时先进的医疗设备,为职工就诊、治病提供便利。本厂职工治病免收医药费,职工家属免收治疗费,半价收取药费,厂外人就诊医药费照价实收。医疗经费来源主要为厂方拨款及工会会费、职工自愿捐助。当时无锡其他一些企业也设有厂办医院或医务室,但以申新三厂职工医院设备最好,服务最完善[8]。除此之外,工厂还建造浴室、理发所,要求工人保持清洁卫生,按时理发、洗澡;添置水塔、热水汀等设备,保证工人能经常得到清洁的饮用水;把旧式的茅坑改造成厕所,并加强管理,减少疾病的传染,改善厂区和周边地区的卫生状况。
三是文体活动。劳工自治区设有俱乐部,其中包括体育、音乐、游艺三个方面的活动项目。区内建有运动场、健身房,供职工开展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运动,并定期举行田径运动比赛,以增强职工的身体素质,愉悦身心。文娱设施方面有娱乐室、影剧场,用以放映电影、上演戏剧,开展歌咏、舞蹈活动。鉴于举行全厂性的大会及文艺汇演等活动,原有场所较为狭小局促,厂方决定填掉一个原来用以养殖鱼蛙的鱼池,盖建一座大礼堂。礼堂的建设耗资近万元,全部来自工厂劳资各方的自愿捐助,贫困无钱者则参加义务劳动,以工代资。连工厂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也在课余由教师带队到各地参加劳动。整个工程历时两个月即告完成。当时申新三厂职工连同家属已达上万人,每逢节假日举行文艺演出时,大礼堂里总是座无虚席,热气腾腾。自治区还建有多处园圃,地面种植草坪,缀以花木,布置为不同的格调,用于职工游憩观赏。
四是其他福利事项。自治区内建立有各类消费合作社,为职工供应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南北货、饮食点心、煤球热水,提供制衣、洗衣、照相、修理等各种服务,减少商贩的中间盘剥,帮助工人节省消费开支。消费合作社由工人合股组建,社员消费享受优惠,合作社有盈利,年终按股金分红。自治区还开设劳工储蓄部,面向工人,降低起储点,以角为单位,随时存取,分别计息,并定期开奖,吸引工人储蓄,积少成多。这些存款实际上被厂方用于生产周转,相应减少向银行、钱庄的借贷,同时也为职工急用或大笔开支提供方便,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劳工自治区还自办劳工保险,包括死亡保险、养老保险、伤残保险、疾病保险和灾害保险等险种,初步形成一种互助互济的机制。自治区还择地建立劳工公墓,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工人办理丧事提供服务,减少开支[9]。所有这些,均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排除那些可能影响工人情绪的不利因素。
此外还有尊贤堂、功德祠和工人自治法庭。尊贤堂陈列历史上抗敌御侮的岳飞、戚继光及民间崇拜的关云长、薛仁贵等塑像。凡違反厂纪、不服从管理、闹纠纷的工人,责令到尊贤堂内向塑像磕头忏悔、宣誓悔过。薛明剑说:“在神像前他们不敢说假话的”。功德祠里立着一些为企业作过较大贡献的已故职工的长生牌位,定期举行公祭。并规定:职工凡因工受伤殒命,或在本厂服务达10年以上并有功无过者,死后可设立牌位,“入祠奉祀”。由此激发工人活着努力干、死后有归宿的认同感。前者用来警戒那些不守厂规、冒犯尊长者,后者则用以表彰忠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职工。所谓工人自治法庭,推举在工人中享有一定威信的员工担任裁判员,负责工人之间各类纠纷的调解、仲裁,必要时也加以惩戒、处罚。所有这些,都是从自我成就和社会交往两个方面,控制和引导职工的情绪和行为,培养工人的团队精神,增强归属感、成就感和荣誉感,达到协调劳资关系、激励工作热情的目的。
四、“劳工自治”的成绩和影响
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实验区办得有声有色,据当时的报道,其福利事业令人“颇有胜过日本在华各厂福利事业的感想”。方案的具体规划者薛明剑曾不无自豪地说:“凡工人出生至老死,均已顾及。申三劳工自治区颇能合于社会制之雏型,将来各厂定能仿行。”[10]这一系列做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冲突,促进了企业内部工人与管理者、投资者的相互协调。当时外地工厂工潮迭起,而申新三厂却基本不受影响,报界因此称之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11]。
1936年,劳工自治区各项设施建设宣告基本完成。统计数据显示,与开展自治前的1931年相比,申三的总产量、日产量和单位产量5年间增加25%,而此前8年间才增加了24%。事实证明,申三的“劳工自治”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国内民族纺织企业包括荣氏的其他企业相继陷入困境,申新系统年年亏损,但无锡申新三厂却奇迹般地一枝独秀,每年都有盈余,这其中“劳工自治”提高生产效率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劳工自治”实验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定工人生活,减少劳资纠纷。劳工自治区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区内建有各种生活设施,又订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允许工人随便离开厂区,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小社会环境。工人工作之余,要参加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参加文体娱乐,也有人侍弄副业,调节日常生活,各有各的事情可做,能较好地避免社会上政治风潮和不良风气的影响,生活相对和睦稳定。所以当外地和无锡一些工厂发生工潮时,申新三厂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生产秩序基本正常。
二是工人收入增加,劳资冲突减弱。实施“劳工自治”后,工人收入有所增加,工资之外的福利得到改善。1930年代初申新三厂全厂工人每人每日平均工资为0.37元,1936年增加到0.559元,增长51.1%[12]。与此同时,工人的文化知识有所增加,懂得对厂内外的情况和条件进行分析,对民族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民族资本家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支持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工厂效益增加,工人福利就能改善;而工厂一旦搁浅、破产,工人将首先陷于失业的艰难困苦之中。利益的相关,促进劳资之间在遇到矛盾时能以合作的态度来谋求解决。
三是加强生产管理,降低设备物料“暗损”。随着工人组织健全,企业管理相应得到加强。工人对产品质量和企业兴衰,从过去的漠视变为主动关心,对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也从抵触转向响应配合,减少了暗中与资方作对、有意浪费原料和破坏机件的现象。企业由此降低成本,减少了“暗损”,同时增加产量,产品质量也有提升。如纱的单产,全面抗战前夕较之1933年,由锭产0.8磅增至1.1磅,而各项费用开支相比每年减少19万元—30万元。企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相应增强。抗战全面爆发前几年,国内民族工业普遍不景气,不少企业关门停产,破产出售,而申新三厂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年有若干万元的折旧和盈余”[13]。
四是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工厂劳动生产率提升。工人经过培训,操作技能和文化素质明显改善,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33年前,申新三厂每万纱锭需用工人450人,1934年降为297人,1937年降为250人。1933年,一名工人只能管2台布机,1934年增至4台,1937年增至6—8台。工人技术水平的提高既使企业增益,也使工人受惠,这正好体现了荣德生“以事业作救济”的企业经营思想[14]。
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实验也影响社会风气的转变。经过各种媒体的宣传介绍,申三劳工自治区引起社会的广泛瞩目。特别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姚惠泉撰写的《介绍一个劳工自治区》,以及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采写的《参观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访问专记,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参观者络绎不绝,各地模仿者也为数不少。自治区给来访者展示了一幅令人耳目一新的生活画卷,在社会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当时报界特别赞扬自治区宿舍整洁,工人生活井然有序,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不能及,懒惰的小姐们见了也要惭愧无地自容”。一些青少年在参观后,“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感化,有了较大的进步”[15]。
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实验在当时国内私营企业中是一项创举,曾被誉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企业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民族工商企业的管理,刚刚从传统工头制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开始模仿、借鉴西方较为严格、细致的管理方法。被称为“棉纺大王”的上海企业家穆藕初,率先翻译、介绍美国“管理科学之父”泰勒的管理学说,应用于他自己创办、经营的德大纱厂,取得显著成绩。其“出品之佳”,跃居“上海各纱厂之冠”,所产宝塔牌棉纱在全国性的工业品赛会上屡夺第一。随后,上海厚生纱厂等一些纺织企业也学习德大的经验,分别施行企业管理改革,推行泰勒制管理模式,以管理“益见完善”、产品质量优异而成为模范工厂。但是,以泰勒为代表的管理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把工人假设为“经济人”“工具人”,即把工人看作是只追求养家糊口的“经济个体”,抹杀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多层次需要。因此,运用泰勒的管理方法,可以借助严格的纪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产出,但不能充分、持久地激励工人的劳动热情,无法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当时国外一些管理学家为进一步改进企业管理,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物”的管理转向“人”的管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在芝加哥西部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了知名的霍桑实验,其立足点就在于:工人是“社会人”而不仅仅是“经济人”,满足他们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包括信任感、安全感、精神归属感等等,才能从根本上激励其劳动积极性,由此把人性化的管理引入企业。无锡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实验,几乎与霍桑实验相同步,而实验的广度和深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注重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因素,尝试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致力于构建企业全体职工共同价值观,从而增强职工对企业向心力的实验,遗憾的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许多设想未能继续展开,更缺乏理论的指导和总结提高。但是这在中国近代企業管理史上依然具有开创的意义,对于今天的企业文化建设,也是足资借鉴的一笔可贵的观念和经验的财富。
参考文献
[1]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1986年印本,第34页。
[2]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1989年印本,第146页。
[3]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薛明剑文集》(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4]严克勤等:《无锡近代企业和企业家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5]薛明剑:《我参加工业界的回顾》(上),无锡市政协文史委:《无锡文史资料》总第16辑,第54-61页。
[6][9]王赓唐等:《荣氏家族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129-130、131-133页。
[7]无锡国棉一厂厂史编写组:《无锡第一棉纺织厂厂史》(油印本),1983年,第56-57页。
[8]薛明剑:《无锡劳工概况》,《无锡杂志》(劳工专号),1934年11月。
[10]薛明剑:《五五纪年》,《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7辑,1986年8月,第25页。
[11]《新闻报》1935年7月6日。
[12][13][15]薛明剑:《我参加工业界的回顾》(下),无锡市政协文史委:《无锡文史资料》总第18辑,第59、60、58页。
[14]《人报》1936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