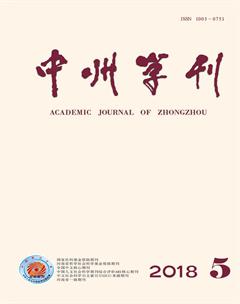《论文八则》:在桐城派视域下的分析研究
张小平
摘 要:邵作舟是晚清维新派先驱之一,维新之路的探索不仅需要在政治上革新,也需要在文学上革新。其1887年定稿的《论文八则》中提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都是针对桐城派的。邵氏的论文扬弃了龚自珍和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揭橥“学识”义旨,认为有“学识”,才会有胸怀。为古文研究与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邵作舟;《论文八则》;桐城派;学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143-06
一
晚清人邵作舟的《论文八则》是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原先只有家藏本和少量印刷本,流传不广,因此没有被《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等集子收录。近些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辑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此稿才得以编在“邵作舟卷”中面世出版。《论文八则》的文学观与那个时代风靡的桐城派文学观截然不同,与其他流派的文论家观点也有所区别,是值得探讨的一部文论著作。作者邵作舟是晚清维新派先驱之一,他的著述很多,除了著名的《邵氏危言》早就出版之外,还有不少没有刊出面世。对他的《论文八则》进行探讨,不仅可以看出这位维新派先驱对于文学的“新”认识,还可以看出他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应缺失的历史地位。
邵作舟是晚清维新派先驱之一,他的《论文八则》定稿于1887年。邵作舟对《论文八则》是颇为自负的,他在《弁言第一》中列举了《文心雕龙》《读书作文谱》以及从昌黎、柳州至顾亭林、方望溪诸作家的文论,认为“求其提纲挈领,巨细毕该,上汇乎立言体用之源,下极乎波折毫发之细,而高挹群言、不落浅近者,盖未之有见也”。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看来,《论文八则》是接近“上汇乎立言体用之源,下极乎波折毫发之细,而高挹群言、不落浅近”的一部著述,是有独特价值的。
清代文坛,桐城派影响巨大。郭绍虞指出:“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①
邵作舟主要生活在桐城派中兴的同治、光绪年间,他的文学思想有什么特点?是否受到桐城派的影响?《论文八则》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呢?
二
邵作舟的治学,经历了四个阶段。他在《弁言第一》中自叙了这段不断探索的艰苦历程:
作舟幼孤失学,姿识弇陋,弱而好文。穷乡僻壤之中,苦于无所师法,遍读唐宋诸大家而心摹手追之。年十八九学于杭州,与程君蒲荪、赵君撝叔游,聆其议论,读龚定盦诸集,而好为艰涩幽险之文。其后习绮体,窥乎宋明诸名集、国朝尤袁洪胡之奥,进而溯乎汉魏六朝。而又好为骈四俪六之文,频年泛骛,厌慕相半,最后爽然恍然,知其皆非三代文章之正也。于是高瞻远瞩,壹志凝神,专寝馈于六经诸子、周秦西汉之文,既愤且乐,誓以终老。
第一阶段是“无所师法”,“心摹手追”唐宋八大家古文;第二阶段是喜读龚自珍文章,“好为艰涩幽险之文”;第三阶段是“习绮体”,“好为骈四俪六之文”;第四阶段是“壹志凝神,专寝馈于六经诸子、周秦西汉之文”。
邵作舟少年时代身在绩溪,心摹手追的是唐宋诸大家的古文。在明清科举时代,通过学习唐宋诸大家的古文,可以提高时文的写作水平,是当时学子的普遍共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晚年编唐宋八家文选,他说:“今为举业者,必有数十百篇精熟文字于胸中以为底本,但率皆取资时文中,则曷若求之于古文乎?夫读书无他奇妙,只在一熟。”②桐城派始祖方苞为国子监就读学生编选《古文约选》,首创以“义法”为标准,约取两汉、唐宋八大家文章,“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方苞认为,掌握了古文“义法”,有助于八股文的写作,“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矣”③。此书刊布后,便成了当时八旗官学之教材。乾隆时,又下诏全国各学官将此书列为官方的古文教科书。桐城派之集大成者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所选文章也是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然后约选前后各朝代知名作家文章作为补充。到了邵作舟少年时代,“姚门四弟子”和“曾门四弟子”继续倡导唐宋古文传统,最终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地位。因此,邵作舟少年时代身在偏远之绩溪,“心摹手追”的只能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年十八九時,邵作舟来到杭州,与程君蒲荪、赵君撝叔游,见到许多新生事物,眼界大为开阔。程秉钊(1838—1891),又名秉铦,字公勖,号蒲荪,胡适先生曾经评价说:“程秉钊是绩溪近代三奇士之一,三奇士为先父铁花先生(传)与邵班卿先生(作舟)及程先生。”④关于程秉钊的生平,山阴蔡元培所撰《绩溪程蒲荪先生遗集序》介绍说:“绩溪程蒲荪先生,先世业鹾吾杭,以钱唐商籍列学官弟子。生数岁,有奇禀,稍长,即知钻研朴学。时未更东南之乱,犹及友事仁和谭仲修廷献、会稽赵益甫之谦、德清戴子高望,此三君皆深究西汉经师微言大义,以绍常州庄氏之学,由武进刘申受礼部、长洲宋于庭大令,为庄氏之正传,递至龚定庵、魏默深,上承申受,下溉谭赵,先生参预其间,耳濡目染,甫及壮岁,学已大成,虽为诸生时,业已名著海内矣。……先生尤嗜《龚定庵集》,自恨身当其后,不及奉手,因以龚学名集。”⑤邵作舟维新思想的启蒙以及后来在经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与杭州这段游学经历大有关系。程秉钊之“尤嗜《龚定庵集》”,影响了邵作舟学龚仿龚,邵作舟“好为艰涩幽险之文”,便是这段游学经历的写照。程秉钊朋友赵之谦(1829—18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与绩溪名士多有来往,对邵作舟的思想也有影响。赵之谦据赵之谦儿子赵寿佺撰《先考撝叔府君行略》记载,赵之谦“少事汉学,十岁后潜心宋学者七年”,后入杭州缪梓幕府,有经世致用之才,与绩溪人胡澍、胡培系等订交,“至于从政论议文牍,老吏见之,欢为莫及”。赵之谦也嗜读龚自珍文章,避居闽中时候,谭廷献藏有龚自珍集外文百八十篇,赵之谦借而抄之。程秉钊在纪念龚自珍的《乾嘉三忆诗之一》中有按语云:“先生没时,予方数岁。年十五,交钱塘沈秀才(方颐),始知好龚先生文。已而与同里胡户部(澍)、会稽赵县尹(之谦)、戴典籍(望)商榷经义,益信先生之学。”⑥可见,邵作舟对龚自珍文章的喜爱,与他们的影响有关。
龚自珍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自负其才气,敢为出位之言”,⑦他的诗文具有追求个性启蒙和人性解放的引领作用,他对卑恶世俗的敏锐感受、对社会危机的独立思考、对黑暗政治的深刻揭露以及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构成了他诗文创作的主旋律,这也是他能够影响一代文风的重要原因。邵作舟之崇拜龚自珍,除了“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經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的时代影响之外,与朋友程秉钊的治学影响也有关系。龚自珍1819年与魏源一起师事刘申受今文经学(即宋学)春秋公羊学教导之后,才开始从中寻找救世良方,汲取公羊学关注现实政治的“微言”精神,以公羊学之“大义”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⑧。程秉钊的学术道路也是从春秋公羊学开始的,他的几个朋友都是公羊学派的学者,“谭仲修廷献、会稽赵益甫之谦、德清戴子高望,此三君皆深究西汉经师微言大义”。邵作舟耳濡目染,也受到了公羊学的影响,这是他崇拜龚自珍的思想基础。
邵作舟崇拜龚自珍,模仿他的文章,“好为艰涩幽险之文”。龚自珍的文章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与清代中叶以来流行的桐城派文风有着显著不同,他在《绩溪胡户部文集序》中说:“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弗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后有文章家,强尊为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计岂有是哉?”⑨古人言情言事,都是说完就了事,哪有什么“文章家”“文章祖”?这里,龚自珍显然是指向桐城派的,所以他主张摆脱一切束缚包括桐城派的条条框框,随笔直书,表达真情实感。但龚自珍有些文章为了达到独树一帜的效果,语句诘屈聱牙,文意艰涩难解。刘师培评价龚自珍的文章说:“龚氏之文,自矜立异,语差雷同,文气佶声,不可卒读,或语求艰辛,旨意转晦。”⑩邵作舟学习龚自珍的文章,后来发现沾上了“艰涩幽险”之弊,于是舍弃了这种文风,从学习龚自珍转向学习骈体。
对于骈四俪六之文,邵作舟“频年泛骛,厌慕相半”,最后爽然恍然,于是又舍弃了骈文,“专寝馈于六经诸子、周秦西汉之文”,他认为这才是三代文章之正,才是文章之源头。
三
《论文八则》是邵作舟个人文章学研究之心得,主要探讨的是文章写作的门径和技法。第一则是序言,第二则是正文之开始。他指出:“今之为文者,不高师法,不讲体要,贸贸焉取古人之文而杂学之,依傍旧意,滥袭成调,剽窃一字一句,自以为古,此以为时文犹且不可,而欲以为古文,吾惑焉。”这里提出了“师法”和“体要”两个关键的问题,《论文八则》全篇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师法”要“高”,这是邵作舟论文的主张,那么,哪个时代的古文才能算“高”?邵作舟设定的“高”标准范文是“六经诸子、周秦西汉之文”。邵作舟提出这一主张,既是自己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前人古文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清代中叶以后,桐城派“师法”韩、柳、欧、苏等唐宋大家的“文统”遭到汉学家的广泛批评,汉学家推崇骈文为古文正统,讽刺桐城文人空疏萎弱。蒋湘南(1795—1854),字子潇,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相友善,在思想上也受他们的影响。他对桐城派提出尖锐批评,否定桐城派古文的正宗地位,认为桐城古文是“伪八家”,是真时文,他在《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中说:“且夫论古文而专以法,此乃伪八家所恃以劫持天下者。不破除此等俗见,必不能以读古书;不读古书,何能为古文?”那么,应该读哪些古书?他说,应该熟读“周秦两汉之文章”:“世之人欲起衰矫弊,必自通经始;通经必自训诂始,欲通古人之训诂,自不能不熟周秦两汉之文章。所谓由文入笔者,真古文之根柢即在于此,伪八家之所以不能自立者,正坐不能如此;此之不能,故以剪裁驾空诸法自雄矣。”B11由此可以看到,邵作舟的古文主张与蒋湘南是一脉相承的。
在邵作舟那个时代,桐城派的“义法”说遭到很多人的诟病。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是鸦片战争后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文论思想,“独不信义法之说”,要求破除桐城派的义法枷锁。他在《复庄卫生书》中说:“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他认为,语言表达只要“称心”即可,反对“周规折矩,尺步绳趋”的模仿剿袭,内容“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有能理而董之,阐而明之,探其奥赜,发其精英,斯谓之佳文”B12。在对待桐城派“义法”的态度上,邵作舟和冯桂芬是一致的,他不仅不信“义法”说,而且认为“义法”也不是桐城派的发明。《论文八则·弁言第一》指出,“至其义法,则有宋以来,若欧苏诸家,若弇洲震川,若荆川石斋,若亭林同人望溪诸君子,皆尝有所论列。独惜其旁见错出,语鲜专门,非杂而无章,则偏而不举”。
邵作舟《论文八则》不信“义法”,批驳“义法”,针对桐城派的“义法”,他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学识”:“盖为文之道,学识为先。”他认为,写好文章,第一位的事情不是“义法”,而是要有“学识”。
邵作舟揭橥“学识”之说,是在总结前人文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唐代礼部尚书郑惟忠向刘知幾询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回答:“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指写作才能,学指知识学问,识是指见解见识。在刘知幾看来,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最为根本的区别,是要有历史的见识。刘知幾《史通·杂说中》说:“夫识事未精,而轻为著述,此其不自量也。”刘知幾说的是史著撰写需要“史识”,实际上,文学创作的规律也莫不如此,文学之“识”的高低决定文学创作的成败。比邵作舟时代稍前的学者刘熙载(1813—1881)在《艺概·文概》中说:“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
邵作舟的“学识”说,与刘知幾、刘熙载的论述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他将“学”“识”合并为“学识”,创铸新词,与桐城派“义法”针锋相对。《论文八则·弁言第一》指出:“至其义法,则有宋以来,若欧苏诸家,若弇洲震川,若荆川石斋,若亭林同人望溪诸君子,皆尝有所论列。独惜其旁见错出,语鲜专门,非杂而无章,则偏而不举。”邵作舟批评“义法”说之“旁见错出,语鲜专门”,言下之意是指《论文八则》是“专门”讨论文章写作法则的著述。
《论文八则》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学识”说。
什么是“学识”?邵作舟认为有七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一曰格物致知,以穷其事理,则文之旨蕴必深矣;二曰博学好问,以富其见闻,则文之凭借必厚矣;三曰浸淫古籍,以高其师法,则文之气骨必古矣;四曰沉潜涵泳,以养其气机,则文之魄力必大矣;五曰讲求体要,以审其施用,则文之格律必严矣;六曰讲求法度,以清其布置,则文之条理必密矣;七曰讲求用笔,以极其变化,则文之精神必焕矣。”邵作舟说:“平时无此七者之功而仓猝握管,求作佳文,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辙。”
“学识”一词,最早用于品评人物,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指的是学问见识。譬如《魏书·于栗磾传》:“(于)忠面陈让云:‘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当今学识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劳于下,我当无忧于上。”《魏书·李顺传》:“初顺与从兄灵、从弟孝伯并以学识器业见重于晨,故能砥砺宗族,竞名修尚。”到了明清,还是这个含义,譬如明高明《琵琶记·才俊登程》:“且在此歇息片时,讲些学识,说些志气何如?”清沈德潜《说诗啐语》:“有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邵作舟标举“学识”,第一次用于文学批评,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一,“学识”说比桐城派“义法”说更有理论高度。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个提法很抽象,很笼统,义即内容,法即技巧,内容与技巧的统一就是文章。但文章内容有进步与落后等差别,写作技巧有自然与雕饰等不同,怎么教导写作者正确地加以区分并选择?邵作舟强调,“为文之道,学识为先”。邵作舟提出的“学识”兼顾事物与文章两个方面,意谓有了很高的学识,就能分辨出内容的进步与落后、情感的真实和虚伪。邵作舟说:“一曰格物致知,以穷其事理,则文之旨蕴必深矣;二曰博学好问,以富其见闻,则文之凭借必厚矣。”首先要做到这两点,写文章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写出的文章才蕴藉深厚。
第二,“学识”说比桐城派文章理论更贴近文学创作实际。继方苞之后,为了说清楚文章写作的特点,刘大櫆以“神”“气”论文。然而“神”“气”毕竟比较虚幻,难以把握,于是刘大櫆要求通过字句、音节去领会,他在《论文偶记》中说,“神气”是文章最精处,“音节”是文章稍粗处,“字句”是文章最粗处。姚鼐发挥了这个观点,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八个艺术要素,认为“神、理、气、味”是文之精,“格、律、声、色”文之粗,文章之“精”寓于“粗”,写文章则要由“粗”入“精”。总的看来,桐城派这些提法还是显得比较虚幻,操作性不强。邵作舟则提出了可以操作的具体门径,他说,“浸淫古籍,以高其师法,则文之气骨必古矣”——即师法古人书籍,可以领会“气骨”;“沉潜涵泳,以养其气机,则文之魄力必大矣”——即吟咏名人佳作,可以养育“气魄”;“讲求体要,以审其施用,则文之格律必严矣”——即熟悉体裁风格,可以严守“格律”;“讲求法度,以清其布置,则文之条理必密矣”——即遵循行文法则,可以缜密“条理”;“讲求用笔,以极其变化,则文之精神必焕矣”——即变化语言笔触,可以焕发“精神”。邵作舟的论述,指导了具体可行的门径,写作者可以一一对应练习。这样的表述,显然要比桐城派更贴近文学创作的实际。
四
邵作舟认为,有了一定的“学识”,“始可为文”。那么,从构思到成稿的文学创作过程,有哪些重要的环节呢?《论文八则·四术第三》指出,有四个环节需要注意:“一曰立意,二曰辨体,三曰布局,四曰修词。”
意,指的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意在笔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晋人以来的文学批评著述,都十分重视立意。南朝·宋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唐代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形象:“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薑斋诗话》中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古人意在笔先,故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致手忙脚乱。”重视“立意”,这是古人在文学创作上形成的共识,因而邵作舟没有对此展开论述。
《论文八则》第四则,邵作舟单独讨论了“辨体”。这里的“体”,指的是文章的体式或风格,邵作舟共分为六类:“一曰肃穆典雅之文,二曰雄骏英锐之文,三曰曲折奥衍之文,四曰灵矫秀逸之文,五曰缠绵委婉之文,六曰洁净精微之文。”西汉之前所有文章,都可归入这六类当中。邵作舟说:“意既立矣,体既定矣。”内容决定体式,“故夫刊碑作颂,以山林疏淡之体行之,则嫌于寒俭矣;纪游赋物,以典谟训诰之体行之,则嫌于官样矣”。
邵作舟把古文总结为六种风格,实际上是对桐城派文学理论的修正。诗文风格的划分,始于《文心雕龙·体性》“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体。唐代以后,愈分愈细。皎然《诗式》提出“辨体有一十九字”: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司空图《诗品》则分为二十四类: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屈、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诗歌这种风格的区分,同样适用于其他文体。桐城派姚鼐认为,文章风格尽管多种多样,按照《易经》的说法,则不外乎阳刚与阴柔两类。姚鼐《复鲁絜非书》:“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萬物世界,没有纯粹的阳刚或阴柔,或偏于刚,或偏于柔,那么凡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都可以归入阳刚一类,凡婉约、幽深、淡雅、飘逸等可以归入阴柔一类。姚鼐阳刚与阴柔的风格区分,以简驭繁,简明易懂,后人经常沿用。姚鼐的二分法虽然简明,但过于概括,文章风格非刚即柔的引导,掩盖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后来的曾国藩对刚柔又进行了细分,“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尽管区分了八种,但还是没有脱离阴阳刚柔的大框架。邵作舟提出六分法是否允当,当可讨论,但他撇开了阴阳刚柔体系进行评论,对桐城派文学理论进行修正,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
邵作舟认为,文章体裁有很多,譬如纪、传、志、状、碑、颂、铭、诔、诏、告、表、疏、序、论、杂体等,“总其大要,不外纪事、议论两端”。这种观点在邵作舟之前就有人提出过,譬如刘熙载《艺概》就认为各体散文的表达手法不外乎“叙事”与“论事”两种,“辞命亦只叙事、议论二者而已,观《左传》中辞命可见”B13。刘熙载《艺概》一书从同治十二年(1873)问世以来,曾多次刊刻。也许,邵作舟的观点来自于刘熙载的启发。对于纪事的笔法,邵作舟总结了十四条,即正笔、旁笔、原笔、伏笔、结笔、补笔、带笔、铺叙立案之笔、提掇呼应之笔、关锁串递之笔、断制咏叹之笔、详略虚实之笔、宾主映射之笔、点缀传神之笔。议论的笔法,邵作舟认为需要注意六个要点:“一曰划清层次,以布其大局。二曰提掇呼应,以挈其纲领。三曰穷源竟委,以洞其本末。四曰反覆推勘,以极其事变。五曰剀切详明,以畅其正面。六曰引喻借证,以助其波澜。”刘熙载在叙事、议论的手法上也提了很多意见,比较概况,而邵作舟手法技巧的总结不仅全面,而且有观点、有举例,写作者容易领会。后来的桐城派作家林纾《用笔八则》总结了“起笔、伏笔、顿笔、顶笔、插笔、省笔、绕笔、收笔”等八种笔法,但其论述之简洁明了稍逊于邵作舟。
《论文八则》第七则,邵作舟提出文章笔阵之“十妙”:“称为大家而不可磨灭者,玩其笔阵,盖有十妙:一曰精,二曰大,三曰雅,四曰整,五曰雄,六曰健,七曰灵,八曰锐,九曰秀,十曰宕。”这里所说的“笔阵”,指的是文章的笔法;所谓的“十妙”,是指笔法的十种品格或风格。这个总结,与前面的“六体”的文章风格论有部分重迭,譬如“肃穆典雅之文”之“雅”,“雄骏英锐之文”之“雄”与“锐”,“灵矫秀逸之文”之“秀”。两者不同之处是,“六体”是指篇章的风格,“十妙”是指语言的风格。邵作舟借“十妙”批评当时文人“动好操筆,刍灵木偶,略具形模,至于此妙,全所未睹。虽蜣螂转丸,自比苏合而满纸涂鸦,适成其为商贾吏胥之恶札而已”。话语虽有偏激,但批评的是桐城派不够重视“笔阵”的研究,邵作舟从写作角度对此做了具体深入的阐述,述前人之未曾述,体现了他对文章写作的独到认识。
《论文八则》最后一则,谈的是文章之九害:“一曰时文之体害之,二曰骈俪之体害之,三曰险涩之体害之,四曰经解之体害之,五曰文集之体害之,六曰尺牍之体害之,七曰官文书之体害之,八曰语录小说之体害之,九曰佛老经咒之体害之。”邵作舟认为,要避免以上之九害,“除浸淫古籍无他策也”。古文,应有古文之面目,清代一些文论家对此就有过讨论,譬如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中就提出,“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章学诚还特别撰写一篇《古文十弊》,指出古文的十弊是:剜肉为疮,八面求圆,削趾适履,私署头衔,不达时势,同里铭旌,画蛇添足,优伶演剧,井底天文,误学邯郸。可以看出,邵作舟关于古文之九害的论述,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有关成果基础上所做的新的总结,视野更加宽广,探讨更加深入。
总之,邵作舟《论文八则》提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都是针对桐城派的。维新之路的探索不仅需要在政治上革新,也需要在文学上革新。桐城派末流走向空疏肤浅,引起维新派人士的强烈反对是历史的必然。如何让文学创作有新的面目?《论文八则》针对桐城派的“义法”说,针锋相对地提出“为文之道,学识为先”。桐城派奉归有光用五色圈点评点《史记》的方法为文学创作“范例”,吹捧为“古文秘传”,实际上开启了后人一味描摩的陋习。邵作舟认为,有“学识”,才有胸怀,才能辨别“古今文体之贞淫正变,源流得失”。邵作舟推倒桐城派崇奉的归有光、唐宋诸家等偶像,要求直接学习“六经诸子、周秦西汉之文”,对当时文坛的模仿陋习确是当头一击。找到本源,才会知道流变,才会写出新面目的文章,这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学古与创新。如何学古?邵作舟的方法与众不同,直接从“六经诸子、周秦西汉之文”的本源入手,撇开了后世奉为楷模的许多文学大家。按照今天辩证法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观点至少是不够严谨的,但在那样一个痼疾缠身的时代,不如此提倡则不能疗文坛桐城派之流弊,这才是邵作舟之用心。
注释
①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上海书店,1989年,第354页。
②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
③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3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2页。
⑤转引自张振国:《晚清徽州奇士程秉钊生平著述及别号考》,《史林》2016年第1期。
⑥王佩诤点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657页。
⑦钱穆:《龚定庵思想之分析》,1935年《国学季刊》5卷3号。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7页。
⑩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428页。
B11B1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8、51页。
B13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4页。
责任编辑:行 健
Abstract:Shao Zuozhou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form movement needs innovation in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 politics.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Eight Articles on Writing Essays completed in 1887, were targeted at Tongcheng school. Shao′s thesis sublated the literary theory of Gong Zizhen and the Tongcheng school, and uncovered the meaning of "knowledge", considering that only when a write has knowledge, can he be broad-minded. Shao′s thesis provided new theoretical findings for the study and criticism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Shao Zuozhou; Eight Articles on Writing Essays; Tongcheng school;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