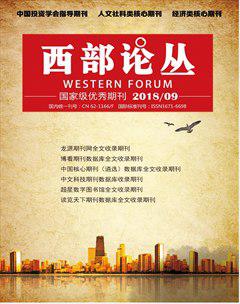戏曲的假定性运用在戏剧呈现的思考
姚东伯
摘 要:中国的戏曲、西欧的戏剧以及在中国的话剧,不管什么时期、什么流派,时空的假定性作为戏剧的本质是永恒存在着的。但由于中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对于舞台时空观念性理解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呈现形式与审美接受。
关键词:假定性;戏剧;中国戏曲
(一)戏剧——“假定”的艺术。
假定性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是在戏剧中约定俗成的以假作真的表现方式。
在戏剧艺术中,则指戏剧艺术形象与它所反映的生活自然形态不相符的审美原理,即艺术家根据认识原则与审美原则对生活的自然形态所作的程度不同的变形和改造。艺术形象决不是生活自然形态的机械复制,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定性乃是所有艺术固有的本性。
尽管假定性从不同于现实生活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一切艺术的本质特征,对于戏剧而言,一种观众和演员之间达成的“契约”使得戏剧演出中的时空假定性显得更加突出。成为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独有的本质特征。当观众走进剧场,一项古老而永久有效的“契约”通常被默然认可并被忠实履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戏剧舞台上,无论认可与履行的程度与方式有多么大的差异,这种“契约”总是存在着并以强大的威力统治着整个舞台进程。可以这样说,缺少假定性的戏剧乃是一种危险的戏剧,因为它时刻都有可能从“艺术”的框范中脱轨而出,成为现实人生的直接映射。一名没有观剧经验的观众,在他还没有接纳戏剧舞台独特的假定性欣赏法则时,在他还没有成为“契约”的接受者时,常常可能会出现“跳戏”的现象。
由此正好可以说明,假定性一旦被忽略,舞台艺术也就在须臾之间从童话世界落入了人间,根本不具备她的一切魔力了。假定性原则,用普希金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真的一样”的舞台原则,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舞台行为和这些行为的终极追求。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乃是因为其不同于真实的本质属性。戏剧艺术在这一点上就体现得更加突出: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的戏剧舞台,都以假定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时空环境为戏剧演出的必须准备,都以假定性的存在为自身之所以成其为戏剧的前提条件。尽管假定的手段和追求的实际演出效果以及所牵涉到的审美理想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假定性”却是它们不约而同遵循的创作原则。
(二)戏剧舞台上的“假定性”
谭霈生教授在解释这个“约定俗成”的时候说:萨塞给戏剧下的定义可以简化为:借助于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东西给观众造成真实的幻觉。所谓“约定俗成”,指的是“假定性”。它是一切艺术固有的本性。戏剧艺术在长期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假定性的特殊表现范围和表现方式,如处理舞台空间的假定性方式等。“假定性”的含义在于对生活的自然形态进行变形与改造,使形象与它的自然形态不相符。在戏剧艺术中,诸方面的假定性程度唯一的限度就是与观众之间的“约定俗成”,它正是凭借这种约定,使得观众获得真实的幻觉,以实现审美的目的,在当代戏剧中,也有人在强调“假定性”这种固有本性时,否认造成“真实的幻觉”的必要性。很显然,其中““真实的幻觉”是一个理解“约定俗成”含义的关键词,而间接地,也就作为了理解“假定性”含义的感性依托。事实上,作为尊崇“第四堵墙”原则和“当众孤独”表演体验的西方传统表演戏剧理论的基础命题,“真实的幻觉”一直被视为构成戏剧呈现必不可少的条件。西方戏剧舞台讲求“幻觉”,要求剧场的氛围乃是生活真实的折射,要求演员的演剧与观众的观剧心态是全身心的“融入”,作为角色融入到剧情和人物本身合二为一。于是演员不成其为演员,观众也不视演员为演员。哪怕演员诵念的是日常生活中绝少可能上演的莎士比亚式台词,观众也因为那种永恒的“约定俗成”而自觉地将演员从其真实身份抽离开去,同时放置入人物的躯体和灵魂之中在这里,演员在第四堵墙之后孤独地表演,体验着角色此时此地的最可能产生的真实心境,以分不清自身与角色的区别和距离为至高境界,以求营造出“真实的幻觉”这一兑现假定性表现原则的最高目标。而观众在长期的戏剧观赏经验或者本能的想象力驱使下,忽略了可能阻隔与“幻觉”和人物心理做最真诚和直接交流、产生强烈共鸣的所有技术性因素,而找到了正在第四堵墙之后孤独着的演员(或者角色)。此时演员与观众在心理时空发生情感上的共振,演员通过角色的声音和形体引发观众的真实幻觉,从而令舞台上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假定。而这种假定性符合西方经典的戏剧理论要求,“真实的幻觉”可以概括西方戏剧舞台上“假定性”的最本质特征。 这种对在“第四堵墙”理论下产生的对制造“幻觉”的近乎苛刻的要求,反映了西方戏剧的基本美學理想。进入现代,西方戏剧在传统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众多流派,比如对二十世纪戏剧理论与实践影响深远的非再现性意象表现的戏剧,就与传统意义上的“幻觉”思想格格不入。
(三)中国“戏曲”假定性对于话剧的作用。
中国戏曲艺术虽源于生活,但却是把生活加以集中概括、并在为一体的基础上,通过夸张变形的美化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必定与自然形态的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产生了艺术的假定性。这是中国戏曲的民族特色之一。在舞台表演当中,演员是真实的,可是舞台上通过幕布、侧幕、布景、灯光、道具制造 了一种假定性很强的舞台环境。演员就在这种风格化的舞台上进行创作。而观众由于认同了舞台的这种假定性,并把这种假定性看做舞台表演的一部分,所以易于接 受演员的创作。而由于这种假定性的环境,也决定了舞台表演的特点。
近年来在中国话剧导演向民族戏曲学习的同时,戏曲也提出了向话剧学习的要求,鲜明地表达了双方彼此借鉴交融的心愿。话剧是从西方舶来的舞台形式,它可以运用“假定性手法”显露假定性本质,也可以运用“逼真性手法”掩盖假定性本质,而中国传统戏曲则是全然使用最显而易见的“假定性手法”袒露其自身的假定性。话剧导演在时空处理上假戏曲舞台充满想象力、空灵感和高度智慧的环境处理方式之力来结构环境空间和心理空间,而戏曲导演则引入话剧营造部分的幻觉以打破传统的全然“假扮”模式以求在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空间的挖掘上更进一步。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将两者的假定性理解相交流的尝试,它们共同的理想应该是构筑“无所不能”的“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的完整而真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