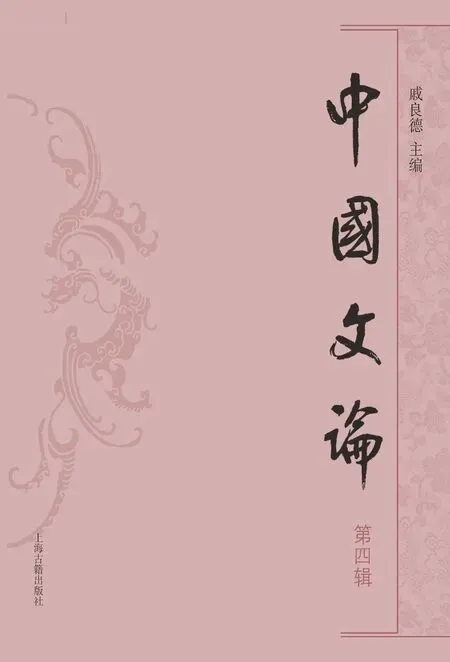刘勰文论的创新与诗学的局限
[美] 林中明
一、 释 题
(一) 综核群伦,识犹未逮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博通诸子,系统井然,文字典雅,博学深究中西文论的学者,咸以为此书是古今中外文论中的经典之作。然而雷打高树,风撼大楼,一些近代学者,在反抗传统国学框架之余,对于《文心雕龙》的权威难免产生反作用力和一些逆向思考,时有疑其思想保守及缺乏创新者。所以博学强记又有小说创作和诗集传世的钱锺书先生,便尝于《管锥编·列子张湛注·评刘勰》中批评《文心雕龙》“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似有意阐明己书之长,以别于刘勰之短。近年更有一些学者开始批评刘勰既然在理论上源本乎道、征师于圣、宗经述诰,而方法和范围又延续《文赋》《流别》等前贤文论,所以他并没有开发崭新的疆域,而且缺乏有分量的原创成绩。忽然间,在二十世纪之末,一位集古典文论之大成的大师,似有遭批遭贬,成为南北朝时期“古典文论杂志”总编辑之势。
(二) 闻之者众,知之者寡
如果要从大家都看得到,而且熟悉的数据,以及刘勰的序文表面文字而言,他确实是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和方法,再加以排列组合,编写出《文心雕龙》。所以乍看之下,似乎批判者的控诉,一审成立。然而一个人能把百千前人的千万册著作“消化”,再用当时是“现代化”的典雅骈文,不加水添油,精炼地写出“一针见血”的文学批评,这在古代固然少见,至于现代,更是稀有。所以二十世纪西方大诗人兼文学批评家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传统不容易继承,如果你需要传统的知识,必须拼命用功,才能据为己有”。二千五百年前《孙子兵法·计篇第一》早就说:“(道天地将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同样的道理,现代的人,多半专修一科,但也不一定都懂得这一科里的现代知识,更不容易消化古代有关的智慧。这可以说是“旧固不易承,新亦不易得”,类似于宋儒说的“理未易明,善未易得”。
(三) 刘勰知兵,通变破旧
所以刘勰能融会如此庞大数目的旧学,这让大部分批评刘勰的用功学者,也不能不佩服他勤学博识的成绩。但是更重要的是,批评刘勰的人多半所没有看见的,是他不仅学通佛儒,而且识兼文武,曾以过人的胆识和行动,竟把《孙武兵经》的兵略消化以后,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大量地融入了他的文论,用于事业,并开发出许多崭新的文论见解和篇章,如《定势》《通变》诸篇,以至于其立论见解都超越了过去的文论典籍,因而正式为世界文论开启了新的天窗。
刘勰博学但是“通变”。他在《定势》篇里特别批判那些“假创新、真搞怪”者曰:“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所以那些批判他“保守”的人,完全是以偏概全地找他麻烦,俾以逐奇而扬识,幸立“一见之言”。但是刘勰不是一个单一课业的“专家”,而是一个博通佛、儒以及兵法等学问,不能简单归类的“大师”。因为“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乃在于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常常超过大多专业学者的理解范围。所以我们要想认识一个真正的“大师”,必须有“瞎子摸象”的精神,从多方面来摸索,作片面性的评价。譬如,他曾抓住机会,孤身奏改二郊祭祀以清净蔬果,取代数千年来(包括中西人类)以残忍的流血牺牲来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这是极其大胆的“反传统”主张和“自反而缩,虽千万人而往”的果敢行动。所以我要劝一些偏颇的学者们,千万不要轻易地给“通变”而“意新”、“执正以驭奇”的刘勰戴上一个“儒家保守派”的“纸糊大帽子”。
(四) 博学强记,负重难远
此外,一个博学强记擅于分析的学者,由于记忆库里不断强力储存信息,和一步一逻辑分析的习惯,往往使他不能分出额外的脑力空间,去突破自己日夜记忆的前人学说和已知的方法及习惯的步骤。我认为钱锺书先生对刘勰的批评,其实反射了他自己对于博学强记而无本身思想见识大突破的忧虑。就像一个浑身佩金戴玉、锦衣珠饰的人,虽然行走时金声玉振、珠光宝气,但是负重过度,担心碰坏身上的珠宝,以至于不仅不能跳高快跑,更不敢独力远行。除非他能偶尔放下身外的“宝物”,“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或是登上新的“知识平台”,远眺天下,那么才可能有一次又一次的大突破。因此,知道越多,思想包袱越重,文论创新的困难之于刘勰,亦如文学思想创新之于钱锺书,是一个倍于常人的“全副武装越野赛跑”的大挑战。钱先生的突破似乎为他的博学多识所掩,未能突显出何为其最重大的“深解”突破,和前人所未能为的创新“立家”。类似的压力也一直围绕着刘勰和他唯一公认传世的著作——《文心雕龙》。似乎刘勰自认足以“立言成家”的大突破也不幸为他的博学精思,和中国文论著作中罕见的井然系统所掩,几乎沉寂了一千四百多年。
为了较全面而宏观地重新探讨《文心雕龙》的特质,以下的讨论将采取“双线平行”且“辩证”的方式,提纲挈领地来探讨“龙学”里至今尚未被积极探讨过的两大问题——“文论创新”和“诗学局限”。“文论创新”的讨论是针对批评刘勰思想“保守”而来,而又以刘勰能融合“文、武”两个对立的观念加以赞扬。“诗学局限”的看法,则是把刘勰的成就还原到他实际的广度,并为“情、理”两种个性之不易齐飞,和社会与政治的局限,为刘勰的“诗学局限”而惋惜。
二、 刘勰文论的创新
《文心雕龙》除了在编辑方法、系统和评论前修、古文之外,有无重大的文论思想“创新”?以下从五个方面来谈:
(一) 动机: 刘勰未写《文心雕龙》时,就准备“创新”立家
评论创新,要由三个阶段来观察比较: 第一,“就地论事”,不应该把那个地区和另一个更先进的地区来比。第二,“就时论事”,我们要以当时和过去的时代来考虑,而不是和一千年后相比。第三,不论“时空”,只论该科历史上的“总价值”。譬如说物理学的发展史,不论时空,牛顿和爱因斯坦必然名列前茅。因为这是和古今中外相比,所以是考虑成就最难的一个关卡。只有几个“宗师”和“主要”的“大师”可以列入。因为刘勰也自知只到“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序志》)的身份,所以还不能算是“大宗师”,因此我们应该就“当时”“该地”而论其“创新”与否,“分量”如何?
刘勰在《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可见他未写书时,就准备“创新”立家。书出了之后,也得到当代博学而且当权的沈约以及梁武帝等的欣赏。可见得《文心》一书,在“当时”“该地”是被权威人士公认为创新而且有分量的佳作。
刘勰立言,自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序志》)所以他一开始就标明《文心雕龙》不是一本为立异而逐奇之书。与时下文艺人没有新意,不能作“有用”的创新,只好把“为反对而反对”当成“新意”;或亦步亦趋,下模仿落子的“东坡棋”;或破坏现有结构,美其名曰时间上的“后现代”和内容上“解构”之类“没有主义”的主义等名家。但刘勰写《文心》,开始就胸怀大志,有意突破前人樊篱,并提出自己的正面看法和新见解。
(二) 先述本,再出新: 《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广义为先、参古在后
今人看一千五百年以前的文论,难免觉得文、意俱古,很容易把古人的“旧”东西,都直觉地当作是过时和落伍的“陈年旧货”。政治人物如此说,我们可以嘲笑他是“泛政治”的动物。但是新一代“逐奇”的学者这么说,似乎显得“新锐”有朝气。但是既然刘勰早已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定势》)。难道他自己不知“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通变》)吗?所以学说立论,要说有此事,比较容易,双证就站得住脚。说“无此事”,则常相对地困难。说刘勰没有“创新”,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学禅宗六祖惠能,当年在广州法性寺,为“风动还是幡动之争”所说的有名机锋评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来评论某些批判刘勰思想保守的学者。那就是,是刘勰的观念保守?还是(某些)学者的观念保守?不能会通?
有些新一代学者最爱批评的就是《文心雕龙》开头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认为刘勰的思想保守,抱“经”迷“圣”,泥古不化。这类话说久了,似乎也成为一种“新锐”的“高论”。其实细看《文心雕龙》开头的三篇,我们就会发现刘勰在每篇的发端,都必先从基本的角度,来看广义的道理和情况。然后才举出他所认为什么是最适当的范例,或是窄义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断言刘勰思想保守,多半是不了解他的写法,浮观文气,因而陷入并反映了他们自己先入为主的“保守观念”。
(三) 刘勰的文论精神和果决行动: 正反兼顾、辩证会通、容异创新
因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引领全书,所以许多认定刘勰思想保守的人,须要细看下面的《正纬》和《辨骚》两篇,才能体会刘勰正反兼顾,兼容并蓄的精神。因为《正纬》篇强调容异,这也不是一般传统保守的儒生敢提倡的开明观念。而《辨骚》篇“参古定法”总结全书最重要的枢纽五篇。在这篇里,刘勰不仅注重人格,而且重创新,望骚赞奇!了解了刘勰这样厚积而跃发的文论思想,谁还能指责刘勰保守?刘勰早期思想必然相当独立,后来成书、谋官到协制素食供奉和自行焚发出家,“趋时必果,乘机无怯”(《通变》),全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行动懦弱的文士。
(四) 谐讔、幽默、讽谏: 对民俗活力和心理学的重视
《文心雕龙》中还有一个突破汉儒传统,回归继承《诗经》和孔子的特别篇章: 《谐讔》。进步的文明,因为文化的开放,都会注重戏笑的娱乐,和“文胜于武”的幽默戏剧、讽刺文学。这些都可以在《诗经》文字、孔子言行,以及古希腊的喜剧里见到。只是后来的政治宗教的束缚,中西都曾分别僵化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在刘勰之前的文论不见文人提到“谐讔幽默”文学,刘勰之后的韩愈,偶尔写些幽默小品遣怀,还被年长弟子张籍批评告诫。对于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民族”(鲁迅评中国人的幽默感)来说,我们回顾东方文学史,不仅要对刘勰的《谐讔》篇致敬,而且面对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高度发展的幽默品位,和对照当前流行“无厘头”式的笑闹,和有些人引以为豪的“全民乱讲”剧目,我们多少要感到一些“幽默感”不进反退的惭愧。
(五) 文武合一: 《斌心雕龙》
以上的四项“创新”虽然值得重视,但是刘勰真正的突破和大创新乃在于他才兼文武,胆识过人,竟把《孙武兵经》消化之后,或显或隐,不见斧凿之力地化入了他的文论,于是他能站在兵略的“知识平台”之上,以“文武合一”的新视角来讨论文艺智术,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文论经典,为世界文论开启了一扇新的天窗。
特别是由于他融会贯通了看似对立的文武之道,所以才能如“滚木石于千仞之上”,举重若轻,有系统,首尾圆合地应用兵法于文论,而让钱锺书等的巨眼都看走了眼。
对于刘勰“文武合一”的文论突破,我的探讨不仅从《文心雕龙》本身去分析其中“族繁不及备载”的句字,更综合了《文心》和《孙子》的精神,用“斌心雕龙”的角度和思维去分析文艺创作,得到一些初步成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最后一篇《程器》的最后一段写道:“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言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这可以说是全书的结论重话。一千五百年前刘勰把《孙子兵法》破天荒地提升到“经”的高度,这是极其大胆的突破和创新!今天仍然让我们震惊和佩服。
谈完了《文心雕龙》在文论上的创新,以下就来看刘勰在诗学上的局限。从辩证的角度来说,这是“文武之道,一弛一张”的运作,而且也符合《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以及给予刘勰《文心》里一强一弱、一明一暗的两大方面以公正的评价。
三、 《文心雕龙》诗学的局限: 避于情,略于质
我们既然大都认为《文心雕龙》是古今中外世界级的文论经典,所以在辨明它的保守和创新之后,就应该以世界诗学的视野和高度,来评论《文心雕龙》枢纽五篇之后,三篇直接讨论诗赋乐府的诗学篇章——《明诗》《乐府》《诠赋》。
(一) 什么是诗?为什么“诗不是文”?
刘勰在《文心》里,用了《总术》《章句》和《体性》等篇来分别“文”“笔”“言”的形式和内涵。虽然后人对这些简略的叙述还是有争议,但是刘勰至少是尝试给它们下了一些定义。但是刘勰与专写《诗品》论诗的钟嵘,却把“诗”当作人人接受和理解的文类,不必再解释。在《明诗》篇里,刘勰没有分辨“什么是诗”,为什么“诗不是文”,而“文也不是诗”?至于要用上许多字来写“诗”?一句和千行,这都还算是“诗”吗?“什么是好诗”和“大诗人的条件”为何?这一类有关诗的“本质”的问题,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不注重,认为这些是“想当然尔”,不言自明的常识,连最慎思明辨的刘勰也不例外。相比于近代西方文论学者,他们又过于喜欢给“诗”下烦琐的定义,但是多半回转于学术术语,汇为专书,但是也很少能用几句话,就把它说清楚讲明白。有鉴于此类的困惑,我曾经借助于《孙子兵法》和现代的常识,试图给“诗”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 诗者,乃“用最少和最精炼的字,借助视觉规范和听觉效果,表达最多的意思和感情,又能强烈感染读者之心,留下最深刻而久远的记忆”者。
根据这个理解,诗、乐府、词、赋,虽然形式名称不同,但是就“用最少和最精炼的字,借助视觉规范和听觉效果,表达最多的意思和感情,又能强烈感染读者之心,留下最深刻而久远的记忆”而言,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同一文类,但它们和“文”或是 “散文”,还是有基本上的大差异,但也不能强行分割,而且还有“混合体”的问题存在。
(二) 逻辑偏颇:“持人情性”者,岂独持于诗?
因为刘勰和其他的中国文论学者都未尝清楚地说明“诗”与“文”的基本差异,所以当刘勰在《明诗》篇里利用文字学给“诗”下定义时,他所说的“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就在逻辑的“充要性”上出了相当严重的偏差。因为如果说“诗”是“持人情性”的文体,那么必须把对立的“文”是否“持人情性”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如果“文”也能“持人情性”,则何不说“文亦宜然”,像他在《程器》篇所作的正反两面讨论?或说“文偶亦然”,以表明“文”偶然如此,但“诗”大部分是如此。可是,如果“诗”的特性“文”也有,则是共性,而非特性。若非特性,何必特别用此一句来“明诗”,岂不是多此一举?
如果刘勰的意思是“持人情性”为“诗”的特性,而“文”不是如此,那么新会梁启超自云为文时“笔端常带感情”,和日人厨川白村写的《苦闷的象征》难道不是“持人情性”的“文章” ?
(三) 何以“指瑕”刘勰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作者尚未见前人有论及者。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分析,乃是针对为文特具逻辑思维的刘勰而发,因为他深受《孙子兵法》朴素逻辑和印度佛学里(因明学)前驱的逻辑理则思考所影响,为文立论,大多相当严整,异于一般感性挂帅、前后定义可以截然不同的文人。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条似乎尚未为学者所疑的定义上,刘勰的逻辑确实有所偏颇,研究刘勰“诗学”和《文心雕龙》的学者,对引用“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一句话时,不可不加以注意和有所约束。
《文心雕龙·诠赋》篇说“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其实也是想针对诗赋的本质来探讨文学,但由于时代知识的限制,刘勰也不能超越自己的环境,来作分析和探讨。相比于爱伦坡以诗人身份,直批“长诗非诗”,和诗人兼骑士的菲利普·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认为希腊的色诺芬和赫利奥多罗斯的散文都是“完美的诗”,他们两位特选范本,针对“现象”,“直指诗心”,反而更见本体。
东西文学由于文化知识背景不同,在本体和实用上的思维分别,就有如五祖见神秀、慧能偈,喟然有各具体用与短长之叹。但从宏观的立场而言,东西诗学的互补,未尝不是一件有益处的分工。二十世纪西方大诗人兼文学批评家的艾略特,在他31岁的时候,大约相当于刘勰开始写《文心》和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年纪,也写了一篇文论的名著《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指出“每个民族,不仅有他自己的创造性,而且也有他自己的批评心态。 但对自己民族批评习惯的缺陷与局限,比之对其创造性天才的缺陷,更容易忽视”。刘勰曾写了《指瑕》篇,指出“古来文才……虑动难圆,鲜无瑕病”。我们挑经典之作的毛病和局限,就是因为承认其成就,所以更希望从它的缺陷处反省,俾以在坚实的基础上,建构出另一个中华文艺的高楼。
(四) 说理叙情,古难两全
讨论诗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文学史上“两难” 的问题: 最逻辑、有理性、重系统的文艺批评家,往往不是一流的诗人和艺术家,反之亦然。柏拉图站在哲学家的高峰上,大力批判另一个绝顶上的诗和诗人,言辞雄辩,似为真理。但他的高弟亚里士多德却写了《诗学》来反驳他的老师,虽然残卷不甚周全,但已是西方诗学开山祖师。可惜他没留下诗篇,这和刘勰擅于论说和写碑文,却无独立诗篇留下,佐证其宏论,这都是文学史上遗憾的事。
诗人下笔以感性为导,时空和人称都有相当的自由。但学者写论文,注重理性分析,前后文意必须衔接,时空不能跳跃反转,受到类似希腊戏剧“三一律”的限制。俄国文艺研究家尤里·泰恩雅诺夫(1894—1943),就曾把电影的“蒙太奇”自由剪辑的手法和诗并论。首创“蒙太奇”观念的爱森斯坦(S. Eisenstein,1898—1948),更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因为学习迥异于逻辑性强的(一维)拉丁字的(二维)图形汉字,而启发了他的“蒙太奇”创作。
刘勰的文章重点在说理,欲成一家之言。再加上定林寺的环境,以及佛学里隐藏的逻辑因明学,都很可能影响、塑造和限制了他的思维,以致不能成为大诗人,也没有留下自豪的诗篇。
一流的诗人和艺术家,往往没有耐心和兴趣去写分析性的文章。因此,刘勰和钟嵘,很可能因为他们自己不是一流的诗人,所以和写《艳歌行》的前贤陆机相比,钟、刘论诗的亲身体会与终极情怀不能超过《文赋》的自然贴切。若与西方古罗马的诗学相比,似乎也弱于擅写讽刺诗、情诗而以书信简谈《诗艺》的贺拉斯。
《文心雕龙·明诗》篇开章就藉大舜之言说“诗言志”,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延续儒家政教为主的“传统”说法。从兵法的运用来说,《明诗》篇“以正合”,但没有提出新意来“以奇胜”。这就好比说阴阳太极图,只描述阳而于阴无所发明,或是《易经》卦象的六爻只说前半的正义,不谈后半部的卦变。所以《明诗》一篇“述而不作”,评旧而未能发新。这是文论大师刘勰的局限,但也反映时代的知识和风气,再大的“才、学”也还是站在时代的“知识平台”上看人情世故。以同样的要求看钟嵘,他的《诗品》也不例外。正应了刘勰自己的话,“文变染乎世情”,不能苛求。
(五) 感物忘人,买椟还珠

近代德国大诗人里尔克在他著名的《给年青诗人十封信》的第一封信中就指出,写诗,应该是从个人的感情经验学识开始,然后才及于外物和自然。没有大才华,开始写诗别写俗滥的情诗,但高手壮笔不在此限。《老子》称赞“道法自然”,因为自然的空间广,时间久,所以文学艺术凡以自然为法者,自然能大能久,而有助于“文化纵深”之外的厚度和广大。好的诗虽然短,但是因为表达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基本感情,和对大自然深刻的体验,所以得“人(情)天(道)之助”,而能够持久和远传。刘勰《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开头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两位文论大师论诗半斤八两,严谨平典有余,只是可惜在人情互感不强,放在现代诗学论坛上时,就难免“未足以雄远人”。
(六) 绚素之章与闲情之赋: 子夏与陶潜之儒
《明诗》篇其后又说“子夏监‘绚素’之章,故可与言诗”,更是脱离了《诗经·卫风·硕人》 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赞颂美女的原意。子夏当年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三句问孔子。孔子用“传统美学”的道理来解释“素以为绚兮”的道理,子夏当然听得懂这种浅显明白的解释,所以用“赋、比”而“兴”的方式,推演其理到“礼”亦为“文饰”本性的作用,所以获得孔子“举一反三”的称赞。但是孔子和子夏都具有“文化纵深”,所以能够同时欣赏美人、美术,及了解礼饰是由“本能反应”转化为“艺术手法”,再提升到“礼饰节制”的考虑。
孔子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宗师,子夏也是第一代的“大儒”,所以见识思想高出后之小儒。后世的儒家学者,“去圣久远”,“离本弥甚”(《序志》),“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征圣》)?恐怕许多人都不能想象《论语》中没有列出的对话和文句之间隐藏的有关意义,难怪以昭明太子之贤之学,仍然要以陶渊明的《闲情赋》为“白璧微瑕”。而不知陶渊明才是真正懂得《诗经》里如春风听鸟鸣的感情,也不能理解《论语·八佾》里,孔子和子夏独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称赞美人。我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没有提到陶渊明,不是刘勰的疏忽,而是写书时刘勰尚年轻,其环境不利于了解《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男女情诗,同时人生经验也尚未足以了解成熟的陶渊明。钟嵘虽然列举陶诗,并以“风华清靡……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来推介渊明,但他和年轻时代的苏轼一样,对陶诗的特性和高妙处也还是一知半解。
《诗》不止“思无邪”,还有“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当刘勰在《明诗》篇首段举出“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以为这才是孔子唯一的教训时,已经局限于忽略了《诗经·鲁颂·駉》里还有“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三句更广泛活泼的话。所以当刘勰又在《乐府》中批评“淫辞在曲,正响焉生”时,《文心雕龙》的“诗学”已经形存而神盲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淫词之病”和“游词之病”分开来讨论。因为好的诗词,非无淫词,然“以其真也,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由此观之,王国维的诗词学比刘勰开明。但是我们也别忘了王国维曾受过西方科学的训练和文艺洗礼,当然应该比一千四百年前的刘勰进步。
四、 刘勰论文重理寡情的原因
《文心雕龙》虽然是中华文论的宝典,但是“吾爱吾师,更好真理”。我们只有在充分地了解了《文心》的建树和立论之后,才能发现和检讨它的一些局限。能了解《文心》的时代局限,才更能欣赏他个人的成就。以下试列举一些可能的情况,来探讨刘勰的诗学重理寡情的部分原因。
(一) 定林佛寺环境的影响
刘勰在佛教寺院校经写书十多年,较长期持续地受到佛教戒律和环境的影响。中华佛教严戒男女、酒肉、歌舞等世俗放荡感情的举止。这必然影响到刘勰写书时的风格与内容。日本和部分藏传佛教不禁男女酒食,可以结婚生子、回家睡觉的作法,不是任何中华正统佛教所能容许的戒律。所以研究断绝男女私情的佛理,也就影响写文论重理寡情的风格和内容。
(二) 儒家政教与民俗艳情的分离
但是刘勰入仕梁朝之后,仍然可以写修订版的《文心》,所以定林寺对刘勰的影响,只能算是一生前半部分,不能算是最后和最主要的影响。况且刘勰在定林寺时,显然还不是佛教徒,因为刘勰在全书最后一篇《程器》的后一段,强调“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摛文必在纬军国……”。“纬军国”岂有不从事佛徒禁止做的战斗杀戮?由此我认为刘勰彼时确定不是佛教徒,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信徒,所以写书也遵循儒家政教的要求。
更有可能的是统治阶级和自战国到汉代以来的儒家教条,使得在官方和较正式的公众场合,官员及学者都遵循儒家的政教理念来看待文艺音乐。以致王室官场政教和私下写作的标准分离。在正式的场合,大家一本正经,谈道遵礼。但在非正式的场合,梁萧王室却悦写艳诗蔚为风气。所以才有徐陵编出《玉台新咏》来取悦贵妇王室。而与此同时又有昭明太子、刘勰、钟嵘等人编写出一本本正经守礼的文选、文论、诗品等书册来。这好比太极图的阴阳共存于一图,又好像粒子和波动两种说法分掌物理世界。
西方罗马的贺拉斯,写诗也不能不听命于统治者奥古斯都的政治与宗教的政策。但好在奥古斯都是一个较开明的独裁者和支持人,所以贺拉斯的诗艺得以兼顾文学和政教的需要。 但刘勰、钟嵘回避情爱文学不予讨论,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不知道另一个“俗文学”和“真性情”的文艺世界的存在。古代“情”和“乐”相关联。1998年刊布的《郭店楚简》,其中的《性自命出》就说“情”多由“乐”起,“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拔人之心也厚”。在钟、刘之前的嵇康,是晋魏时的大音乐家,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因其所有,每为三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但是太开明的文艺理念,也潜伏着在政治上鄙夷专制的心态。他想要争取一些思想自由,保持一些士人风骨,因而遭到杀害。所以“政教与俗情”分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明哲保身的官场文化。
譬如说喜好与元稹应和艳诗的白居易,到了他自编诗集的时候,便有意避开“艳情诗”的分类,而以“感伤诗”名之,我认为他不及元稹编诗分类时诚实。元稹寄乐天书中说他诗集中“……因为艳诗百余首”。但曾任宰相的元稹也不得不小心的加上一句“又以干教化者”,以免被敌人以“不护细行”参奏一本。和西方比起来,东西两大文明都经过“放、收、放”,从开明到黑暗专制再回到人性理性的过程。只是西方的“浪漫时期”率先成了近五百年文明世界的典范,使得中国三千年的诗学突然落后了西方,到现在中国诗人还不自觉地在“情、理”不易共存的传统下挣扎。李商隐的《锦瑟》无题诗,到现在文评家和诗人还不能定其性质,也正是反映了中华文化对“情、理”的说不清,理还乱,不及西方以人性为本来得开明。
(三) 昭明太子的喜好和作风
既然昭明太子性好虚静典雅,他的手下诸臣一定也奉承其所好,走圣贤谟训、正经“无邪”的风格。刘勰作为东宫太子的舍人和御林军队长,自然尽量保持《文心雕龙》典雅的原貌,避免修改“理胜于情”的篇章。但是如果刘勰曾经修改过《文心雕龙》,那么《文心》中不提昭明太子喜爱的陶渊明诗文,则是不合情理的事。所以我认为刘勰为了个人事业的目标,和由于个人性情的倾向,《文心》如果有修订版,受昭明太子喜好的影响也是有限。但是从《昭明文选》选了四篇“情赋”来看,实在让人难以了解,昭明太子为什么要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讽谏不及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的《洛神赋》?难怪东坡要讥笑萧统是“小儿强作解事者”。或者萧统反而受到刘勰的影响,或担心梁武帝的批评,而对陶渊明的《闲情赋》必须表态,作出“白璧微瑕”的批判?
(四) 个人性向与战略目标
由刘勰个人行动果决的性向来看,他在有限记载的一生中,几次运用兵法,采主动,完成他事业的愿望,继续迈向“纬军国,任栋梁”的既定目标。所以以上的三个原因都不是决定性的主因。而最可能是配合他个人的事业目标而预订“作战”方略。更由于他中年以后逐渐变成真正的佛教徒,加上官场文化的限制,我认为即使刘勰后来有机会修订《文心雕龙》,也只是在文字和编排上做了改进。但于“诗学”则遵随传统儒家思想,和更加倾向于梁武帝所益加尊信的佛教思维,所以在文论和诗学上没有更开放或新奇的论点。如果他在晚年还有新作,包括刘勰是否为《刘子》一书作者的问题,刘勰的文笔仍然雄雅腾跃如三十多岁写《文心雕龙》时?这也是另一个可争论探讨的好题目。
五、 诗学即人学
诗学其实也是“人学”和“人道”。不能整体对待人性的诗学,就不能得其全道。所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不逃避人的关系,而分别以适当的态度相面对。《乾卦·文言》说:“龙德而正中……闲邪存其诚。”就是说持中正的态度,闲防邪恶的影响,保存真诚的部分。后儒为了正心诚意防闲杜渐,干脆把真诚的情诗和淫荡的艳诗一起抛开,免得讲学解经时惹麻烦。所以“进德修业”时虽然看起来是像《乾卦·文言》说的“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但是把人人动心感人的情诗抛开,假装没有看到,这其实反而违反了“修辞立其诚”的基本要求!由此可以看到胆敢把《关雎》一诗放在《诗经》之首的孔子(或前贤),心胸是如何的开阔!而后世大部分儒家学者过度的拘谨,竟把真正的“孔子之学”变成了“限制本”的“部分孔学”。于此,作为一位传统政教社会下的学者,刘勰当然也不能跳出社会环境的框架和圈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所以我们研究《文心》,虽然“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但也不必苛意求全,更不应该因惧噎而废汤圆,怕胖而撤八宝饭。
六、 结论: 文武合一,智术一也;情理合一,人性一也
知道了《文心雕龙》“诗学”重理避情的局限,和《诗经》对人类情感如实而开明的记“志”,今天我们研究《文心雕龙》的诗学,就应该把《文心雕龙》和《诗经》一同会通加以研究,这样才能在“古典诗学”的了解上作到“情理合一”,以弥补后世儒家擅自割舍人性人情所造成的视野局限和活力缺失。所以我认为,只有当我们以“文武合一”和“情理合一”的辩证又融合的态度来研究经典,以“现代化、消化、简化、本土化、大众化、全球化”的方法和过程,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中华文艺才能走上稳健活泼,有“文化纵深”的复兴道路。而这样的理念和应用,其实也就是拙著《斌心雕龙》借助新的“知识平台”所开始探讨的新方向,和迈出的几个小碎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