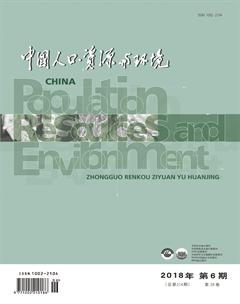收入增长、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
涂正革 张茂榆 许章杰 冯豪


摘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环境污染及其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家庭调查数据(CHNS),結合相应地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数据,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探讨家庭收入提高对健康的正向效应能否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粉尘对健康损害,但并未能抵消工业氮化物(NOX)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理论机制发现,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减缓效应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南低北高”的地区污染特征客观上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抵消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表现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显现出环境支付意愿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减轻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
关键词 家庭收入;大气污染;呼吸系统疾病;健康福利;环境支付意愿
中图分类号 X51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6-0130-10DOI:10.12062/cpre.201801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但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环境高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由50个国家、303个机构、488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发表于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的报告显示,室外空气污染在中国已成为排名第四的首要致死风险因子,1990—2010年由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增长33%,2010年中国室外空气污染导致123.4万人过早死亡(占当年死亡人数的14.9%),以及2500万健康生命年的损失。同时,大气污染的地区差异也直接导致中国居民健康水平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如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供暖政策,使淮河以北城市的总悬浮颗粒(TSPs)浓度平均高出总体55%,进而拉高心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使北方居民的预期寿命相对南方少5.5年[1]。不可否认,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得以全面提升,公众对健康的需求也随之高涨,中国居民已展现出对清洁空气较强的支付意愿(WTP)[2],以减轻大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损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提高家庭收入便能缓解大气污染的健康损害?为此,本文匹配CHNS微观健康数据与省份宏观污染数据,识别住户人均净收入和大气污染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和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以此回答家庭收入的提高能否缓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重要性,而地区大气污染水平和个体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客观与主观因素[3],分别形成被动产生型和主动产生型环境支付意愿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从环境支付意愿被动产生角度,考察南北地区不同的人群在环境支付意愿上的差异,探讨家庭收入在缓解健康风险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从环境支付意愿主动产生角度,比较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居民家庭收入影响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差异。
1 文献综述
环境质量与公众健康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应用不同方法探寻公众健康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收入与环境污染是两大重要因素。一般而言,从营养角度家庭收入提高对公众健康存在显著的改善效应[4],而以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污染是损害公众健康的重要因子。
在研究收入对健康影响的文献中,主要发现收入与健康存在以下两种关系。一种是收入对健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下,收入越高,健康状况越好[4-5]。另一种是收入与健康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甚至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收入继续增长,健康状况反而会变差[6]。此外,还有不少的学者发现健康对收入存在反作用[7]。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文献应用中国数据研究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影响最为广泛文献是采用剂量-反应关系进行量化研究,如赵晓丽[8]等分析了北京市大气污染物对公众健康的损害。然而这些文献存在内生性问题[9],无法排除其他因素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因此国内外学者也应用经济学方法识别大气污染的健康风险,如陈硕和陈婷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并利用3SLS实证检验火电厂SO2排放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收入和污染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两者对健康存在交互影响。这类文献主要是对清洁空气的支付意愿来展开研究。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更有可能通过购买空气净化器、口罩等防护用品,以缓解大气污染暴露程度,甚至为逃避大气污染,选择空气更好的地区居住,并承受更高的住房价格[10]。这些效应得到了中国经验数据的支持[2-3]。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均认为家庭收入和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存在显著影响,研究两者对公众健康交互影响的文献多基于对清洁空气支付意愿的间接衡量方式,其中用住房价格衡量支付意愿需要建立在居民充分了解居住环境的前提假设上[10],这很难在当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成立。为此,本文采用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捕捉家庭收入、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引入家庭收入和大气污染的交互项,重点分析家庭收入的提高能否缓解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同时,充分考虑到环境支付意愿在影响家庭收入转为健康福利中的重要性,分别通过被动型环境支付意愿(用南北地区分类反映)和主动型环境支付意愿(用不同受教育程度分类反映)做进一步检验。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有以下三点边际贡献:①考察收入与污染对健康的交互影响。②多维度污染指标、主客观健康指标的选取。本文用四种大气污染物表示污染状况,而对健康的衡量,既采用客观诊断的发病数据,又选取主观感知的自评健康水平。其中发病数据还能与多数使用死亡率的文献形成互补。③结合环境支付意愿进行作用机制分析。本文考虑到居民环境支付意愿与客观的地区大气污染水平和主观的个体受教育程度密切有关,分别从南北地区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两个层面,探讨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影响差异。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各类统计年鉴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營养与健康所提供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其中主要被解释变量为两类,一类是疾病发病状况,该变量主要参考CHNS 调查表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的利用”部分,该部分设计了过去四周医生诊断病(伤)情况,这便为本文探究污染物对疾病发病概率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本文参考谌仁俊[11]等的做法,从CHNS中提取疾病数据应用于检验收入和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往的文献更多注意在死亡率,而忽视了对发病率的检验,这部分检验更有利于及时把握公众健康的改善情况。);另一类是自评健康指数,调查表的“目前健康状况”部分提供了过去三个月居民对自我健康的评价。本文整理获得1989—2011年被调查省份健康的混合截面数据。其中,获取了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及2011年的第一类指标,同时整理到1997、2000、2004和2006年的第二类指标。此外,本文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不变价住户人均净收入(下文称家庭收入)和单位面积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下文称大气污染)。其他各类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环境年鉴》(1999—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5—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1989—2011年)。
控制变量方面,考虑到人均GDP、受教育程度、年龄以及地区医疗水平会对个体健康状况产生影响[12],且抽烟与近污染源职业群体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可能性较高,本文控制了相应变量。另一方面,地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缓解污染物对公众健康的影响[11],本文选取了四种工业污染物去除率,以期控制地区环境规制强度。
数据处理方面,宏观控制变量以《中国统计年鉴》为准,缺失数据通过《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获得,其中人均GDP的平减为了与CHNS提供的不变价家庭收入统一,通过2011年的实际GDP和不变价格的生产指数(以2011年为基期)推算得到。
处理得到的相关控制变量含义及主要变量统计描述分别见表1、表2。
2.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多元Logit模型研究污染和收入对疾病发病概率的影响;对污染和收入对自评健康指数影响的考察,则使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所构造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H代表微观个体的患病状况和自评指数,I表示家庭收入,污染物排放量变量SO2(烟尘、粉尘、NOX)为AP,Xijt为微观控制变量向量,Xjt为宏观控制变量向量。i表示微观个体,j表示微观个体i所在省份,t表示微观个体i所处的年份。H表示微观个体的健康状况,μ表示仅随城市变化的固定效应项,η表示仅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项,ε表示随机扰动项。β1、β2分别表示收入、大气污染对微观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为进一步研究家庭收入和大气污染对疾病发病概率的交互效应,本文引入收入与污染物的交互项I×AP,构造如下模型:
对模型式(1)(2)需要指出的是,当H代表微观个体的疾病患病状况时,采用多元Logit模型,而H表示微观个体的自评健康指数时,使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进行探索。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将分别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和多元有序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多元Logit模型对交互项的研究中,人均净收入及大气污染对发病概率的偏效应模型分别如下:
对Pi(β3i-β3)正负性的考察是本文对交互项研究的重点部分,若考察大气污染会否降低收入健康福利,则对于回归结果,若模型式(3)中Pi(β3i-β3)大于零则说明对应大气污染物会显著降低收入健康福利,若探究收入能否缓解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则若模型式(4)中Pi(β3i-β3)小于零,则表明收入会缓解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本文还将重点研究收入能够缓解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时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的范围,由模型式(4)整体为负的回归结果中可计算得出收入的范围,在此范围中收入会减缓对应大气污染物对健康的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使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交互项的考察时,偏效应的模型表达如下:
对{g(μj-1-X′α)-g(μj-X′α)}β3的正负性考察中,若探究污染能否降低收入对提高自评健康水平的作用,则对于模型式(5),{g(μj-1-X′α)-g(μj-X′α)}β3小于零说明对应大气污染物会显著降低收入提高健康水平的效能,若研究收入能否缓解污染对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则考察模型式(6)中{g(μj-1-X′α)-g(μj-X′α)}β3大于零的回归结果,此时收入会缓解对应大气污染物对自评健康的影响。本文还将着重研究模型式(5)(6)整体的正负性,一方面由模型式(5)整体结果为正得出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范围,该范围内污染物波动均会对收入带来的自评信心产生抵消作用,另一方面,由模型式(6)整体小于零得出收入的范围,收入在此范围内能够缓解大气污染排放所导致的消极自评。
需要指出,本文使用多元Logit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中,显著性系数是以健康人群为分析口径反映相对于健康个体而言,收入和大气污染对微观个体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的影响方向,而偏效应系数以整体人群为考察口径,反映相对于其他人群(包括健康个体,患其他疾病个体),解释变量对个体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的作用程度。
3 实证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为精准识别大气污染及家庭收入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本文同时考察了客观健康状况与主观健康心理,以期能够全面而客观地展现家庭收入和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交互影响。同时,考虑到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相关疾病的发病存在滞后效应[13],本文引入污染物滞后期进行相关估计,结果与当期污染的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差异,故以下研究均采用当期污染数据。
3.1.1 家庭收入在大气污染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影响中的交互效应
估计模型式(1)得到的表3(回归(1)~回归(4))顯示,在不考虑交互效应时,家庭收入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发病概率。引入交互项后(结果见表3回归(5)~回归(8)),NOX交互项对发病概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因此,总体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提高能显著降低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尤其能减缓工业NOX排放对公众健康的损害,收入带来的健康福利凸显。
3.1.2 家庭收入在大气污染对自评健康水平影响中的交互效应
未引入交互项时,从表4(回归(1)~回归(4))(污染物当期值分析部分)可以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能显著激励公众的自评信心,而工业烟尘排放显著降低了自评健康水平。同样,由模型式(2)分析得出的表4(回归(5)~回归(8))可知,家庭收入和四类大气污染对自评健康水平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和多元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以放松多元Logit模型和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随机扰动项的独立假定,稳健性检验 结果与表3~4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具体结果见表3~4。
3.1.3 家庭收入和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交互影响的偏效应
为捕捉准确的交互效应,本文将模型式(2)的估计结果进行偏效应转换。结合显著性分析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对NOX带来的健康损害产生了显著的减缓效果;根据模型式(3)(4)可得,当家庭收入大于2.62万元时,家庭收入可以显著抵消工业NOX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的正向影响。
3.2 异质性环境支付意愿的微观机制
以上分析表明,家庭收入带来的健康福利被大气污染的健康侵害所抵消。事实上,家庭收入能否缓解大气污染的健康损害,主要取决于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环境支付意愿受到地区大气污染水平和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前者所产生的环境支付意愿偏重客观性,表现为被迫购买环境保护产品;而后者导致的支付意愿更具主观性,多表现为职业选择性与清洁产品购买性支付意愿[3]。基于此,本文从客观角度,假定中国“南低北高”的污染特征有可能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将分南北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从主观支付意愿角度,假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有可能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健康福利,将人群按照受教育程度高低分为两组进行检验,以期找到家庭收入缓解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作用机制及其证据。
3.2.1 南北地区差异比较:被动型环境支付意愿的作用机制
我国南北地区在集中供暖、产业结构和气候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损害也呈现出“南低北高”的特点[1]。因此,北方居民更有可能被迫“培养”出较强的环境支付意愿,被动地将收入用于规避或减低大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在大气污染源上,相比于南方地区来源于农业生产,北方地区主要大气污染源为居民和商业能源消耗[14]。因此在环境支付意愿被动产生条件上 必定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假定南北地区污染差异会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从而使北方地区家庭收入的健康福利表现更为明显。
从呼吸系统疾病的南北分布来看,北方地区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情况要远远好于南方地区。这很难与南北地区大气污染差异不明显的情况吻合,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说明,在同样的大气污染暴露下,北方居民的防护意识更强,被动的环境支付意愿表现更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南方地区收入对健康福利显著弱于北方地区,这就意味着北方居民更加重视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更倾向于通过购买污染防护设备以规避环境风险,这样,收入的健康福利在北方地区更加凸显。由模型式(2)的回归结果可知(见表6),在北方,家庭收入的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烟尘与NOX的健康损害,与此相反,南方地区工业NOX的增加减弱了家庭收入带来的健康改善效应。因此,相比于南方,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更能够发挥减缓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
同时,模型式(2)回归结果(见表7)显示,在北方,粉尘、NOX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对自评健康的鼓励,居民对收入健康福利的期望随环境恶化而抵消,同时,南方居民收入的提高增强了其对健康状况的信心。因此,南北地区居民对收入健康福利的主观差异,导致了健康福利凸显程度的南北差异。
综上,南北方地区的收入对健康的改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南北方大气污染差异,居民对健康情况的乐观程度不同,北方居民较重视大气污染的危害,客观上增加了其环境支付意愿,使得北方地区的收入健康福利得以凸显。稳健性分析系数与表6~7中的回归结果保持了一致的显著性,验证了上述多元Logit模型及多元有序Logit模型分析结果的可信性。
从收入对健康的偏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①从污染物排放强度看,在北方,当单位面积NOX排放量低于281.46 g时,家庭收入能够缓解NOX的健康侵害;单位面积烟尘排放量低于34.46 g时,收入能够降低由烟尘引起呼吸疾病的发病概率;在南方,单位面积NOX排放量小于1.95 g时,收入才能够缓解其对健康的危害。②从家庭平均收入看,在北方,当家庭收入大于4.05万元时,粉尘带来的健康风险得到减缓;家庭收入大于5.31万元时,收入能够降低NOX带来的健康损害;在南方,家庭收入需达到13.75万元才能凸显出这一健康福利。总体而言,相比于南方,高于5万元的家庭收入便能使北方居民产生较强的环境风险规避意识。
以上分析进一步表明,南北方居民环境支付意愿存在巨大差异,“南低北高”的污染特征会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从而更加凸显北方居民家庭收入提高带来的健康福利。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问卷调查的是过去四周的发病情况,有些自评差的个体实际患病了但未及时检查或无法支付检查费用。这类个体会在疾病统计数据中记为健康,实际上就造成了该数据的偏差,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具体体现在上述结论中一些污染物(粉尘、NOX)对疾病发病概率的影响不显著,而这极有可能因为受影响的个体在这四周内还没有发病或者没有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在研究针对于疾病的交互项的过程中,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是不能减缓污染物对健康风险的影响,而这与本文的预期(收入是可以减缓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是有差别的,而这一误差有极大可能是因为收入较低的人群缺乏健康意识,从而不去医院检查或就诊。因此,对自评健康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对前面的分析起到补充作用、对前面的结果偏差进行完善,使分析结果更加符合事实。
3.2.2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比较:主动型环境支付意愿的作用机制
不同人群在环境支付意愿上的主观差异会影响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这种支付意愿的主观差异主要取决于群体的健康意识差异。显然,群体的健康意识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联性,如冠心病患者采用健康信念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可不同程度地增强患者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建立。本文从环境支付意愿主动性角度,考察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家庭收入对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的影响差异。
2000年以来,受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影响我国居民受教育程度发生了大规模改变(见图1)。因此,为减小由于受教育程度人群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划分误差,本文以2003年(2000年入学的大学生受教育完成)为界,在1989—2003年,将学历高中以下和高中以上(包括高中)人群分别定义为低学历和高学历人群;在2003—2011年,将学历大学以下和大学以上(包括大学)人群分别定义为低学历和高学历人群。
从模型式(2)和表8能够发现,在1989—2003年,相比于低学历人群,高学历人群收入可以显著减缓SO2、烟尘引起的发病概率。具体而言,低学历的人群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健康安全意识淡薄以及对环境的主观支付意愿不足,使得其收入的增加不能很好地缓解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相比之下,高学历人群由于受教育程度高,具有较强的职业选择支付意愿与购买性支付意愿。前者主要表现为通过选择离污染源较远的职业来规避健康风险。本文样本数据也显示,相比于低学历人群的87%,只有24%的高学历人群从事靠近污染源的职业,说明高学历人群在职业选择时会更多地考虑工作环境因素,同时通过购买环境较好的房屋[2,4-5]及清洁产品来规避污染。这也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促使人们更多地考虑收入的健康福利。
对2003年以后的人群做与表7相同的回归,结果如下:在2003年以后,相比于高学历人群,低学历人群收入的增长能显著提高其自评健康指数,而NOX能显著降低高学历人群收入对自评的鼓励,烟尘能显著降低低学历人群收入所带来的自评健康信心。进一步分析,根据低学历人群中的年龄分布,30岁及以下和30岁以上分别占比13.54%和86.46%,由于低学历人群中绝大部分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其能够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红利,产生了对健康的过度自信;相较于前者,由于知识水平较高,高学历人群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表现较为保守,风险规避意识较好。此外,本文使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也显示表8估计系数的稳健性。
上述分析表明,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可以使人们更加客观的看待收入的健康福利与污染的健康风险。同样在考虑人群异质性时,通过模型式(3)(4)得出收入与污染物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偏效应如表9所示。于是可以计算出,当家庭平均收入分别大于0.47万元和0.11万元时,高学历人群收入的提高能够减缓SO2和粉尘对呼吸系统疾病带来的健康负效应。因此,学历越高的人群环境意识越强,尽管收入很低,但也会有较高的环境支付意愿,从而来改善自身健康水平。
4 结 论
本文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考察了家庭收入如何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首先利用微观家庭的健康收入数据从总体上估算了家庭收入和大气污染对微观个体公众健康的交互影响,接着分析发现地区大气污染水平和个体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主客观因素[6,8],并比较不同环境支付意愿条件下居民家庭收入对大气污染损害的影响差异。具体地,本文研究发现一下几个主要结论:
(1)总体上,家庭收入能显著降低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尤其能减缓NOX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的影响,收入带来的健康福利凸显;特别是当家庭收入大于2.62万元时,收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减低NOX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
(2)南、北方地区环境污染的差异导致南地区家庭收入所带来的健康福利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收入减缓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的效果北方较南方更为显著;在北方,收入更能减缓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收入带来的健康福利作用的凸显存在明显的南北差異;在南方收入的增加使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过于自信,从而收入无法像北方一样降低健康风险;从污染物强度对比发现,北方居民更容易通过收入的提高来减缓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从家庭平均收入对比发现,北方居民只要收入大于5万左右就会有较强的环境支付意愿,用一部分收入购买防护措施,提高健康水平和降低呼吸系统的发病概率,而南方居民要收入高达14万元左右时才会有此作用。所以北方居民收入的健康效应比较突出。综上,“南低北高”的污染地区特征会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使北方家庭收入的健康福利表现更为明显。
(3)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其环境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导致收入提高对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的缓解作用呈现显著差异。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可以使得收入减缓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的作用凸显,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及其与此相关联的健康意识的普遍提高,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客观的看待收入所带来的健康福利和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进一步计算发现,当家庭收入分别大于0.47万元和0.11万元时,高学历人群收入的提高能够减缓SO2和粉尘对呼吸系统疾病带来的健康负效应。学历越高的人群环境支付意愿越强,尽管收入很低,但也会有环境支付意愿,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购买环境较好的房屋或者防护措施,从而来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概率和提高自身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CHEN Y, EBENSTEIN A, GREENSTONE M, et 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2013 (110):12936-12941.
[2]陈永伟,陈立中. 为清洁空气定价:来自中国青岛的经验证据 [J]. 世界经济,2012(4):140-160. [CHEN Yongwei, CHEN Lizhong. Price for clean ai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Qingdao, China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2(4):140-160.]
[3]SUN C, KAHN M E, ZHENG S Q. Selfprotection investment exacerbates air pollution exposur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7,131:468-474.
[4]BENZEVAL M, JUDGE K, SHOULS 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ealth: how much can be gleaned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1,35:376-396.
[5]齐良书,李子奈. 与收入相关的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流动性 [J]. 经济研究,2011(9): 83-95. [QI Liangshu, LI Zinai. The incomerelated mobility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9): 83-95.]
[6]封进,余央央. 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 [J]. 经济研究,2007(1):79-88. [FENG Jin, YU Yangya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in rural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1):79-88.]
[7]秦立健,陈波,秦雪征. 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 [J]. 世界经济文汇,2013(6): 110-120. [QIN Lijian, CHEN Bo, QIN Xuezheng.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J]. World economic papers, 2013(6): 110-120.]
[8]赵晓丽,范春阳,王予希. 基于修正人力资本法的北京市空气污染物健康损失评价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3):169-176. [ZHAO Xiaoli, FAN Chunyang, WANG Yuxi. Evaluation of health losses by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 a study based on corrected human capital method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3): 169-176.]
[9]陈硕,陈婷. 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以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例 [J]. 经济研究,2014(8):158-169,183. [CHEN Shuo, CHEN Ting. The rise of Chinas coastal areas: power of market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8):158-169,183.]
[10]CURRIE J, DAVIS L, GREENSTONE M, et al.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nd housing values: evidence from 1,600 toxic plant openings and closing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 678-709.
[11]諶仁俊,涂正革,黄必红. 城市环境政策、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 [R].2017.[SHEN Renjun, TU Zhengge, HUANG Bihong. Urba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ir pollution and public health [R].2017.]
[12]王兵,聂欣. 经济发展的健康成本:污水排放与农村中老年健康 [J]. 金融研究,2016(3): 59-73. [WANG Bing, NIE Xin. The health cos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ewage discharge and the midaged and elderly health in rural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6(3): 59-73.]
[13]吴新悦,张城敏,葛秀平,等. 北京市1 272例原发性肺癌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调査分析 [J]. 北京医学,2009(1): 20-23.[WU Xinyue, ZHANG Chengmin, GE Xiuping, et al. Beijing tuberculosis and thoracic tumor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China[J]. Beijing medical journal, 2009(1): 20-23.]
[14]LELIEVELD J, EVANS J S, FNAIS M,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outdoor air pollution sources to premature mortality on a global scale [J]. Nature, 2015, 525:367-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