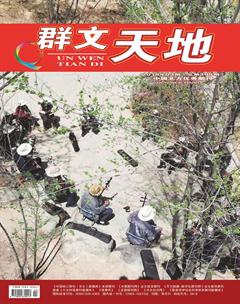浅析曹文轩中短篇小说中的生态审美情结
郑逸群
“生态批评”是于20世纪70年代最先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种文艺批评观。经过40余年的发展,生态批评现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批评潮流。①作为价值批评和伦理批评的生态批评,它的终极目的是唤醒人类一直被蒙蔽的自然意识,从而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批评要求作家构建一种绿色写作范式,这种写作范式主要包含这三项内容:首先,文艺要走进自然、亲近白然并且书写自然,这种书写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欣赏与赞美或借景抒情,而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思想下将大自然视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的绿色书写;其次,作家需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艺术家应放弃对大自然仰视的态度,而应该俯身为自然的一员,从自然事物的本质特征以及独立价值来看待和描写它们;最后,鉴于生态批评的跨学科属性,文艺需要更新话语方式,构建起艺术与科学、想象与写实之间的桥梁。如果说生态批评中的思想文化批评是该批评思想的“硬件”的话,那么对其审美和艺术价值的研究则是完善生态批评的“软件”部分,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构建“生态诗学体系”和“生态美学体系”。
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当代作家曹文轩是一位创作兼学者类型的作家.他的主要成就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其中这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长篇三部曲《草房子》《青铜葵花》和《山羊不吃天堂草》,还有他近几年创作的《火印》与《蜻蜓眼》,这些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皆反映出曹文轩独特的创作倾向与过人的创作才能。曹文轩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中国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以及“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②等重要观点。他的笔触多触及六七十年代苏北乡村背景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皆没有当代青少年那种丰盛的物质生活,他们与山林、花草、河流为伴,大多过着一种和白然乡野融为一体的生活。曹文轩的中短篇作品有一种古诗词的意蕴,而这股诗意与清新主要来源于自然,因此,生态审美情结成为其小说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其中短篇小说中的生态审美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与研究。
一、自然性原则下的生态审美
生态审美的第一个原则是自然性原则。所谓白然性原则,就是我们的审美对象是大自然,而不是审美者本身。生态审美旨在具体表现和感知大自然,审美的过程即感知的过程。从美学意义上来讲,人类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存在三个维度,其一是认识价值,其二是功利价值,其三才是审美价值,同样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也是这样三个维度。传统层面的审美主要体现在工具化审美方面。所谓工具化的审美,指的是把自然的审美对象仅仅当作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把它们当作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③工具化审美的代表人物有唯美主义理论家和作家王尔德以及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尽管王尔德反对将美与艺术作为人类社会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但他却一直将自然美当作表达人类思想情感的工具;雪莱笔下的西风、夜莺、云雀虽美,但它们并不是以自然物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是充当了诗人抒发情怀的工具。
在曹文轩的短篇小说《红葫芦》中,他的水乡生命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小说中小女孩妞妞就住在大河边,每天她一出门就能看见在河里尽情游泳的男孩湾。当地的风俗是,孩子下河游泳总要抱一只晒干了的大葫芦,葫芦的作用跟城里孩子用的救生圈一样,为了便于寻找,人们将这只大葫芦涂成鲜艳的红色。在文中,红葫芦的意义非比寻常,它代表了平静柔和的水乡岁月中一抹活泼好动的生命力,而湾正是这抹生命力的象征。在妞妞的印象中,只要看见湾,他都不知疲倦地浸泡在清凉的河水中,对于家庭生活不幸的湾而言,大河就是他幼小生命的全部,是他平生所有的依恋。在这条美丽的大河上,湾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河心小岛,无法上学的湾把河心小岛当作了自己的学校,岛上的白桦树分别刻上了他想象中同学们的名字。曹文轩将这些诗意纯真的文字于水乡中缓缓铺展开来,而支撑这份诗意和纯真的正是生态审美中的自然性原则。曹文轩笔下的自然风光并不是人们抒发思想感情的工具,它是整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水乡的自然风物皆有其独特的美与价值:
“芦苇丛里钻出几只毛茸茸的小鸭。它们是那样轻盈地凫在水上。它们用扁嘴不时地喝水,又不时地把水撩到脖子上,亮晶品的水珠在柔软的茸毛上极生动地滚着。一只绿如翡翠的青蛙受了风的惊动,从荷叶上跳入水中,随着一声水的清音,荷叶上‘滴滴答答地滚下一串水珠,又是一串柔和的水声。”
这段文字中的小鸭和青蛙,它们和妞妞以及湾一样,都是水乡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可爱的小生灵,水乡的景致才变得多姿多彩起来。在孩子的视野中,河心小岛上的白桦树也可以成为他的同学,他给这些树取名甚至于围着它们追逐嬉戏,这种天真的情愫没有丝毫的功利性,也摒弁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自大。在湾的心目中,大河是他的亲人和朋友,他愿意始终待在河水中,感受河水的亲近与爱抚;白桦树也不是普通的树,而是他可以倾诉与共同玩耍的同学伙伴。以儿童的视角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并且与自然平等地对话,是曹文轩诗性小说的根基,也是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之处。
《再见了,我的小星星》是曹文轩早期短篇作品的代表作,曾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篇小说讲述了下放到乡村的女知青雅姐和农村小男孩星星的故事,雅姐美丽温柔且非常热爱绘画,她所住的当地农家有一个小男孩叫星星,星星喜欢捏泥巴和画画,但周围人不太懂这些艺术,所以无法给他指点,雅姐的到来使星星的绘画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她常常带着星星前往树林与田野写生,星星对大自然敏锐细腻的感知使得他的绘画突飞猛进,而二人的姐弟情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深厚了。在这篇小说中,雅姐和星星对于自然风物的感知并不仅仅停留在欣赏与赞美的层面,也并未将它们视作抒发情感的工具,他们对于姗姗来迟的春以及清晨初生的太阳均带有一丝由衷的热爱和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二者一個是豆蔻年华的少女,一个是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眼中的自然充满神奇的力量,是艺术创造的全部源泉。这篇小说的自然性原则生态审美还体现在星星这个小男孩的形象塑造上,星星喜欢用泥巴捏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妈妈嫌他给家里添乱,不许他再捏泥巴,而初来乍到的雅姐却认为星星身上有一股特别的灵气,这股灵气可以发展到艺术方面。星星身上的灵气可以说是自然赋予的,那个年代的孩子既没有电视电脑,也没有手机游戏机,他们每天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过着没有课业压力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然是维系星星想象和创造的根本条件。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当我们热爱自然并且融人自然时,自然也会反哺我们的想象力和艺术细胞。
二、主体间性原则下的生态审美
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原则是指人不仅要与整个大自然产生联系,也要与具体的、个别的自然物产生联系。在这种审美关系中,人有时需要做到摒弃自我,完全融入,全身心地感受自然本身;有时则需要坚持自我主体性,但却不是把自然物当作客体而是当作另一个主体,与之进行交互主体性的沟通,并在这种平等的沟通中体验自然物的美。④
在曹文轩的短篇小说《妈妈是棵树》中,主体间性生态审美原则一览无余。故事同样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乡村,小女孩秀秀的母亲在生她时不幸去世,她长到两岁时父亲又意外落水身亡,于是秀秀被村里人认为是一个“恶毒”的小生命。后来秀秀被舅舅舅妈收养,但舅舅舅妈只是贪图她父母给她留下的微薄的家产,并没有真心对她好,她小小年纪就要干很多的活,多看几本书都会被舅妈责骂。此情此景下,“命硬”的秀秀只好去认村前地头的大柳树为妈妈。这棵大柳树的来历也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好多年前的夏日黄昏,一只喜鹊口衔一根柳枝飞过空中,落在地头,将柳枝插在土里。从此,那柳树生根发芽,长成了现在这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如今那只喜鹊依旧每日停留在树梢上,守护着当年它种下的柳树。秀秀和柳树的关系在小说中早已不是人类和植物的关系,而是亲厚如母女,大柳树竭尽自己所能给予秀秀温暖的庇护和深切的关爱:
“大柳树酿成了一方湿润的世界。秀秀一来到树下,从头到脚就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舒适。她喜欢它的躯体散发出的清爽而微带苦涩的味儿,喜欢它用枝条千百次抚摸她的脸,喜欢倚在它宽厚坚实的身上,喜欢仰望枝头那只常常凝神不动的喜鹊。她觉得这里是一座房子,一座高大的房子,树冠就是屋顶,那些枝条组成的长长的绿幔,便是墙。她在大树下游戏,在大树下唱歌,在大树下幻想,在大树下尽情显出傻样来。她记不得那是一棵树,她觉得它的生命在树干里流动,一直流到每一根枝条的梢头。她能听见它安详的喘息和春风一样的细语。”
在曹文轩笔下,大柳树化身为慈爱的母亲无时无刻不呵护关爱着寄人篱下的秀秀。当秀秀没有捡到足够的柴火不敢回家时,喜鹊将柳树上的枯树枝一根一根地抛给她,直至她满意为止;当舅妈把秀秀借来的课外书撕掉时,大柳树开始施展出作为一种植物的“报复”,它开始疯长,浓密的树荫一点一点遮蔽住舅舅家的农田,使那些急剧需要阳光普照的禾苗得不到阳光;当秀秀即将要参加高考时,它的大树丫提供给秀秀看书和休息的场所。这株慈母般的大柳树将所有无声无息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给了秀秀,而秀秀也把它当作妈妈,她不许村里淘气的男孩在这棵树上乱刻乱画,当有人用小刀刮树皮时,她会心疼地替大柳树包扎伤口。当舅舅舅妈欲砍倒这棵阻碍禾苗接受阳光的大柳树时,秀秀会以烧房子来“威胁”他们。在小说中,秀秀、大柳树和喜鹊是一体的,他们三个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相依为命,互相帮助。美国图画书作家伊夫·邦廷的《艾莉丝的树》和这篇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艾莉丝热爱农场旁的橡树,对待它就像对待一位莫逆之交一样,但是有一天这棵橡树被一种不知名的化学药物污染了,它就像人生了重病一样慢慢地枯萎下去。作者写艾莉丝的树,笔触并不仅仅只是单纯地写树,而像是在写一个人的一生,同样曹文轩写秀秀的大柳树,也是在写一个人,一个成为母亲的人。
此外,短篇小说《田螺》也有生态审美中主体间性原则色彩,这体现在何九和他救助的那只黑鸽上。何九是一位贫苦无依的单身汉,他年轻时因为贫穷曾偷过东西,还因为盗窃一事坐过半年牢,因此村里绝大多数人都不信任他,甚至对他抱着鄙夷的态度。何九有一回借船去芦苇荡采集芦苇,他把船拴得好好的但到了夜里船却丢了,人们众口一词地怀疑他、孤立他甚至于嫌弁他。这样一个处于村庄边缘的小人物,却开始默默地捡起了田螺,他希望通过捡田螺挣一笔钱然后买一条船赔给村里人,尽管这条船不是他弄丢的。在何九灰暗的捡田螺的日子里,唯一能带给他慰藉的是一个叫六顺的小男孩和那只他从鹰爪下救活的黑鸽,尤其是这只黑鸽,何九将自己所有的柔情都给了这只黑鸽,他将它视作亲人和朋友。小说的结尾,当何九通过卖田螺挣钱买了新的大木船离开村子时,他除了带着自己的铺盖卷以外,就只带走了黑鸽,黑鸽栖息在他瘦削的肩膀上,陪伴着他行走天涯。
三、寻找和回归家园中的生态审美
与成人文学不同,在儿童文学中尋找和回归家园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在成人文学中,“家园”有时并不是值得守候与依恋的温床,相反它是一种需要被摒弁的旧式状态。比如巴金“激流三部曲”中《家》的主人公三少爷高觉慧,他发觉了外表光鲜的高家实际上是一个吞噬年轻生命的陈旧墓穴,因此他选择为革命理想毅然决然地出走;琦君的著名小说《橘子红了》同样旨在对旧式家族的批判,小说中的秀芬正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而读过书的六叔和秀娟也是即将要离开旧家族的新青年。我们不难发现,在成人文学世界中,家族往往是羁绊青年成长的藩篱,青年唯有冲破旧藩篱才能迎来新的曙光。但儿童文学却恰好相反,在著名学者刘绪源的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曾提出,儿童文学永恒不变的三大母题是“爱”“顽童”和“自然”,其中“自然”这一母题的要旨在于唤醒人类被异化后的自然属性,而唤醒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寻找和回归家园。在这一点上,生态文学与儿童文学恰好不谋而合,生态文学所崇尚的审美情愫不是成人文学中的借景抒情或睹物思人,而是希冀人类的心灵可以回归至童年状态,与大自然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纵观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寻找和回归家园都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比如美国弗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小女孩多萝西被龙卷风刮到芒奇金人聚集之地后,她心心念念的一件事就是重返家园;英国作家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一书中,鼹鼠和河鼠对家园都有一种发白内心的深深眷恋;还有约克·米勒的绘本《森林大熊》,大熊冬眠醒来发现森林变成了现代化工厂,他无奈之下来到工厂做工,他最大的渴望还是重返森林并且重新做回一头熊。同样,在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中,寻找和回归家园也是频频出现的主旨。
中篇小说《三角地》实际上就是一篇回归家园的佳作。整篇作品作者以第一人称进行自述,语言轻松幽默,充满浓郁的少年气息和诙谐的调侃意味,读来使人忍俊不禁。“我”和父母及四个弟弟妹妹住在两条街的交汇处,人称“三角地”。家中虽然人口众多,但大家并不齐心协力,相反各自有各自非常严重的缺点,比如爸爸每日酒不离身,常常醉倒在大街上被人笑话;妈妈好赌,常常赌钱赌得忘记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责;大弟虽聪明,但沉迷于踢足球;二弟功课经常不及格,又是个“小滑头”;三弟则更糟糕了,平日里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不良习惯。在这个家中,“我”和最小的妹妹算是两个好孩子了,尤其是小妹,她天真无邪,深切地爱着父母和四位哥哥,是一个让人疼爱的小姑娘形象。可以说,这一家子人尽管住在三角地,除了年幼的小妹外谁也未曾把这里当成过家,家里又脏又乱,像一个大垃圾站,因为人人都忙着做自己的事,谁也不曾记起要打扫打扫卫生。此时此刻的三角地徒有家的外壳,却没有家的实质,大家都过得昏昏碌碌的。后来,16岁的“我”认识了一位能歌善舞又大方可人的姑娘丹妞,那段时间“我”和丹妞形影不离,通常是找一处安静优美的地方,然后“我”弹吉他,她唱歌,这对于“我”而言是一段既美好又纯真的岁月。为了不让丹妞看不起“我”,“我”特意隐瞒了自己的家庭状况,但后来有一天丹妞还是知道了实情,丹妞并不是嫌弃“我”的家境,而是不满“我”的虚荣和隐瞒,于是两人分开了一段时间。在《三角地》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一瞥成长小说的容姿。当丹妞转身离去的那一刹那,“我”青春的自尊受到了无情的打击,“我”决定要改变现状,将名义上的家变为实际意义上的家。之后“我”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包括大扫除、整顿个人卫生、帮小妹买新裙子、买菜做饭、支持大弟参加足球比赛、帮二弟补习功课、纠正三弟小偷小摸的坏习惯等等,都是使这个原本分崩离析的家重新凝聚起来的努力。当孩子们开始重新热爱这个家,开始勤奋上进时,父母、丹妞等人也不再无动于衷,父母开始丢弃喝酒赌钱的坏习惯,丹妞又和“我”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如果说,《三角地》中流露的是作家曹文轩以童心的力量重新构筑家园并且回归家园的审美意识的话,那么《水下有座城》和《甜橙树》所流露出的情感则是儿童对家园充满诗意的畅想和寻觅,当我们结合作品去观照这两篇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时,会发现在这充满诗意的畅想与寻觅背后有一丝人世的苍凉与悲伤,而这正是曹文轩力图捕捉的情愫。曹文轩曾说:“我蔑视那种浮躁的、轻飘的、质量低下的愉悦。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正丢弃安徒生的传统格调,片面地、无休止地去追求那种毫无美感的、拙劣的愉悦。”⑤在《水下有座城》中,男孩槐子和爸爸终日靠着一艘船在水上漂泊着,他们在陆地上没有根基没有可以回归的家园。在一场水灾中,槐子父子俩救助了秀鹊父女俩,秀鹊父女的到来使得他们在船上漂泊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慰藉和欢乐,尤其对于槐子来讲,他多了一个小妹妹和童年伙伴。这两个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寻找水下那座传说中的城池,槐子向秀鹊生动形象地描摹着那座遥远而神秘的城:
“很久很久以前,大概連我爷爷的爷爷都没有出世那会儿,这儿有一座城,突然的,就陷落了,大水漫上来,它就永远永远地沉在了深水里。那城有很多花园,一片接一片,街是用红油油的檀香木铺的,没一丝灰尘。人出门都用黑的马或白的马拉的马车,那马车是金子的,连马蹄都是金子的,用银丝编成的长马鞭挥舞起来,银光道道。到了晚上,一街的灯,人们就在街上散步,听从各种各样的房子里传出来的乐声……”
槐子和秀鹊对于水下之城的殷殷向往,除了与儿童对新鲜未知事物感到好奇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二者皆缺少归属感。在小说中,这两个孩子都没有母亲,槐子父亲善良质朴却时运不济,秀鹊父亲对女儿简单粗暴。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孩子们的心愿每每落空,所以他们将愿景定义为远方,水下那座城满足了他们心目中遥远家园的模样,因此他们永不知疲惫地追寻着。
《甜橙树》中的弯桥是个孤儿,他的养父刘四45岁那年在一座弯桥上拾到了他,故取了这个名字。刘四是个穷单身汉,拾到这个孩子可谓是中年得子,因此他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弯桥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所以脑子不大好使,见到人常常憨憨地傻笑,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单纯朴实的好孩子。整部小说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仅仅是弯桥一大早出来打猪草,临近中午时来到一棵甜橙树下睡着了,同村的几个小孩子六谷、浮子、三瓢和红扇发现了在树下熟睡的弯桥,他们淘气地用黑泥浆给弯桥画了个大花脸。后来弯桥醒来,心地憨厚的他并未发现什么异样,反而喜不白胜地给他们讲起了自己在甜橙树下做的好梦。这些梦通过弯桥讲出来显得格外美好动人,每个都与甜橙树有关,每个都是关于其他孩子帮他实现愿望的梦。这些梦体现出年幼的弯桥对亲情的向往、对友情的渴慕以及对彼岸家园的追寻。当弯桥倾诉完梦境以后,孩子们也在自己脸上涂上了大花脸,他们想用这一举动来告诉弯桥: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你所追寻的家园不在别处就在我们之间。曹文轩用他诗意如水的笔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寻找和回归家园的生态审美范式,即用童心的力量来完成这种高贵的审美。
本文以生态文学理论中的生态审美为支撑点,通过生态审美中的自然性原则、主体间性原则和寻找回归家园原则分析了当代作家曹文轩有代表性的七部中短篇小说:《红葫芦》《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妈妈是棵树》《田螺》《三角地》《水下有座城》和《甜橙树》。在曹文轩的笔下,童年是一首诗意而天真的歌谣,水乡别具特色的景致则是使这首歌谣绵延不断的根基,景物和童年在某种程度上呈平行的趋势铺展开来,水乡景物在其小说中不仅仅是点缀或烘托气氛的东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那里的少年儿童平生所有的依靠与想念。在曹文轩的文学世界中,景物自有它独特细腻的情感,它们和这些孩子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生命平等的对话关系。这正是曹文轩在儿童文学与生态文学的交叉领域所拥有的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
注释:
①杨守森.新编西方文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421-422.
②王泉根.“曹文轩模式”与中西儿童文学的两种形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9):59.
③④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55,66.
⑤李红叶.曹文轩小说艺术与安徒生童话[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65.
参考文献:
[1]杨守森.新编西方文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3]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
[4]曹文轩.三角地[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3,9.
[5]曹文轩.甜橙树[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3,9.
[6]王泉根.“曹文轩模式”与中西儿童文学的两种形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9):56-64.
[7]朱自强.“儿童”作为一种方法——论曹文轩儿童小说的特质[J].当代作家评论,2016(3):72- 75,
[8]陈莉.曹文轩成长小说中的人文关怀[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8):69 - 72.
[9]李红叶.曹文轩小说艺术与安徒生童话[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64-68.
[10]钱淑英.儿童视角与审美想象——曹文轩短篇儿童小说评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6(3):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