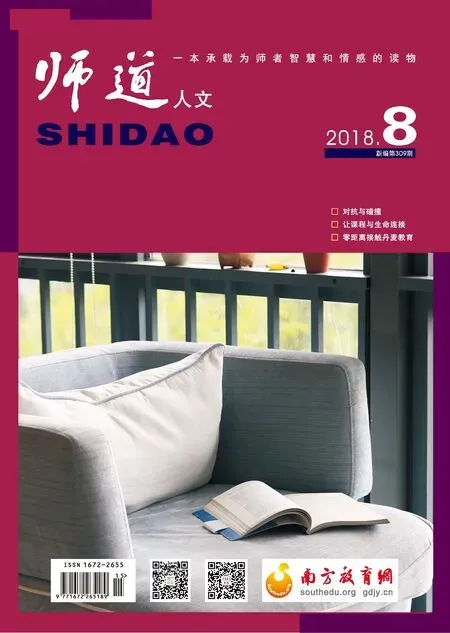对抗与碰撞
成旭梅
每每清晨带着叫人心疼的干净,清洌地躺在暗浊了一夜的我的身边的时候,总不免感激那个雪国的悲痛和寂寞,那个微微氤氲了令人窒息的忧郁的伊豆——苦难与悲哀,像这晨光,照亮与温暖了每个人生的 “孤儿根性”:
“这时我的心情是美好的、空虚的。明天我将带着老奶奶到上野站去买前往水户的车票,这也是完全应该做的事。我感到这一切全融为一体了。……我的头脑变成了一泓清澈的水,它一滴一滴溢了出来,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我心里快活得甜滋滋的。” (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
悲哀的空气总会勾起慰藉,相互温暖里,舞女和青年学生自卑的、灰暗的心变得自信而明亮。
所以每当读到亚里士多德 “女性之所以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托马斯·阿奎那 “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的时候,总会涌起对现世世界的感恩——没有理由不热泪盈眶:这个时代,我不必再重复自人类刀耕火种时期便丢给女人的鄙夷与蔑视,这个清晨,我接受川端康成的空灵之爱,我活得温暖动人。
1.对抗
男人的心脏从 《创世纪》开始,即充满性别对抗。
按法国作家舒波哀的说法,夏娃是从亚当 “多余的骨头”中抽取出来的。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 “女人,一个相对的存在”——法国史学家米什莱这样写道。

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这是埃·莱维纳斯在他的随笔 《时间和他者》中提出来的观点,自此, “他者”就成为男女性别二元对抗之下的命名。
但是,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根据有关达荷美的亚马孙的传说,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时期的女性,有时参加战争,或者参加血腥的家庭复仇,她们表现出与男性一样的勇气和残忍。然而不管女人多么强壮,在与敌对的世界作斗争时,生殖的束缚成为可怕的障碍;亚马孙因之割掉她们的乳房,以杜绝女性在打仗时期怀孕。这正是女性在人类肇始之初即成为 “他者”的残酷备注。怀孕、分娩、例假削弱女性的工作能力,迫使她们长时期地休息,脱离劳动生产;为了保存自身和她们的后代,在她们生育与休假的时候,她们需要男性的保护与扶养;最糟糕的莫过于:她们无法控制生育而导致的不断怀孕,占据了她们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这一切,都使得女性在艰难的原始生活之初,即处于被动的他者地位。
这种地位的确立,更与人类的初始价值共生。首先,人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物种,并不只追求作为物种的延续;人类是计划的动物,他的计划不是停滞,而是趋于自我超越。正因如此,所以原始群体并不关心后代。因为原始人类过着游牧动荡的生活,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存在不体现在任何稳定的东西中,不能形成任何永恒的具体思想,所以他们不考虑延续生命,不要求有继承者,对他们来说,孩子构成一个负担,而不是财富。因而,女性的原始状态并不是“母亲”的骄傲,相反,她们痛苦的分娩是无用的,甚至是讨厌的事。相对于男性作为计划性动物的行动,生育、哺乳不过是自然的作用,其中没有任何计划,因此,女性在其中感受不到对自身生存价值进行骄傲肯定的理由,她被动地忍受自身的生理命运,而这样的生理命运所带来的家庭事务,把她束缚在重复性与内在性中——日常事务以相同形式呈现,几乎没有改变,它们不生产任何新的东西。而男性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不像工蜂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命过程——完成繁殖之后即结束生命,人类男性通过超越动物状态的行为抚育集体,劳动的人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一个创造者。在这种创造性的行动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他提出目的,他设想通往目的的道路——他就是这样作为存在者自我实现。他超越了现在,他展开了未来。正是在女性自然生理贫弱的参照下,男性行为才获得了神圣的性质,男性看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男性尊严被高高抬起。
正是这种原始强力,铺垫了人类性别最本源的差异:人的优越性,不在于给出生命、养育生命的女性,而在于杀死生命的男性——正是因为男性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以其生命为赌注,为群体生存而去弑杀另外物种的生命,由此他出色地证明了,对人类来说,生命不是最高价值,生命应该为比它更重要的目的服务。男性向女性标示出性别优越在存在意义上的思辨论断:正是通过存在来超越生命,人类才保证生命的重复再现,通过这种超越,人类创造了价值——由此,男性彻底否定了 “生命作为生育带来的结果”的女性创造价值与地位。黑格尔以辩证法界定了这种男女之间的主仆关系: “另一个意识是从属的意识,对它而言,本质的现实是动物的生命,就是说,由另一个实体给予的存在。”
存在主义观点让我们明白:正是因为人类在存在中对自身提出了问题,也即人类更偏爱生存理由而不是生命,因而,原始群体的生物学和经济的处境必定导致男性的统治。
当游牧民族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变成农民,制度与法律出现了。人开始通过强加于世界的面貌具体地表现自己,设想世界和自我设想。农业共同体以植根于往昔、与未来相连的观念代替只存在一时的游牧生存观,土地伦理赋予了女人不同寻常的威信。因为在建立于土地劳动基础上的文明中, “孩子”有了全新的重要性:人安居在一片土地上,将土地变为私有,所有制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它要求土地所有者有后代,从而让生存能够超越现时,即在孩子身上自我完成和自我超越。于是,怀孕变成为一种神圣的功能。
这个时期,出现了女神,女性成为在天堂和地狱的遥远区域中的最高偶像,男性的神附属于她。父系制的重要时期的神话、纪念性建筑物和传说中保存着妇人占据很高地位的时代印刻。在希腊神话诸神中,组成核心集体的十二位神分别是:众神之王宙斯、天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战神、火神、海神、信使之神、智慧兼和平女神、月亮兼狩猎女神、谷物女神、美神、佑家女神。梁晓声撰文 《希腊神话中最浪漫之点乃在于,神大抵为女性》指出:其一,希腊诸神中的许多位,在中国神话故事中是缺席的。天后赫拉可以比做中国神话中的王母娘娘,但王母娘娘只不过是玉皇大帝的老伴,并无具体职责。赫拉却是有职责的——保护人间妇女勿受不公平对待。直接由天后来负起保护人间妇女的职责,这一种想象诉求,毕竟是意味深长的,证明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中,妇女不仅仅是男人的性偶,而且和男人一样,也应该受到神的关爱和合理庇护。除了赫拉,还有一位女神,专门负责保护少女的贞洁不受野蛮侵犯。其二,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中,有品质的生活,那一定是人人知识化了的、文艺内容丰富的生活。故在希腊神话中,共有九位女神分别掌管各类文艺和知识,统称缪斯。在古希腊物质和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国王甚至要求每个公民都至少应该擅长一类文艺,或作诗,或绘画,或歌唱,或舞蹈,或器乐,或雕塑,或戏剧,或表演等。甚至恩典惠及奴隶:如果他们中有谁在文艺或知识方面表现出极优的才华,那么将有可能摆脱自己只不过是 “会说话的工具”的不幸命运。伊索便是一例。他后来不但获得了自由人身份,还做过希腊的外派官吏。文艺使古希腊人具有特别浪漫的气质和想象力,比如充满女性之神:时序女神、雨虹女神、夜女神、梦女神,还有妩媚、优雅、纯洁三女神。其三,不和女神在神话中的存在,证明理性思想的哲学萌芽已产生。
历史很快证明,女人的这个黄金时代只是一个神话。列维-斯特劳斯在他对原始社会的研究的结论中断言: “公共权威,或者简而言之社会权威,总是归于男人的。”错误来自于人们混淆了相互激烈排斥的 “他性”的两种形态:其一,作为大地、母亲、女神的形象,女性超越了人的范围,因而对男性来说不再是一个可以构成相互关系的同类;其二,在集体的中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显示出来的二元性,使一部分男人反对另一部分男人。其实,父系制,这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导致人意识到自身、并要加强自己的意愿时的必然命运,即便面对生命、自然和女人神秘的权威,男人还处于混沌不清之时,他也从来未曾放弃自己的权力。这样,女性在一种静态的、封闭于自身的内在性中被视作了绝对他者;而男性,成为创造-超越的唯一体现。
工人的出现直接加剧了女性他者状况。男性工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图制造工具,他通过工具实现自己的计划、征服自然的意志,他由此确定自己为至高无上的意志,因为他的成功不取决于神灵——尤其是女性神灵——而是他们自己。器皿时代在明晰的概念中打开一场新的“性别战争” (引自 [美]奥利维娅·贾德森同名著作),宇宙的整个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人的宗教与农业的时代相连,这是不可约减时间、偶然性、命运、期待、神秘的时代;劳动的人的时代是能够战胜空间的时代,是必然性、计划、行动、理性的时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 《第二性》中指出:“(原始文明阶段)男性是在恐惧中,而不是在爱中,给以女性崇拜。他只有把她赶下台来开始行动,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
女性由于私有制的到来而被赶下台。父系制的胜利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暴力的结果,从人类起源开始,生理上的优势即使男性独自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弗雷泽说过: “男人造神,女人崇拜神。”正是男人决定他们最高地位的神是女性还是男性。恩格斯指出这种蔓延了整个封建时代甚至现代的女性失势的因由: “发明了青铜器和铁器深刻地改变了生产力的平衡,由此女人的劣势确定下来了。”波伏瓦对恩格斯的简单论断显然并不满意,她进一步指出: “对男工来说,女性没有成为一个劳动伙伴,而是被排除出人类的共在,因为女性不参与男性的工作和思考方式,因为她受到生命的秘密控制,男性不承认她是一个同类;因此,她在他眼里保留着他者的维度,男性就只能变成女性的压迫者。”在封建时代,女性地位甚至不如奴隶,正是由于奴隶的劳动比女人所能提供的劳动成效多得多,女性便失去了她的经济作用,从而也就失落了社会地位。
女性的命运在多少世纪中始终与私有制相连,她的历史大部分与继承史有关。这个继承不只是生命的接续,更重要是私有财产的继承。女性是父亲与丈夫的财产,婚姻就是财产的转移。以十一世纪的欧洲为例。这个时期,在日尔曼人的法律中,女性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在缺乏男性继承人时,女性可以继承。这个法律直接催生了女婚妇女的另外一种命运:大量妇女被休掉四五次之多,因为多结几次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是增加他的领地。尽管女性的社会生存状况有所改变,但是女性仍然需要男性监护人。在 《吉拉尔·德·维埃纳》中,勃艮第公爵夫人亲自向国王提出要求,嫁一个新丈夫:“我的丈夫刚去世,但服丧有什么用呢?……请给我找到一个强大的丈夫,因为我很需要他来保护我的土地。”
2.碰撞
马克思说: “人是类存在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如果我们愿意赞同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我们的时代正在实践着这个观点,那么接下来便是性别战争的自然消弥与人的自我实现的平等展开,男女性别之间,不再是对抗,而是基于共同体的良好意愿之上的碰撞与共生。
而今天,碰撞的意义,恐怕更重要的,不在于性别之间,而在于女性在存在意义上的自我求证与主体确立。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呈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脱缚了封建桎梏的女性形象,一个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的命运:当莎士比亚在中学里学会一点拉丁语、语法、逻辑时,她在家中仍然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当莎士比亚偷猎、跑遍田野、同女邻居睡觉时,她却在父母的眼皮下缝补破衣烂衫;即使她像他一样大胆离家,到伦敦去寻找发财机会,她也不会变成女演员,自由谋生:要么她被领回家去,被强迫出嫁;要么她受到诱惑,被人抛弃,名誉扫地,绝望地自杀。也可以想象她变成一个寻欢作乐的妓女,一个莫尔·弗兰德斯那样的女人,就像丹尼尔·笛福生动描绘的那样——无论如何,她不会指挥一支军队和写作悲剧。伍尔夫所指出,是启蒙时代的女性生存境况:一方面,是时代对女性作家的敌意;另一方面,是女性缺乏知识与智慧而导致的主体性缺失的困境。
女性在男性镜像里存在太久了,以至于当男性权威被抽离之时,反而陷入不由自主的深渊。主体意识的建立是女性无可回避的现代性命题,这个道理,如同人类肇始之初男性主体性确立一样。
叔本华强力意志说给人生意义问题一个解答。一个人是否足够坚强有力,在于他能否支配自己与世界,能否给予生命以计划与目的。叔本华指出,世界不是但求自我保存的消极生命的堆积,而是 “一个奔腾泛滥的力的海洋,是永远在自我创造、永远在自我毁灭的酒神世界”,它在永恒的生成变化中 “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回来的东西,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披览的迁化”。生命的肯定者也应当秉承这世界本体的精神,不是消极地但求生命的保存,而是积极地从事创造,成为精神上的强者。从反面来说,正因为人生的意义全在于生命力最高限度的发扬,而痛苦和刺激提高了生命力,加强了力感和生命感,因而也化作了快乐。生命的本质在于强力,追求并且体验这种强力,也就实现了生命的意义。
“人不能被判为奴,他只能自认为奴”,这是康德缄默的忠告。女性主义的历史警示我们,除却生理的自然局限,女性在生命里可以有所为并应有所为,在整个人类性别对抗的历程里,某种程度上,女性地位长期的镜像存在当部分归因于自身的原因:女性放弃了与男性同等的生存自由欲望张力,放弃了自我实现的清晰计划与实践力,而终于导致历史性的人权丧失。因之,女性历史境遇的改变的自我本质,终须在碰撞中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而非停滞于虚妄的女性主义感受而沾沾自喜;人须明白世界之大与生命之重,拘泥于性别之争而沦为时代空壳是多么鼠目寸光。我们创造了这一切,创造出这些那些现象的碰撞,当有同样的理性来清退我们自身于迷乱现场,从人的整体意义上——而非迟滞于性别之争里,在叔本华的 “本质的我”的指引下,在黑菲的书房,书写下另一个金石为开的格局。
一个人感受碰撞以及碰撞带来的精彩与痛苦的能力,是由这个人的精神能力的大小所决定的。古代男性中心的时代取缔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力,某种意义上也即取消了女性建立精神主体的可能性。精神空虚的人,其内在是空虚的,他的迟钝使他无法感知到时刻发生着的碰撞,也就更无法感知碰撞带来的精神与痛苦,因而精神贫瘠的人往往是无聊的。无聊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因而汲汲于向外逐求,以身体性的狂欢与瞬间快感来涂抹虚饰,并在一种重复性的低级的欢愉中求得身体质性带来的刺激性快慰。然如是刻意的碰撞,对于灵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精神丰富的人,对于碰撞是敏感的,叔本华说: “天才的条件就是,具备超越常人的精神力量——亦即超常的感觉能力。”他能够享受着自己卓越的、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所带来的乐趣,充分感受或大或小的碰撞,那些来自外在的碰撞,对其而言,反倒是烦恼而累赘的。
那个神经质的女人伍尔夫,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因为她说“读书不必听人指导”,这种近于骄慢的姿态真是充满了自在的乐趣:“我们读书时,谁会抱有这种预期目的?我们热衷于做某件事情,难道就是因为这件事有实际好处吗?难道追求乐趣,就不能作为最终目的吗?我们读书,难道不能说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吗?至少,我是这样的——我有时会这样的想象:到了最后审判时,上帝会奖赏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立法者和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会得到上帝赏赐的桂冠,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大理石上而永垂不朽;而我们,当我们每人手里夹着一本书走到上帝面前时,万能的上帝会看看我们,然后转过身去,耸耸肩膀对旁边的圣彼得说: ‘你看,这些人不需要我的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只喜欢读书。’”是的,虚妄的追求与自足的乐趣间的取舍平衡永远是人生的必修课程,此时此刻,我明白,人生有所告别,自有所加获,外在的奔跑终究不能取代内心的向度。
女性之美乃源自其天性的敏感与娇柔,因而女性最关切的问题恐怕莫过于如何直面力的较量与心的苦痛。意识到哲学意义的自由的价值乃是 “人”的必需。叔本华这样来陈述苦痛的审美性意义与其在实现人的终极自由上的意义: “智力突出者以敏锐的感觉为直接前提,以强烈的意欲,亦即强烈的冲动为情感的根基。这些素质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情感的强烈程度,造成了对精神甚至是对肉体痛苦的极度敏感。”他们的敏感,一方面使他们对美有远超于他人的感知能力,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世界的精彩,但同时,这种敏感又会使他们受到的伤痛比常人放大数倍。
女性必须承认,在英雄主义书写的历史上,雄性确乎值得仰望:不管是在与自然野性抗争的原始时期,还是国家版图整合的金戈铁马时期,男性无不表现出身体与精神的强力之美。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几位自杀的一流俄国诗人时说:“他们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急剧碰撞之下,愚人与庸人是不会有所感知的,更不会走向清晰的自我认定与自我抉择;只有诗人才会自杀。诗人的自杀,是与过去的信念彻底断了关系的结果,更是勇敢感知碰撞而非怯弱回避的结果。在时代性的道德失范与价值毁灭里坚守自己的信念,这无疑太困难也太痛苦了——在西方启蒙精神受到怀疑之时,多少诗人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界,荷尔德林、斯威夫特、尼采……但精神敏锐的他们在自身信仰的撕裂中,走向价值重建与自我圆满:谁能否认,唯有精神丰富下的碰撞所带来的痛苦,才是心灵的引导和最后的释放者。他们由此成为了自身命运的主人,他们用主宰生命的幅与员来宣示自身才是价值的制定者。
人的劣根总在牵制着我们用恶意揣度从前与未来,试图减轻历史的软弱与当下的赧然。正因一切改变在人性软弱之时总是呈现为被动,我们消费的时代才会反过来塑造着我们。卡尔维诺: “丢掉了讨论问题的谦卑是其次,更严重的是丢掉了寻找正确答案的能力和意愿。”赫胥黎提出 “不再思考”的问题,如今正摆在眼前。
因此最后,面对女性主义的当下,我想说:在前途未卜的将来前,过去和未来都吹着相同的风。世界将永在碰撞,在物质与神灵的碰撞中,女性须在其中,女性须在“现在”,女性须在碰撞中自证着自我主体的存在。
神祗的神圣馈赠不容遭到蔑视,
这些馈赠只能经由神祗的赐予。
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获取它们。
——《伊利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