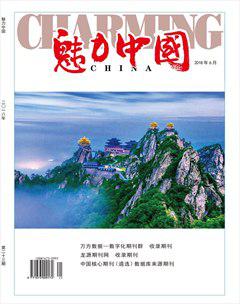末代土司的“边”与“界”
摘要:长期以来,历史学、民族学等各学科对从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同时也基于各自的视角对此进行着各自的解读。郑少雄以明正入司为视角,重新审视在汉藏文明之间,政治权利、宗教权力等各种权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而作为这一地区的政治领导者,明正土司似乎无法置身于权力的交织之外,从而演绎出不一样的土司人生史。
关键词:明正土司;康定;穿行者
一、明正土司的多重身份演化
“土司”首要的身份认同是来源于王朝的权威和任命,只有帝国的承认,“土司”才拥有正统政治身份的合法性。而明正土司身份来源的合理上,作者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的侄子本来是在血缘上是最合理的继承人,但是他却选择去做喇嘛而将土司的位置让给自己的叔叔。这中间体现的的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和对当时康定地区现实的考量,这样才能实现土司家族可以“拿起铃铛做活佛,放下铃铛当土司”。而在另一层面上,这又是一种艰难的心理和政治上的抉择,因为,政权和宗教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意味着,土司必须从两种角色和身份中选择一个。如作者所言:由于土司和喇嘛身份的合一并不容于帝国,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土司的合法继承人如果选择出家,那么土司的职位就必须由家族的其他人来担任。
在末代明正土司的政治身份的演化中产生了不同的政治选择,而他的这种不同的选择几乎看作是一种与他所处的生态空间的分界点之上的。在政治稳定前提下,土司的政治功效使帝国官吏对边臣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这种改观是可以上升到帝国的最顶端的。但是,当这种稳定结构一旦被打破——清末民初的改土归流,同时也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动——设立西康省,将康定划归西康,康定末代土司原有的政治取向立即转向了原来的对立面,接连三次的叛乱的兴起——虽然都是以失败告终,来表明自己已经站在了原来权力服务对象的对立面。原有的政治地位自然也不再拥有。当末代明正土司失去了原来的政治保护和底层的民众支持时,他只能出走关外荒漠之地。在这里,他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西藏的喇嘛,同时,以地域来宣誓自身的族群归属,从而试图摆脱关内汉廷和官吏对他的叛乱者的定位。
在似有似无的三次的叛乱中,土司的合法性没有受到撼动,从而没有让末代明正土司提前淡出历史的舞台。在当时还处于封建一统的王朝社会似乎变得有些匪夷所思。一旦政权转换,明正土司的身份也随之改变。他从一个土司转变成了“康定县总保正”负责管理康定地区的乌拉运输体系,而当时的中央也就是看中了他之前作为地方土司的影响力可以更好的支配这支负责关内和关外互动和转换的运输队,事实上,在乌拉运输制度的形成的那一天起,它就不仅仅是经贸互动,人员流通的承担者。它还负责连接生态阻隔下的汉藏文明的互动,这其中包含了族群认同、宗教信仰以及区域政治等诸多内容。
而关于土司代表政权和喇嘛代表的教权大小的争论至今在学界仍然引发这热议。笔者认为,在集权化的王朝统治中,历代统治者都是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御思想。但是,康定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汇处,它是处于一种“文化的复合地带” ,处于不同的生态条件下的边缘地区和重要的缓冲地带,这就要求我们用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康定地区的政权与教权的关系。这两种权利是支撑这个交汇处的两股力量,它们之间没有刚性的比较,因为,在大环境下,政权和教权都是土司家族的人掌握。
另一方面就是,这两种权力往往都是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喇嘛需要土司发动更多的头人来运送生活物资和信奉佛教,而土司则需要喇嘛向帝国中央汇报他在边疆治理的政绩。而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之间会有平和的自我认知——在什么时候教权地位高于政权,在什么时候政权高于教权。
二、明正土司的“钟摆”
政权与教权的“钟摆”在明代明正土司治理康定地区过程中从未停止过。在现实社会中宗教的存在和传播需要得到当局的官方认可和允许。甚至,许多宗教要依托统治者的认可和国家财政的支持才得以存活。而在康定地区,寺庙和喇嘛掌握着该地区的宗教文化的管理和解释的权力,这种权力看似是出于政权的统治之下的。但是,很多时候教权往往会对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土司的统治和对于该地区的有效治理一定要得到地方宗教的承认和支持,这样土司的统治才得以施行。更为重要的是,在土司官方政治代理者的外衣之下也存在着宗教代言人的身份和角色。长期以来,土司都在这两种身份中自由的转换和摆动,有的时候也是被动的被推向另一边——比如政治外衣被去除和遭受来自政权的威胁的时候。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回到原点,这个原点就是在他的管辖地区能够维持一种文化和地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足以容纳教权和政权的和谐相处。
明正土司的人生发展轨迹与历史特定区域形态密不可分,作为传统华夏文化和政治的“边缘”,明正土司的人生发展历程史跌宕起伏似乎变得有所依据。区域特性也是造就明正土司的“钟摆”状态的重要因素,不管是趋向帝国的权威还是藏区的喇嘛。明正土司作为传统国家和疆域视野下的“边缘地带”的地方土长,始终面临着多重权力的平衡处理。作为帝国的地方政治的代理人,他的权力行使的生态基础是作为汉藏文明交汇处的康定,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末代明正土司的权利是和当地的喇嘛、驻藏官员、锅庄、头人,甚至是外国势力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必然会冲淡土司的权利集中,从而造就一个“权威的中间性” 。在这种生态,族群,区域和信仰的多元化格局下,就很难“将族群当做人群主观认同之结群” 。因此,末代明正土司势必将成为那个多元化格局下的一个——穿行者。
作者将王朝末期的康定区域的土司制度为研究视角,探寻在土司角色在封建社会发展末期的人生史。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特特地理生态条件下的区域制度的认识与思考,以明正土司为中心,将康定区域的各个社会角色、地方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部较为完善的明正土司人生史叙述,也折射出在清末民国初年康定区域社会发展的变迁历程。
三、对现实的思考
一方面,關于民族地方的文化发展。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时期的康定地区一直是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统治边缘的。作为远离统治中心的区域,受传统汉文化的影响有限,必较容易的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交流方式。这些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交往方式在强化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封闭了康定区域经济文化的多元交流,从而导致康定地区的新一轮的非良性的循环。郑少雄笔下明正土司角色的存在正是使这一问题得到折中的解决。明正土司作为王朝施策的地方代理人,在文化传播上也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政治的传导中,土司通晓各种政治典章和相关的礼治制度,能够很好的将王朝的施治方针和政策与康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更有效的治理。
另一方面,关于国家的民族区域制度和施策的建设。在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中,王朝国家的政治强化是确保土司制度发展的政要保证,段红云指出“在土司制度的过程中,中央王朝不断地增强制度建设和统治力度增强这些地区的国家认同,推动边疆地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进程.” 。在康定地区,存在的大量的“二元化”现象,政策、经济方式、文化表达、区域、等方面的“二元化”助推了康藏地区的区域和认知的隔阂,也使得王朝中央对康藏地区的治理实行“二元化”的体制变得理所当然,继而强化了康区作为汉藏文明的边缘和连结地带的地位。这样的达结果是,康定地区的国家认同一直处在汉藏之间摇摆。因此,当今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构建“中华民族一体化”过程中,要避免“二元化”所带来的不平的民族关系的影响,必须强化民族共同发展对国家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是凝聚各民族的重要力量,也是避免其他势力介入国家治理的重要保证。
土司制度作为历史时期边疆民族地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的形成和发展历经了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土司制度伴随着王朝国家的治理需求、统治者的治边认知、民族边疆的现实考量等因素不断的嬗变。康定地区作为中国文明发展与传承的一个重要区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的与周边族群与文化进行交融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是当代国家治理和民族自身的安定发展都应该考量的问题
注释:
1.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2.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所谓的“权威中间型”值得是一个社会中的权威并非终极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增订本,第13页
4.段红云:《明清时期云南边疆土司的区域政治与国家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月第5期,第26页
参考文献:
[1]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转引自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6年
[3] : 萨林斯,;蓝达居等译,刘永华等校:历史之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增订本
[5] 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的人生史[M],北京,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6] 段红云:明清时期云南边疆土司的区域政治与国家认同[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月第5期。
作者简介:王联智,男,云南民族大学专门史研究生,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