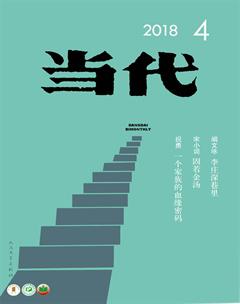时光深处的火车
作者简介:张毅,祖籍高密,现居青岛,有诗歌、散文、小说散见国内刊物。著有诗集《幻觉的河流》、散文集《花园原址》等。
去年夏天,我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一本关于蒸汽机的小说。在开往G城的动车上,我打开一本有关蒸汽机车的书。这本书是一个叫阿历克赛·赛尔的英国人1926年写的。
内容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历数世界铁路发展史,蒸汽机是其中最重要的章节……我向外望去,窗外就是我曾工作过的胶济铁路。我看到一些消失的车站和人物像电影一样迅速划过……在构思时,我发现这篇小说就像一辆火车。开篇如同火车从站台出发,意境朦胧而温情,中间内容恰似途中的旅客,平静背后,却有一段难测人生。火车到站,小说也结束了。
是那种老火车,高高的烟囱,黝黑的机车和昏黄的灯光。
就从我上班那天说起吧。
一
那天是农历正月十六,天降小雪,高密的天空白茫茫的。早晨,我吃了三个高粱面饼子,跟着我爹到火车站报到。路上,风一阵大一阵小,吹落瓦楞上的雪粒。我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从站前街出来,走过一家布店、一家粮店和“胡家炉包店”,就能看到火车站钟表楼了——那是这个小城最醒目的地标。钟表“当当”响了几声,惊飞几只寻食的麻雀,它们在空中扑棱几下,落在路边的树枝上。小广场聚集了一些生意人,卖糖人的、卖烧饼的、卖泥老虎的。一个中年人坐在马扎上,眼前摆着一副象棋残局。一个瞎子面前写着“算命相面”。旅客背着大小不一的行李,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我爹在前面边走边说:小天,你上班后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干工作只要思想对了头,就能一步一层楼。我跟在后面边走边答,我知道,爹,这话你说了九十九次了。我爹继续说:小天,你得好好听领导的话,领导指东,咱不能打西。领导让赶鸭,咱不能赶鸡。我说我知道,爹,这话你说了一百次了。我们爷俩前后走进站长室。站长室烟雾腾腾的,墙上挂着“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站长是个胖子,嘴里叼着一根前门烟,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正在摇磁石电话。他边摇边骂骂咧咧,不知道嘴里咕哝什么。看见我爹进来后,用手指指一边的椅子,意思是你先坐下。我爹摆摆手说,王站长你先忙,不用坐。一会儿王站长把电话挂了。我爹凑上前,把两瓶高粱酒、一条金鹿烟,放在站长桌前,又给他递上一支烟,笑呵呵地说:王站长,我把儿子领来了。
王站长乜斜一眼,说:老丁你客气什么,都是自己人,你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哩。
我爹把我推到站长面前:这就是我儿子丁小天。小天,快叫王站长。
我赶紧上前叫了一声“王站长”。我爹说:王站长,以后孩子就交给你了。王站长说:你客气啥,小天这孩子我小时候见过,一下长成大青年了,成了铁路工人了,呵呵。接着他向四周看了一眼,叫道:张建民,你过来。外面进来一个人,我一看,那不是邻居张建民吗?张建民穿着一身铁路制服,胡子拉碴的,袖子上被烟头烧了几个洞。张建民比我大两岁。他学习不好,经常逃学,还出走了两年。
王站长对张建民说,这个丁……丁……啊……
丁小天。我爹说。王站长接着说:啊,这个丁小天以后就跟着你当学徒,教不好我收拾你个孙子。你先领着他出去看看,熟悉一下车站环境,让他看看咱们车站的大好形势。
张建民扫我一眼说,走,出去转一圈,先熟悉一下环境。我和张建民走出站长室。
风挺凉,一股寒气顺着领口吹进棉袄,我打了个寒战。站台上站着一些旅客,他们有的搓着手,不断走动着,有的着急地望着远方。那辆开往青岛的火车晚点了。钟表楼时钟响了几下。一个姑娘身背一个琴盒,神情淡然地站在那里。她穿着一件黄军大衣,垂到腰际的辫子,在风中摇摆。
男人在抽烟,女人在闲聊。你打哪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用高密方言问。五连。东北口音说。你去哪?俺去黑龙江,三棵树。干哈?看俺姥姥。那疙瘩老远了。得三天两夜。你呢?俺去通化。
一个小女孩在哭。另一个小男孩在地上撒尿。
给她块糖含着。不用不用,别惯她毛病。別客气,都是出远门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伸出手,把一块高粱饴递到孩子嘴里。哭声停了。这是谁的孩子?把尿弄到我鞋上了,欠揍。一个男人在吼。“啪”,是耳光的声音。小男孩的哭声又开始了。
靠后站,靠后站,离警戒线远点,你听见了吗?那个抽烟的,你耳朵聋了?扩音喇叭传来一阵训斥声。抽烟男人连续退了几步。张建民从旁边拉我一把,走啊,怎么走神了?
临道停着一辆货车,十几节油罐车排成一排,像一队头戴钢盔的士兵。薄冰在太阳下一闪一闪的。检车员不断用锤子敲打车轮,传来清脆的金属声。检车员偶尔在车厢横梁处用粉笔画着记号。有节车厢两端画着一个骷髅,挺吓人的。张建民指着骷髅问,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拉危险品的车厢。我问,什么算危险品?张建民摸摸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也不大清楚,大概炸药吧。风裹起细砂粒,拍得车体啪啪作响,空气中有股铁锈味。检车员一边敲打,一边朝我们走来。这个人张建民认识。这是新来的小丁,我的徒弟。张建民走在前面,大拇指朝后一跷,把我指给身材矮小的检车员。张建民接着问:没有什么事吧?老李?老李说,没有事。张建民说,没有就好,大冷天的最好别有情况,有事就惨了。他递一支烟,老李接了,点上,深吸了一口,说,最近检查有点多,大概又要过“特运”了。
那个年代,这条铁路经常往来特运火车。比如运送中央首长的“专列”,运部队物资的“军列”,还有其他运输的“特运”。初中时,每次过“军列”,我就踩着板凳,趴在窗上,看着一辆辆装满坦克的“军列”从眼前驶过。
张建民把我领到一所旧房子前,说:这就是我们联防组的值班室,说完后,“哗啦”把门打开。里面光线暗淡,有股酸臭味道。一张旧桌子上,摆着搪瓷茶缸、铝质饭盒。茶缸和饭盒生锈了,已有些年月了。一把竹编暖壶压在上面。房子中间有个铁皮做的炉子,炉火呜呜响着,铁皮烟囱被火烧红了。
远处传来汽笛声。值班员挥动信号旗,红白相间的臂板信号机“喀哒”落下,一辆火车喷着白烟,缓缓驶来。车轮与铁轨摩擦着,发出尖利的金属声,在站台上慢慢停下。车门打开了,旅客开始下车,上车旅客推拥着,与下车旅客挤成一个疙瘩,又慢慢散開。那个穿黄军大衣的姑娘,随着人流上了车,车门关上了。值班员举起信号旗,向司机发出开车信号。火车开始很慢,渐渐提起速度,车轮越转越快,随后,在闪着寒光的铁路尽头消失了。
中午我请张建民吃饭,算是拜师饭。三爷爷的“胡家炉包店”有年月了。小时候,我每次路过炉包店就不走了,一是听他讲故事,二是惦记那锅炉包,香喷喷的。没人吃饭时,三爷爷坐在旧藤椅上,左手摇着蒲扇,右手敲着藤椅:楞哩咯楞、楞哩咯楞,八月十五霜打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三爷爷经常捋着胡子,给我讲古,讲高密人修铁路时“抗德”的故事。那年,三爷爷七十八岁了,身板硬朗,声音洪亮。讲完后,就用油纸包几个炉包,递给我,说:个小吃闲饭的!我用手托着炉包,热乎乎的,吃两个,给弟弟留两个。三爷爷见我来了,笑呵呵地捋着胡子,说:小子,上班了?我说,上班了,三爷爷。你以后不能再叫我“吃闲饭”的了,我已经能挣钱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跟你爷爷较劲了啊。那个中午,我请张建民吃了两大笼炉包,喝了一瓶高粱白干。高度酒,我喝得晕乎乎的。
二
联防组有四个人:张建民、白秋生、小肖和我。张建民是组长。联防组主要任务是站场巡逻,和现在保安差不多。有时还要配合政治形势和临时任务。分白班夜班,“两班倒”。
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受用。闲散,平常没什么事。白班出去,围着站场蹈几圈,回来看报喝茶聊天。晚上再蹈几圈,看报喝茶打瞌睡。我是新来的,为了要求进步,经常帮车站抄《通知》,比如上级文件通知、迎接检查通知、打扫卫生通知。那天,白秋生见我进来,很远就伸出手,问:新来的?我握着他的手说:嗯。我叫白秋生,白天的白,秋天生的。他顿了一下,问,您贵姓?我说,我叫丁小天。他抬头“哦”了一声,说,有意思,有意思,我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白丁,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嘛。握过手后,白秋生把手一摆,说:请坐。然后打开收音机,喇叭里传来吱啦吱啦的声音。他不断扭动开关,声音慢慢清晰起来。白秋生床头摆着很多书:《天体物理学》《晶体管收音机组装原理》等。还有一本奇特的书《世纪》。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后来知道,《世纪》是法国星相学家纳斯特拉达马斯关于预言人类未来的书。白秋生能组装收音机,他把几个晶体管、电容、电阻等用导线连接起来,用电烙铁焊接在电路板上。很快,这些零件就“活”了,就有声音了。开始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像一个人在水里不停地吐水泡。后来声音越来越亮,越来越俊,还讲普通话: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钟。我问,这些声音从哪里弄来的?他笑着说,从天上。我看看天,什么也没有。他继续笑。
白秋生是青岛知青,个子挺高,奇瘦,眼睛闪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衣服总是整整齐齐。他最早下乡去了内蒙古乌海,因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中途得了梦游症,自己爬火车逃出内蒙古。他在高密下车,托人办了就业手续,成了一名铁路职工。说起内蒙古,他眼神里就有一种苍茫。他说:我一直想逃出去,但是那里太大了,到处是荒野,漫无边际的……内蒙古草原,唤起他奇特的伤感。白秋生收集火车模型。他的火车模型有三大箱子。有不同时期、不同型号和不同厂家的蒸汽机车。我问他:你弄那么多火车模型干什么?他反问:你知道世界上什么跑得最快?我说当然是火车,他说,是,但不是咱中国的火车。十几年前,日本的新干线高速列车,已经达到270公里以上的速度。270公里?我惊奇地问。就是说,从青岛到济南只要两个多小时?那可是太神了。他说是的。我有些不相信。他说,30年后,咱们国家也会有这么快的火车。
张建民没事时常和小肖打牌,两人脸上贴满纸条,白花花的。小肖叫肖新春,是个临时工,家在很远的农村,个子不高,脸黑黑的,眉毛很浓,头发凌乱,神情忧郁,穿黑色土布褂子。他和几个收废品老乡,合租了一间铁皮屋。铁皮屋阴暗潮湿,房顶上的油毡布被积雪覆盖着。我知道他下班后很少休息。他有一辆旧三轮车,经常在货场找活,帮人搬运东西,这样可以多挣一份钱。一次,他要把八吨重的棉纱,搬运到10多公里外的地方。那天,他蹬着三轮车。从早晨开始,一直到晚上结束。来接夜班的时候,我看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同情地说,小肖,今天晚上我替你上班,你回去休息吧。他张着嘴半天才说出,没事,丁大哥,我能行的。
小肖不在时,张建民让白秋生和他打牌。白秋生说,自己不善打牌。他有时会叫我一起去小广场,看那里的象棋残局。我们去的时候,一帮人正围在一起看棋。一个人蹲在那里看了半天,刚走几步,脸色就难看了,又走了几步,输了,那人只好掏出三块钱,认输。白秋生神情淡然,观棋不语。中年人抬头看看他,挑衅地说,兄弟,下一盘?白秋生摆摆手,走了。中年人望着他的背影,说,看你个熊样子,也不像个会下的。这话让他听见了。一日,白秋生过来,一屁股坐在马扎上,他跳一步马,中年人脸色由青变白。又拱一步卒,中年人脸色又由白变青。白秋生转身起来,走了。中年人大呼,高手,尊姓大名?白秋生转身,说,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中年人张着嘴,很久没合上。
张建民经常在大街上跑步,他是我们县的长跑冠军。一年四季,不管暴雨还是大雪,我们总能在黎明的大街上看见他跑步的身影。我跑步的习惯就是那时跟他学的。那年开春,我胃口大开,一顿能吃六个馒头。我娘看着我狼吞虎咽,很快吞下六个馒头、一碗稀饭,瞪着眼睛说,做下了做下了,你看这孩子,像个克朗猪似的,怎么能吃这么多。即使这样,我还是吃不饱。那年月,我一见到点荤腥子就眼放绿光。一天,张建民神秘地说,小子,听师傅的话,带你去个地方。我跟着他,往货场方向走去。在离货场200米外的线路上,停着几节废旧车厢。他在车厢门外前后左右望了一圈,掏出钥匙把门打开,带我进去后,又把屋门从里边锁上。里面黑漆漆的.有股尿臊味。他寨寨窣窣地从草堆里掏出几个铁罐头。他迅速用螺丝刀把铁罐头撬开,一股肉罐头特有的香味扑鼻而来。吃吧,早晚吃够了。我开始有些害怕,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把一个罐头吃完了。他把罐头盒“哗啦”扔到脚下,看我还在愣着,问,怎么?你不稀罕吃这个?我哪能不稀罕,我见都没见过这种东西。我躲在漆黑的废车厢里,狼吞虎咽,以最快的速度吃了三个肉罐头,撑得我下午不停地打嗝放屁。从此我知道了,这些罐头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我问他: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张建民神秘地笑笑,说:小子,好吃的东西多了,以后听你师傅的,保你有好吃的东西。
站台上看见那个穿军大衣的姑娘后,我眼前一直有对大辫子在晃。上白班时,我总有意无意地往站台方向看。太阳在树梢上跳动几下,很快隐到车站后面。站前街小店铺的窗关了,门关了,灯也一盏盏灭了。热闹一天的站前街一下寂寥了。我把联防队的红袖章套在胳膊上,拿起手电筒,开始了夜晚的巡逻。夜里,除去站区孤零零的灯光外,周围一片黑暗。有夜航飞机从天空掠过,两朵翼灯忽闪着移动,虚幻而飘逸,翼灯很快不见了,半晌,空中传来隐隐的轰鸣声。远处那条河在流淌,只听得见河水的声响,却看不到河流的姿态。一排等距离的灯光在黑色地平线上均匀地滑行,那是一辆夜行客车。火车慢慢靠近车站,“咣当”一声停下。下车旅客操着不同方言,在夜色里吵吵嚷嚷地涌向出站口。车厢内亮着黄色灯光,显得很温暖。一个少年从窗口向我张望,我向他摆手,他也友善地向我摆手。他旁边的小女孩依在大人肩膀上,已经昏昏欲睡。临道停着一辆货车。高高的烟囱,黝黑的机车透出昏黄的灯光。机车不断“噗噗”排着水蒸气。一个值夜班的年轻人把水鹤移动过来,准备给机车加水。不远处有个水塔,高高地竖在夜里。年轻人慢慢爬上火车头,一个老师傅站在巨大的机车驱动轮旁,双手握紧水鹤闸阀。年轻人把水鹤的链条往前用力一甩,水鹤转动了。水鹤对准机车注水口,年轻人喊一声“好了”。老师傅说,好的。年轻人飞快地转动红色闸阀,水流从水鹤口倾盆而出,如一道瀑布自夜空落下。
车厢里整齐地码放着集装箱。能看清模糊的字迹。品名:罐头。生产地:山东高密。目的地:阿尔巴尼亚。看到“阿尔巴尼亚”这几个字,我的眼睛迅速穿过夜空,一直飞向遥远的欧洲。那可是巴尔干半岛上空的雄鹰,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啊。大概从我记事起,我们就一直在援助世界上的穷朋友。什么古巴啊,阿尔巴尼亚啊,朝鲜啊,坦桑尼亚、赞比亚啊……长长一串名字。广播里一直说,他们正在进行艰巨的革命斗争。可是我们也不富裕啊,吃肉要用肉票,吃饭要用粮票,烧煤得用煤票。还有布票、肥皂票、洗澡票,缺了哪样都没法生活。我家四口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二两油票,每人每月25斤粮食。25斤粮食管鸟用啊,我和弟弟整天吃不饱。我弟弟这个饿鬼托生的,从小都是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我们碗里经常看不到一块肉,有时连一点油花都没有。我就不明白了,怎么这样还要去支援那么多国家呢?为这事我问过我爹:咱们国家怎么和咱家一样,怎么净是些穷亲戚啊?我爹一个耳光抽过来,说,臭小子,这话你可不能在外边说啊。我爹看看周围没有人,又小心翼翼地说,虽然咱们生活也很艰苦,得勒着腰带过日子,但为朋友要两肋插刀啊。朋友有困难,咱当然得帮助了。我娘也在一边帮腔,说,自古就是穷帮穷,穷不帮穷谁帮穷?帮人一口热饭,胜过三匹大马。毛爷爷不是说过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记得毛爷爷好像还说过,要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还有打败美国侵略者,解放全人类之类的话。我《毛选》学得不好,一读《毛选》就想睡觉,不知是什么毛病,觉得和小时候吃不饱有关系。但想到阿尔巴尼亚,我的感情突然神圣起来,觉得还是我爹说得对。我想起自己和张建民吃过的肉罐头……那一定是张建民不知什么时间偷的。想到这里,心里不覺生出一种罪恶感。
一帮装卸工在汽油灯下往车厢里装棉花。汽油灯芯“啪啦啪啦”响着。高密是产棉大县,每年秋末冬初,火车不断把棉花运往四面八方。十几个装卸工分散在夜色里,形成一条默契的传送带。他们说着脏话,粗鲁地笑着,棉包在手中准确传递着。另一节车厢里有十几匹马。是一群刚集结的军马,脖子上有烙烫的编号。这批来自胶河农场的军马,已达到服役标准。一匹毛色暗红的马,从栅栏里伸出半个马头,这匹马借助光线看见了我。我和它对望了足足十分钟。马打着响鼻,马蹄使劲敲击车底。我听到一匹马蹄在响,接着是几匹马蹄在响,后来,十几匹马蹄在一起响动。车厢里传出一阵阵马蹄清脆的回响。马有灵性,这些马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小城告别。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剧院观看爱尔兰舞剧《大河之舞》,当演员整齐的踢踏在现场响起时,我突然想起这个遥远的夜晚,十几个马蹄在一起响动的情景,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些马在这里集结后,将开始一段漫长旅程。它们要经过几次火车编解,最后去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它们的旅程因这个冬夜多了几分苍茫。
客车启动了。过了片刻,货车也启动了。两辆方向相反的火车交错而行,很快消失在夜色里。站台再次变得空旷寂静。
三
值夜班时,巡逻完后没事可做,我常和张建民到货场仓库逮麻雀。晚上除了猫头鹰外,所有鸟都是瞎子。夜里寒光闪烁,呼出的热气蓝莹莹的。麻雀缩在屋檐下,手电筒的强光刺得麻雀不辨方向,一动不动地等着束手就擒。张建民爬上梯子掏麻雀,我在下面接。他把一只麻雀递给我,麻雀用惊魂未定的小眼睛望着我。我没接好,麻雀发出微弱的声音,伸开翅膀飞走了。我听到它撞在一面墙上,又在地下“扑棱”几下,向着夜空飞去了。接下来,张建民把麻雀脖子一扭,麻雀立刻就没气了。他把死麻雀递给我,我摸摸,身子还热乎乎的,但很快就凉了,我把麻雀装在袋子里。一条狗向我们跑来,狗饿了,眼里有哀求的意思。我说,师傅,狗饿了,咱喂喂它吧。张建民说,你胡说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弄的下酒菜。他顺手捡起一根木棍,朝狗头使劲敲去。狗叫了一声,很快就没气了。张建民说,帮我抬着。我和他一人提一条狗腿。回到值班室,张建民把狗挂起来,开始剥皮。他噌噌几下,狗皮就完全脱离了。他把狗皮抖擞几下,挂在尼龙绳上,然后清洗内脏。清理好内脏,就把狗扔进锅里。随着水温升高,狗在锅里慢慢收缩。我娘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想起平常张牙舞爪的狗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过的。张建民见我一直在看,就说,小天,你别光看,快把麻雀烤上。我把麻雀一只只掏出来,用铁条做一个支架,放在炉盖上,再把麻雀摆在支架上。炉火越烧越旺,铁青色的炉盖慢慢变成暗红色,麻雀“吱啦吱啦”响着,身体迅速缩小,像块小煤球。很快,麻雀特有的香味弥漫开来,馋得我“哧溜哧溜”地流口水。这时,狗肉煮得差不多了,张建民掀开锅,一团蒸汽冒出来。他把煮熟的狗用木棍挑出来,放在案子上,狗肉“噗噗”冒热气。白秋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背后了。他挤过来说:你们怎么弄得这么好的东西?冬天吃狗肉大补啊。张建民回头看看他,说:补你的大腿,去把酒拿来。白秋生把窗台上一瓶高粱白干递给张建民,张建民用牙咬开盖,酒气弥散开来。他说,不喝酒的不能吃肉。张建民说完,自己咕咚灌了一大口。我和白秋生互相看看。白秋生接过酒瓶,也咕咚一口,脸色陡变,狗一样伸出舌头。我试着抿了一口,脖子梗了梗,眼角立刻浸出泪水。接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狗肉肉紧,有点像马肉。我问白秋生,是不是像马肉?他边嚼边说:有点像,只是马肉有酸味。白秋生在内蒙古下乡时吃过马肉。他说那匹马老了,不中用了,他们趁着晚上,把马带到没人的地方,偷偷杀了,吃完后把骨头埋了。第二天向领导说,那匹马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挣开缰绳跑了。张建民边吃边问:怎么样,白大书生?白秋生说:好,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狗肉。他说着掏出一支烟,先让了张建民,又自己叼了一支。狗肉吃完后,张建民一边擦手一边说:弄得满身狗味,咱们去洗个澡吧。白秋生说:你们去吧,我喜欢冲凉水澡。白秋生一年四季冲凉水澡。他说冲凉水澡身体健康,他是在内蒙古下乡时养成的习惯。
车站澡堂24小时开放。进澡堂要买澡票,一张澡票五分钱。张建民认识看门老头,给他递一支烟就进去了。水池里雾气蒙蒙,昏暗灯光下,全是光溜溜的装卸工,他们每天卸完货以后,都要来这里冲洗。他们有的在水池里,不断往身上撩水,有的趿拉着木拖板,挺着晃悠悠的阳物,在水泥地上吧嗒吧嗒的,来回走动。他们的阳物大小不一,粗细不均,样子淫秽而丑陋。张建民脱下衣服,用手捂着私处,我用眼乜斜了一下,看见他那里黑毛茂密发达。澡池边沿坐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挤进池子,一屁股坐下,半个身子没入水中,嘴里嘘嘘地吐着热气。澡池因为浸泡的人太多,水面漂着很多肥皂泡和污垢。我和张建民在池子里泡了一会儿,一个镶金牙的装卸工认出了他,说,张建民,你怎么也来洗澡?张建民没理他。那个装卸工凑过来说,咱们比比屌大小,怎么样?张建民还没理他。他用左手捂着私处,右手不断撩着水。水泥地上,几个装卸工用阳物挂着螺丝,在地上来回走着。他们在进行“屌挂螺丝”比赛。这是装卸工们一天的快乐时光。他们说着脏话,粗暴而放荡,雾气蒙蒙的澡堂里响起一阵阵笑声。他们一边笑,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比毛主席和西哈努克谁的官大,谈女人为什么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无所不谈,很是快活。我和张建民边看边笑。张建民撩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阳物直挺挺的,奇大无比,像根粗壮的黄瓜。
往回走的时候,张建民告诉我,那个镶金牙的装卸工,外号就叫“大金牙”。这人不好惹,最好别理他。我看出张建民和大金牙好像有什么恩怨。
事情有些突然。那天我上白班,车站派出所搜查了我们的值班室。原来是车站上级接到客户举报,他们委托车站运输的肉罐头,在到达后发现有丢失,而这批肉罐头是从高密站发送的。这件事情已经给车站造成了恶劣影响。我们几个人被分别找去谈话,最后,白秋生被作为怀疑对象,虽然没有可靠证据,但有人说,他看见白秋生晚上围着车厢转悠。
白秋生有夜游症,经常夜里下床,赤裸着走出去。有天晚上,我看见他脱下背心短裤,然后赤裸着往外走,心里骇然。他出门后,我也跟着出了门。白秋生在一所旧房子前站住,嘴里念念有词: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来他走进房间,爬上床,呼呼大睡。我怕他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出了问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建民。他说,不要紧,我爹也有这个毛病,只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叫醒他。白秋生再次裸着身子走出去时,我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半小时后,白秋生回来了。第二天,他依然在《东方红》乐曲中起床,穿衣拉屎尿尿刷牙洗脸吃饭出门,就像昨晚的事情没有发生似的。
我知道罐头事件和白秋生无关,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傅,我选择了沉默。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人生难题时保持沉默。这件事情成为我和张建民共同的秘密。白秋生被车站给予严肃批评,责令离开联防组,被发配去帮助货主“押车”。
“罐头”事件就这样过去了。
四
几场暖风吹过,白杨树的叶苞开始膨胀,土地松软了。路上有一行鞋印,歪歪扭扭的,是一双新鞋的印迹。远处,一个女孩正蹦跳着走在上学路上,印迹是她留下的。一对羊角辫在阳光下,一拱一拱的,显出少年特有的朝气。街上有两个男孩在滚铁环。铁环的影子时而重合,时而分开,“唰唰”的金属声在暖风中回荡。
我的讲述里出现了一把小提琴。
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火车站一带异常安静。鸡不叫,狗不吠。我在巡逻时听到一种声音,像是风声,又像山涧溪流的声音,我循这个声音走去。这是站前街的一条窄巷,我沿黑漆漆的巷子走进一座大院。院子异常空阔,灰暗天空下,石板地面泛着白光。穿过黑暗的过道,眼前出现了模糊的光线,声音来自院子里的一间厢房。我悄悄躲在厢房不远处仰望,微明的灯光下,一个姑娘在拉琴,她有一对长长的辫子。虽然光线不是很明亮,但我还是看清了,她就是我在站台上看见的那个穿黄色军大衣的姑娘。我看见她站在房间里,屏住呼吸,用手调了调弦,然后用舒缓的动作运起弓来。曲子轻松明丽,细腻多情,时而缱绻温存,时而如泣如诉,后来,曲子渐渐悲怆起来,我想起苍茫的原野和风中的树枝。一辆火车驶过,火车的轰鸣掩盖了委婉的琴声。月亮越来越圆了。慢慢的,几个起伏之后,小提琴的旋律渐渐盖过了火车的声音……那个晚上,我在她窗外站了很久。
一个周末上午,我看见她在站台上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米色风衣,背着一把小提琴。她上车前似乎回头看了一眼,她右手抓住车门的把手,身子往前一弹,迅速进入车厢,我也尾随着进入车厢。车厢里站满了人,她在窗口的位置坐下,我也在离她十米远位置坐下。火车启动了。阳光洒在她宁静的脸上,她眉宇间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像丁香在春日最后的闪耀。那是一辆温暖的火车,车窗时而飘进火车头的煤烟,春天的景色迅速退去,一些陌生的车站从眼前划过:姚戈庄站、芝兰庄站、胶东站、蓝村站……车厢里虽然杂乱,却温馨而安详。听着咣当咣当的声音,我心里一阵忘情,觉得火车要把我带向一个神秘世界。
青岛站到了。我跟在她后面,随着涌动的人流向出站口走去。
我看见她穿过马路,我也跟着穿过马路;她坐上一辆公交车,我也跟着坐上那辆公交车;她下了公交车往一条林荫道走去,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她。她在林荫道拐弯时似乎往后看了一眼,我急忙往树后躲去,她一定是看见了我。走了一会儿,我找不到她了,我的眼前全是高楼和汽车,我的心情沮丧极了。我觉得自己太没有出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去告诉她,说自己喜欢她呢。我一个人失魂落魄地穿过陌生街道,又失魂落魄地往海边走去。第一次看见海时我有点头晕,我不敢确定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是幻觉还是现实。我想,海怎么会这么大,海水怎么又这么蓝呢?我使劲把眼闭上又用力睁开。海风“呜呜”地吹着,海面往来着很多大货轮。好像退潮了,海在喧响着,远处漂浮着几个岛屿。这一天,虽然我把她跟丢了,但是看见大海,我的心情慢慢变得晴朗起来。
我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她叫吴若云,在车站俱乐部工作。我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在看电影的晚上。
那时候,车站小廣场经常放露天电影,都是老片子。一天傍晚,小广场再次竖起白色幕布,我向正在拉幕布的人打听放什么电影,他说是《多瑙河之波》。我起身回家拿上手电筒,往小广场走去。那天我有预感,我觉得她一定会来看电影。这种感觉太奇怪了,但我相信自己的预感。路上,很多看电影的男女扛着凳子,陆陆续续来到小广场。幕布下一只灯泡发着白光,人们一边喧闹着,一边听放映员大声说话。我听到放映员在麦克风里说,观众同志们,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会越来越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放的电影是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罗马尼亚是我们的革命战友,《多瑙河之波》是一部革命影片……我在人群里使劲往前挤着,希望能找到一个好位置。旁边的人一边推搡着我,一边骂骂咧咧地说,一个大青年,在女人堆里挤什么挤,想赚便宜是吧?我装作听不见,硬是在人堆里挤出一个位置。放映员又讲话了,同志们,大家不要吵了,大家要是再这样吵,我们就什么也看不成了。放映员说完后,场面迅速安静了。我看见在离我不远处,有一张熟悉的脸,在灯光下一闪,又被人群挡住了。因为场子里的人实在太多,但即使这样,我也能在众多面孔中准确认出她,我知道今晚她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开始在人群里小声喊她的名字:吴若云,吴若云。我连续喊了两声,我相信她可能听到了,但是她没有回头。这时,灯光灭了,电影开始了……片子很旧了,画面出现一道道划痕,像夜空的闪电。风吹幕布“噗噗”作响,幕布上的人物不断随风声变化着,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歪歪扭扭的,像一幅达利绘画。电影中的人物在喇叭里大声说话,底下观众在黑影里窃窃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