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形而上学的功能与命运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207)
一 问题与界定
哲学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早就有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记载了泰勒斯凭星象学而赚钱的故事[1]34-35。故事中,世人和泰勒斯都承认了从有用即功能角度质疑哲学的合法性,而且这种功能跟当今的实用功能是相当甚至相同的,所以,从实用角度质疑哲学的合法性,古已有之。
但是,这个故事只能证明星象学有用,而不能有效证明哲学有用,因为古希腊的哲学所包括的内容远大于今天的哲学。因此,有必要对哲学作一个限定。本文所讨论的哲学特指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或哲学-形而上学,philosophy-metaphysics),不包括逻辑学,也不包括分析哲学、伦理学等。本文讨论的哲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第一哲学”;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则是那些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学术;更一般地讲,则是存在论(ontology)。出于方便,下文有时使用“形而上学”,有时使用“哲学-形而上学”来指称哲学-形而上学,而“哲学”则包括但不限于形而上学。另外,先借用下文的讨论,本文其实可以绕开哲学-形而上学,不直接以之为对象,而把对它的讨论转化为对全域命题的讨论。
形而上学在20世纪遭到了猛烈的批判,逻辑实证主义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认为形而上学是在说废话。虽然逻辑实证主义也有自身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要退回形而上学。只要形而上学无法表明其具体功能,它就无法获得存在合法性证明。其实,休谟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批评神学或经院哲学没有包含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也无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推论,只有诡辩和幻想[2]145。休谟的意思,也是认为形而上学只不过在说废话。
但是,形而上学为什么是废话,并未得到彻底的解释。相较于前人之论,本文的批判仍有独特性。本文的进步之处在于:本文从更基础的层面,用更简单、更可理解和更可辨明的方式证明了形而上学即便正确,也是废话。亦即:本文的创新不在观点上,而在论证方法上。(1)预设很低。本文不需要对形而上学的具体内容进行批判,而假定其正确性不容置疑。但是,运用归谬法,即便形而上学正确,它也不具备区分具体事物的功能,因而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2)论证方式简单。本文在功能角度,基于观念与方法的区分,通过证明形而上学只能提供关于全域的观念来证明其功能(极其有限且日渐衰竭),进而断定其命运(无法逃避灭亡)。(3)批判彻底。本文采取的是归谬法,是在承认形而上学正确性的基础上论证其功能与命运,因此论证强度很强。此外,本文不是文本研究,而是问题研究[3]。
为避免误解,需要强调:本文所说的“功能”以及“有用”与“无用”,其外延乃是对事物进行区分的功能,而远远大于世俗意义的实用价值(即大于质疑泰勒斯的人所认可的实用价值)。有用的必要条件是区分。此有两层含义。第一,一物(A)能区分的具体事物(即A的功能)不同于另一物(B)能区分的具体事物。若A与B能区分的具体事物相同,则二者实为同一物。第二,因为第一,所以,A与B本身即是不同的,能被区分(为不同的事物)。第二层含义是第一层含义的逻辑后承。例如,说刀是有用的,其必要条件是,刀能区分的具体事物(刀的功能,如能切菜,即能区分菜)与其他事物能区分的具体事物不同(如镜子能反光,即能区分不同事物的影像),这是第一层的区分。由此区分可知第二层区分,即刀与其他事物不同。但是,形而上学在第一层含义上就不能区分任何具体事物,不满足有用性的必要条件。一切实用价值都具有区分功能,但反之却不然。关于这一点,下文有具体展开。
本文持的是哲学-形而上学无用论,也是哲学-形而上学灭亡论,而哲学-形而上学无用论是哲学-形而上学灭亡论的根据。本文的论证思路为:在功能角度看,哲学-形而上学只能提供关于全域的观念,而不能作为方法,所以它不具备区分功能,即无法区分具体事物,也就不能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任何有效帮助,所以,哲学-形而上学无用;所以,它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
二 观念与方法的区分:判定哲学-形而上学命运的理论根据
观念与方法的区分,乃是讨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功能与命运的理论根据。
从能否有效区分事物的角度分类,一切理论都可以分为观念与方法①。一个理论由一个或多个命题构成。如果一个理论T针对一个问题Q,Q包括了许多具体的对象Q1,Q2……Qn,这些对象构成Q这个问题所针对的对象的集合,这些对象也就是元素,这个集合就可以用Q表示,并且T认为Q具有属性P。那么,观念与方法的区别是:如果T能给出的信息是Q中所有元素Qi具有P属性(这里称为“能描述集合”),但不能把Q中的这个元素(Qh)与那个元素(Qk)的属性作有效区分(这里称为“不能区分元素”),那么,T就是观念;如果T既能描述集合,又能区分元素,那么,T就是方法。这就是观念与方法在功能上的区别。简言之,观念的充要条件是能描述集合但不能区分元素,方法的充要条件是既能描述集合又能区分元素。观念可能在集合层次进行区分(即可能将一个集合与另一个集合进行区分),但不一定能在集合层次进行有效区分,如“鸟是动物”是对鸟这个集合的描述,但并不是对鸟与其他动物的有效区分。把理论二分为观念与方法,这样做的理由是:一个理论要么能区分元素,要么不能区分元素,二者不能兼容,而对一个理论能否区分元素,是可以明确有效地判定的,所以,对理论做观念与方法的二分是成立的。如果一个复合理论中既有观念也有方法,则将该复合理论视为方法。观念与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是,当用观念来描述对象时,会产生这种现象,对于不同的主词(被描述对象,即元素),所有谓词都是一样的,这可以形式化为:P(Q1)∧P(Q2)∧……∧P(Qn),因此无法区分Qh与Qk。P(Q1)的含义是“Q1是P”,其余类推。当用方法来描述对象时,则会产生这种现象,对于不同的主词,谓词一定在某些情况下有所不同;即便相同,那也是因为主词本来就是相同的,这可以形式化为:P1(Q1)∧P2(Q2)∧……∧Pn(Qn)∧(∃Ph∃Pk(Ph≠Pk)∨((Ph=Pk)→(Qh=Qk)))。例如,“人都是要死的”,这个理论就只是观念而不是方法,因为虽然任何人都是要死的,但是这个命题并不能把张三的死与李四的死有效区分开来。但是,“矩形的面积在公式S=ab(a代表长,b代表宽)中都是可解的”,这个理论就是方法。给出任意矩形,矩形面积公式都可以对之给出确切回答。因此,矩形面积公式能够区分Q中的这个元素(Qh)与那个元素(Qk)。
方法与观念还有一种重要不同:凡是方法,必定是观念。因为一切方法都对对象集合作出了无区分描述,再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元素作出区分性描述。譬如,“矩形的面积在公式S=ab中都是可解的”,本身也是观念。因此,方法的内涵完全包含且大于观念的内涵。
由于观念与方法具有不同的功能,致使二者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观念的重复使用,边际收益(即边际信息)一次性下降为零;而方法的重复使用,边际收益大于零。这里的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借用的是经济学概念。解决一切问题都有方法对于目标的有效性问题,所以都有成本与收益的问题。这对于理论亦然。一个理论显然有目标,并需要寻找有效方法,所以,任何理论都有成本与收益问题。对于理论来说,成本是创造、学习与使用理论的所有付出,而收益是获得的对事物的有效区分。理论对事物作出的有效区分就是它所提供的有效信息。也就是说,理论的收益就是它提供的有效信息,而理论的边际收益则是它提供的边际信息(下文交替使用边际收益与边际信息这两个概念)。对于一个不知道(或忘记了)某个观念的行为者(假定该观念正确),知道该观念显然是有用的,但是,行为者从第一次知道(即从不知道到知道)该观念到第二次重复使用该观念,他的边际收益一次性骤减为零。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观念,行为者只需要一次性地知道,而第二次重复使用该观念就无法再帮助行为者区分具体事物而获得收益,所以,第二次重复使用该观念所产生的边际信息为零。既然重复使用的边际收益为零,那么,即便边际成本再低,重复使用也没有价值可言。形象地说,对于一个观念(假定它正确),第一次说出时是真理,第二次说出便是废话。例如,“哺乳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人都是要死的”,对于这些观念,第一次知道,是知道了一个真理;而第二次重复,则是说废话。但是,方法的重复使用,可以不断帮助行为者区分具体事物,解决问题,所以,边际收益大于零。这种边际收益不是别的什么价值,就是行为者重复使用方法时,方法对具体事物进行了区分,从而帮助行为者作出判定。由于方法的重复使用的边际收益大于零,所以,对于行为者来说,方法对解决具体问题有切实帮助。甚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方法在后面的使用解决了比先前更重要的问题,后面的使用所产生的边际收益还可能大于先前的使用。同时,由于重复使用,对方法的掌握与使用越来越熟练,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
又由于观念与方法的使用价值不同,致使二者发生作用的条件不同。观念只有在不被知道的情况下才表现出其价值(即便该观念正确),一旦知道该观念对集合作出的描述后(从不知道到知道),该观念对解决具体问题就没有帮助,因为观念不能区分具体事物。但是,方法只有在被掌握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因为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用之区分具体事物。
但是,切不可把观念重复使用边际收益为零误解为观念没有价值。许多观念都有价值,如“哺乳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人都是要死的”。而对于一个有效的观念,如果它越能将它所判定的对象集合与其他集合相区分,即它提供的判定越具体、准确、针对,则它的价值越大。或者这样说,对于一个有效的观念,如果其谓词(即用来描述对象集合的语句)越是只适用于其主词(即对象集合),那么,该观念越有价值。例如,“鸟是能飞、有羽毛、有脊椎的动物”与“鸟是动物”相比,虽然两个观念都是有效的,但是,前者显然更具体、准确、针对,因为“能飞、有羽毛、有脊椎”显然更能将“鸟”这个集合与其他集合相区分,即更能将鸟与非鸟区分,而“鸟是动物”将鸟与非鸟相区分的程度就要低很多,因此后者的区分功能更弱,也就更少价值。正是因为观念越能将其所判定的对象集合与其他集合相区分,其价值越大,所以才需要学科分类,具体学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针对特定的对象集合(小于全域),寻找该对象集合尽可能准确的类本质,再进一步寻找区分集合中具体元素的方法。
关于观念与方法的区分的这个理论是一个二阶理论,也是一种方法,具有方法论价值。因为它能够有效判断一个理论究竟是观念还是方法,且有助于判断一个理论的有效程度。
对于本文来说,关于观念与方法的区分这个理论有两个直接帮助。(1)可以判定形而上学的功能以及相应的命运。形而上学只能提供关于全域的观念,而不能作为方法,所以,它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2)可以使上述判定达到无预设。因为完全可以承认哲学-形而上学理论完全正确,而只要明确它只能提供关于全域的观念,就可以判定其功能与命运。
三 哲学-形而上学只能提供观念而不能作为方法
哲学-形而上学自称其任务是探求万物的普遍本质。哲学-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探求本质呢?按照杜威的说法,人为了逃避危险,寻求安全,所以总是要寻找确定性。形而上学就是寻求确定性的一种特定的方法(杜威所言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认为,如果找到了万物的本质,就能把握万物,获得安全。所以,形而上学要寻找那个常住不变的本质。但是,在方法上,形而上学拒绝数学分析,拒绝实验,拒绝经验(经验主义认为知识源自经验,但这个二阶命题本身并不是经验的),试图通过冥思苦想获得本质[4]18-19。
不论杜威对形而上学要寻求确定性的解释是否合理,可以肯定的是,形而上学的任务是探求本质。并且,可以搁置形而上学找到那个本质的可能性,而假定它能找到,然后考察:那个本质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它是观念还是方法?
假设本质为P,P可以是一个命题,也可以是命题集;用x表示万物中的任意一个,x的论域为全域。由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存在者整体,也即万事万物,因而,形而上学所描述出来的本质是要适用于万事万物,其论域为全域,即这里的x。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所获得的本质,是以万事万物为主词的命题,在语法上表现为“万事万物是P”这个一般句式,也即x是P。例如,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的,万事万物都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演化等等,就是这样的全域命题,而形而上学的核心命题都是这样的命题。这又意味着,本文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其实可以转化为对全域命题的批判。全域命题的特征和功能也是形而上学核心命题的特征和功能,只要否定了全域命题的价值,也就否定了形而上学的价值。
因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命题是全域命题,所以,即便形而上学找到了本质P,P也只可能是观念而不可能是方法,那么,P根本不能区分万物,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与控制万物。试证明如下。
既然P是万物的本质,这就意味着,万物皆有属性P,用谓词逻辑表示,则为:∀xP(x)。显然,∀xP(x)不能区分任意x,P对任意x都是一样的。反之,如果P对某些x不一样,那么,至少有两个特指变项α与β的本质(分别用Pα与Pβ表示)不一样,那么,Pα与Pβ相异的属性Δ为非空集(即:(Pα∪Pβ)-(Pα∩Pβ)=Δ,Δ∈P,Δ≠φ)。这就意味着,Δ或者不是α的本质,或者不是β的本质。进而,P中有部分属性Δ不是任意x的本质,这与P是万物的本质这个假设相矛盾。所以,万物的本质无差别地适用于万物,即∀xP(x)不能区分任意x②。
根据上文关于观念与方法的区分,可以知道,即便哲学-形而上学找到了万物的本质,这个本质也只能是观念,只能对集合作出描述,而不能对集合中的元素作出区分。用日常的话说,形而上学完全不能说出具体的此物与彼物之不同。并且,由于形而上学从来就没有打算提供具体知识,而希望找到万物背后那个不变的本质,所以,形而上学只能提供观念而不能作为方法。根据前面对观念与方法的区分,形而上学所提供的本质,对人们来说,虽然并非无价值,但是,该本质不具有重复使用的价值,即该本质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一次性递减为零。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则是:形而上学完全不能给出具体事物的区别或不同,也不能对具体事物作出预测。而就形而上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看,形而上学的确只是提供了一些观念,而形而上学可能涉及的某些具体知识或经验知识,都不是形而上学自己提供的。
因为哲学-形而上学只能提供观念,并且以全域(或大全、万物)为对象,只能提供全域观念,如绝对观念(黑格尔)、纯粹先验意识(胡塞尔)、存在(海德格尔),具体学科则以小域为对象。所以,哲学-形而上学只能提供关于万事万物的全域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③。根据这个结论,就可以断定哲学-形而上学的功能以及与其功能相应的命运。
由于哲学-形而上学只能提供关于全域的观念,不能区分任何具体事物,即不具备有用性的必要条件,所以,它无法为生活中的任意具体事情提供任何实际帮助——这是很强的命题与结论。一切实际帮助,即便不能对需要处理的事情与其他事情作出完全准确的区分(或判定),也至少能作出一定程度的具体的、针对的区分。也就是说,一切实际帮助对于行为者来说,收益都必须大于零。虽然在描述集合时,哲学-形而上学所提供的观念可能提供一次性的新鲜信息,但除此而外,形而上学没有任何独特功能与价值。当重复使用那些观念时,边际收益骤减为零。也就是说,当要在元素层次上区分具体事物时,形而上学(所提供的观念)完全无能为力,完全不能区分具体事物。由此还可以引申,有效解释的必要条件是对被解释对象与其他对象作出或多或少的区分,所以,哲学-形而上学不可能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和具体事物作出任何有效解释。
哲学-形而上学似乎可以谈论整个世界、大海、森林,但对一粒尘埃、一滴水、一片树叶的具体性状无法给出任何解释以及预测,也无法对这粒尘埃与那粒尘埃、这滴水与那滴水、这片树叶与那片树叶作出区分。如果解释者能作出一定区分,其区分也是来自经验或具体学科提供的知识,而非来自哲学-形而上学(的训练)。例如,“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即便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对任意具体事物的运动作出具体说明,更不能帮助人们预测与控制具体事物的运动。而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一切事物是否都是运动的,而是人们所面对的某个具体事物是如何运动的,并通过知道或预测该具体事物的运动来控制该事物,以有利于人们的生活。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如当下构成)都不能对任意具体事物进行区分,因而都只是观念而不是方法。但是,逻辑、数学、物理学、化学,乃至很不精确的文学、艺术学等具体学科,都能够作为方法,对对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分。并且,如果这些学科对两个对象的描述是相同的,那就意味着,在该学科内,这两个对象本来就是相同的。例如,如果化学认为某两杯水的化学构成一样,那么,在化学中,这两杯水就是一样的。但是,哲学-形而上学却完全没有区分功能。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来理解全域观念完全没有区分功能,因而完全无效。假定从一些非全域观念的信息A(A是任意的)能够得出B,即:A→B,A加上全域观念(不管该全域观念是不是由哲学-形而上学提供的,中国文化中也有全域观念),仍然能并且只能得出B,不会增加或减少什么,此即:((A+全域观念)→B)=(A→B)。(这里用“=”比用“↔”更严格。)这意味着,加上或不加上全域观念,对于处理任何具体信息都没有用,因而全域观念完全无效。但是,A+小域观念,却可能得出多余或少于B的信息。因此,这里的论证只适合全域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形而上学号称解决根本问题,但其实它根本不解决问题。
四 哲学-形而上学没有具体且独特的公共功能
以上一小节为基础,本小节更有针对地讨论形而上学没有具体而独特的公共功能。
其实,并非只有形而上学才提供观念,许多学科都要规定其研究对象的类本质。许多时候,一个学科的假设就是观念。差别在于:(1)具体学科不仅仅提供观念,还可以提供某些方法,从而使具体学科具有独特的区分功能而具有独特价值,但是,形而上学只能提供关于全域的观念,不能区分任何具体事物(不具备有用性的必要条件),这使它没有任何独特价值。(2)具体学科既具有私人功能,也具有独特的公共功能,但是,即便形而上学具有某种功能,也只具有非独特的私人功能。(2)与(1)直接相关,是(1)的逻辑后承。下面,对(2)展开讨论。
先对私人功能与公共功能作区分。私人功能是指对某个行为者有效的功能,即让某个行为者感觉到他获得某种收益的功能;公共功能是指针对不同行为者(至少两个)有效的功能,即让不同行为者都感觉到他们获得某种收益的功能,并且他们获得的收益是可以相互理解与交流的。私人功能与公共功能不是二元对立的,公共功能就是可以公共化的私人功能。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具有私人功能,才能成为公共功能,所以,一种功能可以同时是私人功能与公共功能。不过,当谈论私人功能时,不需要考虑公共交往。只有在公共交往中,谈论公共功能才有意义。
具体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区分功能不仅针对研究者有效,让他觉得他从具体学科中获得某种收益,如果其他人经过一定的训练,则这种区分功能对他人也有效。所以,具体学科的区分功能既是私人功能,也是公共功能。同时,具体学科的公共功能都有独特性。即便不精确的文学、艺术学(不是艺术活动),不同行为者也可以利用它解决一些问题,其功能也各具独特性,如美术可以通过视觉使人获得审美体验,音乐可以通过听觉使人获得审美体验。至于其他更有确定性的活动(如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等的活动),其公共功能更加独特而明确。但是,由于哲学-形而上学只能提供关于全域的观念,在元素层次上没有区分功能,所以,它不可能具有公共功能。而只要形而上学不具备公共功能,它就不可能改造现实,也就不可能具有海德格尔所期许的功能——“我们讨论的一切问题,海德格尔补充说,将对当今现实产生作用”[5]。海德格尔的话说明了他希望并相信他的哲学具有改变现实的功能。但是,对现实的一切改变都必须以对现实进行有效区分为前提,所以,实际上,他的哲学(以及所有形而上学)没有这种功能。所以,海德格尔永远不能实现他的理想。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不把哲学-形而上学视作一个学科,而是作为个体活动,对于形而上学工作者又有无私人功能呢?答曰:可能有,但这种私人功能不是独特的,其可替代性很高。当然可以说,形而上学家在形而上学研究中可以获得精神满足,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所从事的活动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只要他自得其乐。从一个活动中获得精神满足,可以不考虑该活动是否能为他人提供有益的东西,也可以不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仅仅依赖于自我评价与自我感觉。一个人可以在数星星中获得精神满足,而这样的行为,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显然是极其枯燥无聊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具有私人功能,但并非一切活动都具有公共功能。所以,虽然形而上学能够给形而上学家带来精神满足,但这种满足并不是它的独特功能,我们无法根据它的这一功能将形而上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
或许又有人会为形而上学的私人功能辩护,认为形而上学带给人的是思想体验,是思想上的自我满足,而艺术、宗教等不是。但是,什么算是思想体验呢?凭什么不能说进行艺术欣赏与创作的行为者的想法也是思想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件艺术品很有思想(内涵)”这样的说法。如果一种思想不具备区分功能,这种思想算是一种有效的思想吗?甚至,它还算是思想吗?形而上学活动与其说给人带来思想体验,不如说仅仅是无价值的胡思乱想。形而上学可以给人带来精神满足,但这只是私人的满足,而无法转化为公共的满足,即无法从私人功能转化为公共功能。但是,文学、艺术等活动不但可以给不同行为者带来具有公共性(即可以相互理解与交流)的满足,即具有公共功能,并且其公共功能是独特的④。
具体学科具有公共功能,是从它可以作为方法这一特征推论出来的,而哲学-形而上学不具有公共功能,也是从它只能提供观念这一特征推论出来的,所以,以上对(2)的讨论,不但证明了形而上学最多具有私人功能,而具体学科兼具私人功能与独特的公共功能,并且证明了(2)是(1)的逻辑后承。
形而上学家在表达其形而上学思想时,有时运用了概念推理,如分析风格较浓的康德对概念推理的运用较多(黑格尔的所谓“思辨”,根本不具有严格性与预测性,其“逻辑学”根本算不上逻辑),这对于读者来说,有助于训练概念推理能力。但是,其一,概念推理不是形而上学的独特功能,许多学科都在运用概念推理,并且现代数学、逻辑等推理方式日益发达,以及结合数学与逻辑的概念推理也日益发达,使得形而上学的概念推理能力在所有推理能力中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小。其二,由于哲学-形而上学主要以全域为对象探求本质,越来越难找到新的问题与对象,从而使它提供新的推理的能力越来越弱(参见下文)。二者相结合,使概念推理并不构成形而上学的独特优势,不但可替代品很多,并且许多替代品优于形而上学。不过,尽管形而上学在概念推理上没有独特优势,但将历史上的形而上学文本作为训练概念推理能力的一种教材未尝没有价值,这也许是形而上学唯一的价值了。可惜,许多哲学工作者(尤其是我所知的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看重的却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推理,使得形而上学的唯一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
五 几个加强讨论
(一)哲学-形而上学与智慧何干?
哲学-形而上学标榜爱智慧。如果在“爱”上讲,哪个学科不认为自己是爱智慧的呢?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区分,就没有智慧。
那么,形而上学有智慧吗?——近乎没有,并且越来越不能产生智慧。
几千年来,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些关于万物(全域)的观念。对于全域,只能在内涵角度描述,形成“万物皆有y(属性)”这样的命题,如“万物皆动”,“万物皆有生有灭”,因为在外延角度描述“全域是(属于)X”,X只能等于全域,所以,这个命题要么是同义反复,要么是错的。并且,对全域的内涵的描述,不能通过数学、逻辑、实验、调查、实践等方法获得,而只能通过所谓的“直观”而获得。而验证关于全域的直观命题的方法,就是举反例。如果举不出反例,就可以说该直观命题是正确的(或有效的),如“万物皆有生有灭”。
对全域属性的描述,不能使用具有区分功能的副词、形容词等,一旦使用,就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命题。因为一旦对属性作了区分,这个属性就不能无差别地适用于万物,就不是万物的本质。具体证明如下。

上述证明意味着,只有没有被限定的谓词才可以描述全域。迄今为止,形而上学对全域的有效描述已经穷尽了。这个结论增加了“有效”这个限定,其意义何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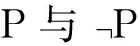
如果某理论P为真,事物S为真(或假),并且当P变为假时,事物S也相应变为假(或真),则P对于S有明确影响,则P对于S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或简言之,P是具有有效性的理论。具有有效性的理论不只有方法,许多观念也有有效性,只不过不同观念的有效性不同,而关于小域的观念较容易具有很明确的有效性。例如,如果矩形面积等于长乘以宽,则长为20米、宽为10米的矩形的面积等于200平方米;如果矩形面积不等于长乘以宽,则长为20米、宽为10米的矩形的面积不一定等于200平方米。这是方法有效性的例子。如果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并且狗是哺乳动物,则狗是脊椎动物;如果哺乳动物不是脊椎动物,并且狗是哺乳动物,则狗不是脊椎动物。这是观念有效性的例子。
除去错误与无效的观念,形而上学还能提供多少有效的观念(即未必证伪的观念)呢?——不能了。若此,形而上学无法再产生智慧。
(二)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关于形而上学没有区分功能,无法提供任何具体有效的信息,还可以换一种很容易操作的方法,用一个简要的公式来作强化证明。
公式:“如果p,那么q”。这是条件句的基本形式。这一公式的含义是:如果一个命题是有效的,那么,或者可以从它推出有效的命题(q),或者它可以从其他命题(p)推出来。
给出一组命题:
(1)世界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演化。
(2)世界是纯粹先验意识的产物。
(3)世界是理念的产物。
(4)世界是精神的,其他一切都是从精神派生出来的。
(5)事物的呈现是非现成的。
(6)人都是要死的。
(7)矩形面积等于长乘以宽。
(8)一个人的财富与其身高成正相关关系。
若在“如果p,那么q”这一句式中分别代入上面的命题,则有两种代入方式:(a)若这些命题放在p位置,可以推出q该是什么?(b)若这些命题放在q位置,可以反推出p该是什么?通过(a)(b)两种代入,可以判断被代入命题是否有效。对于(a)(b)两种代入,只要有一种代入可以得出有效命题,则被代入命题就是有效命题。
代入命题(1),那么q该是什么呢?或许可以说,任意x(如苹果、法律)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演化,这种推论毫无意义,不能区分任何具体事物,即不具备有用性的必要条件(前文已论)。或者反过来:如果p,那么(1),试问p该是什么呢?命题(1)的主词“世界”乃是全域,这种命题不可能再从其他命题推出来,除了同义反复。所以,从“世界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演化”这一命题得不出任何有效的命题,也无法从其他任何有效的命题得出“世界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演化”。因此,“世界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演化”这一命题是无效命题,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命题(2)-(5)的主词和(1)一样,都是全域,都是无效命题。
代入命题(6),可得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命题(6)的主词是“人”,是小域,而不是全域,故此种命题也有一定价值(前文已论)。
代入命题(7),可得出:长为20米、宽为10米的矩形的面积等于200平方米。
代入命题(8),可得出:甲高180厘米,乙高170厘米,那么,甲的财富比乙多。但是,可以发现,经常出现甲比乙高,其财富却比乙少。这意味着,命题(8)是错误的。这意味着,命题(8)的有效性是可验证的,但(1)-(5)这样的形而上学命题根本不可验证。
虽然以全域为对象的命题并非全无意义(如“万物皆有生有灭”,但即便有,也很小,边际收益一次递减为零),但(1)-(5)这样的命题,作为某些哲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却根本不能为人们提供有效信息。
(三)对苏德超的简要批评
对于苏德超《哲学无用论为什么是错的?》一文[6],我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苏德超没有限定哲学的范围,致使讨论对象模糊。哲学中的伦理学、语言哲学等是有用的。准确说,凡是能构成区分的,都有或多或少的经验功能。我的文章将讨论对象限定为哲学-形而上学。由于讨论对象不同,所以,我和苏德超的观点的差异完全不构成分歧或冲突。苏德超应该回答:哲学-形而上学是否有用?
第二,苏德超说哲学具有澄清观念这样的思维训练功能,这没有问题。但是,学术、思想也有竞争。根据竞争原理可知,“高级的东西(产品、知识、工具、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可以让低级的东西衰落,甚至报废”[7],如果人类发展出了更高级的思维训练方法,哲学-形而上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苏德超只能证明哲学-形而上学在过去有思维训练价值,而不能证明它今天和未来还有。
第三,苏德超认为哲学能够建构人生意义,其实非也。人生意义必须来源于一些确定的信念,但哲学的不断反思和探究总是要质疑甚至摧毁这些信念。真正为人生意义提供信念支持的,是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属于道德教育的一种形式)。
第四,苏德超认为哲学能捍卫自由,这并不可靠。根据他的逻辑,哲学是通过澄清观念和建构意义来捍卫自由的,但因哲学无法建构意义,所以很难捍卫自由。从历史看,自由和反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背后都有各自的哲学理论。这意味着,哲学与自由没有必然关系。
所以,苏德超的论文或许可以论证哲学的非形而上学部分具有价值,但对于哲学-形而上学的价值的论证,该文是失败的,或者说是阙失的。
六 结论:哲学-形而上学无法逃避的命运
对于有几千年历史的哲学-形而上学来说,证明它的灭亡,的确是令人哀惋的事。但是,哲学-形而上学既然宣称自己具有批判精神,那它就应该面对问题本身,对自己也保持批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哲学-形而上学文本毫无价值。过去所产生的哲学-形而上学永远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并且有些好的哲学-形而上学著作仍可作为训练概念推理的教材。但是,由于哲学-形而上学只能提供观念,无法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任何帮助,同时哲学-形而上学几乎无法产生新的有效观念了,二者相结合,就决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未来命运(灭亡)。
注释:
①有人质疑我对“观念”与“方法”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否合乎常规,其实,这并不重要。虽然人们对“观念”与“方法”的使用并无明确、固定的区分,但本文的区分大致是符合通常的使用习惯的。这里将之约定并明确化。
②维也纳学派说“存在”不能作为谓词,正是因为“存在”不具有区分功能,无差别地适用于万物,根本不能向人们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所有表达全域的概念都不能作为谓词。其实,在使用而非提及的意义上,“存在”不但不能作为谓词,且不能作为主词。因为,若说“存在是x”,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恰当的x,使该命题是有效的。如果x等于存在,那么,该命题是同义反复;如果x小于存在,那么,该命题是错的;如果x大于存在,该命题也是错的。由于“存在”既不能作为谓词也不能作为主词,还可以得出有效理论的必要条件:面对有限的问题,从有限的前提出发,经过有限的论证,得出有限的结论。在四个环节的任一环节使用了无限,该理论都是无效的。无限包括存在、理念、绝对观念、万事万物,以及中国的道,等等。此四个有限,犹如“奥康的剃刀”,可以剔除许多无效理论,可让人们少走许多弯路,少做许多无用功。但是,满足四个有限的理论未必是有效的。在此四个有限的基础上,一个好的理论还应尽可能追求论证过程与结论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③若以提供全域观念为形而上学的标准,那么,中国古代也是有形而上学的。例如,老子的“道”,朱熹的“太极”,也是全域观念。而这些观念也是无效和无用的。
④对形而上学是否有独特功能,还有一种辩护是:形而上学提供的是整体感。但是,第一,宗教也可以提供整体感,甚至文学也可以通过描述整体而提供整体感。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形而上学要提供整体感,只需要一种哲学(形而上学)就足够了(如黑格尔的世界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演化),让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整体感。如果形而上学不断自我批判,用一种整体理论批判另一种整体理论,反而会打破人们的整体感,增加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