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价值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本文所谓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指的是俄藏本Ф-242a(L.1452,以下称“俄藏本”)和法藏本P.4884、P.2707、P.2543(以下称“法藏本”)四截残卷。俄藏本从今六十卷本《文选》卷十九束广微(晳)《补亡诗六首》起,到卷二十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一首》止,包括“诗甲”类“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四种。计有束广微(晳)《补亡诗六首》、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诗一首》、张茂先(华)《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共五篇。俄藏本有注。这里所讨论的是其中的韦孟《讽谏诗》的诗序和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曹植此表,又载于《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虽名为“表”,但萧统并未将其归入“表”类,而是放在“诗”类曹子建《责躬诗一首》前面。其内容为曹植奉诏上疏作《责躬诗》《应诏诗》的缘由和内心情感,与二诗密不可分,实为诗序①。丁晏《曹集铨评》说:“表以献诗,正一时事也。”[1]270《文心雕龙·章表》篇也称“表以陈请”,又说“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理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2]406-407,故本文将其归为诗学文献。法藏本为今六十卷本《文选》卷四十六“序下”颜延之和王融两篇同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法藏本无注。这四截敦煌写本《文选》卷子,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有录,本文所用即据此本。
一 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著录
法藏本的情况,据王重民考证:“甲卷著录号码为二七〇七,仅存九行,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乙卷为二五四三,存五十四行,亦《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起‘用能免群生于汤火’,讫《王文宪文集序》开端两行”[3]319-320。王重民还将法藏本与今本《文选》的异文罗列出来,嘉惠学林,功不可没。王立群的《敦煌白文无注本〈文选〉与宋刻〈文选〉》一文也涉及到法藏本王元长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异文。本文的考论即在此基础上展开。
饶宗颐见到的法藏本P.4884包括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和王元长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此截“白文无注。颜序得四行,起‘〔币筵禀〕和,阖堂衣(依)德’句;而第一行‘情磐景遽,欢洽日斜,金驾总驷’句,‘情磐景’缺去右半边,下缺八字,‘驷’字在第二行。王序得五行,首二行完整,而第三至第五行缺去上半截八至十字。止于‘固不与万民〔共也〕’句”[4]4。饶宗颐所得见的法藏P.2707承接法藏P.4884而来,比王重民所录多了一行,“惟第十行仅见‘忘餐念’三字之右半边,而缺去‘私法含弘而不杀,具明废寝昃晷’数字”[4]4。
俄藏本Ф-242a(L.1452)的情况由俄国汉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孟列夫)主编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以下简称“《叙录》”)所载:
《文选》。
手卷,368×28,首尾缺。9纸。纸色白,纸质薄。两面均有经文:
(1)185行,每行13字。画行很细。楷书大字,有小字双行注释,捺笔画粗,笔道苍劲有力。分卷法及释文与《四部备要》不相符。据狩野直喜判断,这是以前佚失的释文。(参看狩野直喜著《论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藏〈文选〉古写卷残卷》,《科学院通报》,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分院,1930年第2期第135—144页)。题字佚失,仅有经典标题。经典从[《补亡诗》]起,束广微著,第6首,到《上责躬应诏诗表》,曹子建著。注明日期7—8世纪,不早于630年,(李世民登位时间,因为把“民”字写成“”字),不迟于718年(5位作者做注释的时间)。从“其性从仪明明后辟言有明明之德后辟君仁以为政言仁”,到“召齿录至止之日言使至□[驰心辇毂]谓天子□□□”。[5]577-578
今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第35页至第46页俄藏(L.1452)敦煌写本《文选》影印照片如《叙录》,但偶有行14字者,如韦孟《讽谏诗》“穆天子临照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4]41、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诚以天罔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4]45。
饶宗颐说:“开元时,《文选》且为赏赍外蕃之秘笈,《旧唐书》一九六《吐蕃传》云:‘(开元)十八年十月,名悉猎等至京师,悉腊颇晓书记,时吐蕃使奏云:(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疏奏不省。’而《唐会要》三六云:‘开元十九年赐金城公主书,内有《文选》。’”[4]17-18但俄藏和法藏敦煌写本《文选》可能比这个时间更早由中原传入西域(详后)。李善注完成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五臣注完成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西域使者为全城公主求赐《文选》的开元十八年(730)、十九年(731),时隔李善注完成73年、五臣注完成13年。按道理说,“赐金城公主书”内的《文选》似乎应该用李善注或五臣注,但今俄藏L.1452敦煌写本《文选》中的注释与今本李善注和五臣注不同。法藏P.4884、P.2707、P.2543为白文无注本。于此可见,敦煌写本《文选》中的这四截诗学文献的来源恐属于另外一个系统。
二 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价值
俄藏和法藏敦煌写本《文选》中的诗学文献与今存《文选》无论是原文还是注释均有出入。今用韩国奎章阁本《文选》(以下简称“奎章阁本”)②为底本,通校此四截俄藏和法藏敦煌写本残卷,参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的《宋尤袤刻本文选》(以下简称“尤刻本”)、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的胡克家重刻尤刻本《文选》(以下简称“胡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周勋初纂辑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以下简称“《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以下简称“六家本”)、中华书局2012年据《四部丛刊》本影印的《六臣注文选》(以下简称“六臣本”)和江苏凤凰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的刘跃进著、徐华校《文选旧注辑存》(以下简称“《辑存》”)。由此可以看出,俄藏和法藏敦煌写本《文选》中的诗学文献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以下举例证之③。
(一)补充注释原文
1.卷十九“诗甲·述德”类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
(1)述德[6]460
无注。尤刻本、胡刻本、六家本、六臣本、《辑存》同。俄藏本注曰:“前言孝子之养亲,此言述祖之有如此德,亦言孝也。宋永嘉太守,曾祖安,祖玄,破(扶)[苻]坚贼,大有功勋,得七州(刾)[刺]史。”[4]35《辑存》敦煌本同俄藏本。案:俄藏本所谓“前言孝子之养亲”,指的是“诗甲”首篇“补亡”类束广微(皙)《补亡诗六首》中的《南陔》和《白华》。这两首诗的序说,“《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絜白也”[7]3690,3697。
2.卷二十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
(1)献诗[6]466
无注。尤刻本、胡刻本、六家本、六臣本、《辑存》同。俄藏本注曰:“献天子之诗。”[4]45《辑存》敦煌本同俄藏本。
(2)舍罪责功者[6]467
无注。尤刻本、胡刻本、六家本、六臣本、《辑存》同。俄藏本注曰:“责,取也。舍罪戾责取其功勋也。”[4]46《辑存》敦煌本、刘明《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校释》下“取”字作“收”[7]3795[8]。案:俄藏本是。《辑存》敦煌本、刘文恐误。该字似为“取”字。“取”因漫漶而缺笔,右边作“又”,非作“攵”,如作“收”,恐至文意不明。
(二)补充李善注和五臣注
1.卷十九“诗甲·述德”类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
(1)谢灵运[6]460
张铣注:“沈约《宋书》云:‘谢灵运,陈郡人也。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及。初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后为临川郡太守。’述其祖谢安、谢玄之德。后为有司所纠,徙广州。有诏斩于广州市。”李善注:“为有司所纠,徙封广州。遂令赵钦等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纂取谢,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罚。诏于广州弃市。”六家本同。六臣本“张铣曰”作“铣同善注。述其祖谢安、谢玄之德”。六臣本、尤刻本、胡刻本李善注“为”上有“沈约《宋书》曰”至“诏于广州行弃市刑”数句。俄藏本注曰:“为败苻坚等,故作此诗。丘渊之《新集录》曰:‘灵运,陈郡阳夏人。祖玄,车骑将军。父渔,秘书监。灵运历秘书监、侍中、临川内史。〔以罪〕伏诛。’谢灵运,字灵运,陈郡〔阳〕夏人,小名客儿。晋世以仕,至宋时为侍中。初为永嘉太守,非其意,乃归(会)稽。〔会〕稽太守孟顗譛之反。运乃驰入京,自理得免。乃迁之为临川内史,(祑)[秩]中二千石。于临川,取晋之疏从子弟养之,意欲兴晋。后事发,徙居广州,于广州犯事,被煞。其人性好急躁麄疏。曾谓孟顗云:‘若(生)[升]天,在运前;若作佛,在运后。’顗问:‘何谓?’运对曰:‘丈人蔬食好善,故(生)[升]天在前。作佛须智慧,丈人故在运后。’因此,孟顗遂致恨之。孟顗是运之丈人。灵运作诗,意述其祖德。其祖玄有功于晋,曾祖安亦有功于晋世。父名奂,本作□,一人。”[4]35《辑存》敦煌本同俄藏本,惟“渊”作“渆”,“若生天”之“若”字作“君”。案:“渊”、“渆”,古同。“若”作“君”,恐误。此当为“若”字,正与下一“若作佛”之“若”字对照。《宋书》卷八十一《顾琛传》附《丘渊之传》曰:“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也。太祖从高祖北伐,留彭城,为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渊之为长史。太祖即位,以旧恩历显官,侍中,都官尚书。卒于太常,追赠光禄大夫。”[9]2078-2079《世说新语·言语》篇“谢灵运好戴曲柄笠”条,注引丘渊之《新集录》同俄藏本引而微殊。如“渔”作“涣”,上“秘书监”作“秘书郎”,“伏诛”前有“以罪”二字[10]159。《宋书·谢灵运传》“涣”作“瑍”,上“秘书监”作“秘书郎”。据此,俄藏本恐误“涣”为“渔”,误“郎”为“监”。涣、瑍、奂、□,一人,为谢灵运父名。丘渊之与谢灵运同时,其《新集录》所录谢灵运与孟顗事当为可信。“杀”,俗作“煞”。《广韵·黠韵第十四》:“杀,杀命。《说文》:‘戮也。’煞,俗。”[11]491“丈人”,年长者尊称。梁章钜《称谓录》卷三十二《尊称》“丈人”条,曰:“《易》‘师,贞丈人吉’。注:‘丈人,严庄之称’。《论语》‘遇丈人’。皇〔侃〕《疏》:‘丈人者,长宿之称也。’《吕览·异宝》‘见一丈人’注:‘丈人,长老称也。’”[12]404-405
2.卷十九“诗甲·劝励”韦孟《讽谏一首》
(1)劝励[6]461
李善注:“劝者,进善之名。励者,勖己之称。”尤刻本、胡刻本、六家本、六臣本李善注、《辑存》同。俄藏本注:“劝励,谓劝励取用贤相意也。”[4]38《辑存》敦煌本同俄藏本。
(2)韦孟[6]462
张铣注:“《汉书》曰:‘韦孟,彭城人也。为楚元王傅也。’”李善注:“《汉书》曰:‘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尤刻本、胡刻本、六家本、六臣本李善注、《辑存》同。俄藏本注曰:“韦孟,彭城人。汉玄成五世祖。”[4]38《辑存》敦煌本同。
3.卷二十“诗甲·献诗”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
(1)曹子建[6]466
李周翰注:“植尝与杨修、应玚等饮酒,醉,走马于司禁门。文帝即位,念其旧事,徙封鄄城侯。后求见帝,帝责之,置西馆,未许朝,故子建献此诗也。”《辑存》陈八郎本、六家本、六臣本李周翰注同。胡刻本、尤刻本、六家本、六臣本、《辑存》同奎章阁本,“曹子建”下无李善注。俄藏本注曰:“曹子建名植。武帝时依铜雀台诗门、司马门禁,于时御史大夫中谒者灌均奏之,遂不(在)[恠]。后文帝即位,念其旧事,乃封临(□)[淄]侯。又为鄄城侯。唯与老臣廾许人,后太后过追之。入朝,至関,乃将单马,向清河公主家求见。帝使人()[逆]之,不得,恐其自死。后至,帝置之西馆,未许之朝,故遣献此诗。太后谓皇后,清河公主遣之。”[4]45《辑存》敦煌本“”作“淄”,“”作“轻”,“”作“逆”。案:“”是“淄”的别体。《龙龛手镜·水部》:“,,或作淄,今侧持反。水名,州名。”[13]228“関”,《辑存》敦煌本同。刘明释读为“阙”[8],恐误。“関”,今简体作“关”。《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略》曰:“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官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服王服。”[14]564
(2)臣自抱釁归蕃,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6]467
吕向注:“釁,罪也。蕃,鄄城也。刻肌刻骨,湥自诫也。”张铣注:“戾,恶也。昼分,日中时也;夜分,夜半时也。寝,卧也。”李善注:“《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师,后归本国。’而《魏志》不载,盖《魏志》略也。杜预《左氏传》注曰:‘釁,瑕隙也。’贾逵《国语》注曰:‘釁,兆也。’谓罪萌兆也。《孝经钩命决》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尔雅》曰:‘戾,罪也。’《韩子》曰:‘卫灵公至濮水,夜分,闻有鼓琴者。’”六家本、六臣本同。尤刻本、胡刻本、《辑存》、俄藏本“釁”作“舋”,李善注同。俄藏本注曰:“舋,罪也。按杜预《左氏传》注云:‘舋,瑕也。’归藩,谓为临()[淄]侯也。肌,(宍)[肉]也。戾,恶也。昼分而曰午也,夜分,夜半。”[4]45案:“舋”即“釁”之变体。《龙龛手镜·興部》:“舋,变体。釁,正。许靳反。罪也。又瑕隙也,动也,远也。古作衅。”[13]203“”,已见前。
(三)辩证讹误,以补校勘
1.卷十九“诗甲·劝励”类韦孟《讽谏一首》序
(1)孟为元王傅善本作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诗讽谏善本有曰字[6]462
吕延济注曰:“元王,高祖少弟也。薨。子郢客嗣,是为夷王。薨。子戊嗣。戊与七国同反,故无谥号。”李善注曰:“《汉书》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立交为楚王。薨。子郢客嗣,是为夷王。薨。子戊嗣。’”六臣本李善注同。吕延济注无“元王高祖少弟也薨子郢客嗣是为夷王薨子戊嗣”二十字。六家本吕延济注同,李善注作“善同济注”。胡刻本、尤刻本、《辑存》、俄藏本“傅”下有“傅”字,“谏”下有“曰”字。案:俄藏本释文分段不同,于“孟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下分三处注。曰:“元王,汉高祖弟,名文由。谥曰元。于《谥法》:‘始建都国曰元。’谓初都彭城”;“元王次子名郢客,享四年。。谥曰夷。《谥法》云:‘静以安众曰夷。’”“戊,郢客之子名。无谥。所以无者,戊与七国连反,所以不谥也”[4]38。《辑存》敦煌本“四”作“国”。疑误。《汉书》卷十四《诸侯王年表第二·楚元王交》云:“孝文二年,夷王郢客嗣。四年薨。”[15]397相比而言,俄藏本释文断句不同,且意思更加明白,如言郢客为“次子”,两引《谥法》释“元王”和“夷王”,分别言元王、夷王及子之名等。《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曰:“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颜师古曰:“官为楚王傅而历相三王也。”[15]3101
2.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1)方且排凤阙以高游,开爵园而广宴[6]1121
六家本、六臣本、《集注》、胡刻本、尤刻本、《辑存》同。法藏本“方”下无“且”字。《辑存》刘跃进案曰:“敦煌本无‘且’字。”[7]9153案:疑法藏本是。此文为骈文,六朝骈文,讲求对仗,前两句为“怅钓台之未临,慨酆宫之不县”。“且”为递进之词,若作“方且”,有拖沓之嫌,阻碍文气。古“方”字、“且”字多单用,少有“方且”连用之例[16]32,309。
(2)并命在位,展诗登善本作发字志[6]1121
六臣本、六家本同。法藏本、《集注》、尤刻本、胡刻本、《辑存》“登”作“发”。案:疑作“发”是。奎章阁本、六家本、六臣本误。《周易·豊卦》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孔颖达《正义》曰:“信以发志者,虽处幽暗而不为邪,是有信以发其丰大之志,故得吉也。”[17]68《集注》引陆善经曰:“展,陈也。”[18]773
3.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1)逍遥襄城之域[6]1121
胡刻本、尤刻本、六家本、六臣本、《集注》、《辑存》同。法藏本“域”作“埜”。《辑存》刘跃进案曰:“域,敦煌本作‘埜’。”[7]9159案:法藏本作“埜”是。各本皆误。域,即“或”字,古指邦国。《说文解字·戈部》:“或,邦也。从□。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曰:“《邑部》曰:‘邦者,国也’。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域即或。”又曰:“既从□从一矣,又从土,是为后起之俗字。”[19]637又依李善注引《庄子》“〔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20]647,作“埜”是。“埜”,同“野”。
(2)雷风通饗[6]1122
六臣本、六家本、尤刻本、胡刻本、《辑存》同。饗,《集注》作“響”,法藏本作“嚮”。《辑存》刘跃进案曰:“饗,集注本、九条本、北宋本作‘響’,敦煌本作‘嚮’。”[7]9163案:法藏本是,作“饗”误。“嚮”、“響”,古通用,谓響应。《汉书·张释之传》“疾于景嚮”,颜师古注曰:“嚮读曰響。”[15]2309《说文·音部》曰:“響,声也。从音。乡声。”段玉裁注曰:“浑言之也。《天文志》曰:‘郷之应声。’析言之也。郷者,假借字。按《玉篇》曰:‘響,应声也。’”[19]102-103又《食部》曰:“飨,郷人饮酒也。从郷。从食。郷亦声”段玉裁注曰:“郷、食,会意。”[19]223
(3)泽普泛善本作氾字而无私[6]1123
胡刻本、尤刻本、六家本、六臣本、《集注》“泛”作“汜”。《辑存》作“氾”,法藏本作“汎”。案:法藏本作“汎”是。“氾”与“汎”同。余本作“泛”、“汜”皆误。《说文·水部》曰:“汜,水别复入水也。从水。巳声。”段玉裁注曰:“上水字衍文。《召南》传曰:‘决复入水也。’谓既决而复入之水也,自其水出而不复入者。”[19]558又《水部》曰:“泛,浮也。从水。声。”段玉裁注曰:“《邶风》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上‘汎’谓汎汎,浮皃也。下‘汎’当作‘泛’,浮也。汎、泛古同音,而字有区别如此。《左传·僖十三年》‘汎舟之役’,亦当作‘泛’。”[19]561又《水部》曰:“汎,浮皃。从水。凡声。”段玉裁曰:“皃,当作‘也’。《邶风》‘汎彼栢舟’,毛曰:‘汎,流貌。’《广雅》曰:‘汎汎、氾氾,浮也。’”[19]553又《水部》曰:“氾,滥也。”段玉裁注曰:“玄应引此,下有‘谓普博也’四字。《楚辞·卜居》‘将氾氾若水中之凫乎’,王逸云:‘氾氾,普爱众也。若水中之凫,群戏游也。’《论语》‘汎爱众’。此假汎为氾。”[19]554法藏本“汎”字正是假“汎”为“氾”,意谓齐王恩泽惠施,普爱众生也。
(4)奇翰善本作幹善芳之赋[6]1126
刘良注曰:“善芳,远国异鸟名。”李善注曰:“《周书》曰:‘成王时贡奇幹善芳者,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鸟名。不昧,不忘也。’”六家本、六臣本同奎章阁本。胡刻本、尤刻本、《集注》、《辑存》“奇翰”作“奇幹”。刘跃进案曰:“善芳,敦煌本作‘菁茅’。”[7]9196法藏本作“奇幹菁茅”。《集注》引〔李善〕曰:“文□□□。一曰云奇幹。则钺当越。”又《集注》引(□□)[《钞》曰]:“菁茅当为‘〔善〕芳’字之误也。善芳,鸟名。今言之赋,则鸟非赋物,菁〔茅,善芳〕,二途尚疑,请俟明者也。”[18]824案:依李善注和孔晁注,胡刻本、尤刻本、《集注》、《辑存》、法藏本作“奇幹”是。又法藏本“善芳”作“菁茅”,疑是。《集注》引疑似《文选钞》言,则一本“善芳”作“菁茅”,与法藏本同。菁茅为贡物。《尚书·禹贡》曰:“匦菁茅。”孔安国曰:“匦,匣也。菁以为菹,茅以缩酒。”[17]149《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责楚曰:“尔贡包茅不入。”杜预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17]1793
(5)于时青鸟司开[6]1127
胡刻本、尤刻本、六家本、六臣本、《集注》、《辑存》同。法藏本“司开”作“司关”。案:法藏本是。余本皆误。《周礼·地官·司徒》曰:“司关,上士二人。”郑玄注曰:“关,界上之门。”贾公彦疏曰:“此司关亦是总检校十二关,所司在国内。”[17]699又《地官·司关》曰:“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郑玄注曰:“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自外来者,则案其节输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17]739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俄藏本的注释较之李善注与五臣注,兼有二者之长。李善号为“书簏”,注释体例以征引为主,注重典实训诂,但凡所征引仅出书名,不为章句;五臣解义,却又失之以粗疏。俄藏本既注明出处,又解释字义和句意,使文句意思更通畅,读者更有所获。例如上面举到的“补充注释原文”的第一个例子,俄藏本所谓“前言孝子之养亲”,指的是“诗甲”首篇束皙的《补亡诗六首》中的《南陔》和《白华》的诗序,而“此言述祖之有如此德。亦言孝也”,说的是谢灵运《述祖德诗》的内容。“亦言孝也”,表明前后相续,上下勾连,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昭明太子和“东宫十学士”编辑《文选》的用心。法藏本白文与今本《文选》偶有差异,相比之下,法藏本更接近《文选》原文,如上举“方且”作“且”、“普泛”作“普汎”、“善芳”作“菁茅”、“司开”作“司关”等。因此,敦煌写本中的这几篇诗序,无论是有注的俄藏本还是无注的法藏本,它们在研究今本《文选》的版本和考订文句上很有价值,既可以补充解释今本《文选》的正文,校正今本《文选》的某些讹误,也可以补充今本《文选》的李善注、五臣注,甚至还可以补充《集注》本中的注释。
三 余论
就本文涉及到的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而言,其中有无注的法藏本,也有有注释的俄藏本。这个无注的法藏本是否就是“萧统原本”?或者是现存的无注三十卷本?俄藏本的注释与现存李善注和五家注都不一样,是否像饶宗颐说,是另外一个注本系统?它们的书写时间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时候传入西域敦煌?这些问题都关乎我们进一步了解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价值。以下仅就此作一推测。
关于俄藏本的抄写时间,大致分为李善注之前和李善注之后两种。罗振玉根据“衷字缺笔作哀,定为隋代写本”,王重民认为罗振玉“举证虽未必确,然统观此四卷,渊字民字并不讳,则为唐以前写本无疑也”[3]320。如前所述,俄国学者孟列夫认为俄藏本抄写的时间不早于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登位时间),不迟于718年(开元六年),如果是这样,那俄藏本的抄写时间就在李善注和五臣注以前(李善注成于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五臣注成于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饶宗颐则认为,敦煌写本《文选》俄藏本L.1452残卷束广微补亡诗六首“原非李善注,而为另一注本。谢灵运事下引丘渊之《新集录》;韦孟《讽谏诗》下引张辑《字诂》,张茂先《励志诗》引江邃释蒲卢一名,有裨辑佚”[4]2-3。刘跃进在《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中也说,这份残卷(指俄藏本L.1452——引者注)“抄写工整细腻,为典型的初唐经生抄写体。其注释部分,与李善注、五臣注不尽相同,应是另外一个注本,具有文献史料价值”[7]20。罗国威认为,敦煌写本中的谢灵运诗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为唐人注《文选》的别一种。就其中谢灵运诗注而言,不失为唐人注谢诗的一珍贵写本”[21]。傅刚说残卷的注本“是产生在李善之前,并为李善作注所依据的初唐注本”[22]。范志新不同意傅刚的看法,他认为“当在玄宗之后”[23]。徐明英、熊红菊认为是“产生于唐高宗时的李善注本”[24]。许云和的观点更为具体:“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残卷抄写于唐代宗李豫时代,创作则在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唐肃宗李亨时期。……结合现存史料来进行考察,可以确定它是开元年间明经试及进士试要求对以往应试所用读本进行改革的形势下的产物。”[25]黄伟豪则说是“穆宗以后的唐写本,或为当时士人参考李善注与五臣注的应付科举之书”[26]。刘明据俄藏本《讽谏诗》中的“颜监曰”和其注多引《汉书注》,考证出俄藏本的抄写时间不会早于颜师古《汉书注》的完成时间,即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高宗永徽元年(650)这九年里。也就是说,敦煌写本中俄藏本抄写时间在李善注和五臣注之前[27]。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刘文说“撰者可能即曹宪”,并进一步推论到此卷为“经过抄写者改造后的曹宪的《文选音义》”,恐还缺少充分的证据。而且《汉书·楚元王交传》谓元王“字游”而不名“文由”,俄藏本谓楚元王“名文由”,可补正《汉书》。刘明谓此写卷《文选注》完成于颜师古注《汉书》之后,如果是这样,此处不应有别,故刘说还可再议。
从上面的观点看,关于俄藏本的注者和抄写时间,分歧较大,从唐高宗(650—683)到穆宗(821—824)之后,跨度几近三百年。说它是“穆宗以后的唐写本,或为当时士人参考李善注与五臣注的应付科举之书”的观点恐难成立,如参考李善注和五臣注为应付科举所作,当比较规范,但上举“谢灵运”一条注释,丘渊之《新集录》误“涣”为“渔”、误“郎”为“监”,则不类科举参考之书。俄藏本与李善注和五臣注都不一样,显然是另外一个注本系统。但注者为谁,尚待考证。
下面谈法藏本的抄写时间。一般而言,越接近原作的写本越能反映原作的真实样态。现存敦煌写本《文选》中有“萧统原本”残卷四截(P.2554、P.2493、P.2645、P.2658),据王重民研究,“此四卷约均与《文选》原编为最近”[2]317。甲、乙两卷为“陈隋间写本”,丙、丁两卷“均不避唐讳,盖亦并为六朝写本,在李善注以前”[2]316。王重民从乙卷《演连珠》第二首(今本《文选》卷五十五)“是以物称权而衡殆”句,今本“称”作“胜”,李善注“胜或为称”来看,“则此卷与李善所见或本合。意者善注此卷,采用刘孝标旧注,殆遂以刘本易昭明旧第,而又校其异文以入注?然则善所称或本,其即萧统原书耶?故能与此本相同”[2]316。刘孝标卒于普通三年(522)。先师屈守元先生考证,《文选》编辑的时限在普通七年(526)到中大通三年(531)这六年之间,而且《文选》不录存者之作[28]28,今《文选》卷五十四录有刘孝标《辩命论》。如此,则刘孝标所注的陆机《演连珠》在《文选》编撰前就已完成。如同采用綦毋邃《三都赋注》一样,李善注《文选》时恐直接采用了刘孝标的陆机《演连珠》注,同时又用另外一个编辑进《文选》的刘孝标的《演连珠》注本来进行校勘,即李善所谓的“或本”,或“古本”。如王立群所说,这个本子“应该是《文选》较早传播的状貌,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反映了萧统编纂之旧貌”[29]。
再一个例子是,王融的《三月三曲水诗序》“奇翰善芳之赋”句,奎章阁本、胡刻本、尤刻本、六家本、六臣本均同。此数本李善、五臣注“善芳”为鸟名,但《集注》引它注则存疑。《集注》同时又引(疑《文选钞》)“菁茅当为〔善〕芳字之误也”[18]824的话,这说明《集注》编者曾经看到“善芳”作“菁茅”的它本,而作“菁茅”则与法藏本同。作“菁茅”的这个本子是否就是法藏本的底本呢?也就是说,萧统《文选》编成之后,到李善作注之前,甚或在萧该撰《文选音》之前的五六十年间,即有人开始抄写萧统原本《文选》,或为《文选》作注,而这种《文选注》似包括了类似刘孝标《演连珠》注一类的已有的单篇注本,甚至也包括有如李善所说的“古本”《文选》。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今法藏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原文有可能是梁陈之际的《文选》“古本”。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梁陈之际的《文选》原本何以传入西域敦煌?前面讲到,罗振玉、王重民都认为法藏本抄写于陈隋之际,孟列夫认为俄藏本抄写的时间不早于630年、不迟于718年。现在看来,如果说李善注《文选》之前就存在“古本”《文选》,或“或本”的《文选注》,或刘孝标的陆机《演连珠》的旧注,那么法藏本传入敦煌的时间有可能更早。
南北朝时期,虽然南北对峙,时有烽火狼烟,但文化交流、互市聘问却经常进行。特别是在萧梁王朝,南北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当年梁武帝诏令编撰的《华林遍略》,刚刚编成便被人抄写传入中原,沈约的作品被魏收等人抄写模仿;《文选》编撰重要功臣刘孝绰的作品,“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30]《刘孝绰传》,483;“侯景之乱”和“江陵败亡”之后,梁朝的文人和文集、文献又被掠至北齐和北周。《梁武帝集》、《梁简文帝集》“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31]《萧大圜传》,757即是明证。萧该在江陵破亡后被虏至长安,于开皇(581—600)初撰《文选音》。这些都有可能为《文选》的北输提供条件。
此外,从书法风格上看,敦煌写本中的俄藏本《文选》“画行很细,楷书大字,有小字双行注释,捺笔画粗。笔道苍劲有力”[4]577的书法风格与今存南朝梁陈间敦煌写本经书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捺笔下斜而顿收之法十分明显,例如俄藏本的“大”字和法藏本的“之”字。文末附图是南朝陈后主至德四年十二月(586年12月15日—587年1月19日)彭普信书写的《摩诃摩耶经卷上》(局部一、局部二)和《摩诃摩耶经卷上》“题记”与敦煌写本俄藏本L.1452《文选》束广微《补亡诗六首》、法藏本P.2543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书法对照。
两相对照,从书写的风格和用笔上,例如“大”字、“之”字等的捺笔十分相似,二者的书写时间似很接近。而南朝梁陈间敦煌写本经书,一般由荆州竹林寺、建康瓦官寺和白马寺“辗转流传,始得保存于西陲之敦煌”[32]67。如前所述,俄藏本“两面均有经文”,敦煌写本《文选》是否随南朝陈代写本经书一道传入西域敦煌?或直接由经生写在经书上?这些问题,都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文选》成书后不久,有可能在梁陈之际历经“侯景之乱”和“江陵败亡”,即由建康和荆州等地被侯景或于谨大军所掠,或于南北互市聘问之际,或随写本经书等传入中原和关中地区,再由中原和关中地区传入西域敦煌,以至千百年来历经劫余,散落域外。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敦煌写本《文选》在梁陈之际即传入敦煌地区,但俄藏本Ф-242a(L.1452)的抄写在唐太宗时期,法藏本P.4884、P.2707、P.2543的抄写时间在陈隋之际,应该没有多大争议,而且其内容与今本《文选》不一样。就这一点而言,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价值就弥足珍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图1.写本《摩诃摩耶经卷上》题记、写本《摩诃摩耶经卷上》局部一[3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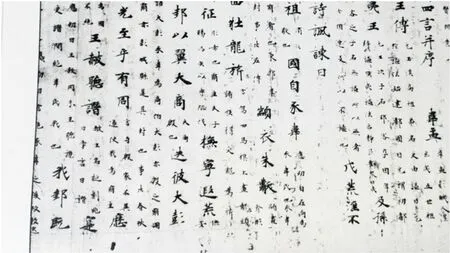
图2.俄藏本L.1452《文选》束广微《补亡诗六首》[4]35

图3.《摩诃摩耶经卷上》局部二[3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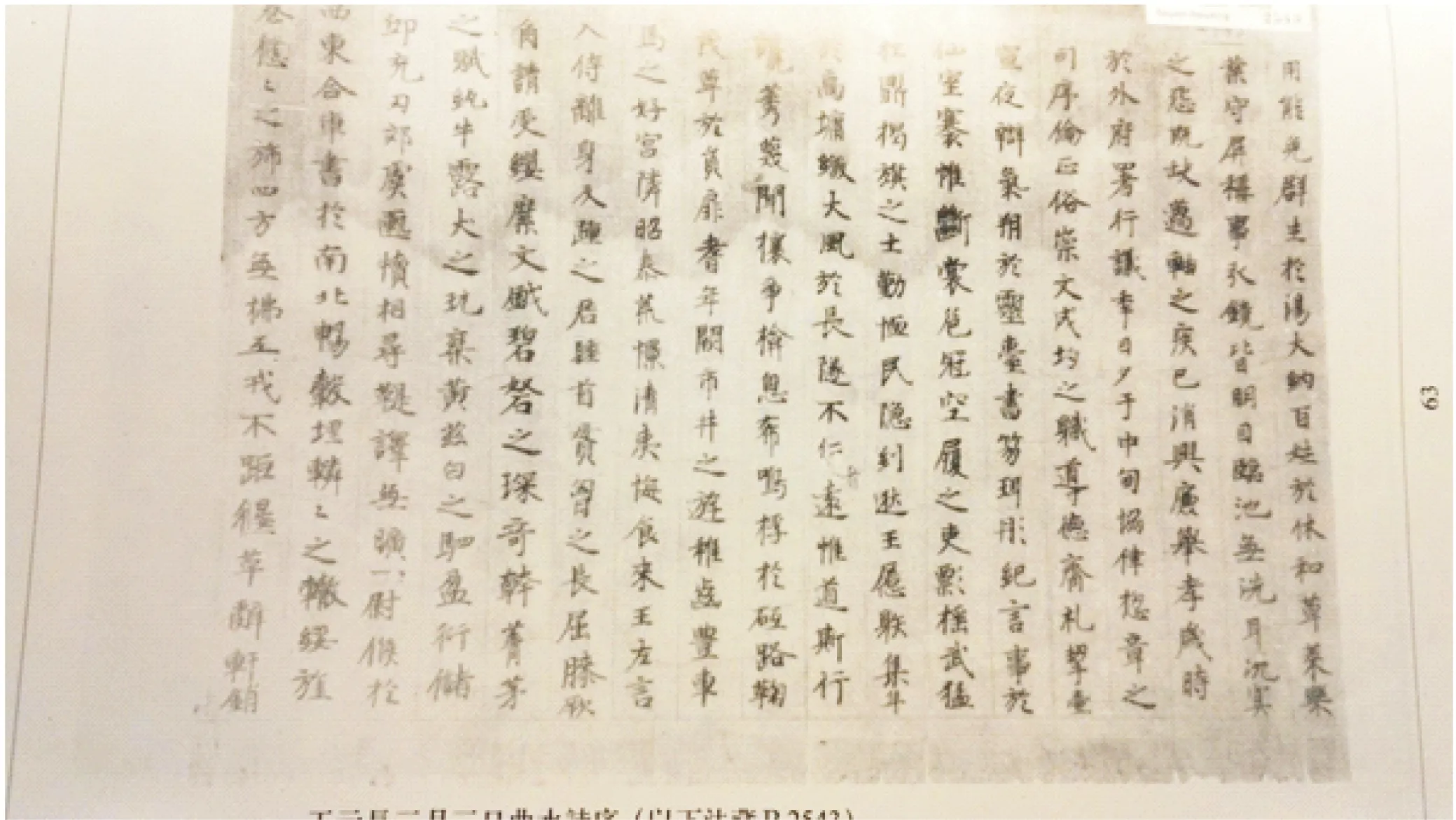
图4.法藏本P.2543《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4]63
注释:
①刘跃进《文选古注辑存》引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国学论丛》1928年10月第1卷第4期)说:“表犹诗序也。于诗选中有表一篇,殊不类。宜改为《上责躬诗》。旁注‘四言并表’四字。”又引:“九条本页眉记有‘《决》作上责躬诗一首并序。’”(刘跃进著、徐华校《文选古注辑存》第7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8页)案:刘盼遂所说似有一定道理,如《文选》“献诗”类潘岳《关中诗》的《上诗表》,萧统并未放在《关中诗》之前。今李善注引有潘岳《上诗表》,曰:“四言。岳《上诗表》曰:‘诏以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但曹植诗为《责躬》、《应诏》两首,二者有内在联系,如无此“表”在前,其作诗之意难明。此二首又均为应诏所作,不敢不献,献则有“表”,不得用“序”;但实际上此“表”又是《责躬》、《应诏》二诗之序,与《文选》“表类”中其他选文有所区别,故萧统编入选诗中,其意恐在此。
②韩国奎章阁本《文选》(韩国,1996年影印本)为现存最早的并李善注与五臣注为一体的版本,以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州(今浙江嘉兴)州学本为底本刊刻于朝鲜世宗十年(1428,明宣宗宣德三年)。有关奎章阁本的情况,请参傅刚《〈文选〉版本研究》下编《〈文选〉版本考论·论韩国胡刻本〈文选〉的文献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奎章阁本校记或注释以小号字体别之。
③凡文中俗字别体,今以“( )”括注,后以“[ ]”号标注通行字。漫漶不可识者,今以“□”号代替。为使文义顺通,笔者所增之字,以“〔 〕”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