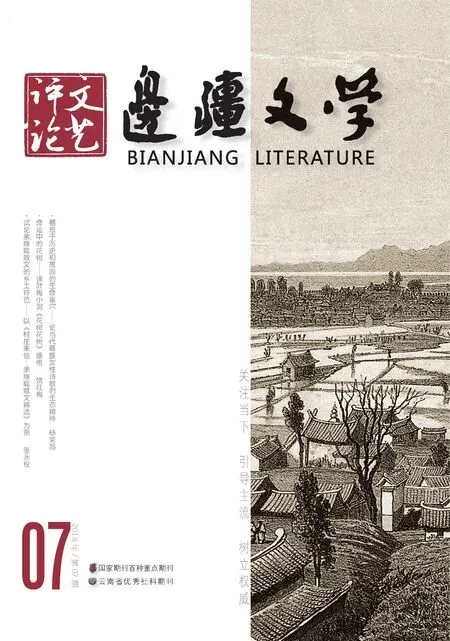说什么很重要,怎么说也重要
——昭通诗人麦芒诗歌创作简评
朱海燕
2018年5月22日,昭通诗歌届的奠基者和开创者——麦芒老师的作品研讨会在昭通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举行,同时也印刷出版了《麦芒诗抄》《麦芒小诗精选》和《诗痴麦芒——麦芒诗文评论集》,前两本是诗人四十年创作成就的总结,后一本代表着诗人的荣誉。风风雨雨四十年,就像《评论集》主标题的称呼“诗痴”一样,麦芒不断地用诗歌书写生活,用诗歌确证生命的意义,诗歌在其生命中,像融入进血液般绵绵流长,鲜活,生动,深刻。
麦芒诗歌“说什么”
纵观人在世界中的关系,无外乎是由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我三种关系构成。这三种关系在《季羡林谈人生》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1]我们常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么对于作为文学主要门类的诗歌而言,更是如此。不管是面对自然摇荡性情,还是面对社会人事,抒情感怀,诗歌都是抒情性作品的典型代表。如果以人类社会关系的三个方面来看麦芒的诗歌,可以看出诗人“无所不包”的创作胸襟,他的诗歌涵盖了上述“三个关系”,也就是在“写什么”这个话题上,诗人呈现的是一种开放宽广地用诗观照世界的方式。翻开《麦芒诗抄》和《麦芒小诗精选》,厚厚的、沉甸甸的,像用手拎起了整个世界与生活。
麦芒诗歌是生活的“万花筒”,散开来,可以发出五彩光芒,仅以《麦芒小诗精选》中的诗歌为例,比如:写宇宙,《太阳》“太阳/下山了/宛如/一个句号//明天呢/它照样升起/带着/满脸微笑//鸟语!花香!”、《星星》“含泪的夜的眼睛”、《朝阳》“大海边的一滴血”、《月亮》《夜》等;写自然万物,《独秀峰》“是怒吼/是呐喊/也是高歌”、《瀑布》《小草》等;写政治,代表作《雾》“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官场》“一个大染缸”、《岁月履痕》组诗之《一九五七年》“55万顶帽子/在空中飘飞//她在寻找——意中人”、以及《一九六○年》“斑驳冰凉的烟囱里/怎么也冒不出/一缕/烟//大眼/瞪小眼”等;写亲情,《祖母》“一盘石磨/光亮了六十载//孙女的一双高跟鞋/被她摩挲了半天”、《题“全家福”彩照》《母亲》等;写爱情,《初恋》“一瓶泸州老窖/风烛残年时/好香!”、《给妻》《爱情的花苞》《爱情》等;写友情,《挚友》“夏日里/一盅矿泉/冬天里/一盆火焰//心与心/没有距离”、《与欧嘉年影别》《茶友情》等;写田园风光,《山水图》“一株树/倒立在/陡峭的岩石边/一个渔夫,撑着/双桨/悠然地划过/波涛滚滚的海面”、《百花园》组诗、《果树园》组诗等;写日常生活,《菜市场》《写在商品上的组诗》《在列车上》组诗、《生活杂吟》组诗、《生活随笔》组诗等;写给自己,《我》“我走我的路/我唱我的歌/哪怕/只有一个读者/只有一个听众”、《我的生日》《我的血型》《我的长相》《为自己画像》等;品评人物,《昭通作家群》组诗、《人物速写》组诗,还有单诗,如《胡风》“硝烟里/风浪里/岂止经历了三次/碱水中/血水中/岂止浸泡了三次//一位不弯腰的诗人/一位挺立着的战士”;读史,《读史札记》《紫禁城》等;品读汉字,《品读汉字》组诗,如《伴》“横看,竖看——/一半是女/一半是男”、《夫》“谁能顶天立地/谁就是/英雄豪杰”、《囚》“锁在铁屋里的人/是否/都犯了罪?”;此外,还有小人物书写,像《赌徒》《酒鬼》之类。随手可拈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的生活哲理,随时可感的社会现象,随时随地的生活抒怀,都是诗人创作的最好素材,这种把生活诗化与审美化的创作态度,也成就了诗人的高产。他以诗歌感念生活对人类的厚遇,他留给了我们丰厚的精神馈赠。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在文字碎片化的时代,当我们被快餐文化、大众文化冲击地找不到生活方向感的时候,麦芒用他的诗歌告诉我们,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有时惬意,有时深沉,有时简洁,有时深刻,有时高雅,有时随性……
他的诗歌赋予存在以意义,让我们看到了生存的本质,也让我们怡养性情、升华灵魂。就像作家阿来在电视节目《朗读者》第二季第五期中“他说1989年的那一年我同时出了两本书,那个时候旁边人叫你诗人,叫你作家,但这两个词,不管今天贬值多少,在我内心至今,我觉得是两个非常神圣的词,我觉得我当不起。”的确,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的时候,文学也以迅猛的速度完成了其市场化进程,作家、诗人,这些曾经代表社会精英、代表社会责任感与良心的知识与正义的化身,在一切都以金钱、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市场经济中,逐渐被贬值,当然也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失落。我们知道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作家创作出第一文本,经由读者的阅读与再创造可以产生出第二文本,虽然“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但是无论怎样的解读都超脱不出第一文本的阈限,所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理解的共识,而这个共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就可以凝聚人心,塑造人格,提升精神,可以间接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所以,阿来说“诗人、作家”是两个非常神圣的词。对于从事诗歌创作有四十年之久的麦芒老师,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无论是他对于诗歌创作的崇敬探索态度,还是他丰厚的诗歌产量,都是今天物质极其丰富而人文精神匮乏的时代我们精神上应该秉承和学习的榜样。
麦芒诗歌“怎么说”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其言说的过程及其结果大体上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2],对理论批评是这样,那么对于理论批评产生的基础和依据——文学创作,同样也具有这样一个问题。探究“说什么”与“怎么说”,可以看出“说什么”指的是文学言说的内容与对象,对于麦芒诗歌“说什么”第一部分已作论述,而“怎么说”则是文学言说的方式。进入20世纪后,西方兴起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文学批评理论,将文学批评由作家中心论转向了文本中心论,尤其注重文学的言说方式,在小说创作中发展了新叙事学理论,而在诗歌中,注重诗歌新的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开启了新诗的现代性探寻之路,自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新诗为新诗诞生标志,至今中国新诗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历史。相比古典诗词,新诗的历史确实很短,但是在这中间,数不清的诗歌理论家、诗人都为新诗的探究与发展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现代诗人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戴望舒等到中国当代那些著名诗人,因为抒情与表达方式的不同,还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流派,使现代新诗这种独立的文体,经由不同的诗人不断地探索,具有了越来越多样的言说方式,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审美特质。
“什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就是更充分地利用一种语言的内在潜能以表现一般的社会群众所没有或很难进行表现的一种情感的或情绪的感受,使这种语言具有更深厚、更丰富的内涵,更隽永、更浓郁的意味。”[3](P.109)那么,在这个语言艺术的探寻道路上,作为昭通作家群前辈级的人物——麦芒为昭通文学中的诗歌创作作出了表率,早在1979年文革刚结束,麦芒就在《诗刊》(1979年10期)发表了自己的一句成名诗《雾》“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并从此执着于小诗创作。他以自己的诗歌实践证实,小诗不仅能“载道”、“抒情”,还可以具有反思社会的功能,以有限寓无限,发人深思。既具有诗歌独特的审美艺术感染力,又具有政治意义和深厚的社会内涵,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巨大表现力,具有无限生成意义的艺术张力。在对待中国进入现代之后的新诗问题上,著名文艺批评家王富仁指出:“我不把中国现代新诗视为中国古代格律诗发展的直接产物”,“中国现代新诗必须在现代白话文的基础上重新生长。怎样生长?不是现成地接受中国古代的或外国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点一点地用白话语言感受事物,感受世界,感受现代的中国人,同时也感受自己。”[3](P.109)作为中国当代诗人的麦芒承继着现代文学中的新诗传统,坚持用小诗的形式书写大自然与各种社会人生现象,由最初的一行诗、两行诗、三行诗写作,后来又拓展了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行诗。麦芒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孜孜不倦,使诗歌形式就像诗人手中的魔术杖,随便向生活一指,生活便向万花筒般炸开,色彩缤纷,五彩斑斓。而读者读其诗歌,不光有视觉的生活感,还会侵占心灵,带来灵魂的震颤。中国新诗是以白话——现代汉语言为基础,尤以自由体诗为主要形式,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之一,是借诗歌形式的转变以求打破僵硬的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内涵上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性。中国著名的诗学理论家吕进提出“呼唤新诗的二次革命,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4]在诗体重建这个问题上,吕进进一步指出“在无限多的诗体(而不是为数很少甚至单一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倡导现代格律诗。”[5]吕进在进入21世纪,对中国提诗歌界提出的“诗体重建”命题,实际上昭通诗人麦芒在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之初就已经在作出实践了,而且这一实践就是四十年。
《麦芒小诗精选》,这本书的编写体例就是按照麦芒诗歌从一行到十二行的诗体形式特征编排的。一、二、三行诗无分节;四行属于二二式,如《老街》“木板房;小洋房/石板路;水泥路//瘦了/童年的梦”、《一九六六年》“一场大火/烧了十年//不见/消防队”、《梧桐树》“看似木桩/不是木桩//春风一吹/便绿了”、《雪》“六角形的花瓣/编织成一床鸭绒被盖//被盖下面,卧着一个翠绿的春天/”,二二式四行诗,前两句写景、写事、状貌,后两句点睛升华,或哲理思索,或现象升本质,或景物转情感;五行诗作也有涉及,但是篇目较少,在《麦芒小诗精选》中,只编进去15首,有的是二三式,有的是没有分隔,质量不是很高;六行诗,数量比较多,诗人曾经出版《六行诗一百首》,在对六行诗的探索上,诗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写作上相对成熟,主要以四二式为主,略举几例:《盆景》“失去了天然风采/剩下了一盆古怪/该生发的没有生发/该开绽的没有开绽//只要主人露出笑脸/扭曲变态心甘情愿”、《笼中虎》“关得住/四肢和身躯/关不住/自由的憧憬//莽莽林海/心的王国”、《一九六零年》“斑驳冰凉的烟囱里/怎么也冒不出/一缕/烟//大眼//瞪小眼”、《喜欢》“有人喜欢星星/有人喜欢月亮/有人喜欢大海/有人喜欢蓝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四二式的前四行是事件陈述或事物状貌描摹,与二二式前两句功能一样,只是扩充了两行,增加了诗歌的容量,事件陈述更深入,状貌描摹更细致,最后两行,仍然承担升华主题、点睛、让表象本质化的任务。六行的二二二式也很有韵味,如《红豆》“一粒红豆/一串苦瓜//一串苦瓜/一捧泪花//一捧泪花/一副骨架……”,首尾相连,层层深入,韵味无穷。在麦芒诗歌创作中,一行诗、两行诗、三行诗以精短著称,也彰显了诗人语言文字提炼的功底,具有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语言张力,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和魅力。除此外,就是六言诗了,六言诗不长不短,诗歌界把12行(含12行)的诗歌定位于小诗,而六行诗与七行诗同处小诗行数的中间位置,但是因为六行诗为偶数行,在美学中对称是一项重要的美学原则,四二式的六行诗就具有这种审美艺术感。另外,六行诗扩充了一、二、三、四行诗歌语言含量,使诗歌情感更加饱满,读起来更能随着情感的起伏而充满节奏感和音乐美;七行诗,有五二式、三一三式、二二三式等不一而论,数量不多;八行诗有二二二二式、四四式、二四二式等,八行诗诗体美感较强,从上面几种八行诗体例来看,比较具有节奏美感,行数越多,起伏变化的空间相对增大,也更利于发挥诗歌的抒情功能;九行诗,多以三三三式为主,每三行都独立成一个意义单元,然后,三个三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综合体;十行、十一行与十二行诗,行数比较多,没有太多的规整性,形式组合自由,诗歌信息含量也较行数短的诗歌增大很多。
从以上各种行数的小诗形式分析可以看出,在麦芒诗歌创作40年的历程中,面对广阔的生活面貌与深广无边的哲理人事探索,诗人非常注重“怎么说”,并亲身实践了小诗各种行数的创作,在云南、甚至国内诗歌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反常化’(或奇异化,更多的译为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6]形式主义者的论断把对文学形式的重视发展到了极端,忽略文学言说内容的重要性。但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其积极意义在于,诗歌语言表达的方式,也即是“怎么说”的凸显,将日常熟悉的景物和日常经验变得生疏起来,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让世界在读者眼前重新变得鲜活起来,唤醒对生活麻木的心灵感受,从而凸显生活无处不在的乐趣及哲理,获得审美人生的存在价值。麦芒不是用“自由体”来创作的,他亲身实践了十二行之内各个行体的书写,麦芒诗歌即是平常景、平常事、平常情、平常理等的书写,但是借助“怎么说”的独特展示,让其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读其诗,可以使我们看得见生活的美好,思索到平凡的日子所遮蔽的深刻哲理,生活不只吃喝拉撒,还有精神心灵需要触及的美好,而诗歌就是我们触及生活美好的媒介。
“文学是孤独、寂寞的事业,麦芒是精神家园和守望者。多年来,他以罕见的毅力和热情,不断地驰骋感性的才思与理性的智慧,用一生的执著求索充分诠释文学的本真和魅力。”[7]这段话是昭通小说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天敏老师对麦芒及其诗歌最中肯的评价。在当今娱乐至上,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学的滋养,我们更需要像诗人麦芒那种执着于文学探索和求真的作家,引领我们进行诗意人生的享受。

刘贤能 国画 私语
(作者系昭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