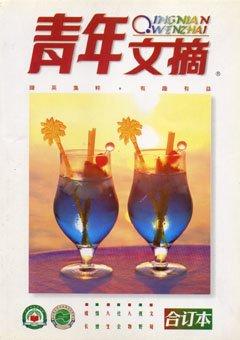问天不如问自己
杨嘉利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18岁那年所经历的一幕:当我怀着希望和不安,拖着扭曲的形体,敲开成都一家报社编辑部的门时,竟把几个胆小的女编辑吓得跑了出去。那一刻,我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和这笑容一起凝固的还有我的梦和办公室里的空气。后来,当我颤抖着从破旧的军用挎包取出一叠稿纸时,编辑们才明白我的来意。他们接过稿纸,展开来,那皱皱的稿纸上是我用左手写下的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将纸船/放进小河里漂走/梦,像断线的风筝那样自由……
我看见女编辑的眼中汪起了泪水。
妈妈哭着搂着我说:“你只能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
1970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半岁时,一场高烧持续不退,医生已经绝望,告知后果,劝母亲放弃。母亲流着泪回答说:“不管他残成什么样,我都会养他一辈子!”
母爱的力量竟使奄奄一息的我又活了过来。由于脑神经受损,我成了终身残疾,双手不能自由伸屈;嘴斜了,失去了准确的发音;脚也跛了,走路一拐一拐。直到五岁多时,我才开始蹒跚学步。我常常趴在窗台上,羡慕地看着楼下那些健康的小孩们奔跑游戏。有一次,我看着看着走了神,幻觉中我也有健康的身体,也在奔跑,在跳跃。突然,脚下一滑,我从站着的凳子上滚到地上,头上顿时撞起了一个大包,我又吓又疼,大哭起来。中午,妈妈下班回来,搂着我,眼里含着泪对我说:“小三,你是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不可能去跑去跳,你只能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不久后,我家就从四楼搬到了一楼。我好高兴。我可以出去玩了。但当我一拐一拐地来到院子里时,那些同龄小孩便围过来冲着我起哄、怪模怪样地学我走路,甚至将我推倒在地,吐我口水、揪我头发。每当这时,我从来不哭,而是倔犟地从地上爬起来,用一双迷惑的眼睛看着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恶作剧般地欺负我。
家里的墙上有一道补了又补的深槽,磨砺我的雄心
到了应当上学的年龄,我渴望去读书。我对几本早已翻破的小人书上的那些方块字充满了好奇。可是,当爸爸带着兴高采烈的我到学校报名时,却被拒绝了。12岁那年夏天,爸爸带着我第6次来到子弟学校报名入学。爸爸恳求老师:“收下这个孩子吧,我可以每天按时接送他,照顾他上厕所,不会给学校增加麻烦,这孩子爱读书。”我也哭着对老师说:“收下我吧。我会好好读书的。”
但,发榜时,一年级新生名单上仍然没有我的名字。我失去了最后一次入学的机会。
妈妈搂着已经哭哑了嗓音的我,哽咽着说:“孩子,不上学一样可以学知识,爸爸妈妈教你。”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母和已经上中学的姐姐成了我的老师;姐姐的旧课本和那几本翻过无数遍的小人书成了我的教材;右手残疾得不能拿笔,我就锻炼用稍稍灵活的左手写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由于写字吃力,那张紧靠墙壁的小圆桌竟在墙上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槽。
就这样,我用了一年多时间就自学完小学课程,然后又自学了中学课程。
在青春的雨季里,我成为成都最高文学奖“金芙蓉”的最年轻的得主
我自学的事在工厂传开后,感动了年过半百的子弟学校周荣升老师,他主动收我做了“校外学生”,晚上专程来给我辅导,修改我字迹不清、歪斜难认的作业,指导我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1986年,16岁的我开始写诗,用诗表达我心灵的情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但是,写诗并不像我刚开始时想像的那么容易。我有个小纸箱,里面装满了退回来的稿件,这对于每写一个字都很困难的我,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母亲不忍看着我一次又一次失败,劝我说:“算了吧,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可我不愿放弃,再难我也要走下去。
1988年秋天,我的一首小诗终于在省内一家青年报上发表了!捧读着变成了铅字的处女作,我内心的激动无法言表。那一刻,我想到了许多许多:童年的苦涩、心灵的创伤、读书的希望、父母的艰辛……而在心中,我更在大声呼喊: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此后,我一发不可收,诗歌散文像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至今我已在国内数十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300多首诗歌和几十万字的文章。1993年,在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筹钱为我自费出版了诗集《青春雨季》,并在1994年获得了成都市最高文学奖“金芙蓉”奖,我成为这个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1996年3月,我被四川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写作于我,需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甚至伴着伤痛,伴着屈辱。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别人也许可以一挥而就,但我却要吃力地磨上大半天。近几年来,我又开始写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新闻报道,并被一些报社聘为特约记者。有时去查找资料或采访,为克服自理不便的困难,我常常不敢多喝水,揣一个冷馒头就是一天。但最使我感到委屈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人们的不理解。有几次,我去公共汽车上采访无人售票新举措,竟被人不屑地推下车来,人们很难相信我这样一个行动不便嘴歪眼斜的人会是记者。每当这时,即使我拿出特约记者证,换来的也常常是一阵奚落和嘲笑。我采写的一些引起过较强社会反响的报道,就是在这种屈辱的笑声中艰难完成的。
我不是报社的正式记者,没有固定收入,每月仅靠微薄的稿酬维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父母生活。
当爱情的燕子飞临的时候,我一次次地问这是不是做梦
尽管我身有残疾,但也是一个有情感的年轻人,同样渴望纯真的爱情。在我23岁那年的夏天,一个姑娘闯入我的心扉。
7月的一天,几个文学青年在成都杜甫草堂聚会,一个新来的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叫燕,正在读成人自考。端庄秀丽的燕没有加入我们热烈的讨论,而是安静地坐在一旁,阅读着我新出版的诗集,并不时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无意中,我的目光接触到她的目光,心中不由一阵紧张,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是啊,在我23岁的生命中,还从来没有过姑娘用这样一种眼光看过我!可是,当我低头看见自己残疾的双脚时。我又很快恢复了理智,不得不痛苦地收敛起自己的非份之想。后来,燕告诉我,初次相见,她就从我的诗中读到一颗热爱生活不残的心,也读到了我的苦难、伤痛、挣扎和呼唤……几天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她的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的关切,并约我再次见面。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从此后,在公园、在河边我们经常相见;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文学。尽管我们从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但从彼此的眼神中,却能明白无误地读懂那份沉甸甸的真情。
可以说,自从认识她那天起,我的心情就一直处在矛盾的痛苦中。一方面,我为燕大胆、真诚的爱所感动,我曾不止一次幸福得流泪,也曾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是不是做梦?我能给她一生的幸福吗?特别是当我们在大街上并行时,我总能够从人们异样的眼光中看到我们之间的差异,读到“悲剧”这两个字。多少次,我曾想写信对她说:收回那份不切实际的爱吧,让我们只做真心的朋友……但每次,写好的信,我却没有勇气交给她。我不愿失去这份珍贵的爱。
在初恋的炽热和矛盾的折磨中,1993年的冬天来了。
有一天,燕对我说,春节她要和哥哥一起回北方老家过年,叮嘱我要好好保重身体。尽管燕说过完年她很快就会回来,但我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燕的父母都在北方,只有一个做生意的哥哥在成都照顾她的生活。父母知道女儿在和我这样一个残疾人谈恋爱,当然竭力反对,但燕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据理力争。这一次,回到北方,她的父母还会让她再返成都吗?
在一个寒气逼人的阴冷的早上,我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我们彼此都难舍难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一刹那,燕突然从窗口上伸出头来,俯在我的耳边急切而热烈地说:“我好想再吻你一次……”那一刻,一颗苦涩的泪滴落到我脸上……
从此,她果真没有再回来。
我不怨她,甚至也不怨她的父母。只是,我仍然在年复一年地苦盼着,尽管理智告诉我,这是无望的等待。我珍视在自己所走过的27年人生旅途中,这惟一的一次爱,不管是拥有,是失去,还是梦幻……
今后,还会有许多苦难和伤痛在等着我,但我仍会在人生这条风雨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耕耘希望,播种梦想,在这个世界上,坚强地活着,勇敢地活着。
(马珲、李世玉摘自《深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