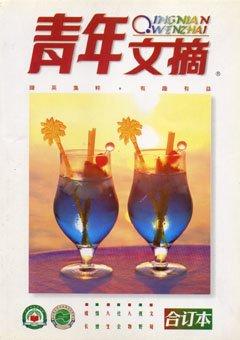骆驼赋
肖复华
31年前,我由北京去青海柴达木当一名石油工人时,便听说了这个故事,它足以让我记住一生。
1954年,当第一支石油勘探队踏入这浩瀚的“生命禁区”时,运载物资、陪伴他们而行的只有“沙漠之舟”——骆驼。
一次,一个勘探小分队在大风中迷了路,他们走了六天,一峰饥渴难忍的骆驼猝然倒地,它张着大嘴,仰天长啸……
驼工向队长苦苦哀求:“给它点水吧,救救它吧。”
8个人的小分队只剩下两桶水了。眼下,队伍又去向不明,这两桶水维系着全队人的生命呵!
望着眼前这片被戈壁疯狂蹂躏的沙砾,小分队的人们仿佛也在睁着枯涩的眼睛在哀求:给它点水吧,它还能活……
望着远处绵延起伏的阿尔金山.那被风沙撕裂的道道褶皱也在哀求:给它点水吧,它还能活……可茫茫戈壁,戈壁茫茫,只有沙砾只有沙砾……
队长姓葛,他望望乌孜别克族向导阿吉老人,老人望望仅剩下的两桶水,坚定地摇摇头。全队人都明白了,面向骆驼脱帽肃立。
葛队长挥挥手,示意走吧。可大家的腿像灌了铅,一步三回头……
队伍行进不足十米远时,那峰骆驼竟顽强地支撑起前蹄,毅然站立起来,迈着沉重的驼步,蹒跚地追赶着队伍……
这个勘探队最忠实的伙伴,迈着沉重但充满无限希望的驼步,一步、一步向勘探队走来……
驼工再次跪倒在地,失声大哭:“救救它吧……”
全队的人都被那驼步声和这嘶喊声,震撼得落下热泪,谁也再不肯向前走一步了。
葛队长仰天长叹一声,甩下一串热泪,从一个保卫人员肩上取下一支枪,同样迈着沉重的步子向骆驼走去。全队人都惊呆了,驼工一下明白了队长的意图,紧紧抱着队长的双腿,哭喊着:“你不能这么做,你没有权力这么做呵……”
葛队长急了,冲天扫了一梭子子弹,大喊:“我的权力是战胜死亡,全队立即出发!”他的声音在戈壁滩的上空回荡。
大家一下清醒了,是的,我们必须战胜死亡,走向希望。队伍出发了,谁也不敢回头再看一眼那峰骆驼。
那峰不屈的骆驼站起来又倒下,倒下又站起来……
傍晚,队伍终于找到据点,驼工顾不上吃饭,灌了一桶水,刚要走。阿吉老人拦住了他:“孩子,不能去,会迷路的。”驼工说:“不会,有月光,我顺着驼印走……”
驼工走了,再没回来。
一个月后,勘探队在一个叫“开特米里克”的地方发现了他,在盐碱滩上,他仰天长卧,已成为不朽的人,上衣撕开,袒露的胸膛上遗留下无数条深深的血迹,上衣兜里,只有5元人民币。这钱是他第一个月留下的工资,准备寄给河北老家双目失明的老母亲。
他手里紧紧抓着那个歪倒在地上的水桶,水,在盐碱滩上留下一圈深深的水渍……
“开特米里克”蒙语为小山包。勘探队员们在这个小山包上安葬了这位十八岁年轻的生命。没有水泥,没有木板,自然也就没有了墓碑。茫茫的戈壁紧紧地把他拥抱。
“开特米里克”,这个沙砾堆就的金灿灿的小山包,深情地包容了这位在青海油田死亡档案里记载的倒在勘探路上的第一个人。他叫范介民。
今年秋天,我再次返回我在那里生活了28年的青海柴达木。当我站在“开特米里克”面前时,那峰骆驼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仿佛听见范介民说:我永远和骆驼同在了。
不远处,已建成了一个百万吨的油田了,钻塔林立,钻机轰鸣,现代化运输车队川流不息。油沙山下,正耸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为勘探和开发油沙山而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
我们到纪念碑下,凝视着远方。
远方,范介民牵着骆驼向我们走来。31年了,他和那峰骆驼一直走向我的心灵深处。
(王华摘自1999年3月1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