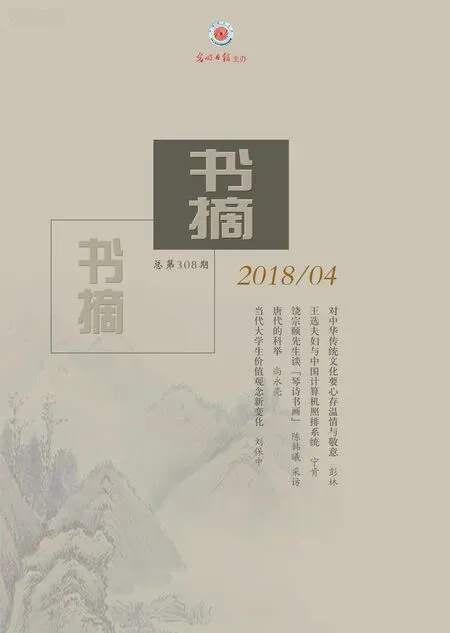渐行渐远的手艺
☉王向阳
漆匠
小时候,家乡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木匠怕漆匠,漆匠怕亮光”。木匠刨得光不光洁,油漆以后,一览无余;漆匠漆得均不均匀,亮光一照,纤毫毕露。
农家新做的木制家具,考究一点的,都要油漆,尤其以床、香几、漆桌、椅子为多。一件漆得好的家具,用了上百年,依然光亮如新。当然,油漆这门手艺学问深,难掌握。
浦江县城后街有一个名漆匠,叫周建峰。他从小听爹娘的教导“学手艺水冲不去,火煨不过,饭有得食,麻雀撑根肠”。一九六七年,他十二岁,就跟着爹娘学油漆;一九七二年,他十七岁,正式做漆匠。
做油漆有句行话“生漆打底,熟漆盖面”,先用生漆油,再用熟漆油,反复匀漆,越漆越亮,从乳白色转为红色,转为黑色,转为光亮。一件好的油漆作品,要做到三个字:黑、青、亮。底打得不好,油漆后的家具没有亮光不说,还会起泡皱皮。
凭周建峰的经验,最难的是调漆,根据一年四季气候的不同,气温的高低,湿度的大小,随机应变。业内还有一句行话“头层油皱打徒弟,面漆油皱打师傅”,底漆没有油好,没有光亮,起泡皱皮,这是徒弟的责任;面漆没有油好,是因为漆调得厚薄不均匀,这是师傅的责任。
当年的油漆是土漆,从漆树上割下来的,皮肤碰到了容易生漆疔,俗称“被漆叮了”,皮肤红肿,叮骨头痒,实际上是皮肤过敏。治疗漆疔的土方,就是用杉树皮浸泡出来的水洗一洗。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家用上化学漆,不会生漆疔了,可有毒副作用。
周建峰的造诣离不开家学渊源。早在清朝光绪末年,他的太公周大忠从诸暨同山周都村迁居浦江县城,开了一家小木家具店,兼做油漆。周大忠把这门油漆的手艺传给儿子周烈山,周烈山传给儿子周志宝,周志宝再传给儿子周建峰,如今已经是第四代了。
早在民国年间,杭州净慈寺大殿的天花板上要画一百只白鹤,每只形状不能重复,要求高,工钱也高,共有百块银圆,当时一担谷才卖四块银圆。通过堂弟的介绍,周志宝穿着土布长衫,前往净慈寺。东阳师傅穿着绸衫,拄着卫生棒,也来到净慈寺,一副包工头的派头。寺里的和尚要求他们先画样品,品评高下,再作取舍。东阳师傅说三日后交样品,要回东阳,请别人画;周志宝说当晚就画,次日交出样品。到了第二天,和尚一看周志宝画的样品,当即决定把工程承包给他。于是,周志宝站在大殿的天花板下,仰着头画白鹤,每天画七八只,前后画了半个月。

还有一次,周志宝的三弟承包浙江兰溪县一个祠堂的油漆工程,一半由他做,一半由东阳师傅做,互不通气。东阳师傅抢先在一只牛腿上画了五彩,三弟势必要在对称的另一只牛腿画上完全相同的五彩,可对方不会告诉五彩的配方,肯定有色差。三弟无计可施,只得回家把周志宝请到兰溪,周志宝灵机一动,连夜把一扇祠堂门拆下来,画上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第二天,东阳师傅一看,知道在另一扇祠堂门上画不出一模一样的门神,于是前来商量:“两只牛腿我画,两扇祠堂门你画。”只此一招,周志宝就帮三弟解了困。
一个好的漆匠,不光要会油漆,还要会绘画、雕塑和雕刻。到了一九七九年,周建峰进入浦江工艺美术厂,从事油漆工作,其间曾到浙江省进出口公司举办的美术学校进修深造;一九八一年,他开始从事竹编产品的设计工作,这与他的绘画功底分不开;后来,他又从事竹木的雕刻工作。由漆而画,由画而雕,周建峰成为漆匠中的全才。
篾匠
“篾匠学得会,鸡屎食三坨;篾匠学得精,鸡屎食三斤”,家乡流传的这句谚语,道出了篾匠生涯的艰辛和无奈。小时候,经常看到篾匠一手持篾,一手持刀,用牙齿咬住篾片,把它慢慢地扯开来,拖到地下。家家户户养鸡,鸡屎遍地,难免沾上篾片,进入篾匠嘴巴。

每一个行当,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传说篾匠的祖师爷叫泰山师,曾经向鲁班师学木匠,不够专心,偷偷跑到竹林里练习劈篾编织。鲁班师嫌他不长进,把他辞退了。后来,泰山师干脆学篾匠,搞竹编,打笠帽。鲁班师建造凉亭,天晴开工,下雨停工,很是不便。自从戴上泰山师编的笠帽以后,无论晴雨,都可建造。鲁班师这才知道泰山师的好处,说了一句“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篾匠还有一套行话,叫做市语。石宅派顶村江晓明曾经做过篾匠,记得许多行话:毛竹叫青龙,青篾叫老青,黄篾叫老黄;玩女人叫劲尺,胸部叫蒲包;吃饭叫兴夯,早饭叫早夯,中饭叫午夯,夜饭叫夜夯;食肉叫兴胃,豆腐叫白塌,面条叫长纱;老太婆叫尺佬,小孩叫小毛头,老头叫老毛头,小姑娘叫红花佬;干活叫操摊;做篾的工具叫龙扇,篾席叫横三两,畚箕叫阔口,大麻篮叫大四角,小麻篮叫小四角,床叫横山。在外行听来,真如天书一般,如今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一门手艺,不知要吃多少苦头,尤以蔑匠为甚。家乡有句顺口溜“有囝不学篾匠,站起来活和尚,蹲下来孵鸡娘”很形象:篾匠站着剖篾,双手并用,嘴巴补凑,像和尚边念经边数佛珠,蹲在地上补地垫,像伏在鸡窝里的孵鸡娘一样。
一九三三年,郑宅西店村的郑兴庭才十三岁,就跟着师傅到浙江於潜(今浙江省临安市於潜镇)学篾匠。到了第二年,因为力气小,他还不会剖篾,故意在手指上砍了一刀。师傅无奈,只得帮他剖篾。他在编地垫的时候,转角处总是凑不拢,被师傅打了一个耳光,才肯教他技巧。有时候去迟了,东家问他吃过没有,只好说吃过了。否则,东家给他烧饭,耽搁时间,只有半天的工钱。每过十五天,郑兴庭要帮师傅到镇上去买一次煤油。十三四岁的小孩,实在苦不过,曾经想一个人偷偷逃回浦江,又怕回家要挨骂,只好作罢。挨了三年,师傅付给他爹二十块银圆,作为工钱。为此,他奶奶还骂他爹:“你这个黑心的,这么小就把儿子弄开去!”
有的篾匠子承父业,照样受苦。一九三六年,前吴村的吴金生才十岁,就跟爹爹学篾匠。第一天,他到东家,扫好地,搬好凳子,无事可做,站在一旁。爹爹看他闲站,一时火起,随手把锯子打过来,砸在他的头部,血流满面。东家用烟丝帮他止血,没看医生。晚上回家,他哭了,他娘就骂他爹狠心。苦归苦,第二天他还是跟着爹爹去做东家生活。这一做就是七十八年,直到八十八岁高龄。
一九七三年正月十五,礼张和祥山头村的初中生张珠生来到寺前湖山村,拜一个六十五岁的老篾匠为师。当晚,他住在师傅家。第二天一早起床,他发现床上散落着一分、两分硬币,大约有一角钱,而他只有爹给他的五元钱,没有零钱。他跑去找师傅,师傅问他:“是不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人家丢的?”他一一否认,捡起硬币,放在桌上,烧火打水去了。事后,才知这是师傅在考验他。
最初的一个礼拜,张珠生待在师傅家里,白天蹲在地上补地垫,晚上膝盖钻心疼痛。第二天,他忍着疼痛,继续补地垫。师傅跟他说,熬过半月,就不痛了。后来,师傅带他出门做工,教他做人的规矩:“口稳手稳,天下走尽”,东家有东西不看,有话不听:吃饭的时候,先捧碗,再拿筷,人要坐直,不能“黄狗扒”,吃饭不能发出声音;东家的菜,只能夹面前的一碗,不能伸手夹远处的,平时不能吃肉,到活干完后才能吃一片。
有一天,师傅叫张珠生先吃晚饭。他一看是切面,桌上还有一碗肉,就夹了一片。第二天早上,师哥拷问他:“有没有偷吃肉?”他矢口否认。师哥又说:“坦白从宽,改过就是好同志。”他只得承认。当天晚上,师傅用篾尺打了他一顿,还罚他把所有的工具磨一遍。做完生活,张珠生到师傅家去割草籽,继续接受惩罚。
师傅还有一条规矩,学手艺期间,张珠生中途不能回家。这对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到了年底,师傅本该付给他二十块工钱,扣除送给他的一双扎箕、一个火熜以及伤风感冒的医药费,只剩下十三块。从此,他再也不愿回到师傅身边。
俗话说“廿年媳妇廿年婆,再过廿年做太婆”,从徒弟熬成师傅以后,有的篾匠忘了自己当年所受的苦楚,打骂徒弟;也有的师傅不打不骂,循循善诱。
花桥里黄宅村的篾匠陈顺伙做徒弟的时候,有一天补菜篮底,需要用二十四样篾片,怎么也做不起来。师傅看了,给他吃了一个“爆栗子”,在众人面前破口大骂:“昨天刚刚教过,今天又忘记了,你是饭桶啊!”此事对他刺激很大,印象很深。后来,陈顺伙做了师傅,先后带过四个徒弟,认为越是做不起来的时候,越是人多的场面,越是不能打骂徒弟。
一年到头跟锋利的竹篾打交道,篾匠的两只手被划得伤痕累累,“手指头斩得炀去了”,格外粗糙。山里有一个叫朱学顺的老篾匠,有一次,他的手指头不慎被竹篾刺了一下,也没在意。不久,手指头慢慢红肿,越来越胀,越来越痛,吃不香,睡不好。他几次拿出篾刀,想把手指头剁下来,都被家人劝住,盼着有一日脓透了,挤掉就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个过路郎中,看了他肿胀的手指头,说能治好,要两块钱,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天文数字。死马当作活马医,篾匠同意郎中的条件。随后,郎中用布条把篾匠的眼睛蒙上,叫村里的几个壮汉把篾匠的手脚死死按住,自己用小刀在篾匠肿胀的手指上猛然一刺,再用嘴巴从伤口中吸出脓水,吸一次吐一次,足足盛了一小碗,最后在伤口上敷药末,包扎好。经过一番折腾,篾匠痛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连帮忙的几个壮汉都累得汗流浃背。后来,篾匠的手指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花桥大头湾村有个老篾匠,叫周美兴,人称美兴师。他十一岁开始学手艺,师傅叫他一天到晚蹲在地垫上补洞,补好一个,像青蛙一样跳到前面,再补一个。为此有两句形容小篾匠补地垫的顺口溜:“身高没有工具长,从小离开爷和娘。蹲下身子补地垫,跳几跳几田鸡样。”
美兴师从小爱看戏、听戏和唱戏,戏班演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生活做到哪里。最长的一次,他一连看了三十五夜戏。村里有个什锦班,学唱《平贵别窑》,薛平贵出场之后,有四句念白“头戴金盔一点红,身穿盔甲响玲珑。红纱洞降烈火马,唐王驾前立大功”。唱薛平贵的那个人学了一个礼拜,还是不会念。有人提议十三四岁的小美兴试试看,果然一学就会。
“裁缝篾匠,门口等天亮”,篾匠的职业习惯就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常走夜路,黑灯瞎火,心里发虚。尤其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冷坞,晚上常有野兽出没,更加令人胆战心惊,自从学会唱戏之后,美兴师走夜路就不害怕了,因为他边走边唱,歌声解除了寂寞,驱走了害怕,还锻炼了身体。
到了七十岁,美兴师不做篾匠了,闲暇常与一班老伙计唱唱戏。这时,他的儿子周子清已经成为浙江婺剧团的当家小生,以演《断桥》里的许仙而远近闻名。他常常自豪地说:“没有我这个爱看戏的老子,哪有他这个会做戏的儿子!”
白铁匠
小时候,我跟妈妈去赶集,常听到街边传来“笃笃笃,笃笃笃”的声音。循声望去,只见有个胡子花白的老师傅正在敲白铁(洋铁),铺前挂满各式各样的器具,有畚箕、漏斗、喷壶、烟囱、水桶、火熜、洋油灯……
敲白铁没啥理论,全在实践。一要剪得好。一刀下去,或圆或方,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或直或弯,准确无误。剪多了,浪费材料;裁少了,成不了型。为此,预先要精确计算,里面包括三角几何等知识。而白铁匠像其他手艺人一样,没读过多少书,更别提数学知识了,靠的是师傅传授技艺,自己苦心琢磨,勤于实践,做到熟能生巧。二要敲得好。敲得不够,接不密缝,且不防漏;敲过头了,伤了铁皮,容易生锈。
白铁匠既能敲打新器具,也能修理旧器具。当时农家常用的洋铁锅,烧得日子长了,锅底破了,需要修补。如果是小破损,一般是用锉刀把破的地方锉平,用小刷子在上面刷镪水,将火上烧热的烙铁粘上锡料,补在破损的地方,过会儿再放在砧子上,用锤子敲平;如果是大破损,剪下旧锅底,换上新锅底,然后将两者咬合焊实。
一九七一年,家住浦江县城的陈怀林被县二轻系统的五金厂招工,拜了一个东阳师傅,做了白铁匠。他进厂第一年的工资十四块,第二年加到十六块,第三年出师时加到十八块,后来陆续加到二十七块、三十三块、三十七块,到一九八六年加到四十五块。后来,五金厂并入汽配厂,他不愿意去,就在县城四牌楼开了一家白铁店。
除了像陈怀林这样开店的坐商,敲白铁这行也有走家串户的行商。小时候,经常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白铁匠上门吆喝。他皮肤白皙,一脸络腮胡,刮得很干净,有点发青,不高不矮,不瘦不胖,模样斯文,不像手艺人,反倒像教书先生。

听长辈说,这位白铁匠出生大地主人家。他的爷爷广置产业,当年整条街上的店面房都是他家的;他爹开始败家,走下坡路;到了他手里,吃喝嫖赌,打架斗殴,把家产败光了,正应了“富不过三代”那句老话。
公子爱俏,姑娘爱钞。想当初,这位少爷出门买欢之前,上楼取钱,从柜子里抓整把整把的银圆,放进长布衫卷起的下摆里,装得满满的。下楼的时候,银圆太沉了,从长布衫里掉出来,“哗啦啦啦”在楼梯上滚得欢。他娘听见动静,知道儿子不干好事,也不责怪,反而说:“你拿这么多银圆干吗?好再拿一次的。”
有一次,这位少爷来了兴致,下杭州,游西湖。在湖边,他看见有一帮小孩在草丛里捡瓦片和石子,在湖面打水漂,玩得不亦乐乎。看到这里,他不假思索地从裤袋里摸出一把银圆,在湖面打起了水漂,似乎银圆不是钱,就是瓦片石子。
为了抖威风,这位少爷网罗了一帮不三不四的喽啰,前呼后拥。他每次跟人打架斗殴,总会使出程咬金的“三板斧”:第一“板斧”,摘下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作为武器掷向对手;如果偏了,再使第二“板斧”,捋下戴在手腕上的手表,掷向对手:如果还是不中,就使第三“板斧”,叫手下的喽啰一拥而上,帮他打架。那时候,乡下的穷苦人家连闹钟也买不起,而在他眼里,金丝眼镜和手表跟路边的石块也差不多。
除了嫖娼、打架,他嗜赌如命。平日无所事事,就叫家里的长工陪他一起赌,演绎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戏:
“少爷,我们都是穷人家,袋里没钱,哪里敢赌!”长工们说。
“没钱没关系,我借给你们。”少爷说。
“如果赌输了,老婆孩子就要饿肚皮了。”长工们还是不敢赌。
“如果你们输了,我把钱还给你们就是了。”少爷回答得很爽快。
“如果我们赌赢了,是不是也要把钱还给你?”长工们又问。
“不用不用,你们赢了我的钱,拿走就是了。”少爷以赌博来打发时间,根本不计输赢。输也是输,赢也是输,乡人把这种只输不赢的赌博,叫做猪头赌。他的名字里有个水字,于是人家在背后给他取了一个绰号——水瘟猪,倒也恰如其分。
家里出了这样的败子,就是有金山银山,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正好解放了,他把家产败光了,竟然变成贫农,省了一顶“地主”的帽子,因祸得福。
为了糊口,这位少爷学了一门敲白铁的手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正好印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古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