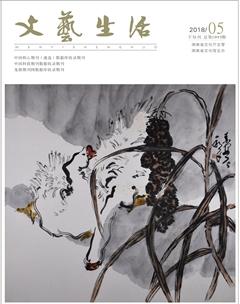论舞蹈与武术在艺术形式上的借鉴与融合
彭媛
摘要:中国艺术历史上有着“武舞同源”之说,这一说法起源于原始时期,是先祖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生存技能与自娱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武舞同源”不再只是体现生活场景、战争之功,而是有了更高的艺术审美标准。随后舞蹈与武术逐渐分流,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征,但在“个性”之外,舞蹈与武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仍存在着“共性”。笔者在舞蹈与武术相融相通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段进行舞蹈创作,对岭南优秀文化艺术——咏春八斩刀进行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舞蹈;武术;艺术形式;咏春八斩刀;武舞同源
中图分类号:J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5-0078-01
一、咏春八斩刀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一)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性
在岭南文化这片沃土之上,有着语言、建筑、画派、民俗节庆、戏曲歌舞、武术等不同特色的文化板块。其中咏春就属于岭南武术文化中的代表之一。咏春武术里面包括了广为流传的咏春拳法以及咏春器具——八斩刀和六点半棍。据说咏春八斩刀是咏春拳创始人严咏春与当时反清组织红船梨园弟子交好,在互相切磋武艺中,基于咏春拳的基本原理之上,红船弟子黄华宝、梁二娣等人创造出的刀法。后传至佛山人梁赞,逐步将刀法规整;及后传至叶问手中发扬光大。“刀无虚发,棍无双响”这是咏春里著名的一句话,代表了咏春器具的厉害之处。句中的“刀”指的便是咏春八斩刀。八斩刀因其有八节主要刀势而命名,包括:夹刀、掇刀、摊刀、耕刀、滚刀、一字刀、问刀、极刀。而笔者主要以咏春八斩刀的八节刀势为动作基础,进行舞蹈作品《义行天下》的创作。这个笔者将在下文进行叙述。
从上个世纪开始,“功夫”、“咏春”、“李小龙”这些标志性的符号,就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成为了中国特色文化的名片之一。近些年来,咏春功夫发展迅速。在广佛地区的一些武馆中,咏春八斩刀的武术技法得以保留与传承;在信息化如此发达的时代,咏春八斩刀被改编成记录片、电影,在全世界进行传播……“2011年,佛山市申报咏春拳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获得成功,于2012年2月由省政府正式公布列入广东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种种,是咏春八斩刀的传承与发展。文化既要传承也要发展,因为不同的时代赋予了传统文化不同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当肩负起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同时,迎着时代的发展,给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
(二)将舞蹈与武术相结合的作品创新
笔者在探索岭南文化——咏春八斩刀时,发现了刀的招式极具特色,它不仅变化丰富,且与舞蹈身体语汇有很多对应与相融之处。比如说:咏春八斩刀的第八式扱(xi)刀,腰带动手肘发力,使得刀的动势由上至下,形成一个抛物线。这与舞蹈语汇中的“风火轮”可以对应,且刀的空间画面与舞蹈空间的高、低空间相融。八斩刀中的“耕刀”的要领为:短、快、劲,而在舞蹈中可处理为收缩动作,并与带有爆发力的“跳”融合在一起。咏春八斩刀已有的招式元素给了笔者灵感、以及创作来源。因此,有了舞蹈与武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借鉴与融合。舞蹈作品《义行天下》是以岭南特色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创作基点,通过舞蹈、武术语汇配合道具舞美为艺术表现形式来编创的。作品是在武术与舞蹈的“结合”中,对咏春八斩刀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二、创作手段上的“形式之美”
任何艺术都包括了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特征,两者互相作用、不可分离。一般来说,形式脱离不开内容,内容也需要由形式来进行传达。那么研究形式之美,就不可以抛开作品形象背后的内容与意义。何为形式与内容?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其著作《情感与形式》中指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用现代符号学的观点来说,形式与内容就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能指”,是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即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所指能传达的思想情感或“意义”。
(一)表象之美
与常用的语言性符号不同的是“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表象性符号。”直观性是艺术“表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编导在舞蹈创作中首先要注意的环节。舞蹈与武术都是以人体为主要载体的艺术,给人以直观的形象之美。在作品《义行天下》中,笔者以传统八斩刀的八节刀势为基础,配合舞蹈肢体语言,进行了动作的线条性、造型性的再塑造以及队形空间的改变,从而使作品更具直接观赏性。咏春八斩刀的刀法强调快与劲,动作往往短促而有力,在此原理基础上,笔者通过将舞蹈中“长、直、柔”的动作加入其中,使得动作既刚劲有力又飘逸柔美。比如说:连续不断的耕刀动作,加入踏步翻身,在动作完成了3/4时,腰处带劲,手持刀往上挑至最高点后,紧接着一个低顿,蹭步横刀冉来一个有力的耕刀。如此,在原有动作的基础上,加入舞蹈动作的原理,使得动作的线条性更加突出,造型感更强,更具美观性与技艺性。
刀的步法主要以原地的二字钳羊马、偏身转马以及流动的战马、圈马为主,雖有流动,但比较单一。而在腿法上,最常见的是前扫脚、正踢腿、斜撑腿,这些腿法强调起脚最高只打到胸口,这样的要求对于创作中空间与队形的变化十分不利。笔者借助舞蹈中的跳跃、翻身来打破空间队形的局限,同时帮舞蹈动作的“极致性”运用到基本动作中去,使动作稳中求变,以简化繁。舞蹈创作中借助了刀的直观形象性来突出作品中“镖师”的人物形象,同时,舞蹈的线条性与技艺性使得武术动作更灵巧鲜活。舞蹈与武术之间的借鉴与相融,使得作品兼二者之长,推陈出新,更具色彩。
(二)意蕴之美
黑格尔曾说过:“意蕴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艺术意蕴指的是艺术作品内在的含义和意味。美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曾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里的意味也就是意义,是艺术作品的所指意义。而中国艺术自古讲究“象外之象”、“意外之韵”、“立象以尽意”,这正是艺术形式的意蕴之美。
在笔者的作品《义行天下》中,笔者运用了舞蹈与武术共有的动静疾缓规律与圆曲规律,来传达作品形神之美。“中国艺术追求‘狡兔暴骇,将奔未突的美感,那是未发前对力的凝聚”。在作品开头部分,笔者运用了大量的顿步、以及曲蹲的造型感,形成一种护镖途中“紧迫”、“压抑”的气氛。直到主旋律响起,舞者们从极静中缓缓而动、然后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形成了一条川流不息的“人群队伍”。此时动静的对比,以及动速的层层叠加,使得观众感觉到了舞者们“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若没有前面静的压抑之感,就突出不了其后畅快淋漓的流动之感。在作品中,笔者运用了大量的停顿,力求“飞动中含凝滞,越凝滞越飞动”之美感。如在双人舞段的设计中,四对舞者跳跃、奔腾、托举、旋转,在一系列密集动作过后,进行停顿:每对舞者背靠着背,手持八斩刀,眼神坚定且警惕地注视着远方。此时突然的动作停顿,代表着情绪上的一种转化,是敌人来袭的警觉。舞者们在一静一动中、在疾涩顿挫中,使作品中“沉着冷静、勇敢无畏”的人物形象得以凸显。
中国艺术向来追求“圆曲”的意蕴之美,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笔者将在下一章节中进行主要论述。武术讲究“松合圆展”;中国古典舞讲究“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扬先抑、欲冲先靠”,这无一不是“圆曲”的审美体现。“圆曲”的审美体现在:其一是动作弧形路线的意味之美;其二是一波三折、迤逦不尽的深邃之美。笔者在作品中既有表现古典舞韵律的“平立圆”的动作变化;又有来而反复的队形、空间变化,表现出连绵不断之感。如在表现镖师们抵御敌寇时,笔者采用一竖排队形的横向流动与空间变化。先单一的出4人,在动作未止歇时,再出4人,4对人发生上下托举、方位变化;其次冉出8人,进行交错的舞姿变化;最后合并成一竖排,进行连绵不断的动作变化,从前到后如“多米诺牌”一样进行反复流动。通过动作、队形、空间的反复变化,继而烘托出“紧张”、“激昂”的气氛。
三、结语
作品《义行天下》是以咏春八斩刀文化为题材,在传承岭南优秀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实践创新。在创作过程中,笔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挖掘、艺术特征的理解、传统文化的研究,初步探索了舞蹈与武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借鉴之因与相融相通性。未来,随着对跨学科领域更加深入的研究,舞蹈与武术借鉴与融合的探索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