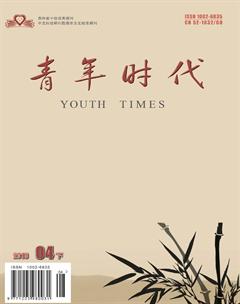还思想予思想者
赵航
摘 要:自复仇的延宕问题提出后,思想与行动脱节、缺乏行动能力几乎成了哈姆莱特最本质的特征。人们将太多期待置于哈姆莱特身上,并往往以“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为前提来评判哈姆莱特。纵然复仇行动表面看去是延宕的,然而延宕背后却是深刻而伟大的思考。以往研究者往往将哈姆莱特定义为“行动上的矮子”,本文将论证哈姆莱特思想的价值,指出他的理性之光以及对复仇的超越,“还思想予思想者”。
关键词:哈姆莱特;理性之光;复仇;超越
如果一味复仇,哈姆莱特或许只是挪威王子之流,其复仇的延宕与性格的复杂,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体现思想的伟大。当莎士比亚将他创造出来时,他就以不同于传统复仇骑士的形象屹立于世人面前,展现其独特的价值。
一、行动上的矮子?思想上的巨人!
被世人奉为复仇王子的哈姆莱特,并没有始终带着勇敢和坚定,积极地推进复仇行动的实施。相反,在复仇过程中,复仇行动本身一再延宕。当哈姆莱特父亲的灵魂要求哈姆莱特必须替他报仇时,哈姆莱特感叹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是哈姆莱特复仇行为的第一次“延宕”。在克罗迪斯祈祷和忏悔时,哈姆莱特在复仇的绝佳时机再一次犹豫,在他看来:
“我现在解决他,却是趁他把灵魂洗涤清净、准备成熟的时候,这能算报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一个更凶的机会:等到他喝得爛醉了,等到他正在发怒,等到他在床上放纵乱伦的欲情,等到他在赌博,在诅咒,或者在干什么一点也没有得救希望的勾当——那才砍倒他,叫他两脚跟踢着天,叫他的灵魂像地狱一样漆黑,直滚进地狱。”
由此,他错失了复仇的绝好机会。在一次次延宕行为的背后是一次次思考、怀疑和自嘲。例如著名的“生还是死”的自白。德国的弗·施莱格尔强调哈姆莱特“天性中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不停思虑的理智上,他行动的能力都完全破坏了”,表现了“人类心灵无法解决的不和谐性”。另一位批评家马尔里奇则指出,“哈姆莱特”生性是个哲学家的头脑,他有完成伟业的意愿与能力,但那必须服从他自己的思想而通过自己独立、独创和创造性的力量去实现”。批评家维歇把这种行动的犹豫归结为“思辨的过盛”。他说“思辨永远不会导致行动。思辨可以无限延长……而人在思辨中却寻找一个绝对恰当的时机,事实上这是没有的,永远也不会到来。”还有英国浪漫派莎评最重要的代表柯勒律治说“用幻想来代替实质”,最终“变成只会沉思默想的生物,而失去了他行动的自然力量”。
这些评论大都说明了哈姆莱特耽于思考和幻想而不善于行动,且多以“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为哲学前提。然鹅,哈姆莱特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大于行动的人,以一“权威”或“流行”价值标准讨论未免太过苛刻。哈姆莱特曾将自己与挪威王子相比,与“为了一点点幻梦和虚名的挪威小王子”正是“过去”的哈姆莱特,传统故事与复仇悲剧模式中的骑士英雄,但是,即使在挪威小王子面前感到惭愧,他仍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存在。具有“思想上的巨人”特质的哈姆莱特,展现了其长久的魅力与价值,使“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哈姆莱特”。
二、理性之光的闪耀
哈姆莱特的思想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理性,“理性之光”贯彻了整个复仇旅程。
首先,在面对父亲鬼魂揭露真相、面嘱复仇的第一反应是:“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他铭刻于心的,不是个人与家族的怨仇,而是由此而及的对时代危机的认知,以及自我对于时代、历史的使命的自觉。其次,面对父王鬼魂的控诉,哈姆莱特在第三幕第二场戏中叔叔暴露真相前,都是半信半疑的,他说他害怕“所看见的那个鬼也许是魔鬼”,会“趁我的软弱,我的忧郁”,“骗我去害人害己”,因此他还要搜寻切实的证据——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复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可能真正复仇。
再次,哈姆莱特在内心深处对以血还血的的复仇本身可能造成的负面伤害,有慎重的考虑。这一点在他要不要向母后复仇这一问题上暴露得很清楚。第三幕第二场结尾处哈姆莱特决定找母亲谈话前有一段独白,他一面强烈感觉到内心难以遏制的复仇欲望“我简直喝得下热血/干得出青天白日所不敢正视的狠极的勾当”,另一面他又竭力控制这种复仇欲望,特别是不要让复仇之火投向母后,他警诫自己:“我的心可不要迷失本性;不要让/尼罗(古罗马杀母暴君)的灵魂钻进我坚定的胸怀。/我尽管凶狠,可不要变成忤逆;我对她,口要出利剑,手不用尖刀。”这至少说明,哈姆莱特采取以血还血的复仇手段带有很大的被动性,他的本性更倾向于爱,他最初也是个“快乐王子”。
与莱阿提斯进行对比,哈姆莱特的理性意识更加凸显。莱阿提斯直言不讳地高喊“忠心,滚进地狱去!/信誓,叫魔鬼抓去!/仁义道德,直落到无底的洞里去!/我不怕自己下地狱。我意志坚定,/上天也罢,入地也罢,我不管,/有什么尽管来什么,我只要为父亲/痛痛快快的报仇!”只要达到复仇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在他看来,复仇是非道德、非理性的,是可以全都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蛮对杀父娶母之仇,哈姆莱特也没有丧失理性,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理性与动物性斗争的伟大胜利。
三、对复仇的超越
哈姆莱特对复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他对道德的秉持,更体现他对复仇问题的思考。
首先,哈姆莱特在初步得知自己的杀父仇人是自己的叔叔时,纵使满腔痛苦愤怒,“我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个下流女人似的,只会空言发牢骚……”,但仍保持怀疑,仍考虑到是否得体公正,尤其对象是他的亲人叔叔,这种道德原则是哈姆莱特对复仇的超越,促使他再次检查证据。
其次,他逐渐认识到,为父王复仇不仅是个人问题,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父母的悲剧和他所受的打击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他看到自己的家庭正在遭受的和整个社会正在遭受的,甚至全人类正在遭受的痛苦……”,以及“丹麦是一所监狱”,乃至全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监狱”,而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最终,他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样就将个人仇恨升华为对国家的忧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再次,他将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宫廷政变的切身痛苦感受,上升到理性的怀疑与否定。在第二场第二幕的著名对白中,哈姆莱特发出对人文主义者的“自然”、“宇宙”、“人”的观念的怀疑:“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人,并不能使我欢喜。”他对奥菲利亚的提问“你贞洁吗”、“你美丽吗”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审问。他的怀疑和否定,不仅是对人世、对人、宇宙,也是对自我的彻底怀疑与否定——“我们都是十足的流氓;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这样看来,哈姆莱特不仅远脱离领导那些仅有匹夫之勇的传统骑士英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崇拜人与自我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难怪有研究者说他不是个人文主义者了。
最后,他的思考上升到了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对现实人生采取什么态度这一人生哲学的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面对“苟活”还是“反抗到死”的活法的选择,人们似乎很容易拒绝“苟活”。然而哈姆莱特又尖锐指出“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且这未知的梦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更进一步指出“不可知的背后”,可能是“不可知的痛苦”,清醒粉碎“未来是一劳永逸地结束痛苦的天堂的幻想”,由此造成了活下去还是不活都两难的选择。由此,按钱理群先生的评价,“所谓哈姆莱特的忧郁、犹豫不决、缺乏行动性,正是根源于他对未来未知苦难的疑惧、清醒與正视——这才是典型哈式命题;这也正是哈真正的人格和事业所在——正因为彻底抛弃了一劳永逸地结束一切矛盾与痛苦的自欺欺人的精神幻梦,用彻底怀疑的眼光看待已知与未知的一切,就永不会停止独立思考、探索与追求。这样,哈姆莱特式的命题也就必然成为人类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自觉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也在一切自觉只是分子的参与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四、结语
哈姆莱特的思想之光,似乎超前了几个世纪,展现其长久魅力。或许,我们该对“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这一作为哈姆莱特延宕行为问题的前提提出质疑,“还思想予思想者”,才能更加正视哈姆莱特与《哈姆莱特》的宝藏。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丰富的痛苦[M].北京:三联书店,2015。
[2]肖四新.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朱宾忠.欧美文艺思潮文学批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4]哈罗德.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