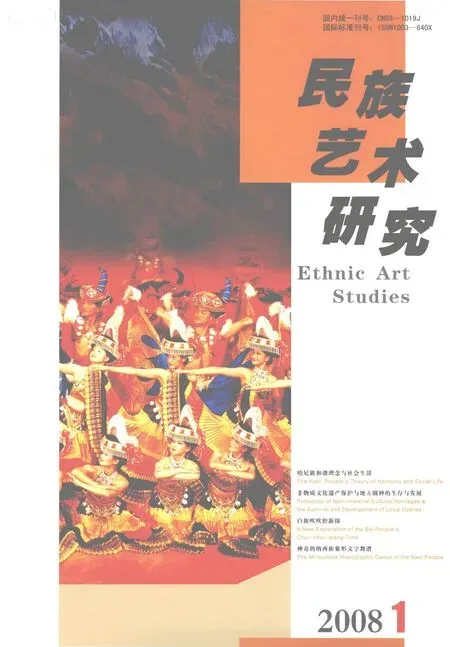国家文化工程中的声音记忆
——以集成志书中的音乐记录为例
李 松
一、背 景
人类对于音乐的记忆,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民族、地域的自我文化认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在文化研究领域,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关于共同体的文化“想象”使得记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此,将我国的传统音乐档案置于国家记忆的语境中定位,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话题。回顾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档案建设,粗略地说,随着声音记录传播技术的发展,主要以满足研究、传播、商业甚至是个人收藏需要,和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广泛存在。首先,如果将20世纪初至80年代为一个阶段,传统音乐档案主要是指出版物中的老唱片和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工作档案,它由相关机构或个人保存。同时,在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里,伴随着专业的田野工作,也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作为国家专门的音乐研究机构,它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时间段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再往前追溯,应该说在不同的区域,应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需求所遗存的音像资料,我虽然没有看到专门的研究成果,应该说主要留存于老唱片和部分电影厂、广播电台的资料档案中是大致的状况。总体来说,如果要总结这一时期的传统音乐档案,我认为,严格意义上,它不构成一个国家概念下的音响档案的记录,作为多元需求、分散存在的声音档案,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国家档案意识。
二、作为国家记忆的集成
另一个大的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从国家层面来做的传统音乐文化典籍工作,对传统音乐进行国家注册、登记和著录,是以“集成”工作为代表的。该项工作从1979年开始开展,包括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曲艺五个门类,分为《中国民歌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十个系列,统称为“十大集成志书工程”,它是和中国传统音乐密切相关的一个系统工程,十大系列丛书中有八部有传统音乐内容,四部完全由音乐内容构成。可以说,“集成”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民间的声音为重要内容构成的一种国家记忆。它是记忆的一个声音体系。“集成”是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实际上还有中国文联以及各有关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系统性的日常工作由文化部组建和管理的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前身)负责。就广义的声音记忆而言,传统音乐范畴的国家典藏,它在中国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收集工作中并非是第一次,但是就规模之大、全面系统(曲谱和文字等信息的注录)和声音的记录而言,它的确是第一次。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包括后来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以项目记录为主的工作,就全面性和历史资料的珍贵性而言,仍未有超过这个规模的国家工程工作。就此项工程的实施机制而言,“集成”是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负责总体的政策把握、组织管理、经费保障,在专业内容上集中全国有关机构和相关专业的学者,自上而下地组织各级文化系统和专业人员协同工作的系统工程。
关于“集成”这一大型工程的主要内容,首先,它是全面普查,是直接面向社区的。它要求音乐与曲谱同步,同时,它也对采集地点、表演者的相关信息等做了出版意义上的规范性的要求。包括演唱者、记录者、翻译者、整理者等,即对音像资料来源做出了出版意义上的标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它是以口头传承为主要记录对象,并以民族学的学术范式为主要出发点。这个工程不是跨文化研究,不是他者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研究,而是在地的,由各地区做的自我文化的记录。它只是由国家,由专家规定了统一体例,但是它依然是各民族、地区自己声音的表达,因此它更具有民族学的学术范式意义。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音乐学的“采风”,不是“采走”,而是由当地逐级向上推选。此外,关于田野作业规范的问题,当时也没有足够多的人才,而参与“集成”工作的人员构成则包括各地学者、基层文化工作者、社区文化精英(骨干),有几万人参与其中。各地学者主要包括大专院校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学的研究人员队伍,还有各省、各地方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中的持续参与者目前都成为已退休的各地方的音乐专家和顶级学者。而“集成”初期时,参与者也有很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大量的工作是对地方的群众文化馆站和地方的县、区级文化工作者做简单培训之后开始进行田野作业。但是这个过程也培养了一大批从集成中成长起来的专家与后来的“非遗”专家。
由普查开始的“集成”,全国动员十几万人在不留空白点的总体要求下做了全面的普查,在此基础上的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总体历时三十余年。目前“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还在编纂澳门和香港诸卷,并进行音乐形态的记录。澳门“民歌卷”也正在进行最后的整理。总体上,“集成”基本完成了对存在于大众日常音乐生活中的民族民间音乐做全面收集整理的工作。四部音乐集成(民歌、器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以国家卷的形式编纂出版了大约有11万首曲目。“民间歌曲集成”出版了30卷,收录了4万余首民歌,共有5250万字,主要为曲谱。前期普查的民歌资源总量约为出版数量的10倍,大约有40万首。而“戏曲音乐集成”的收录下限至1985年,主要包括代表性的戏曲传统剧目中的唱段。“民间器乐曲集成”则收录了2万多首乐曲,共5000多万字。“曲艺音乐集成”则涵盖了现存的或者说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并可以演出的包括300余个曲种,共2000万余首曲目,有4350万余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者说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典籍,就音乐而言,是这样构成的。音响或少量影像方面的资料情况,在音(响)、谱(简谱)同步的总体要求下,“集成”的普查与收集总量应该不少于50万首音响,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仅民歌方面收集和普查到的曲目大约为40万首。而戏曲、曲艺方面还有大量的资料沉淀在各类档案和介质里。此外,这些资料目前主要分散在各地的艺术研究院所,这个“各地”是一个抽象数字,暂且列为30个,如一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一个艺术研究院所。这些艺术研究院所大多是于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集成”工作而恢复的。此外,由各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一批艺术档案馆以及相关研究机构(音乐学院等)也保存了一批资料,特别要说明的是,有大量的相关资料保存在各个层面的专家个人手中。总的来说,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主要工作目标是文字和曲谱的出版,音响或少量影像的资料保存比较碎片化,存储方式相对落后,注册水平参差不齐。就记录的技术手段而言,与目前的技术条件相比则相对落后。需要说明的是,“落后”一词必然对应着相应的时代。尽管与现在相比较为落后,但在当时却也是竭尽全力。当时,在全国展开这样大面积的音像档案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在“集成”初期,小型的、专业的录音设备很拮据,而省级或者地、市级机构需要专款才能有一个相对好的录音设备。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这30年间技术手段的变迁非常巨大。20世纪80年代“盒式录音机”已经是专业的设备,但是现在一个手机已几乎囊括了当时一个省编辑部的所有设备,尽管如此,“集成”记录的大量资料,比如音响资料,仍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我们知道,从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中国民间音乐消失的速度令人吃惊。80年代中期,典型的、成熟的传承人大约在50至70岁之间。我们可以设想这些人现在的年龄以及他们下一辈传承的可能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资料具有不同的时间跨度。实际上,戏曲与曲艺的音响资料大量来源于早于“集成”时期田野采风的时间,而电台早期的包括20世纪50—60年代的播音以及老唱片,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
三、技术变迁与声音的处理
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相关工作在理念、策略、方法上的变化和创新。也会涉及抢救、记录、保存、管理、使用、传播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中心”作为一个国家的专门机构,自21世纪初至今,一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针对集成的存量资源进行比较规范的、专门的抢救性修复和数字化处理,专业化的注册和集中保存管理是从国家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的。在技术层面,对以多种技术格式保存的音乐信息,掌握的基本原则是:不做任何加工和美化,尽可能对原介质采取保护修复性措施之后进行数字化转换。这是一个要求非常细致、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海量工作,文化部为此在“中心”专门设立“重点实验室”,专门从事相关工作,十几年来已帮助各地多所艺术研究院所完成相关工作。
关于各种相关技术手段,首先是文化信息磁记录,即以物理和化学的方式对老介质的保存展开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老介质包括唱片、钢丝带、老蜡筒等。集成工作时使用的最多的介质是小的盒式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在80年代最多,也有一部分开盘带。按技术指标而言,这种磁记录的方式在25年之后,所有数据指标都会严重衰竭,珍贵资料面临二度丧失,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在整个音乐记忆体系中,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当大家对于某些资料还处于模糊的了解状态时,这个资料可能就已经报废了,相关抢救工作十分紧迫。因此,从21世纪初开始,“中心”这方面的工作就已经展开。而磁带的老化机理和人工干预的修复工作中有很多技术内涵,包括理化的处理方式。近几年“中心”的国家音响修复重点实验室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一批具有相关技术专利的工作基础,尤其是老磁带的覆膜等技术,很多要用专门研发的设备来完成。
其次是关于老唱片,对不同年代、不同规格的各种老唱片,“中心”也非常关注,其中有些专门技术处于领先,国内有很多机构以及学术团队、技术团队也在做此工作,但目前还没有统一方法。但我认为应该遵循不做任何加工和美化,尽可能对原介质采取保护修复性措施之后进行数字化转换的基本原则。
此外,我们的再记录和抢救工作还包括传统乐器的声学测量。在这一方面,“中心”与中国计量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科技系、内蒙古、新疆、延边、西南等地的院校乐器测量工作,总体技术手段已经到了消音室测量的水平,这是以前的技术手段完全达不到的状态。我相信,在亚洲我们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关于声音符号系统(记谱)的数字化,我们的工作首先是针对简谱,因为“集成”是以简谱出版的,目前,简谱的数字化乐谱,呈现出的符号系统是图像式的呈现,但要考虑的是,数字化的音符(无论是简谱还是五线谱)放在数字体系中的音乐语义问题。目前,“中心”对简谱在语义记录和表达研究方面进入了一个接近成熟的阶段,可以期待更好的交互性为记录、研究、创作、交流和传播等领域提供具有变革意义的应用基础。
四、技术变迁与文化的整体性数字化表达
这里的关键词是一个“元数据”。数字化后面紧跟着的问题是面对学术本体与艺术本体研究的压力。数字化所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真正的类型研究、形态研究和标准化注入体系。在“集成”资料基本找齐了的基础上,集成后的研究非常必要。严格意义上,没有这个研究无法完成全面的数字化。而如果仅完成了介质意义、单曲意义上的收集工作,十几万首曲目搜索起来将会没有头绪,非常困难。
“中心”数据库和元数据的建设工作自2002年左右开始已持续了十多年。第一批我们设立了7个项目。有一批音乐学家对民歌、器乐曲、宗教音乐、戏曲音乐做了宏观上的类型研究,但曲艺暂时没有做。现在召集曲艺音乐方面能在全国层面进行类型研究的人员很困难,这件事很遗憾中断了。这方面工作的复杂性,以汉族民歌中的劳动歌为例来对分类工作做简要说明,如劳动歌题级下号子的分级,就分到了7级,非常复杂。我参加国际档案学术大会的艺术学档案学会会议时,所有的外国专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做出这个分类,我回答说一定会做好,只能做好,因为它是国家记忆,因为中华文明有这个基本特质,就是多元一体,合而不同,如果连这种事都做不好,我们怎么落实文化自信?
应该强调的是,在元数据的系统研究领域,要注意与国内外相关标准化研究的兼容性,“中心”的主要关注是世界记忆、TC标准和图书、文物领域的标准化体系。如果试图数字化就牵涉到收集、记录、整理、表达与研究。这种元数据工作整备到精细化、条目化的程度,最小的文化单元如何定义,这些都是基本问题。而关于基础资源在数字化条件下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我们仍在探讨。这是关于数据标准的探索和研究,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给整个民族民间文化数字化表达造成非常大的工作压力和创造性空间,从人类学角度关注文化事项之间的关联,这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研究。我们非常希望大量做本体艺术研究的学者、研究者以及学生们能够多参与其中,这里的学术空间非常大,也非常有意义。
以学术研究和新技术应用为基础,“中心”开展的对于地方音像资料的抢救工作。近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常态,主要以省为单位逐步展开。例如四年前,我们把云南省“集成”中的民歌和器乐曲的所有资料都做了数字化,数量大概有2万多首。之后,我们与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仔细协商后给了他们标准化的标注体系(或者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标注体系),请他们做标注工作。他们请回了部分做“集成”的老同志回院工作一段时间。而一个月前,我询问他们的院长具体损失数量,他说大约为5%。这个损失指的是尽管音响仍完好,但是相关信息丢失,包括记录者、录音地、歌词内容等不清楚的问题,这些几乎要报废的声音大概占5%。这已经是万幸,因为这些音响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当初做田野的人不在了,实际上它的价值就会变得非常低。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二度流失的现状和二度抢救工作。
这方面工作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整体性”记录。它是以学术视野的扩展为基础的,这方面,“中心”正在组织实施的两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和《中国史诗百部》。这两个大型国家项目当中,从可视听和完整性两个学术指向上较之集成工作均有较大的拓展。
《中国史诗百部工程》与“集成”有所不同,它除了对传承人的完整演述做可视化记录以外,它也是语境化的记录,记录社区文化生态、传承人的生活状态等。它要求资料的标准化注入,包括语言和社区表达等,还对技术体系也有规范要求。总体上来说,它要求资料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对各种文化关联性因素的关注。它的视频记录所具有的不仅仅是传播意义上的,而首先强调的是国家档案的意义,它是完全按照人类学和音乐学的一些规范要求做全面的记录,而更加具有学术意义。这是后集成时代的显著特点。另外就是《中国节日志》项目中的《中国节日影像志》,是以影像的方式记录节日文化,当中包括大量声音、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仪式音乐)的记录。其实,拍摄影像之后的工作还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包括海量资源需要迅速整改,这也给标引带来了压力。据我所知,一般的科研机构所做的视频记录以及我们所拍摄的照片都呈现出获取快、著录慢的“消化不良”状态,也就是缺少背后适当的资料体系来支撑。很多学生的田野报告、学术论文在写完之后,剪辑好的片子被认可并传播后,剩下的资料实际上非常碎片化,而且损失非常大,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被积累。为此,特别希望所有的学术机构,应该高度关注数字化背后的资料积累研究和实际应用。
以上的《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百部工程》这两个项目的影像工作,全国有子课题250个,即250个国家重大课题的子课题,而每一个课题都是由一批对当地文化有深刻了解的专家组成。仅仅就影像记录而言(还未涉及文本工作),队伍中大概有2000-3000位硕博研究生参与其中,以及接近100多位各学科的博士生导师们。这两个项目的时间跨度均为8至10年。“节日志”目前已经进行了七年,大概还有三年结束,“史诗工程”应该已经进行了四年,可能还需要四、五年才能结束。所有的音像成果除正式出版的以外,最终需要碎片化,即做成数据库里面的文化“切片”,“切片”是“颗粒度”合适、可操作的一种文化资源,这是这个项目的总目标。这个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主要的参与队伍90%以上是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和老师。
总体上,要将国家记忆与大众生活、艺术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推进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推进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文化保护、传承与创造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