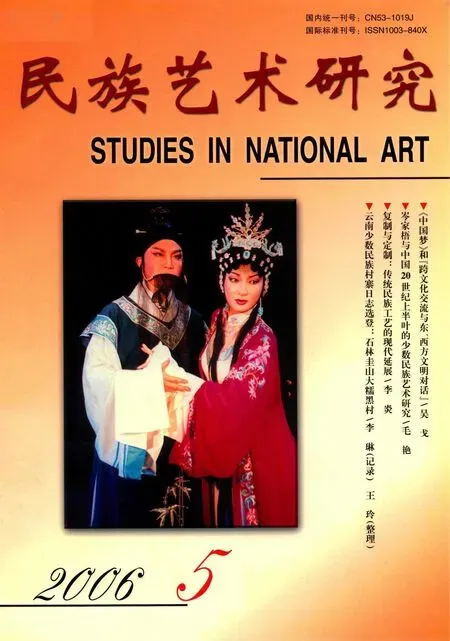再思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问题
赵书峰
在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理论的影响下,当今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学科边界模糊,更加强调研究理念、思维与视角的音乐学理论研究。然而,在强大的西方学术话语表述语境的冲击下,致使包括中国音乐学理论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严重的学科身份认同危机的尴尬局面,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有部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者纷纷提出构建具有 “中国学派”②魏柳塘:《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之形成及其特色——清商乐研讨会纪略》,《人民音乐》1992年第11期,第8-10页。特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即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问题的建构。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真正系统化、规模化地进入大陆音乐学界 (以1980年的 “南京会议”为里程碑)。此时的中国大陆刚刚进入思想观念的转型时期。受此影响,学界开始吸收、借鉴西方音乐学研究的学术理念、视角、思维展开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然而,此后的数十年从大的研究趋势来看,主要还是对我国各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形态分析为主。从1980年、1982年前两届 “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①②《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1980年第2期,第151页。看出,只有高厚永、董维松、沈洽先生的文章涉及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史、理论与观念、研究动向介绍与思考,其他学者提交的论文主要还是针对民间音乐的“五大类”展开的形态学、乐种、史学、乐律学等方面的分析研究。③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音乐研究》1980年第4期,第8-25页。可以看出,“南京会议”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一大批地方基层民间音乐文化研究者大多还是基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路向进行的学术考察研究。比如,1984年8月召开的 “全国民族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 (沈阳片)”,主要还是集中于研究汉族传统音乐 (包括民歌、戏曲、曲艺、器乐和歌舞音乐)结构形态的研究。④陈应时:《开创民族音乐形态研究的新局面—读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沈阳片论文》,《中国音乐》1984年第4期,第46页。然而,同年7月召开的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贵阳片)”会议上,在 “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的研究中,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念展开对我国各民族民间音乐 (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正如本届会议综述内容中指出:
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从方法上开始注意了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既注意了民族民间音乐形态方面的微观研究,又考虑到它与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边缘学科的宏观方面的因素。强调了要从少数民族生活土壤中探源溯流,以少数民族的生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更多的是从音乐形态去考察和研究,在民族民间歌曲、戏曲、说唱、器乐音乐、歌舞音乐等五大类音乐的研究方面卓有成效。今天面对复杂的文化现象,就不能再囿于该族音乐的形态分析,而开始注意研究民族文化艺术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氛围,民族文化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分析在某些民族文化中保留的文化沉积现象和周围各族文化的融合现象,又考虑到民族迁徙、社会变革对其文化的影响,使我们的研究有着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⑤甘亚梅:《民族音乐学的盛会——第三届民族音乐学 “少数民族音乐专题”年会》,《人民音乐》1984年第9期,第40页。
所以,从 “第三届民族音乐学学会 (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研究)”研讨内容可以看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思维已经开始运用到我们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之中。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一批从美国、中国香港高等院校毕业的民族音乐学博士为代表,他们开始针对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展开了系统性、区域性的学术研究,如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华南卷、西北卷、东北卷、华中卷等等成果的系统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才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发展与传播时期。这批民族音乐学博士学成归来后纷纷在国内各大艺术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系统开设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并招收该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可以说为民族音乐学理论在中国音乐学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储备与智力支持。与此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界的两大学派⑥当然笔者的这种界定是受到美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历史的影响。(即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学派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人类学派)的 “博弈时期”,并且上述两者之间都在不断地提出立足学科本位的学术诉求。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仍然坚持注重以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分析为主的学术研究路向,强调对律、调、谱、器的分析研究,同时在受到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人文社科理论的影响下,也兼顾与音乐相伴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研究。而具有 “人类学派”理念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人类学)者则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范式,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人文社科理论充分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更强调音乐与其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将音乐的风格特征与文化象征所指的深层内涵置于当下的音乐表演语境中进行分析。重点分析考察形成这种音乐风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是由哪些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导致的?因此呈现出鲜明的人类学特性的研究。当然两者之间主要的分歧就是: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过于强调音乐形态的本体分析,过于将音乐形态的结构语法特征剥离其原生性的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考察,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则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 “去音乐化”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越来越偏离音乐本体研究的轨道,形成了一种“去音乐化”或 “泛音乐化”的学术研究。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所吸收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一种社会现实的表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语境不同,所以不能用西化的理念来表述与阐释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上述双方 “博弈”的问题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既不要盲目地做西方学术理论体系的 “搬运工”与 “拿来主义”,同时也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一味地排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于中国音乐理论所给予的研究启示与贡献。
二、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理论表述体系的提出
针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个性特征,以及面临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强大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早在1982年在北京 (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届年会”筹委会提出的口号中明确指出:“……尽早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①董维松:《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筹委会在京举行》,《中国音乐》1981年第4期,第41页。可以看出,正是基于在西方学术话语的强烈冲击下,近年来包括老一辈的学者以及多位年轻学者纷纷提出构建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的母语表达体系②主要有:胡建 《建立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范式的几点启示——读黄翔鹤先生文集<黄翔鹤文存>的思考》(《交响》2011年第9期,第145-151页)、余鑫 《质疑 “本土化”——民族音乐学研究之我见》(《音乐探索》2004年第4期,第70-72页)、汤光华 《音乐文化模式的选择与整合——兼谈民族乐学的本土化》(《交响》2013年第3期,第35-39页),等学者的研究针对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问题从不同角度与立场给予剖析与回应。,即 “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化”或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如有学者认为:
目前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队伍,在长期的摸索中,已逐渐创造与掌握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田野作业”与文献学的结合;文化人类学 (即社会人类学、结构人类学、民族学)观念的确立及其研究方法之运用;唐宋伎乐制度的宫、官、营、家与当代民间音乐及宗教音乐的俗、巫、僧、道的“八方考察”;整体、系统、全方位、立体化地研究问题等。……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家们正在采用的这套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是历经漫长的甘苦岁月后共同创造出来并完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带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这标志着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中的中国学派,已经在20世纪九十年代形成!这个学派的特色及其个性,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质,因为它的前身是音乐形态学、社会学等综合化的 “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及历史音乐学领域的 “中国音乐史学”这两支队伍 (的会合)。③魏柳塘:《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之形成及其特色——清商乐研讨会纪略》,《人民音乐》1992年第11期,第9页。
从上述内容看出,有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的 “中国学派”已经建立与形成,但是,当下的学者为何还在各种学术会议场合继续倡导构建中国 “本土化”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理论话语体系呢?笔者认为,这说明构建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的问题至今是学界探寻的一个学术难题,因为其理论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梳理与总结。同时这也是基于当下西方强大的学术话语体系造成的学科身份危机而做出的一种反思与回应,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成果与精髓。还有学者认为: “‘南京会议’以来,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体系理论建构的探索,反映出相关社会群体通过国学——科学——学科之系统性学术理念,自觉承担重塑 ‘国家认同’与 ‘民族精神’等文化使命的社会实践过程。”①钱建明:《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多维共生及学科影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2016年第1期,第19页。所以看出,近几年以来,陆续有学者在各种学术场合仍然在为倡导构建中国音乐学本土化理论的表述体系呐喊。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届学术研讨会”②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网站 [EB/OL].http://yy.zjnu.edu.cn/2017/0830/c1371a204908/page.htm.,就是为构建中国音乐理论本土化的表述体系做学术探讨。
三、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问题的理论思考
首先,当下在多学科互动交叉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在逐渐走向相互吸收与融合阶段。比如具有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就是有别于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仅注重音乐的共时性研究,开始注重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学术思维范式的研究,可以说丰富与弥补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的缺失。中国民族音乐学在大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由早期 “水土不服”到现在相互彼此融合的局面来看,两者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研究)之间彼此不再 “剑拔弩张”,而是携起手来共同建构具有中国 “本土化”特点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范式研究。同时,两者之间也不再针对研究对象、学科理念发生激烈的论争,而是逐渐意识到面对研究对象不能做静态、孤立的理论分析与描述,而是应基于音乐表演活动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进行整体关照与考量。尤其意识到仅仅做孤立的抽取与剥离文化语境性质的静态的乐谱文本分析,很难完整表达音乐文化的所指。
其次,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过程就是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相互交流、吸收与融合的产物。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与内特尔早期提出的民族音乐学 “复数”③④内特尔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复数概念 (Ethnomusicologies)。他认为,当印度学者学习了西方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当地音乐中运用了印度传统音乐研究和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后,他的研究已不再单纯是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而属于印度的民族音乐学,因此Ethnomusicologies可以包括印度的民族音乐学、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日本的民族音乐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西方的民族音乐学也仅仅是Ethnomusicologies的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笔者认为就是指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问题)概念不谋而合。因为任何新事物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语境中必然经历博弈到融入阶段。因此,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坚持各自学科本位的基础上,彼此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两者都在基于西方学术理论思维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理论精髓来反思与填补自身的学术弊端与学术盲点,为构建具有 “中国学派”特点的民族音乐学理论表述体系进行着各自的努力。正如项阳认为:“虽然学界有观点认为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代表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时下有各自独立存在的空间,但不能不看到两相结合可能更具学术优势。虽然研究有侧重,但整合起来会取长补短,毕竟面对的是同一学术对象;以民族音乐学为学术理念进行研究,更是要倚重传统音乐理论所积淀的诸种学术成果,绝非另起炉灶、对既有研究成果视而不见,那种不尊重前辈学术积淀的研究难以修成正果。在以民族音乐学为方法论的学术实践中,把握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以乐为主线拓展学术领域,可以真正彰显学术优势。”⑤项阳:《伍国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拓与践行者》,《中国音乐》2012年第1期,第58页。杨民康认为: “音乐 (形态)分析、音乐学分析和民族音乐学分析(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文化分析)被视为可供中国传统音乐 (含汉族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进行选择的三种典型的音乐分析范式,彼此之间存在共性、个性之分。”①杨民康:《音乐形态学分析、音乐学分析与民族音乐学分析——传统音乐研究的不同方法论视角及其文化语境的比较》,《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第69页。
第三,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必将是跨学科交叉互动背景下的产物。一些学者认为过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势必导致 “去音乐化”问题的产生。笔者认为,用跨学科的理论思维共同观照音乐本体,是为了 “深描”音乐表象背后深层的文化逻辑结构,绝不是“去音乐化”或 “泛音乐化”的研究。笔者在 《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科跨界趋势》一文中谈到:“少数民族歌舞音乐文化是作为某一族群最原始、最本真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存在的,它更强调作为文化象征性质的民俗功能,与真正的作为审美功能的舞台化表演相差甚远。面对这样的音乐文化样态,我们要重点观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表演形态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民俗信仰语境的互动因素。我们更倾向于将少数民族的歌乐舞表演视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而不是单一的艺术形态的存在方式。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术定位与研究理念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的文化特性、艺术本体样态、音乐文化的族性而定。所以,杨民康研究员认为的 “艺术切入、随缘选择”话语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诠释与回应。”②赵书峰:《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科跨界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 (艺术学版)》2016年4月18日。试想,当我们将音乐本体剥离出其依附的原生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与考察,我们只是看到了音乐的 “大动脉”框架,而忽略了为之提供生存环境的肌肉与新鲜血液,甚至是“毛细血管”的存在。正如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年鉴派史学家认识到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是毫无生命的,费弗尔即明确指出:‘所有的发现不是产生于每个 (科学)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产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交界线,在这些地方,各学科相互渗透’。”③何兆武,陈啟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页。比如,当下的音乐表演体系研究需要心理学、美学、符号学、传播学、社会学等相关人文社科理论的支撑来开展研究。因为,表演者技术流派与风格的形成在某种情况下是受到受众阶层与知识结构互动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也与表演语境中的声场、剧场以及与观众的互动效应密不可分。
第四,中国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过程决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学科思维。当前的中国音乐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将音乐学学科边界划分的得格外清晰。部分学者仍然坚持学科的本质主义思维,人为设置音乐学学科之间的边界,一味地搞学科认同,尤其在学科问题上主观地设置学科边界,对于其他跨学科的知识与理念不认同也不接受。有学者指出:“学科与学科之间,由于各自研究对象、方法及表达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使不同学科内部逐渐建立起了自身学科的学科规范和标准,造成了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封闭。在同一领域的教师,形成了一个以学科为中心的‘圈’,圈中的人们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念、工作模式、作业方式等,人为地使得学科壁垒的封闭性更加坚固。”④邹农俭:《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的必然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5页。然而,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拓展与深化,其学科之间的边界逐渐走向模糊,甚至是消解。当下,我们再用本质主义的学术思维看待中国音乐学学科发展问题,难免有点保守,过时。纵观欧、美、日等国音乐学学科之间只有方法论或学术理念的不同,没有研究对象的差异。音乐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性研究已经成为当今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趋势。比如民族音乐学与音乐美学之间的交叉性研究,音乐科技研究领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性研究,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学科无边界,理念最重要”,这是当下中国 (民族)音乐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潮流与趋势,也是学科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学术诉求。正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桑兵教授认为:“摘下单调的有色眼镜,打破学科的此疆彼界,能够贯通无碍,入木三分。”①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封底语。
第五,构建基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髓基础上的民族音乐学分析模式是民族音乐学“本土化”的学术诉求。正如项阳在评论伍国栋先生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时认为,他是 “在引入外来学术理念的同时将其消化吸收并用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探索的实践之中。经过多年对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系统梳理并加以夯实,然后将既有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两种学术理念整合,从而形成‘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②项阳:《伍国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拓与践行者》,《中国音乐》2012年第1期,第56页。我们知道,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结构的深层逻辑结构具有典型的东方传统美学与哲学特征,因此,结合母语化的民族音乐学分析模式,以局内人视角的音乐学分析表述,才能相对合理与接近真实的一种学术表达。比如,中国民间音乐的旋律形态发展模式不能用西方曲式学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因为,西方曲式学分析概念体系的形成与的发展是受到古典音乐作曲家的审美创造、生活的时代特征、审美理念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综合影响而致。而中国传统音乐旋律的形态结构多是一种民俗生活语境下即兴、互动建构而成的一种音乐文本。这些音乐文本的形成绝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地丰富发展、补充的,因为不同的表演语境中受其他社会原因的影响互动下形成的表演文本与上一次的表演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一个 “去语境化”“再语境化”③④理查德鲍曼认为,表演意味着 “从来不是第一次”,其本质在于话语的去语境化 (decontextualisation)和再语境化 (recontextualisation)当中,而后者尤为重要。事实上没有一个表演能够原封不动地加以重复——表演总是呈现出新生性维度。的表演。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仪式音乐基本上是即兴的,变化性的扩充反复建构而成的,用西方音乐分析的理念来说就是以一个母体为基本元素的变奏而成的,是一种 “变奏曲”的性质民俗仪式音乐。所以,我们在分析民间音乐的各种表演文本时,不能脱离其文化语境的音乐形态的分析与描述,而是将其音乐置于其具体的表演语境中进行动态的分析,我们不能对其音乐文本 (乐谱)做静态的分析与描述,而是要结合表演语境 (表演前、表演中、表演后)⑤杨民康:《以表演为经纬——中国传统音乐分析方法纵横谈》,《音乐艺术》2015年第3期,第110-122页。三个过程进行立体观照。所以,当下的民族音乐学分析研究不能完全基于乐谱文本与音声 (音乐产品)的静态分析,而是将表演者在特定表演场域中的互动对象 (人、神),表演者 (音乐文本制造者的心理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因此看出,当下的民族音乐学分析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分析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分析模式不断地进行理论升华,逐步摸索一种具有中国 “本土化”特征的理论建构与话语表达。当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分析方法要视研究对象而定,比如中国西南与西北少数民族音乐在音体系上区别很大,如南传佛教音乐、西南道教音乐文化圈内的少数民族音乐与西北伊斯兰教音乐文化圈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之间在旋律样态上区别较大,相比而言前者的旋律结构与形态相对较民俗化,即兴性因素较多,而后者的旋律形态与发展手法较为丰富与复杂。如西北区域内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音乐的旋律更注重音乐的节奏与旋律形态的艺术化表达,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旋律形态结构更强调内敛化情绪下的一种民俗生活方式的社会化表述。有学者认为,“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现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套用汉族乐理的观念描写少数民族音乐形态,或套用某种既成的乐理观念描写地方音乐风格。”⑥杨燕迪:《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4-75页。所以,当下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分析应主张多元化的分析模式,应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取适合的音乐学分析路径,因此看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分析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动态开放性的分析为主。因为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分析与传统音乐研究的分析理念不同,前者是将音乐文本的风格特征与建构过程置于当下的表演语境中进行分析。尤其是注重语言学层面的分析,将语音学、语义学、语用学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将音乐在场的声音符号代码赋予语音学范畴的分析范围,而在场语境中的声音代码符号的所指系列与表演语境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符号与逻辑内涵则属于语义学的内容进行,最后每个当下的音乐活动的表演所产生的声音符号的背后意义,只有置于当下的表演语境中观察声音与民俗仪式文化象征的互动指涉时,才能真正观察到声音符号代码具有的实际意义。若是一个空洞的所指,即零语境或不在场的静态的声音产品 (主要是指乐谱),则没有实际的文化含义。因为这种静态的乐谱文本已经脱离了语境,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所指。
第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过程的产物。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当然还不包括民间的口述历史文献,这些丰富的官方历史文献与民间私家文献的相互补充共同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这些文献不但包括历代王朝系统化的官方历史文献的编撰,同时民间的各种笔记、小说、家谱、族谱、碑刻、方志等为当下的中国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来源。当下学界倡导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矫正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中缺乏历史性研究的弊端,同时也丰富与开拓了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论与视野,因此可以说属于典型的民族音乐学“本土化”理论研究。当然虽然这个概念不是中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但是这是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在传播到世界各国 “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种学科反思,同时也是学科理念与视角、思维的一种调试与补充,当然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功不可没。从 “第二届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 (1982年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内容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率先提出音乐史学应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畴。①《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届年会 “会议纪要”》,《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第1页。虽然理查德·韦迪斯 (Richard Widdess)、蒂莫西·赖斯 (Timothy Rice)、谢勒梅 (Kay·K·Shelemay)等等学者都率先关注到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性研究。但是真正从事历史学性质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还是得益于中国学者的对其传统音乐文化的考察与研究。
第七,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是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过程的一种尝试。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就是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研究。因为,由于多种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与周边相邻国家较多,因此,跨界族群也是当下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中最具特色的研究对象。所以,自2011年9月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 “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论坛作为里程碑,可以说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 (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个热门词汇。同时,这也是中国学界向世界民族音乐学提供的一种较新的学术贡献。正如张伯瑜教授认为:“在以往的数十年中,中国学者跟随美国学者学习,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是,我们贡献于世界的认识却很少。未来能否有所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的理论是否有独特的视角,且又能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视角,即跨界族群的音乐研究。”②张伯瑜:《人群关系: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第6页。虽然其他国家也存在跨界族群现象,但是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相邻的国家十分多,所以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特色。当然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明显是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界有关跨界族群研究的影响。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当然也会涉及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同源族群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同时也会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的政治、社会等外部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跨界族群涉及人员的流动、文化的迁徙必然导致文化的濡化与涵化。因此,我们必须要结合分析音乐差异表象背后同源族群在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中所具有的不同的深层叙述逻辑与文化表征。所以,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过程的产物。
四、面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问题质疑的反思
目前针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问题时常会有一些 “杂音”出现,如有人认为学科主要过于依赖西方现代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充当西方话语理论的传声筒,“拿来主义”等等。为此,有学者近两年分别在不同期刊撰文,针对 “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质及研究局限”“民族音乐学某些观念的片面、绝对以后现代发展的极端倾向”“民族音乐学传人后对我国已有传统音乐研究的否定”,①杨善武:《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八届年会上的发言》,《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21-23页;杨善武:《民族音乐学的西方根源西方视角与西方观念——<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质及研究局限>之一》,《交响》2015年第4期,第5-12页;杨善武:《民族音乐学某些观念的片面、绝对及后现代发展的极端倾向》,《音乐研究》2015年第6期,第72-85页;杨善武:《民族音乐学传人后对我国已有传统音乐研究的否定—— “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一》,《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20-35页;杨善武:《从梅里亚姆的界定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质——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质及研究局限”之二》,《黄钟》2016年第1期,第36-45页。等等问题给予了深刻的批评与反思。虽然这些研究成果言辞较为激烈,及其学术观点存在诸多商榷之处,但是应该足以引起我们的学术反思。比如有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理论从根本上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否定②杨善武:《民族音乐学传人后对我国已有传统音乐研究的否定—— “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一》,《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20-35页。,但是纵观学科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其事实确实是那样的吗?其实不然。如前辈学者伍国栋先生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伍先生不仅拥有深厚扎实的传统音乐研究的理论功底,同时也善于吸收与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充实到自己的研究中,绝不是削足适履式的学术研究。他的 《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③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的研究理念就是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充分吸收、融合后的产物。所以,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难道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理论的否定吗?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是相互的借鉴、吸收与融合。虽然还存在某些消化不良的现象,但是不能否认民族音乐学理论与研究观念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张伯瑜认为:“1980以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之间便开始了一种 ‘暧昧’关系。各自独立?还是相互融合?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共同之处是,无论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还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两者都受到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影响。”④张伯瑜:《人群关系: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第5页。比如,当下有学者尝试运用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念,为我国传统音乐的 “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提供很多智力支持。因为,应用民族音乐学是基于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基础上,将研究成果运用到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中。因此,盲目排斥西方理论其实就是在走向自我封闭的学术语境,试问,当下我们在不断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难道不是西方的学术表述体系吗?
其次,针对某些学者质疑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观念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一个发展态势,是对启蒙主义运动以来注重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绝对主义 (尤其是实证主义)思想观念的一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理论根本上是对元理论的一种否定 (利奥塔语)。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史学并不否定过去的真实不妄的存在,而只是强调,由于文本性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触知过去;而任何通过文本来对过去企图有所把握和领会的努力,就都已经注定了要包含主观的、解释的因素在内。”①彭刚:《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当下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囿于本质主义的思维导致无法全面解读的文化现象,我们是否可以结合反本质主义理论进行解读呢?如清代编户齐民背景下,湘、桂、粤过山瑶多被编为汉民,从此可以享受科举,教育等分享社会资源的权力,由此改变了他们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所以,族群边界的移动绝不是由文化趋同性唯一特征决定的。同时,在处理汉族与少数音乐文化的互动研究时,我们不能只关注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运用,而忽略了少数民族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反作用。换然之,我们不能只关注从 “中心”到 “边缘”的单向流动所造成的文化涵化,同时要看到 “边缘”对 “中心”的反作用影响。因此,面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小甫教授认为:“世纪之交,学术研究方法呈现一些新的动向,最明显且有较大影响的一个是社会科学理论对人文学术研究的渗透,还有就是后现代思维方式 (认识的语言转向,从而突破了 ‘唯心’ ‘唯物’的畛域)渐次为学界所认可和熟习。……于是尝试借助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重新观察、分析和认识我所熟悉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以及内亚史,取得了一些研究心得,……我认为这些都从不同层面进一步发掘了史料的价值,提出了更具广泛性和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②王小甫:《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集》(自序),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7页。当然,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过度强调对 “元理论的否定”的学术理念,比如新历史主义史学研究中对兰克实证主义研究的否定,质疑传统史料的真实性,以及史料的主观与有选择的书写等等问题我们要给予认真对待,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掉进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五、中国民族音乐学“本土化”概念的审思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思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概念问题。即,何谓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包括哪些?是不是凡是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念展开对中国境内流播的所有音乐文化事项的研究就是 “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国学者的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 (或跨界族群中的国外音乐部分的研究)是不是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学者的国外传统音乐研究 (或中国学者的 “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是不是属于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范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是不是就只包括 “中国学者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等等问题,上述关于 “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与范围以及学者的研究身份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所以,通过对上述概念的分析与反思可以看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概念的提法在很多概念问题上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其次,当下的学界并没有真正归纳出具体化、系统化的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理论表述体系。纵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虽然有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已经形成③魏柳塘:《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之形成及其特色——清商乐研讨会纪略》,《人民音乐》1992年第11期,第8-10页。,但是结合当下学科的发展现状看出,这种断言未免为时过早,其实它目前仍然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笔者认为,所谓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过程,就是基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分析理论基础上,充分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知识,来解读与阐释音乐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民俗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做 “搬运工”式的复制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分析理论来分析研究对象,而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语境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模式。如果是这样的结局,我们谈中国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概念不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了吗?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也有必要深思,构建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理论话语表述体系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以及中国境内流播的所有音乐事项的研究是否真正有效?因此,谈中国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包括哪些内容?我们在一味地强调构建学科的母语化理论表述体系同时,是否也曾思考过其学术范式是不是万能良药?比如是否适合对城市中的流行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以及海外民族音乐的研究。我们知道,上述音乐事项结构的生成特点有的并不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理论的分析特点,难道我们可以套用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削足适履的分析与描述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术思维是不是又陷入了 “汉族文化中心论”的怪圈?或者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理论相比,是不是陷入了 “换形不移步”的尴尬状态。所谓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汉族传统音乐的结构分析方法,因为,汉族传统音乐的结构分析相对系统与体系化,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大多依附于特定的民俗语境中的多以即兴性的表演为主,缺少所谓的系统与体系化。所以,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理论话语体系的分析对象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成语境中的,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音乐事项的研究,但针对中国学者 “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事实上是无效的,因为国外音乐事项的本体语法特点并不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逻辑生成的,所以无法运用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理论体系对其进行分析与描述。
面对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问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研究的理论范式是否具有有效性值得思考。尤其是受西方音乐语境影响下的传统民俗音乐文化出现很多重构问题,那么假如我们面对这些按照西方音乐思维重新 “发明”的 “传统”音乐的研究时,我们运用 “本土化”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是否具有有效性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理论研究范式决不能一味地排斥西方音乐文化的理论表述体系,而应中西相互贯通,使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选取合适的理论分析模式。正如杨荫浏先生认为:“世界的音乐,已随着西洋的文化,渐渐地流注入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有接受的必要。国乐最后有与世界音乐互相融合的必然趋势。为准备这个时期的来临,为求将来融合的适宜,我们便不得不为了国乐而研究一些西乐的理论与技术。因此,用比较公正的眼光去看国乐,所取的范围,决不能过于狭小;所做的准备,绝不能过于片面。”①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6页。总之,笔者并不反对构建所谓的民族音乐学的 “本土化”理论表述体系,因为,只有认真打造民族音乐学的 “中国学派”,才能真正实现中西音乐文化的互融、互通,才能使中国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理论研究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注入更多新鲜的活水,这样的研究才真正具有国际意义。
结 语
总之,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形成之际也就真正代表 “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成熟之时。然而我们清醒地看到,构建这种母语化的理论表述体系的道路任务极其艰巨。诸如,“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概念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它是指关于 “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还是“中国学者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前者包括不分国籍身份的学者针对中国境内流播的所有音乐事项的研究,后者主要指具有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具有中国籍身份的学者关于海内外音乐事项的研究,比如 “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所以,我们再谈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问题之前,务必厘清其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的界定是否准确与合理。中国民族音乐学与 “本土化”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二元并置还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因为既然包含 “民族音乐学”这一关键词,其研究理念就会与西方学术范式的表达相互勾连,而 “本土化”过程则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一种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两者之间需要一种高度融合与包容的关系,绝不是打造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理论范式的中国音乐学理论表述体系。总之,从“南京会议”到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经历了37年的发展路程 (而立之年),在即将进入四十年的这个 “不惑”之际,构建民族音乐学 “本土化”理论表述体系之路依然艰巨。因此,我们的研究者决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要以宽广与包容的胸怀,吸收与接纳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学术理念。当下学科交叉互动在中国音乐学研究领域已大势所趋,我们务必在承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精髓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与借鉴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知识,不断摸索一条真正具有中国 “本土化”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