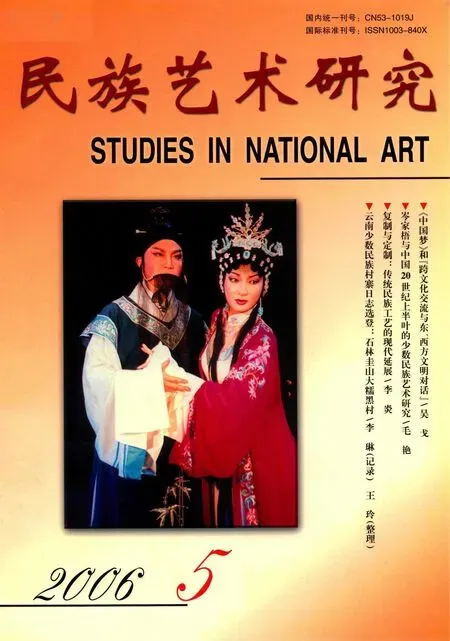中国电影中的季节叙事策略
——以 《春蚕》和 《小城之春》为例
王海洲,张 琳
四时,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样由于有与其相伴的物候的变化,又是一个空间概念。中国人对季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从 《诗经》中的 “风、雅、颂”到近代有着章回体叙事结构的小说,它始终在其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艺术表现和审美习惯。季节与中国传统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无数文人墨客、诗人画家的艺术灵感来源,是文艺作品象征与隐喻的载体,是情感寄托与艺术表达的对象。它不仅将农业社会背景中的时间诗化,更是一种生命的表征。季节的韵律渗透进每个时代的文化表达中,也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西汉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①(汉)董仲舒撰,曾振宇注说:《春秋繁露》,石家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可见,四时与个体生命的情感和世界整体合一的哲学内涵间的遥相呼应。
在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中,诗歌、散文、小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应和着四时的变化,南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写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乐,也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②(南北朝)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必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694页。这说明了诗人对四时变化及物候最为敏感。而在小说领域,明清小说以其季节叙事的结构而闻名,季节变化与时事动荡相关联。由四时而延伸出来的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则在艺术表现中拥有更多空间,无论是绘画、书法、民俗方面,季节与中国的传统艺术都紧密结合,分析其美学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季节美学研究在文学领域早有先例,着重于季节叙事、季节审美两方面。在季节叙事论中,国内学者梅新林、张倩的 《<红楼梦>的季节叙事论》就 《红楼梦》里的季节轮回和叙事节奏进行探讨,并对 “季节叙事”的概念进行总结,即 “是指以春夏秋冬等季节为叙事时间,重点通过季节变换与循环表现人生经验与人世沧桑的一种叙事形态和方式。”①梅新林,张倩:《红楼梦季节叙事论》,《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期。学者张晓青的 《中国古典诗词的季节表现:以中国诗歌为中心》则将重点放在诗歌与季节的联系上,探究古典诗词中的季节美学内涵;陈红凌的 《明清小说季节叙事论:以六大古典小说为中心》对明清小说中季节叙事与小说结构、情节、形象和审美意蕴的关联进行研究;陆邹 《巴金小说的季节叙事和文化内涵》则对巴金个人的创作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分析巴金小说中的季节循环、季节秩序和季节意象的叙事策略。这些研究涵盖诗歌、明清小说、古典小说及现代小说等多种形式,较为成熟地开辟了文学中的季节叙事研究领域。但在电影领域,对季节美学的研究相对而言就稀缺一些,只有武汉大学胡雨晴的 《日本电影中季节物语的生命与歌》对日本电影中的季节物候与电影的情感表达进行分析研究,而学界对本土电影中的季节叙事及其民族审美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将此研究方法拓展到电影领域,从电影的叙事和传情等方面分析季节美学的文化内涵。
《春蚕》(程步高导演,1933年)作为中国第一部讲述农村养蚕人生存状态的电影,片中的春蚕作为叙事的主要载体,是主宰着主人公老通宝一家人生活的经济命脉。改编自茅盾同名小说的 《春蚕》,在季节叙事上采取了以春天这一季节为背景,依据蚕的生长足迹的时间顺序进行叙事,展现了特定时代下中国农村人的生存面貌。“春天”在影片中是表现主体,直接参与叙事,它影响蚕的生长,也时刻决定着主人公的情绪和命运。同样选取 “春天”这一季节背景,《小城之春》(费穆导演,1948年)采取的叙事策略则更具象征意味,季节在影片之中并未成为表现的主体,甚至连基本的描述也省略了。片名《小城之春》中的 “春”在影片之中始终处于一种 “失语”的状态,除了始终萦绕在主人公和观众心理的季节象征,它不参与任何故事推进,却以一种中国千百年文化积淀环境中对季节的本能感应与体会的姿态氤氲于镜头语言的叙事笔触里,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和审美效果。
一、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季节叙事
中国的四时概念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之前,在传统的农业大国中,春为播种,秋为收获,所以将 “春秋”视为一年的时间。从《尚书·尧典》中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贵,以正仲冬”②(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0页。,可见当时的四时观念已初具雏形。到了汉初,经历年年战乱之后,农业重新开始繁盛,彼时 《淮南子·天文训》中便完整记述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以及一些物候表征,“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③任今晶:《二十四节气的审美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而到了西汉,也产生了七十二物候之说,将季节中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分成七十二种表征进行区分,包括风、雨、雷、电、花等自然景观,以此形成“物候”。
季节是韵律与生命的合奏,“是介于阴阳与万物之间的一级形而上的哲学范畴,是内在于万事万物的构成要素与构造模式。”④郝相国:《四时的美学意义》,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在中国早期的电影作品中,季节叙事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周而复始,更多作为空间中的象征和隐喻而出现。
卜万苍执导的 《桃花泣血记》 (1931年),开场字幕出现 “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字样,以桃花这一春天的物候来隐喻主人公琳姑的命运, “桃花含苞待放日,琳姑情窦初开时”,交代了随着季节循环,桃树与琳姑将会共同成长。孙瑜导演《野草闲花》(1930年)中,故事发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阮玲玉饰演的母亲咬破手指喂养襁褓中的婴儿,季节的在场渲染了人物悲凉的境遇,同时也隐喻了冷酷、恶劣的时代背景。插曲 《寻兄词》中 “风凄凄,雪花又纷飞;夜色冷,寒鸦觅巢归。歌声声,我兄能听否?莽天涯,无家可归!雪花飞,梅花片片;妹寻兄,千山万水间,别十年,兄妹重相见,喜流泪,共谢苍天!”其中关于冬天的物候包括 “风”“雪花”“寒鸦”“梅花”等,在叙事中交代了人物的悲苦命运,也完成了电影的内涵表达。《小玩意》(孙瑜导演,1933年)前半部分描绘了太湖之滨的桃花村的春景,在春意盎然的日子,每个人都神采飞扬、与春同行。但在影片后半部分“春天再来,又是一年以后了,在那曙光欲晓的一刹那,我们的湖光依旧是那样的美丽”,“但是那暖和的春风,哪能吹到贫病交加的老叶心中?”在相同的春色风光里,人物的命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季节的周而复始不仅作为一种时间的具化,更是人物情感的具化,其中的季节美学正应验了古诗物是人非的伤春情感。
最为典型的是电影 《马路天使》 (袁牧之导演,1937年)中周璇演唱的 《四季歌》,导演运用声画蒙太奇的方式,展现了主人公小红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经历,同时又表现出一个流亡人对被战火摧毁的家乡的绵绵思念之情,在季节的流转中讲述家国兴衰的故事。除此之外, 《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郑君里导演,1947年)中通过一组桃花盛开和桃树结果的画面推进故事叙事节奏,象征女主人公素芬结婚、生子。“开花结果”是季节的物候表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象征着传宗接代,影片在此处运用季节更替作为转场的载体可谓是绝妙之笔。中国早期电影中运用季节来推动叙事、表现空间和塑造人物的例子比比皆是,在 《春蚕》和 《小城之春》中也有不少运用。
二、季节的在场与失语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不仅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更是洋溢着一种新生命诞生的欢喜。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在 《清江引·立春》中写道 “金铁影摇春燕斜,木杪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①蒋星煜:《元曲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0页。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立春画面。但与此同时,春天中的一些物候,如短暂盛放的花、连绵不绝的雨,以及一些民俗,如清明节追悼已逝的故人等,又往往能引发人们对生命易逝的感叹,故而引发中国文人的“伤春”传统。
电影 《春蚕》和 《小城之春》都将季节背景设定为春天,但二者的运用又完全不同。
《春蚕》,由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程步高导演,夏衍编剧,讲述了蚕农老通宝一家在清明节养殖春蚕的故事。整部影片采取线性叙事的手法,完全依照季节的变化来展开。“春天”既是影片的叙事背景,也是影片叙事的动力,以百分之百的 “在场”的身份推动情节和人物矛盾。季节的物候特征在影片中充分展现出来:老通宝在卖布回家的路上,春风吹拂、阳光明媚、杨柳飘飘,河面上的船只络绎不绝;尔后洗簸箕,春蚕幼崽孵化、成长,漫山遍野的花儿,盛放的油菜花等;到清明的雨水,而后春蚕吐丝等。季节的细微变动在 “蚕”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叙事上,老通宝对荷花的敌视也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推进,“雨水”天气中达到顶点,在暴风骤雨中达到叙事的高潮。
同时,影片也不断通过字幕来告知季节的细微变化,老通宝在河边休息时 “天也变了,刚到清明边,就这么热”,借此告知电影故事的时间背景。“一个春风骀荡的下午”之后,出现快速跳切的春景画面:油菜花、稻田、野花等,老通宝一家也开始了热热闹闹的养蚕计划。“今后一个月,他们便要整日整夜地和恶劣的天气和不可测的命运相搏斗”,“这样的一个季节,这就是那幸福诗人留恋着的残春”,紧接其后的就是大雨天气的降临。“蚕”是季节的实体化,它无时无刻不 “在场”,并推动故事发展;另外一条故事线索即老通宝对荷花的敌意也因为季节的变化、蚕的茁壮成长而推动,老通宝最终选择接受荷花。
《小城之春》中,季节作为时间的具化则呈现出零散、破碎、失语的状态。影片中并未有任何清晰明了的镜头展现春天的季节物候,从开场周玉纹在城墙边散步,到被战火摧毁的戴家老宅,无不显得萧条荒凉。破败的城墙、坍塌的房屋、满园的杂草,季节在镜头语言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不仅如此,随着叙事的推进,季节似乎并未发生丝毫改变,即便是矛盾主体章志忱的到来给人物心理和叙事造成巨大波动,但对季节失语状况的改变也没有任何作用。从片名来看,《小城之春》显然应该是季节占主要叙事时间背景,但却以失语的形态出现,不得不说是 “诗人导演”费穆的巧妙安排。正是由于对生命主体的观照,本应是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季节与战火中的家园及流离失所的集体心境产生强烈对比,季节的失语就如同片中被隔绝的空间一般,是必须客观理性地来看待的,“该片镜头语言尽量避免主观变形镜头,避免作深度表意的单人近景、特写,避免沉入记忆幽深处的闪回,少用分割性对切,多两人及多人镜头,形成一种更开远、更整体性的空间感受。对个人性灵激情和创伤性体验具有一种更复杂、多重的观照态度”。①应雄:《小城之春》与 《“东方电影”(上)》,《电影艺术》1993年第1期。《小城之春》中季节在叙事推动和氛围营造上不像《春蚕》那般直接,片中的季节失语犹如人物的失语一般,以 “不在场”而强调 “在场”、以 “无”来凸显 “有”,体现着中国艺术中意蕴悠长的 “伤春”意味。
三、季节的自我指涉和象征
电影 《春蚕》始终围绕着老通宝一家养殖春蚕这一事件,“蚕”成为 “春”的实际载体,是季节的体现、人民劳动的结晶,但它更是一种生命强大意志的展现。影片从卖布出发,故事最终也由卖蚕丝终止,形成一种环形封闭的叙事结构。影片完整地讲述了蚕的一生,也全面地展示了老通宝一家世代生活的轨迹。影片中的季节叙事是季节的自我指涉,即老通宝一家已经与 “蚕”合为一体,他们对季节的触感就如同春蚕一样敏锐,生命节奏跟随节气变化而改变。影片通过蚕对季节变化的反映,来表现老通宝一家在动荡年代被时代左右的命运:春天来了,气温回升,蚕宝宝开始孕育新生,此时的老通宝一家也正积极地准备着这一年的养蚕计划,蚕与老通宝一家都充满着朝气与希望;在“春风骀荡的下午”,蚕宝宝成功孵化出来,弱小的身躯拥挤在狭小的孵化纸上,它们可以被从纸张上转移到簸箕里,而此时老通宝一家也喜气洋洋地和其他村民喂养蚕宝宝;暴风骤雨来临的夜晚,一些蚕宝宝受不了恶劣的天气而夭亡,此时的老通宝一家与荷花的矛盾也在升温;风雨停后,双方和解;蚕宝宝没有足够的食物面临着饿死的困局,其时的老通宝一家也因为桑叶的涨价和蚕丝的降价而无法生存;这里导演安排了一场 “最后一分钟营救”式的交叉蒙太奇,蚕宝宝的生命与老通宝一家的命运都依靠着 “在路上”的桑叶。与其说 “春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不如说老通宝一家以及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的命运都依附天气的变化,季节的自我指涉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
与 《春蚕》明显不同, 《小城之春》中的 “春”不仅是大自然的时间意象,更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在该片中,大自然的 “春”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失语了,而每个个体身中的生命意志则苏醒了。“春”在这部电影中,更多地体现在人物的内心深处,是欲望与希望。破碎的婚姻如同破败的小城,病恹恹的戴礼言、冷漠决绝的周玉纹就如同被战火摧毁的家园住宅,残缺不全、毫无生气。而“春”以拟人化的形象 (也即章志忱)出现——他打破腐朽与宁静;他如春风拂过平静的湖面掀起阵阵涟漪;他之于这个家庭,就如同春天之于一个腐朽的国度。章志忱就是季节的化身,所有季节的物候在他身上都有展现,他似春风吹动周玉纹的内心,似繁花给予妹妹戴秀广袤的眼界,似朝气抚慰戴礼言的绝望之情。同时,他也如春天一般,是短暂、易逝的,但正是他的短暂绚烂造就了《小城之春》绵延不绝的伤感愁绪,使它成为影史经典。
大自然的草木枯荣、花谢花开归根结底是生命的繁衍与延续,季节变更中渗透的是生命循环的本质,因此也在文化中被吸收与传承。无论是讲述蚕农故事的 《春蚕》,还是男女之间爱情故事的 《小城之春》,都有着浓厚的、基于季节体验下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季节之于艺术作品而言,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其中流淌的强烈的对生命的热爱;而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历代传承并被广泛接受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必然是其中包含的对大自然、对生命的无限敬畏。
四、季节的文本叙说与情感寄托
四时是不断循环的,由此产生的叙事结构多是基于时间的线性顺序,并形成封闭、循环的文本结构。游飞在 《电影叙事结构:线性与逻辑》一文中提出 “物质现实的因果关系可以称为 ‘事理’,与现代性叙事结构的‘心理’及后现代叙事结构的 ‘超验’形成对照,也据此界定了事理结构、心理结构和超验结构三种电影叙事的结构模式。”①游飞:《电影叙事结构:线性与逻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事理结构是线性的,心理结构则是非线性、混乱的,超验结构则更加复杂。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季节叙事结构纳入事理结构、心理结构的电影叙事模式中,进而讨论其线性结构下的季节叙事的不同功能。
探讨 《春蚕》的季节叙事之前,需重新考量这部电影的叙事对象。虽说故事的主人公是老通宝一家人,但几个出场的人物仅仅只是被简单的线条勾勒了模样,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原本值得展开的线索,如荷花与多多之间超越友情又并非爱情的情感、荷花的内心世界、女儿照顾蚕宝宝的波动情绪等,都没有进行挖掘。囿于左翼文艺运动的时代背景和当年电影叙事艺术探索时期的不成熟状态,影片并没有着力在电影叙事的情节价值,而更注重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表达和唤醒普通大众的价值,这导致 《春蚕》在人物塑造、情节构置上的弱化,相反将季节推上主体地位。 《春蚕》中,季节成为人物矛盾、故事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不仅完成故事背景搭建,同时融入叙事文本之中,成为叙说的主要对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春蚕》的文本并不是围绕老通宝,也不是蚕形成的,而是那个季节,是经济动荡背景下千千万万劳苦群众经历的那个播种的季节。
《小城之春》则将季节的功能更推进一步,隐去其建构故事情节的作用,主要承担氛围渲染和情感寄托的叙事空间营造。不同于叙事文学,电影的影像语言表达一直在试图达到诗歌表达的效果,“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们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②[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小城之春》无疑就是一部以诗的语言讲述的电影故事。中国诗歌最常用的手法便是移情于景和托物言志。景物无疑是季节的一种物候表征,影片中杂草丛生的断壁残垣、碧波微澜的湖水、萧索孤寂的野花等,无不在描绘着一种本该热闹却无奈宁静的初春景象,无不为勾勒一群毫无生气的人、一个破败的家、一个衰落的国而服务。季节的物候勾勒出影片的画面空间,同时,长镜头的场面调度、人物的内心独白都在建构着影片的诗意叙事空间,通过视觉语言展现出的人物内心矛盾与纠结。在这部电影里,季节“春”内化为人物身上的气质,它微妙地展现出人物内心星星点点的希望,温柔、细腻、不为人所察觉,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入人物的灵魂,并感染每个受众。这是中国早期电影继承传统文化中 “立象尽意”的叙事手段的运用。
结 语
对比 《春蚕》和 《小城之春》,前者在季节叙事策略中突出展现季节叙事的时间性,而后者则更强调季节叙事的空间特性,二者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季节叙事策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叙事效果和艺术风格。四时中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能给电影的语言带来更多的表现空间和可能,其作为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化时间与空间,不仅仅在早期的电影中有所体现,而是一脉相承地隐匿在许多创作者无意识的叙事策略中。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主题下,中国电影中季节叙事值得被更多人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