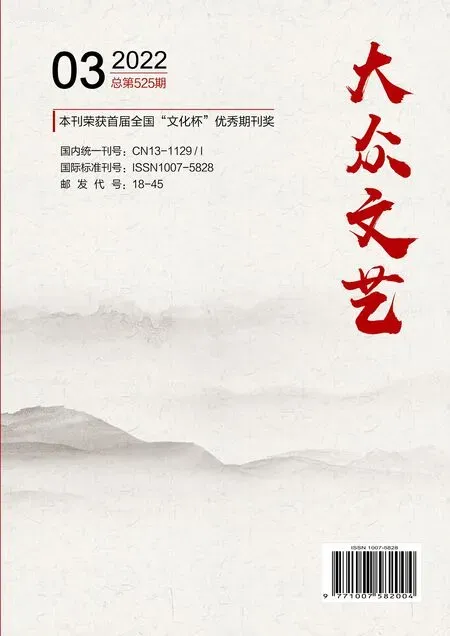拨开层雾见森林
——关于艺术的几个问题
谈论关于艺术的问题免不了需要拨开层雾见森林,种种案例不胜枚举。西方前卫与古典主义学院派之争,中国前卫与旧的意识形态及商业媚俗的双重媚俗之争,形式美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题先行”之争,艺术市场冲击下“成功学”标准的重申等等,归根到底艺术的核心问题还是最基本的人性表达。
回过头看,前卫艺术或说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乃是“围城内外”、“地上地下”的斡旋。同样对于并行变化的中国画来说,避免用并行发展的词汇表面了我的观点,传统中国画作为古老文化的残余“枯枝”决定了本体上只可能被保护、被保留,而不是假借革新、变革来博取表面上的热闹繁荣。新文人画、新水墨亦如此,前者无疑是“新瓶装旧酒”,后者是动憾了水墨之所以为水墨的根本,并不是说水墨拒绝被“实验”,而是说为挪用现代主义的表皮改变了水墨的属性还是应该为扩展了现代艺术的边界而高兴?
从“后文革”中苏醒的“伤痕”“乡土”算是“人道”的觉醒,“85思潮”到80年代末算是“人文热情、理想真实的热情”的追寻,90年代公寓艺术的崛起算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探讨,那么新千年至今算是人性的回归和人的纯粹性追求。如果把人道、人文、人态、人粹这条线索当作主线,那么艺术空间与政治空间张弛关系、国际艺术机制和标准、学术行政化、行政“江湖化”、艺术教育产业化等问题犹如层层迷雾。至于迷雾笼罩下的森林,无数批评家或是文化学者已经前赴后继争相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无外乎基于三点:艺术本体、艺术体制、艺术市场。
先来看艺术本体。论争的焦点在于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国画(与京剧、唐卡同类)及其现代主义外壳下的变体与当代艺术孰具有艺术史意义的本质。可笑的是,最近有学者另辟蹊径找出一位古老文化的“鬼魅”代表溥心畬来论证作为自律性状态下的中国画样貌。这里不仅涉及保守派与否的问题,暂且苟合作者忽略人的社会性,也不能接受对西方文化冲击下被动变化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背景的熟视无睹。退一万步,设定溥能代表自律性发展下的中国画面貌,按照传统中国画的脉络轨迹,无法不谈师承、技法、笔墨、韵味乃至儒道佛趣味。而在溯及距溥最近正统画家乃属“四王”。我认为,从“四王”后至“五四运动”数百年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画家,那么这巨大的断层凭溥一人之力如何弥合?至于潘先生的“一个自觉、四大主义”就更是“官话”了。
前人对体制的探讨批评已经着墨颇多,留给后人可挖掘的空间极小,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我的天才造就了无数蠢材。以颇具影响力的直指意识形态的“形式美”开头,当然这也与政治空间与艺术空间斡旋部分地重合,其后关于画院、全国美展、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的讨论不曾间断。吴冠中、陈丹青、李小山、栗宪庭等艺术家针砭时弊的学人风范不禁使笔者联想起民国时期的相似景象:鲁迅、胡适的笔诛纸伐,这恰巧就是李约瑟写作《中国科技史》时发现的一个奇特规律:前一朝代的发明创造经过一段时期又重新发明。特别有意思的是,体制与收编可谓一对欢喜冤家,避而不谈当代艺术的前卫性在于其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个人批判价值。而随着昔日在传统土壤上攻城掠地的前卫艺术家(如方力钧)的主动收编或“被收编”,这一身份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前卫艺术的否定之否定的针对性和力道。再说说展览。“85青年美展”、“89现代艺术大展”之所以作为分水岭而不是开端,字面上理解应是其高度。不是艺术创作的高度,而是其理想主义高度和参与文化建设的力度。更不用说李先生批评的美展背后的“贫乏”了。从那以后,经过了“公寓艺术”短暂的挣扎,终于迎来了危机时刻——当代艺术日益增长的媚俗趋势,即政治、商业媚俗与学术批评媚俗。宏大的叙事只消翻翻历史书,举个身边的看似不起眼却如“牛氓”般存在的例子。前些日子,读研那时的同学要出本画册,叫我写写文字什么的。起初我是拒绝的,但又抹不开,终究还是把要白话的东西写到这里了。称其为白话,是因为按照要求、标准写作实在不是我的风格(曾经古书画鉴定老师让我按照条条框框的规定写作业,我愣是照抄了拍卖行的鉴定意见——不知这种过程叙事算不算行为艺术?)可是让往日叱咤风云的批评家(托尔斯泰、鲁迅、陈丹青在内)写软文,请免开尊口。笔者只是一个楞头青,还称不上死读书的书呆子,但也知既不能做“坐台”口舌,也不能做艺术家中的“社会活动家”。然而实际上,市场需求刺激生产,有众多的写手在等待这份差事(当然不乏质高价廉的教授)。毋庸置疑,正是商业体制与官方体制的联姻诞下了庸俗社会学,而这些都与艺术无关。谈论围城内人与事的钻营已经无济于事,而波西米亚状态的艺术家自有其一套画廊、美术馆经纪的系统,那么,无法不寄望于科班出身的学子们。但实际上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批新新青年的大多数已经吃了有毒的开口奶,算是已经早夭了吧。
赘述过多无外乎为了引出艺术的定位问题。无论如何它不再是中世纪宗教的图解、也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它们本来就是上层建筑内平行的关系),而是还原拉斯科洞窟岩画的原始纯粹性。当然也不可能要求艺术家假定高更、马蒂斯似的原始寻根,何况现世还没到必须“返祖”才能重新激活艺术的地步。就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来说,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前人的背影中,就好像我又拿20多年前“未来艺术的坐标”来影射我的惰性:既不在过去,也不在西方,而在于当下。
说到当下,仿佛就要把刚才的白话再说一遍,于是就不消说了吧。
[1]李小山.我们面对什么[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2]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