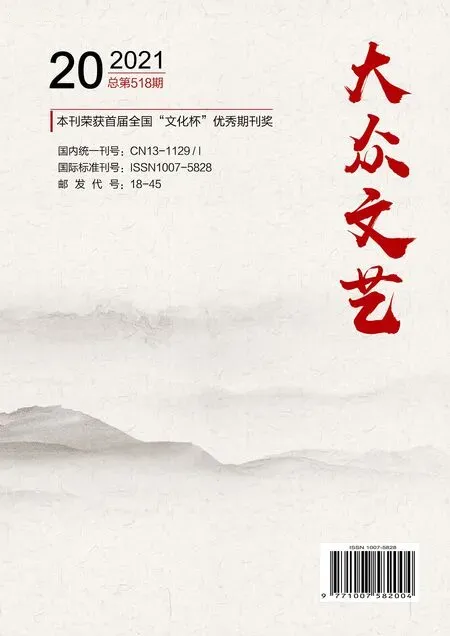别一种风景
——唐代西域马赋浅议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 134002)
在唐代历史上,马因自身在唐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而备受重视;马意象也一直因其所具有的丰厚的文化底蕴与多样的象征意义而颇得有唐一代文人青眼,并成为后者传情达意、述志明理的重要载体。在盛唐文学作品中,“渥洼马”“天马”“汗血马”等关涉西域骏马的意象开始大量出现,并于中晚唐时期延续鼓荡于唐人创作之中,折射出作者希冀以此而抒写情志、阐发哲思的心理趋向。本文即将唐人西域马赋置于唐代马文学的谱系中,以求管窥唐赋的特征面貌。应该说,此类作品虽数量有限却别有意味:一方面,多数辞赋虽类型不一,却皆与军事政治内容有所关涉;另一方面,赋作中的马意象虽大多仍担任引出叙事脉络、点明抒情意向的角色,但其背后赋家针对相关内容而进行的追溯、强调与联想却更为宏富。受此影响,唐代赋作中各类具有不同审美内蕴与思想意义的马意象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主题共指与主题互融,在客观上也体现出了作者更为复杂多样的创作态度与创作理念。
一、唐代西域马赋的创作概况
有唐一代,时人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几乎无一人不好马爱马。因其优良的品质,西域之马在大量进入中原后备受时人推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而成为入唐以后文人咏叹的热点。
从创作方面来说,唐时与西域之马有所关联的作品大约有二十篇左右。这其中,无名氏《舞马赋》(二篇)、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乔彝《渥洼马赋》、王损之《汗血马赋》、胡直钧《获大宛马赋》及谢观《吴坂马赋》七篇赋作径取舶来于西域的马匹为题而详论,并以此为基础而衍生开去以表达志意;牛上士《古骏赋》、李濯《内人马伎赋》、王起《万年县试金马式赋》、吕鎛《万年县试金马式赋》、张仲素《千金市骏骨赋》、纥干俞《铜马赋》、徐寅《朱云请斩马剑赋》、王起1《燕王市骏骨赋》、无名氏《汉文帝却千里马赋》《骥伏盐车赋》十篇赋作并未直接以西域马为表意对象来生成创作,但观其文中“渥水龙媒,朱旄逸才”(《古骏赋》)“踊跃其液,渥洼之形未出”(《万年县试金马式赋》)“鬣上朱明,沟中血走”(《汉文帝却千里马赋》)等语句,作者自觉以渥洼马、汗血马等西域良驹来比拟摹写自己笔下的马匹,这仍然代表了中原文化对西域传统的接纳与利用。此外,韦执谊《市骏骨赋》、王起《朔方献千里马赋》、独孤申叔《却千里马赋》等数篇作品书千里马事而演为寓言;作者所述之马虽不具备明确的西域特征,然唐代社会中的“千里马”本就大多关涉西域,故而这些以此为题的作品或多或少仍然昭示着马意象所具主题内蕴与输入、凝聚于马这一价值载体上的西域文化之间的天然关联。可以说,在唐代的辞赋创作里,“西域宝马”这一意象或隐或显,出现在诸多的主题、题材之中,阐发着特殊而多样的伦理趋向与文化观念;它也因此而成为了我们借文学研究来把握传统文化的系统脉络、理解胡汉文化的交融过程的一个窗口。
二、政治功利化的马意象与赋家写作心态
在唐代文学中,唐诗、唐文乃至唐传奇中存在着大量关于西域马的书写;它们具有着丰厚的内涵与多样的观照角度,素来学界对之多有瞩目。与之相比,唐赋中事关于此的内容虽值得重视却乏人关注,仅有个别研究者曾论及唐代赋家以西域之马作为譬喻来阐述文化精神或反映社会样貌的现象2,但尚未将之视为主要对象加以深入探察。事实上,唐代以西域马为主的辞赋创作有着属于自己的特点表征。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文学中的西域书写,更可能发现探究赋体特征与赋作意象之间关系的新途径。因此,本文将侧重于考量、忖度影响辞赋作者意象观照的社会因素和文体因素,以图借此获得与西域辞赋相关的更具广度与深度的认识。
自赋体形成之后,历代文人便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用多有强调。从班固为《两都赋》所作之序中,可以窥得适时儒士所秉持的赋体创作观念: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在这里,班固秉承了《诗大序》中“厚人伦,美教化”“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说法,认为辞赋应当具备颂圣德之美、讽帝行之失的效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除为统治者服务外,辞赋在政治生活方面往往也会与人才选举发生联系。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之作而上动天听,得武帝激赏而获取官职后,历代因作赋中试、献赋得遇而获得帝王赏鉴甚至步入仕途的文人可谓不绝如缕;另一方面,文士倘若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也难免会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中所描写的那样,用辞赋来抒写自己心中所郁结的忧愁悲愤。
与历代传承不已的借赋以言说政治的风气相似,唐代事关西域马这一意象的辞赋也大多被用于表露才士对功业的热忱、对国事的关切。大多数唐赋往往着意于以马比人;赋家往往或评述君王对待西域良马的态度,或诉说在君王手中的西域良马的境遇,以图借此来表现贤人才士对自身所具政治价值与人生价值的认识。前者如王起的《燕王市骏骨赋》与独孤申叔的《却千里马赋》。这两篇赋作的作者分别使用了燕昭王千金买千里马骨与汉文帝拒绝千里马的历史典故来阐释当政者对良马的不同态度,对象化的寄寓了文人的政治志向与文化心理。后者如牛上士的《古骏赋》与乔彝的《渥洼马赋》。《古骏赋》对来自于西域的良马遂君王意(“飞奔肃肃,恣意驰逐”)与失君王意(“绊权奇而不用,空倜傥其焉如”时的不同境状予以对照描述,借此而强调了身有长技者为君所用的必要;《渥洼马赋》虽通篇对笔下“生乎天涯”“产乎渥洼”的骏马称颂不已,却于赋作收尾处微露讽谏,发出“愿以求马之人为求贤之使,待马之意为待贤之心”的慨叹,认为相对于宝马,贤者方是君王理政审政的更好选择。
表面看来,唐代辞赋的作者对西域良马似乎各有臧否、作意较广;然详作体察不难发现,上述作品其要义相去不远,所言不离政治环境、人才察选等关涉功利的主题。这里有两点须加注意:
从历时性角度来说,唐代西域马赋所贯彻的“重贤者”、强调“贤者”之政治功用的创作理念虽有迁转但未质变,只是在主观用笔上渐趋显豁直接。在分处初盛唐与中晚唐时期的以西域马为主题的辞赋中,作者对西域马的认同态度渐趋淡薄。由于唐代论说西域之马的辞赋在立场重心方面有所变移,于是有研究者认为上述文学现象反映了文人两种不同的为政理念,即“治国以武”“选良马”与“治国以德”“重贤人”3。以笔者浅见,此说似可商榷。盛唐时期的赋作在讽谏之时尚多委曲作意者,而舶来自西域的马匹向来因其卓越的身体素质及其在军政上的重要地位而为国人所喜爱崇拜,很容易被对象化为特征与其相类的人才的象征:这也是多数以良马而譬喻人才的辞赋的渊源所自,《古骏赋》4也不外如是。在这里,作者描述良马在君王面前的得意与失意实则正是为了比拟贤者的穷达,从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表述自己企望皇帝重视贤能之士的志愿。中唐以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儒家诗教观在古文运动的推行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加之国事日非、文人生活处境恶化,唐赋其讽谕之意也有所增加。也正是因为这样,《渥洼马赋》才对帝王重骏马而不重贤者的行为给予直接讽谏,而非托物以寄。
从共时性角度来说,中晚唐时期的西域马赋以律赋为多;它们偏重以事例隐喻国家之政、以论说阐明才士之志,客观上也得力于适时试赋的社会风习与论赋的批评风尚。一方面,唐代科举虽以诗赋取士,然中唐之前的举选过程更加偏重于经帖的考察。开元后,科考采用律赋作为选材的固定体式,这一创作体式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渐趋紧密。另一方面,中唐后论者对闱场中出现的律赋虽褒贬不一,或认为“原夫诗赋之意,所以达下情,所以讽君上……(闱场赋)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或认为闱场赋“亦不违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但双方均将这类作品于国于君所应当起到的效用作为议论的出发点。无论孰是孰非,闱场律赋与政治、君王之间的紧密结合状态都为论者所默认。基于以上两点,科场内外的诸多赋家的律赋大多都会将关乎君王、人才的政治感怀通过创作而予以呈示,以西域千里马为主题者也不能外。清代就曾有人这样评价《燕王市骏骨赋》作者王起的律赋:“《文苑英华》所载律赋至多者莫如王起……大约私试所作而播于行卷者,命题皆冠冕正大。”独孤申叔虽不似王起般专擅类于“场中试赋”的创作,然其本人亦出身科场,《却千里马赋》本身同样在体式上隶属于律赋;其文章用典取意并不违于讽颂政局的赋旨,作品仍能发挥“咏怀察政”之功能。
此外,与意在借咏叹西域千里马而言说社稷之志的作品相对应,唐代以贡自西域的舞马为题材的辞赋重在描述这些专用于娱乐的马匹表演的盛景,托物作喻,借此恭贺天子圣明、称誉升平气象;这些作品多以对君王的奉承谄谀作为主题,本身并没有多少思想意义。不过,作品在论说“舞马”之时亦曾将之与过往典故中的“良马”意象置于一处,在两相比照之后对前者加以颂扬:“逐逐良马,终万舞而在庭。岂比夫汉皇取乐而同辔,鲁侯空牧而在坰?”(无名氏《舞马赋》)“虽燕王市骏骨,贰师驰绝塞,岂比夫舞皇衢,娱圣代,表吾君之善贷?”(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赋作者将君主以舞马自娱、娱人的庆赏仪式提升到新的高度;众多舞马“在庭”“舞皇衢”的局面正代表着开创“圣代”的君王的开明睿智、知人善用,赋作自身实际从另外的侧面寄托了文士阶层实现人生价值的希冀。在这里,西域舞马虽具有一定的异质文化色彩,但它和千里马一样,仍然只是被“马喻贤人”的传统文化理念所统合了的符号与象征。
要而言之,在面对西域马这一胡汉文化交融环境下的产物之时,受到社会风尚的浸染与文体类型的拘限,唐代赋家对其所具有的军事政治意义往往有所侧重,并由此而展开了文化层面上的多角度讨论;这既具象的反映了有唐一代的社会面貌,也真实的体现了创作主体较强的功利意识。
三、喻指多样的马意象与辞赋创作生态
从意象本身所喻指的含义上看,唐代的西域马赋尽管所涉题材不一、所述情志各异,但这些不同类型的题材在内容上却往往互相联通。应该说,相对于旨趣较为单一的同题材诗歌与小说,以西域马为核心而展开叙述的唐代辞赋形成了怡悦性情和抒写豪情共存在,颂圣贡谀与寄寓劝谏相交织的复杂面貌。
在无名氏所作二篇《舞马赋》、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以及李濯《内人马伎赋》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双重主题的存在。一种为形而下者,它们描述了马匹“类却略以凤态,终宛转而龙姿”“忽兮龙踞,愕尔鸿翻”的曼妙样态以及“可以敷张皇乐,可以启迪欢趣”的娱乐效用,叙写了适时社会喜好玩赏行乐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另一重则有形而上的意味,赋家借舞皇衢之良马、娱时人之马伎等娱乐内容来称赞君德,进而由此抽象出“唯才是用”“激君子之磨锐”等主题,以伦理化了的儒家正统人才观进行评判。《古骏赋》与《获大宛马赋》《汉文帝却千里马赋》中也每有类似的“一笔而二歌”的情况出现:这三篇辞赋或以马喻拟不遇之士的怅惘激愤,或借马言说士人对施政之君的认知,作品本身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不过,这类反映作者创作初衷的诉求始终是外在的,处于陪衬地位;占据辞赋主体位置的仍然是诸如“驵骏奇状,超摅逸才”“悉可耀威华夏,夺魄獯戎”这样借陈说异域骏马之英风豪行来烘染彰显君德国威的描述。
概而言之,唐代诸多西域马赋的作者在行文上往往并非只对事关马意象的某一主题作单独陈说,而是将其与其他相关主题勾连交融,在整体性视域下予以观照,从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彰显这一意象的文化价值。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创作现象的原因并不单一,它实际得力于有唐一代辞赋自身的文体特征与辞赋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同影响。对此亦可分而述之:
首先,赋体意在讽谏的创作原则与以颂美为主的创作方式共同确定了一种吊诡而富有张力的写作传统,而唐代西域马赋在相当程度上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从而造成了唐代以之为核心描述对象的赋作的杂化。我们对此可以一分为二的来加以论说。
一方面,赋体以颂美为主而尾以讽谏的创作模式对唐代西域马赋的影响。西汉辞赋初兴之时,司马迁便对这一文体所具有的讽谏意义予以强调,并评价司马相如之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认为赋体于闳侈钜衍的描述之后的曲终奏雅实际正是其讽谏君王的要义所在,值得肯定。这种以铺陈称颂为主体、借讽谏批判而收尾的写作方式也在后来的班固等赋家的笔下得到了继承与体现。由汉至唐,以此为主题的辞赋可谓时有继作。不过,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间文化环境、文体类型以及文人兴趣的差异,这些本以谏君讽时为目的的作品在侧重点上却始终于“称颂”与“讽谏”二者间摇摆不定,甚至于如魏晋散体大赋般偏向于只颂不讽。要之,唐前辞赋已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创作意识;这种意识体现了同时作为君王的臣子和监督者的辞赋作者双重身份的创作投入,进而左右了辞赋观照君权社会下相关意象的视角。而在唐代,舶来自西域的骏马既因其出身而体现着胡汉文化交融的情态,又因其禀性而承载着悲不遇、建功业等文化意涵:这些都使得以之为核心描述对象的辞赋自然而然的包含着一层事关君政的隐义。正因由此,唐代的西域马赋才会于君王对臣子的迎拒、臣子对君王的讽颂以及臣子对社会的褒贬等方面多有涉及,并在同一篇文章中以不同的叙述题材与叙事态度而构思出意旨并不单一的内容。
另一方面,赋体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对唐代西域马赋的影响。西汉末年,扬雄在谈论赋体创作之时综合了司马迁有关于赋的观点,并由此而加以铺衍拓展。他认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很显然,扬雄反对赋体华丽铺陈的特征表现,认为其容易导致欲讽反劝的接受效果,使讽谏对象不能得悟所失。有鉴于此,扬雄以儒学诗教观为基准来评述赋体的创作,认为赋的主体当与《诗经》中的风诗一样以讽谏为目的,进而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的指导原则。不过,由于“欲谏则非时”,扬雄在《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中本着“推而隆之”的目的,盛赞理想中的帝王形象以曲说现实中后者的失政,足见这种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其实也存在着表意不明的问题。在此之后,在堪称赋体特例的《七发》(枚乘)、《七激》(傅毅)、《七命》(张协)以及《七启》(曹植)等“七体”文中,作者多于最后盛颂时世以招隐者出山,似乎是在对作品创作时昏暗不堪的时局予以反讽,亦可称之为以颂为讽的创作表达。不过,由于多数七体文的创作背景已然不可尽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是完全契合还是迥不相侔,客观上殊难判别。此外,七体文作者的主观动机也并不单纯。他们或多或少采用了“六过一是”(《七激》为“五过一是”)的模式来进行创作:作者往往会先以不无欣羡之意的笔墨来铺陈描述诸多不为隐者(实即作者本人)所欲的几件事情,之后方曲终奏雅,于结尾一事中描写隐者所认同的观点;这又不免使其和相如赋一样,回到了“劝百讽一”的路径上。
概而言之,唐前以颂为讽的各类赋作本身就存在着多样的客观解读可能与主观创作缘由,而这些又导致其托物所言之志意较为曲折幽隐。应该说,这种较为泛化的叙述艺术谋略也在唐代包含有相类套路的西域马赋中得到了延续。在二篇《舞马赋》等作品中,作者将主要笔墨放在了对今之明君“圣文神武”“承天之祐”之德的描述上;在《获大宛马赋》《汉文帝却千里马赋》等作品中,作者则对孝武帝、汉文帝等古之圣主不吝赞词。只就字面意义上看,这里的描述无疑是作者对帝王德行的揄扬。但是,前者写就时唐王朝已于盛极间隐伏乱象,文人笔下的舞马表演愈是婉媚多姿、热闹纷呈,就愈令读者感觉是在正话反说;而后者出现时胸怀广志、自比“良马”的文人更是对已难以维系的王朝统治忧心忡忡,他们在借关涉西域之马的典故而对明君之能为大加称颂之后,也难免就此申而论之,言说一番自己对古今帝王施政得失的见解:结尾既已颂极而行讽谏,则主体部分的颂扬自然亦有其言外之意在。与其说这些赋作自身表现了颂君赞君的主旨,毋宁说它借助于适时的时代语境以及“西域马”这一具有多样文化特征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在精神表现与内容表达方面存在着多重阐释可能的主题。
其次,唐代各时期间不尽一致的社会文化环境与赋家具有共同特点的个人经历共同造就了辞赋表征不一、内容杂糅的创作面貌。由于其意象与伦理政治间所存在的先天关联,唐代牵涉西域马的赋作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一些: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虽有所拓展,但受到赋家个人境遇与才识的拘限,它们往往会在叙述中旁顾左右而言他,难以专注于对现实的讽谏,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所欠缺:这些同样是造成其题材多元化的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唐代与西域之马有所关联的赋作约有二十篇;对之细察可知,除《古骏赋》作者牛上士、《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作者钱起及二篇《舞马赋》的作者5外,唐代题涉西域之马的辞赋作者基本生活于乾坤摇动、国事不幸的中晚唐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格调志向上明显不同于盛唐:对于生逢中晚唐的文人而言,他们已经很难再像盛唐文人那样,将积极参政、辅弼君王视作自身的人生目标;同时,他们对自我命运与国家气运的期望也在不断降低,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了对适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文人阶层的痛苦不幸的反思上。如在对屈原、扬雄等赋家的评价上,盛唐文人多以为其赋作缺少讽谏之效,称之为“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之辞,甚至于为此发出“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顾”的感慨;而韩愈、柳宗元诸人则因其忠而见谤、易老难封的遭遇而产生了内心上的共鸣,于行文中对此予以重点表现,对屈原“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抢攘兮,遭世孔疚”的遭遇多有嗟伤,并肯定了扬雄作品“不平而鸣”的一面6。中晚唐西域马赋作者生逢其时,在这种嗟时伤世的思想精神的笼罩之下,自然也会于创作过程中借用西域良马所具有的怀才不遇、襄助功业的文化意涵来讽谏时政、吐露衷曲。
不过,中晚唐时期借西域良马而入题的辞赋所采用的这种借题讽谏的方式实际受到了作者身份与创作情境的限制,个人表达也时常会让位于现实需要。如上文所言,此类作品以出于闱场的试赋居多;创作者大多希望以此为进身之阶,得到当政试官乃至上皇的青目而入仕显名。为了现实的需要,士子们不可能完全在写作时以一己好恶为中心,尽情抒写而全无顾忌——“几乎不管在什么样的题材规定下,(唐代试赋)作者总会在扣题行文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予以歌颂和粉饰。”适时的赋家确实会借马意象来诉说一些对个人身世与彼时时世的感兴,但其讽谏大多点到即止,并不具备强烈的个性色彩与批判力度;作品中占有主体位置的始终是典重宏丽的祝颂内容。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上,乔彝的《渥洼马赋》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给予我们一些参证。在张固《幽闲鼓吹》的记载中,《渥洼马赋》的成篇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试官令引入,则已曛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便欲首送……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
在这个故事里,乔彝因嫌弃“幽兰”之题过于绵软妩媚、不合血性男儿之本色,便乘醉向试官以命令式的口吻提出“改题”之求且一挥而就,尽显文人恃才傲世、放诞不羁之态;也正因为这种锋芒毕露的个性化行为,乔彝遭到了降级录用的处罚。不过,考诸史籍,《幽闲鼓吹》所载这则故事的可信度实际并不高。《渥洼马赋》为大历十二年(777)府试之题,而《幽兰赋》则为大历十三年(778)进士试之题;这两次考试乔彝皆有参加且留下试赋,并无刻意更题之事。二赋分别以良马与幽兰来对比才士,前者对才士处境颇有忧虑,乃于文中颂扬君德,并借机陈说“愿以求马之人为求贤之使,待马之意为待贤之心”的政治主张;而后者同样因适时“兰在幽兮其芳满丛,士守业兮其道未通”的境状而心怀忧戚,其中“倘一借于韶光,庶余香之可袭”等句亦是贤士借颂君而求进之口吻。它们虽在措辞与行文上有所差异,所言者却都是“内匡君之过,外扬君之美”的“忠臣事君”之道,并没有尖锐的批判锋芒。显而易见,中晚唐如乔彝般能赋之才士在进入科场之时,出于热衷禄位之心而称颂君王,隐却自身个性、避谈国事之非才是他们的现实创作常态,傲岸自信、顶撞君权的言行实则只存于文学想象中。以西域马为主题的科场赋作其实同样存在上述情况。不过,由于马意象与政治间的天然联系已为文化所认同,它所具有的讽世之意也较一般科场赋作更为直白显露一些,客观上也使得作品本身的题材更为形态多端。
总而言之,唐代西域马赋之发生存在着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的因缘:它既受到政治环境与文学环境的左右,又受到文化因素和文体因素的影响。在多重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唐代西域马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特征,其叙述在题材方面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构成方面则具备显著的复合特性。对上述特征进行研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辞赋创作主体感知文学、认识自我的思维方式,把握唐代事涉西域题材的辞赋的创作生态。
注释:
1.此赋《全唐文》题王起作,《文苑英华》不题撰人,学界大多认同起为作者,今从。
2.参见侯立兵:《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水”“马”意象》[J].《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
3.参见侯立兵:《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水”“马”意象》[J].《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
4.据卞孝萱先生考证,《古骏赋》作者牛上士之子牛肃至迟出生于武周圣历(公元698-700)年间(参见《冬青书屋文存》卷三“牛肃与《纪闻》”),由是逆推,则上士大略应诞生于唐高宗年间,称之为盛唐时人当无疑问。
5.此二篇赋作作者虽名讳不详,但学界大多依据其所涉及的题材内容而认同其出自盛唐时期的判定。
6.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