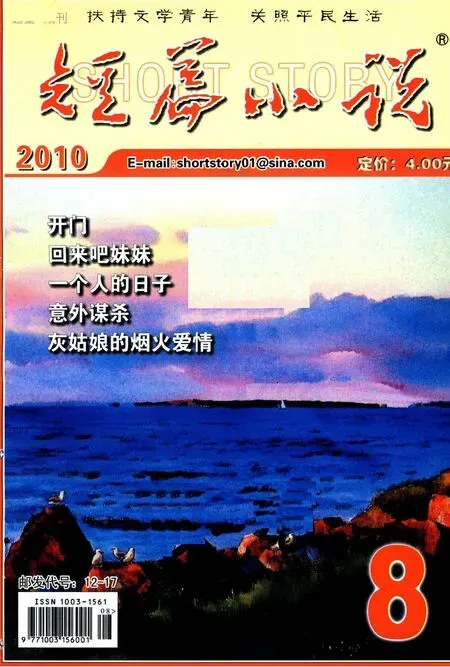换面
◎夏艳平
母亲连着喊了几声连生,没听到应答,就走出门来,大着声朝着对面竹林里喊。这次有了效果,母亲一声连生刚喊出,脆嫩的回声就小鸟般扑楞着从竹林里飞过来,接着,钻出一个泥猴似的少年来。这个少年就是连生。
连生只穿了一条短裤,手里握着一只蝉,蝉鸣悠扬,走一路叫一路。母亲说,好你个孽畜,叫你莫要捉蝉你偏不听,恁热的天,不怕热死你!
连生的心思全在手里握着的那只蝉上,哪听得进母亲的骂?母亲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整天地疯玩。
母亲抬起一只手,想为连生擦一把脸上的汗,没想到画出了一幅画。
画是大写意,有山有水,煞是好看。母亲禁不住笑了。笑着的母亲顺手在连生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骂道,真是一个脏猴儿,把我的手都弄脏了。连生使劲眨巴着眼睛,还真的有几分猴子的模样。
蝉知道此时不能沉默了,一个劲地在连生的手心里挣扎着,弄得连生的手心痒痒的。连生不由加了劲,原先半握的拳头又往里紧了几分,这样,蝉的挣扎就变得徒劳了。
但蝉不会放弃,仍不停地挣扎着,蝉鸣再次响起。再次响起的蝉鸣悠长而哀怨,像是在哭诉。连生忍着手心里的痒,把手握得更严实了。母亲看着连生握着的手,说,你听,蝉在向我求救哩,叫我让你放了它。
连生竖起一对小耳朵,听。听了一会,又疑惑地看着母亲,说,我怎么没听到?连生把握着的手藏到了身后,身子也慢慢向后退去。母亲的目光跟追光灯一样,亦步亦趋,紧紧地追着连生。
母亲说,它是说给我听的,你当然听不到。还是放了它吧,我去打盆水来帮你把身上洗一洗,看你满身脏得像什么样子。
母亲说着,就去厨房里打来了一盆清凉的井水,放在连生的面前。
井水在盆子里漾着,母亲的笑脸也在盆子里漾着,像是一朵开在盆子里的莲。连生最爱看那朵莲了,目光柔柔地落在盆子里,跟着井水一荡一荡的。
母亲说,洗干净了,帮我做点正经事去。
母亲将一个装了麦子的提箩交给连生。连生看着母亲,惊喜地问,要换面?母亲点了点头。连生一把提起那个装了麦子的提箩,围着母亲打了两个转,边转边喊,换面哟,有面吃哟。打完转,连生就往门外走,母亲说,你莫要慌着走,二婶家也要换呢,你一起带去换了。说着,领连生去了隔壁二婶家。
二婶早准备好了,他们母子一进屋,二婶就将一个装了麦子的暗花提箩递给连生。二婶说,连生,我和你二叔下午都要出工,要麻烦你了。接着,二婶关切地问,两个提箩不轻呢,连生,你能提得动吗?
没待连生回答,母亲抢先答了,母亲说,这么大个伢儿,提这点东西都提不动,不白吃了这多年的饭?
听了母亲的话,连生示威似的将两个提箩举过头顶,嘴里还“啊啊”地叫着。母亲忙说,你个孽畜,显你本事大是吧?要是把麦子弄泼了,看我不抽你的筋。
二婶上前抚了一下连生的小光头,笑着说,怪二婶瞎担心呢,我们连生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好后生,你看,这小胳膊多有力啊。
连生两只手提着两个提箩,只好把蝉埋在麦子里。
正是夏日的午后,日头正毒着呢。连生边走边留意着提箩里的蝉,脸上的汗也顾不得擦。
蝉很狡猾,不时地从麦子里探出头来,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连生哪会让它的阴谋得逞,待它差不多要爬出来时,就放下提箩,又将其埋进麦子里,让蝉白费了努力。
连生与蝉游戏着,一个人的路也走出了许多的滋味。
走过了一半路程,有一段田埂路,很窄,还有些松软,人走在上面,像踩在弹簧上,一闪一闪的。连生走得很谨慎,蝉知道,此时的连生难以顾及其它,就趁机爬到了麦子上。
连生有些急了,但又不敢放下提箩,只有大步往前走,想走到田头宽敞的地方再作处理。蝉哪会放过这一良机,连生刚走出两步,蝉就“吱”的一声飞走了,飞到对面田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去了。
连生本想放下提箩,再去把蝉捉回来,但怕耽误了换面,对着大柳树看了一阵,还是转身走了。
牵面房在大队小学旁,也就二里多的路程。二里多的路程本就不经走,加之连生熟门熟路,又走得急,牵面房很快就到了。
牵面的是一个跛腿老头,人称二先生。二先生矮、胖,脸圆圆的,又白净,像是一个揉好的面团。
二先生手艺好,牵的面,细如丝,白如霜,又劲道,怎么煮,都不糊汤,一根一根的,很好吃。有人说,二先生的面,压全县。更重要的是,二先生人品好,老少无欺,从不短人斤两。有了二先生,当地人多了一道口福,干活累了,吃饭没胃口,就提几斤麦子,再添几角钱加工费,找二先生换一箩儿面,煮着吃。吃了二先生牵的面,寡淡的日子就平添了几分滋味。
慈眉善目的二先生,见人一脸的笑,见了小孩更是亲热得要命。连生一进门,二先生就招呼说,连生,你来换面呀?看把你热的,快坐下来凉一下。说着,将一个大蒲扇递给连生。
连生说,嗯,我二婶家也要换。连生说着,将两个提箩递给二先生,然后接过蒲扇,胡乱地搅动着。二先生说,连生真有用呢,这么点小伢儿换两家的面。
听了二先生的赞,连生低了头,脸微微地红了,人也变得安静起来。
在连生坐下来歇凉的时候,二先生一瘸一拐地称麦子,倒麦子,然后,装面,称面。二先生称好了面,对连生说,连生,天太热了,你凉一下再走吧。连生说,不嘞,我要回去。
连生心里惦记着那只飞走的蝉呢。
二先生知道留不住,就再三嘱咐连生,路上不要玩水,不要把面弄泼了。连生答应一声,就提起两提箩面出了门。
连生手里提着两提箩面,感觉比来时还轻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那棵大柳树下。大柳树上有好几只蝉在叫,一只比一只叫得响亮,像是在比着赛。听到蝉叫声,连生就有点走不动了,放下提箩朝着树上看。
连生听出,刚才那只飞走的蝉也正在使着劲叫呢。那只蝉的叫声格外悠长,格外响亮,为抓那只蝉,连生在竹林里守了好长时间。听到那只蝉叫,连生的心跳就加快了,猫了腰往树上爬,像只灵巧的猴子。
快接近目标的时候,连生稳了稳情绪,放慢了攀爬速度。连生知道,蝉精明着呢,你若弄出半点响动,它就“嗖”的一声飞走了,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让你干瞪眼。连生才不做那样的蠢事呢,他借着枝叶的掩护,慢慢地往上爬。
连生是捉蝉的高手,听一听蝉叫声,就能确定蝉所在的位置。连生朝着那只飞走的蝉悄悄地爬去。爬着爬着,突然手一扑,那只蝉就在他的手掌心里了。别的蝉受了惊吓,“吱”的一声四散而去,尿水像一阵毛毛雨,全洒在连生的脸上。这是蝉的报复,蝉不喜欢人打扰它们的生活。
连生手里握住了那只蝉,满心欢喜,脸上的蝉尿也不擦,几下就溜回到地面上。连生喜欢蝉,喜欢蝉在掌心里鸣叫时,那种麻酥酥、触电般的感觉。
连生是不会让蝉再次逃走的,他解下裤腰上那根细小的麻绳,一头系住蝉,一头系在提箩上,蝉就只能在提箩周围打转转。
连生高兴地站起身,短裤却“哗啦”一声掉到了脚跟处,露出了裤腰下那一圈耀眼的白。连生哪还记得,自己已将裤腰带挪作了它用。
连生急忙弯腰提起短裤,紧张地向四周望了望,见四周没有人,这才提着短裤走到田埂边,用力扯起一根古轮藤,捋去上面桃形的叶,将其系在裤腰上。
连生重新回到提箩旁。看了一眼两个提箩。一看到那两个提箩,连生的心不由一紧:提箩里的面好像少了。他记得,从牵面房出来时,两只提箩都是满满的,这下都变得浅浅的,特别是二婶家那个暗花提箩,好像浅得更厉害些。
莫不是有人趁我上树捉蝉的时候,把面偷走了?连生又看了看四周,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大家都在忙着搞“双抢”呢,哪有闲人?莫不是土地菩萨把面偷去了?连生马上又摇了摇头,否定了。上学时老师讲了,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神仙鬼怪。那么是……
连生抬头望了望天,天上一轮白花花的太阳,刺得他睁不开眼,连生只得低下头来看地上,看那两个提箩。两个提箩里的面好像更浅了。连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抬起手来在自己的光头上一气乱抓,抓出了一头的汗水。
连生有些急了,自家的面少了还好说,顶多挨母亲一顿骂,二婶家的面少了就不好说了,二婶像母亲一样爱着自己,我可不能对不起二婶啊。
连生把手上的汗在短裤上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手臂擦得发热了才停下来。
反正不能少了二婶家的!
连生看了看自家的提箩,又看了看二婶家的提箩,然后弯下腰,从自家提箩里拿出一挂面来,放进二婶家的提箩里。二婶家提箩里的面,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而自家提箩里的面浅了。
那是一大碗面呢!
连生记得,有天晚上,母亲煮了面,他觉得很好吃,就多吃了一碗。他吃完面,发现母亲的碗里没面了,最后,母亲只喝了一点面汤。为此,他责怪了自己好多天。这下,又无端少了一碗面,到时肯定又会少了母亲的。
那不行!
连生弯下腰,把刚放进二婶家提箩里的那挂面,又拿了出来,重新放进自家的提箩里。看了看自家的提箩,连生觉得心里好受了一点。可目光触到二婶家的提箩时,他一下子蒙了,二婶家提箩里的面,少得他不敢看了。他连忙扭过脖子,但脸上仍发起烧来,心也跳得急了,像作了贼一般。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贼,不然,二婶家的面怎么就少了呢。
连生把扭过去的脖子回了过来,把那挂面又放进了二婶家的提箩里。他说,不能让人说我是贼,我不是贼!可看了自家的提箩,他又心痛了,那可是一大碗面呢,我又没偷。他想将那挂面重新拿回来,可手伸了几次,还是缩了回来。
此时,那只蝉因麻绳的拉拽,飞不上天空,不停地鸣叫着,连生听得有些心烦,就解开麻绳,放了那只蝉。
连生闷闷地回到了家里。
连生觉得很累,放下两个面箩,就躺在了竹床上。没过一会儿,一只蝉飞到了他的面前,连生一眼就认出,是他刚放生的那只蝉。连生问,你回来做什么?蝉说,你的面不是丢了吗?连生看了蝉一眼,没有理会。蝉说,我带你去找回来。连生说,真的?蝉说,你跟我来。蝉说完就张开翅膀飞,连生也跟着蝉一起飞。他们飞到了一个地方,像是二先生的牵面房,又不全像,那里堆放的面,比二先生那里的还多。连生装满了两个提箩,可往回飞的时候,提箩太重,他提不住,两个提箩全掉到烂泥田里了。连生一惊,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
因了这场梦,连生更郁闷了。母亲收工回来,见他像个蔫茄子,坐在家里不动,有些惊讶。母亲问,你不舒服?连生不答,母亲追问得更急了,还把手搭在他的额头上,试体温。也没有发烧啊,母亲疑惑地看着连生。这时,隔壁的二婶过来了。二婶是提着那箩面过来的,手里还捏着一杆小秤。
二婶说,嫂子,二先生的面称错了。
母亲一惊,称错了?不会吧,二先生的秤向来称得准。
二婶笑了笑,说,这次称得不准了。
母亲看了一眼连生,又转过头来看二婶,问,是不是称少了?少了多少?
二婶说,不是少了,是多了,多了半斤多呢。
多了?怎么会多呢?母亲和连生一齐把目光投向二婶,还有二婶手中的那个暗花提箩。
二婶说,真的称多了,我回家提起那箩面时,觉得沉沉的,比我装的麦子还重,用秤一称,还真的是重了。
母亲接过二婶手中的秤,也把自家那箩面称了一下。一称,母亲的脸就阴了。二婶问,么样?多了还是少了?母亲说,少了,少了半斤多呢。
怎么会这样?母亲和二婶一齐把目光转向连生。此时,连生的情绪比先前明显地好了。看到情绪好转的连生,母亲的心情也好了,毕竟跟儿子比起来,多半斤面少半斤面太小菜了。
不过,母亲还是想问个清楚明白,连生就把路上的事说了。听连生说完,母亲和二婶都大笑起来,二婶笑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待到两人停了笑,连生说出了自己的疑惑。连生说,提箩里的面怎么看着比原来浅了呢?母亲说,我的傻儿子,你提着走了那么远的路,撞来撞去的,原来的空隙就撞没了,所以你看着浅了。
听了母亲的解释,连生一下子跳将起来,低着头朝门外跑去,一直跑到了那片竹林里,二婶在后面喊,连生,晚上在我家吃面呀。没听到回声,只听到竹林那边,传来一片悠扬的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