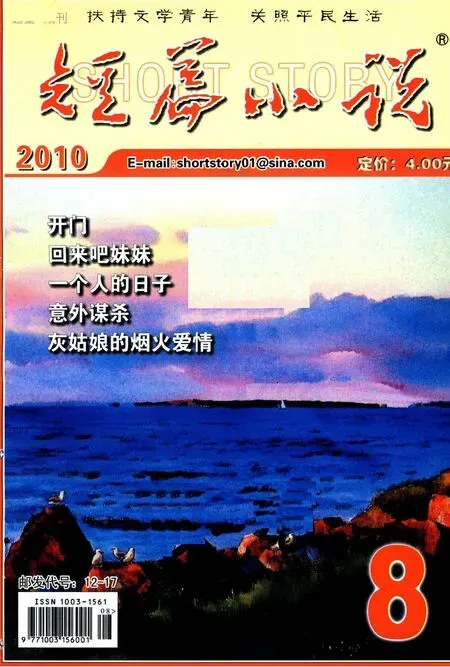一碗黑鱼肠
◎王生文

维云老汉明天就要过六十岁生日了,老伴舒婶试探着问他想吃点啥,维云老汉随口说:“以前怎么过还怎么过。”
舒婶听了,忙说:“那不成,这次是过花甲的生日,一碗红茶蛋不行的,要不,我去买一条猪腿?”
“说得轻巧,一条猪腿八九块,你不知道?”
“那就把那只芦花母鸡杀了,给你下酒!”这回舒婶说话的口气不是商量了。
“杀了那只芦花母鸡,一天一个鸡蛋你下?”维云老汉更凶了。
维云老汉越凶,舒婶就越是难过。这些年老伴没有过一个像样的生日,要怨就怨日子没有过出水,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缓了缓,舒婶一半商量一半央求似的说:“我找秋喜买一条黑鱼总可以吧?”
不想维云老汉说:“黑鱼有什么吃头,要买你就买一碗黑鱼肠给我下酒。”
乡间有“宁丢黑鱼娘不丢黑鱼肠”之说,意思是说黑鱼肠好吃。可黑鱼肠长在鱼肚里是没地方买的,说到底维云老汉还是舍不得让舒婶花钱。不过,舒婶暗自拿定了主意。
快晌午时,秋喜挑着空空的摊篮从远处走来。秋喜每天早晨进两摊篮鱼去菜市场零卖,其中一个摊篮卖杂色鱼,一个摊篮专卖黑鱼。舒婶看着秋喜走近了,叫住她。秋喜停住脚,放下摊篮,一边朝冻得通红的两手哈气,一边等舒婶。
北风头上不是拉家常的地方。闲话了几句,舒婶问:“黑鱼还抢手吧?”
“抢手呢,那些单位上的女人兜里有钱,只挑黑鱼买。”
舒婶接过话说:“黑鱼好吃是好吃,可她们的手娇嫩,怎么杀得了那‘霸王鱼’?”
“可不是?那些个女人揣着个暖手宝,巴不得我杀好了给她。哼,人分贵贱,皮肉一般,不说每斤加一毛,就是加两毛,我也不赚那钱!”秋喜愤愤然。
可舒婶的手沟壑纵横,娇嫩不起来。起初只是想帮秋喜去给买黑鱼的人杀鱼,换一些黑鱼肠回来给老伴过生日,没想到杀鱼还能赚钱,就凑近一步说:“我闲着也是闲着,要不明天帮你去杀鱼?”
“那好啊,有婶子帮忙,我的鱼肯定卖得更快。”秋喜高兴得不得了,临走,还不忘回头叮嘱一句:“婶子,刀和砧板你自己带啊。”
第二天蒙蒙亮,维云老汉还在睡,舒婶就麻利地起了床,提着砧板和刀往菜市场赶,她赶到时,秋喜的摊篮才放下。舒婶见机眼快,拖出一旁放着的脚盆,去水龙头那里提了水倒进去,然后把摊篮里的黑鱼一条一条往里捉。
很快人就多了,秋喜扯着嗓子喊:“黑鱼,黑鱼,包杀,两块六一斤。”
果然就有穿着羽绒服、袖着暖手宝的中青年女人过来了,用嘴唇和下巴支使着秋喜“我要这条”“我要那条”。秋喜用网兜兜出黑鱼,过完秤,就交给蹲在身旁的舒婶。
舒婶瞅准机会,翻过刀背,往黑鱼头上一击,黑鱼的威力就少了七八分,舒婶便趁机张开粗糙的左手手指,扣进黑鱼的牙腮里去,黑鱼挣扎着,尾巴左右摇摆,把它铁刷般的腮刺扎进舒婶手指的裂口里去。舒婶忍着痛,开始除净鳞片,剁掉鳍翅,再剖开鱼腹,取出鱼肠,切下鱼头,然后将鱼身切成一圈一圈的薄片,堆在砧板的一头。接下来该处理鱼头了。黑鱼头又叫鱼盔,很难剁开的,但舒婶并不剁,而是翻过鱼盔,把刀刃切进去,再换左手稳住刀柄,抬起右手手掌,对准刀背拍下去,三下,顶多四下,舒婶的铁砂掌就将鱼盔分开了,再二分为四,鱼盔就算处理好了。
这一过程需要七八分钟,站在嗖嗖寒风中的女人们,大多把脖子缩在羽绒服的绒毛里,她们见舒婶处理完鱼盔,大多都结账走了,更有人连鱼盔都懒得要。
舒婶一刻不停地忙了两个多小时,等终于停下来时,脚盆里只剩一条黑巴膏子了。乡下人把几两重的小黑鱼叫黑巴膏子,形容其小。秋喜兜出黑巴膏子,放进舒婶装鱼肠鱼盔的塑料袋里,这等于是送给舒婶了,然后从钱盒子里取出五元八角钱给舒婶,舒婶接过钱,把八角零钱又放回盒子里,说:“哪能白要你的黑鱼呢。”
舒婶洗净了砧板和刀,在市场花三元五角给维云老汉买了一瓶老白干,想了想,又花一元四角给他买了一双手套,才快步往家赶,那么多黑鱼肠理干净要时间。
早饭的时候,维云老汉往桌前刚坐下,舒婶就将老白干拿出来放在桌上,维云老汉正要开口问,舒婶又端出一大碗香喷喷的黑鱼肠放在他面前,刚要转身,维云老汉一把抓住舒婶的手——那双手除了像锯齿一样,左手拇指上还有一条深深的刀口……
维云老汉这次没有凶舒婶,他抹了一把眼睛,低头走了出去,不管舒婶在身后怎么喊他。
也就一根烟的工夫,维云老汉回来了,他给舒婶买了一张创可贴和一支维生素E膏。酒杯子也多了一个,这是四十几年来舒婶第一次被维云老汉逼着喝几口,还真像他说的那样酒暖身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