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文学雷达
■
我和雷达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末。近二十年来,无数次相逢,无数次采访,也无数次聆听过他的发言。真诚坦率,掷地有声,雷达的评论和他的为人一样实实在在。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十楼会议室,雷达有一个几乎固定的位置,即主席台右手的头个座位。多数研讨会步入专家讨论的正题时,雷达总是第一个发言。”2010年9月22日,《中华读书报》以《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为题刊发我和雷达的对话,开头就这么简单。
雷达看到后打电话给我:“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写,这是你的观察。”随即他说,万一我不是这个位置呢?我说,我只管实事求是地写。
曾经连续十年,《中华读书报》每到年底组织文章进行文坛回顾,雷达是我必须采访的评论家之一。不同的是,每次侃侃而谈之后,他总会反复提出修改意见。
谨言慎行。这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我理解他推敲斟酌自己的每一句话,是因为他尊重并体贴作家们的劳动,他知道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评价,将可能给孤独的写作者带来莫大的鼓舞和动力。这也使得他的评论即便批评也是充满善意。他总能发现作品的优长,不会轻易否定某个作家作品,他的恳切、真诚,不由得让你心生敬意。
2018年初,他的《黄河远上》和《雷达观潮》先后出版,我们曾围绕这两部作品多次通话,我认识他近二十年,这时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倾诉的欲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
这个想法后来用作我们访谈的标题。文章于2018年1月31日刊登,成为我和雷达的最后一次对话,也是雷达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
蒙田说过:“如果我希求世界的赞赏,我就会用心修饰自己,仔细打扮了才和世界相见。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
雷达喜欢这段话。因为他的文章正是这样的呈现。他曾经说:“如果有一天,我远离了我的朋友,他们重新打开这些散文,将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性格和一张顽皮的笑脸。”
2018年3月31日。“有一天”突然到来,令人猝不及防。一位德高望重的评论家走了,留下那些会说话的文字,让想念他的朋友们追忆那张“顽皮的笑脸”。
1
雷达于1943年出生在甘肃天水,三岁时父亲去世,担任音乐教员的母亲守寡一生把他抚养成人。上小学前,母亲逼雷达每天认三个字,常常是记不住不准吃饭。母亲对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有很好的感悟力,但性格忧郁敏感甚至有些暴躁,她对雷达的影响是终生的。而雷达后来选择文学,和他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朱世豪密不可分。朱老师曾不断表扬雷达的作文,并借给他鲁迅选集。之前一向喜爱数理化的雷达,转而报考了文史类。这一改变决定了雷达的终生去向。他在大学时开始尝试写作关于杜甫诗歌的阅读札记,投到甘肃广播电台后被连续播出,电台编辑甚至以为他是大学老师。那时候,雷达的文章已初显老辣。

雷达
雷达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最早是从王蒙开始的。1978年初,雷达写了一篇关于王蒙的访谈和评述,叫《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发表在文艺报。
四十年过去了,雷达写了多少评论文章没有具体统计过。可以确定的是,有相当一批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第一篇评论或最早的评论是雷达写的。他参予撰写并主编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以最能体现近30年文学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本质的若干问题作为论述焦点,把复杂的现象和浩瀚的作品糅合到一系列问题的阐述中去,描绘出近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思潮起伏的画卷;《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作家出版社)充分肯定了当前文艺创作的优秀成果,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起了文学界强烈的反响;《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搜索当代文学关键词,聚焦茅盾文学奖,构建作家作品档案,并由此引发边缘思絮,是一部颇多创见的论著。继《黄河远上》(民主与法制出版社)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雷达观潮》。后者是雷达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设的“雷达观潮”专栏为主体,结合创作实际,提出的诸如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代际划分的误区、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文学与新闻的纠缠、非虚构的兴起、文学批评的“过剩”等一系列前沿问题,思想活跃,敏锐深刻。
毋庸置疑,雷达评说了不同时期的重要的作家作品,为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作家贾平凹赞赏说:“对雷达的评论,可以用‘正’‘大’来比喻。‘正’,是他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经历的事多,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涵着传统的东西;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大’是他有大局意识,看问题常从大处看,看趋势,能‘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文章也就会写得通达顺畅,文采飞扬。”
有人认为,雷达属于“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一脉。马列文论对他的影响很深,同时,十九世纪的别、车、杜以及后来的泰纳对他影响也很大。新时期以来,雷达尤其注意吸收国外社科的思想成果,既喜欢读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也喜欢读本雅明、巴赫金、福柯、伊格尔顿、杰姆逊,但都不系统,用他的话说,是“随兴之所至”。他的评论里感性比较丰沛,非常注意捕捉典型形象;感性和直觉并不意味着没有深度,理性的洞察通过感性的方式同样可以深入表述。他对作品的解读和定位比较准确,能抓住对方的灵魂和要害,从文本、话语出发,而不是先验的、从概念出发,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常有让作者意想不到的地方。
实际上,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学术界的认知度可能比较低;但对从事者本人来说,付出的劳动却往往是艰辛的,要求必须有大量的阅读、活跃的思维以及足够的信息来支撑。雷达一直站在当代文学的前沿,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理解做出准确的判断,很多观点在不同时期发生了较大影响。比如,总结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有人认为主潮是现实主义,或是人道主义,或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有人则认为无主潮,而雷达提出“不管文学现象多么纷纭庞杂,贯穿的灵魂”是“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主潮,这才是长远性的。再如,1988年3月,在《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中,雷达提出了“新写实”作为新的审美意识的崛起和它的几个主要特征,那时雷达称之为“新现实主义”。1996年,他最早提出“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提出“主体意识的强化”“新世纪文学的生成与内涵”“当前文学症候分析”“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与拯救”等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重要作品和文学现象,《白鹿原》《废都》《古船》《平凡的世界》《活着》《红高梁家族》《厚土》《少年天子》等等,雷达都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评论家白烨评价“雷达是名符其实的‘雷达’”。这确实是一个准确生动的说法,四十年来,雷达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他在评坛乃至文坛的地位,无可替代。
2
有的文学评论擅长说理,出言即是自成体系的理论,却将人拒之作品之外,越看越晕头转向;有的也擅长说理,但言之有据,不由自主跟随他的语言进入文学世界,总能有意外的收获。
雷达是后者。他的评论建立丰富的文学史和理论素养之上,从文本出发,感情充沛,真诚质朴而鲜活生动;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梳理者,“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大文学现象,他均作了及时的、充满生命激情和思想力量的回应”(刘再复语),因而充满一种“理性的激情”。

《雷达观潮》
很长时间,雷达曾为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的“正常”而困惑,他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与过去相比,现在文学批评的批评主体、批评资源、批评环境、批评话语、批评类型、批评方式,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但是在雷达看来,文化批评取代或遮盖了文学批评,相当多的文学批评也是以文化研究为指归,比较纯粹的文学批评不断边缘化,虽然有人坚守,空间仍在不断缩小。

《皋兰夜语》
这与文学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所占份额和影响力的减弱是不可分的。文学批评在面对当今的时代思潮、历史语境、现实生活、创作实际时,表现得比较被动、窘迫、乏力,缺乏主体性强大的回应和建构性很强的创意。人是一种不但能感觉自身存在,还能够反思自身存在的存在,那就必须在物化世界之上,构建一个意义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现在批评的问题是,很难构建起这个世界来。而现在恰恰需要重建批评的理想和公信力,强化批评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增强批评的批判精神。他也曾不止一次为“大作品”的缺失探讨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既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有丰厚的生活体验的积累,又获得了广博的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素养,相互撞击,使得他们往往能够站在世界的和人类的、同时又是中国经验的高度来驾驭和创作;而当下我们的作家缺乏的正是这样广博的文化修养和眼光。
从事当代文学研究,阅读作品是个跨不过去的基本功。再高明的批评家再怎么穷经皓首,大概也有拿不准的作品。雷达也不例外。当他与某些新现象猝然遭遇时,甚至出现过失语。比如,面对1980年代中期的某些实验性作品,语言革命和叙事圈套,雷达就曾坦率地表达过自己准备不足。是的,任何批评家都不是万能的,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个性和口味偏嗜,都有自己拿手的领域或隔膜的圈子,都有可能去寻找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但无论何种情况,他在面对批评对象时,始终充分准备并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保持着批评的良知和公心。他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史,已成为中国文学思潮的见证史。
他也坦承在读书生活中存在不能驾驭的危机,并深深为之苦恼。他每天被书所困:要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总也读不完;想读的东西总是堆在那儿,总也读不了。他的困惑,其实是时下书界、文坛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苦恼着,一方面,他仍然怀有坚定的信念,他想总得给心灵的阅读留出空间,让读书回到读书的本意上去:不再是精神的桎梏,而在精神原野上的自由驰骋。
3
雷达的评论权威,这是文坛公认的。贾平凹在分析“雷达为什么能有权威”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几点:一是他对中国有着认识和把握,能做大事,敢担当; 二是他对创作有感觉,散文写得好;三是对文坛的情况了如指掌,看作品能放在全国的大盘子上比较,看问题能从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来考量;四是他的性情除真、直以外,有些孩子气外,在坚持里多变,在诚信里表现出多疑、独立、特行、强势,这种性情是成大事的性情。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雷达的散文不亚于评论,但因评论做得久,文章做得多,散文的成就便被遮蔽了。
四十年间,雷达多从事文学评论,惯于用概念、理性、逻辑说话,其实他同样热爱散文,并希望在散文中让血肉饱满的形象说话,所以在编选《黄河远上》散文集的时候,他完全剔除了议论和思辨色彩的文字。《黄河远上》中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亲历的,毫无粉饰的,同时也充满各种历史的或个人的波折。雷达的写作,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切身经历展开的。正如评论家古耜指出的,作家从亲身经历出发,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全无粉饰的敞开,其强烈的纪实性和现场感,以及浸透其中的披肝沥胆的自我解剖和真诚言说,足以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这组作品书写作家经历,但又不是纯粹的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很自然地渗入历史镜像与地理人文,于是,作家那一片片丰饶的记忆沃土,开满了社会心理,民间传说,历史事件,地域风情,时代氛围的花朵,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甘肃省乃至整个西部风俗史和精神发展史的部分。
民间记忆,个人化记忆的价值在今天已是无庸置疑,但雷达不太主张过于纯粹的个人化记忆,否则面太窄,圈子划得太小,容易陷入一己的悲欢,意义也会受限。个人记忆和时代风雨裹挟在一起,无形中成为风俗史,心灵史的一种表达,作品才会走向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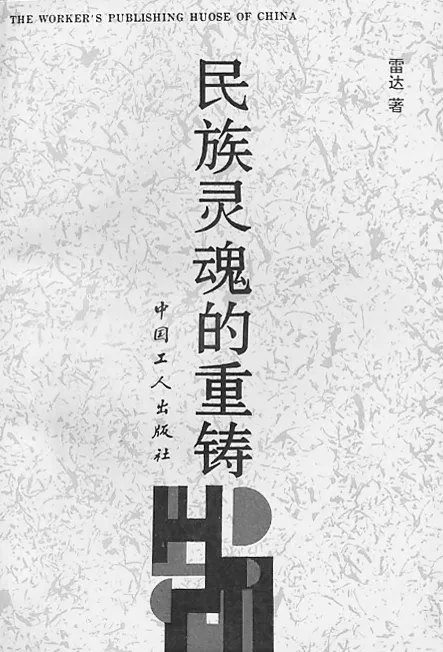
《民族灵魂的重铸》
如何做到既带有自传色彩,但又不是刻板的自传,而具有散文的广延性,抒情性,联想性,雷达的探索值得思考。《黄河远上》一开始,雷达写了亲见的西北战场最残酷的恶战——兰州战役。当时雷达只有六岁,血与火的记忆却终生难忘。接着写了震动全国的“邱家血案”,也不是故作惊人之笔,这是雷达每天上学的路上发生的真事,是他凭着记忆写出的。《梦回祁连》是以四清运动为背景的,既无法不交代四清时的政治情势,但又不能陷入政治评价中不能自拔。这么大的全国性的运动,从何处下手?的确很难驾驭。雷达以“我”为中心,连结乡土人物和工作组长,将其它推到背景,将主要的空间用来描写当年河西走廊的风土人情,写出了人性的美丽与残酷,写出了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情调”和“风光”。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
真正能够叩响心弦的才是好散文。真情实感永远是散文的命脉,这恰恰也与雷达朴素本质的性格吻合。真实是分层次的,表象的真实,较深层次的真实,以及能直抵灵魂引发共鸣,引起疼痛感或撕裂感的真实,是各不一样的。它们取决于作者投入生命的深度,观察、体验、内省的深度,以及艺术表现的能力。这是无法伪装的。在《黄河远上》一书中,雷达还原了与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风俗史、精神史、心灵史,表现了在极限状态下历史的呼吸、人性的残酷与微妙。文学是靠形象说话的,雷达塑造的形象是多义的、内敛的,所以才更厚重,也更感人。
在《黄河远上》中,雷达不但写甘肃,在《新阳镇》《皋兰夜语》等作中,富有西部特有的地理标识、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陕西宁夏青海新疆他都写过,如《走宁夏》《依奇克里克》《乘沙漠车记》《圣果》等。而散文《韩金菊》写遥远而凄美的初恋,委婉多情,特别令人感动。
这是一篇原本没打算写的散文。他不想触动一生的痛。然而随着一天天老去,那段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藏在心里,他总觉堵得慌。可一旦写起来,却又伤心得写不下去。他笔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无一丝虚构。文章发表后又在微信上推出,点击率上万,留言之多,超乎想象,很多普通读者留言说它“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读来“几度哽咽”,甚至“每读一遍,都要流一次泪”。
再比如,《费家营》的开头,本是朋友带雷达游览一个新景点“黄河湿地公园”。他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当走到一个最大的鹅卵石水坑前,旧景重现,他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呆立无语。他暗自揣测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他们曾洒下无数汗水,连抬着沙筐走路都要睡着或栽倒的那块地方。后来根据对地理方位的反复核对,发现正是那块地方。至今还没有任何人道破过它的秘密,更没人想到过它其实是1958年“大跃进”一个遗迹的巧妙利用。于是,当年“劈北山,挖渔池,大炼钢铁”的震耳的口号声顿时在雷达的耳边炸响。回忆的大幕就此拉开。
这个开头被读者称做“华丽转身”。但雷达的写作,并非出于技巧的需要,而是生活本身就这样巧合。除了在叙述风格上努力做到客观,冷峻,质朴,丰腴之外,如何打通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也即实现某种“穿越”,唤起读者的共鸣,雷达的尝试是成功的。《费家营》被评为2015年“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散文类的榜首。
其实,雷达在取材上没有任何优势。他既不是出身名门之后,将相之后,耳濡目染过多少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能自然而然地写出读者渴望了解的名人逸事,历史传奇及某些秘密;他虽然一生也是磕磕绊绊,但并没有九死一生,大起大落,骇人听闻的苦难经历,那样的人下笔即能感染读者并且触发历史反思。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雷达曾经表达过自己的疑虑:“我常想问人也问我自己,这些以亲身经历为背景的东西,究竟谁会看,有哪些东西可能是人们需要知道的,是有价值的,它有可能吸引哪些人的眼睛和心灵?是否可以这样说,它包含着历史情景的,西部人心灵史和文化史的信息,一个人如何成长的过程,人的灵魂怎样遭遇风暴袭击的,人战胜自我和环境的隐秘的关键,以及从这个人身上折射的近六十多年来的动荡与曲折,它可能还有激励西部封闭境遇里的青年的作用,激起他们的自豪感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勇气,从自卑中挣脱出来。总之,不是简单的褒扬,也非故作高深,不是要迫不及待地肯定什么,更非钓名沽誉,而是以人为本,写出性格来,写出人生来。”
他一边疑惑着一边未曾放弃努力,同时也在不断的求证中增强了信心:
“我仍然可以告诉读者很多,我这个人,或这颗灵魂,他做什么既重要,也不重要,他有何业绩既重要,也不重要;但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热烈的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一个绕系着文化精神冲突的人,一个心灵在场,注重从体验出发的人,一个与我的年代的生活和心灵紧紧相连的人。”
雷达的散文写作,是个人命运与时代面影的交叠合一,“历史真相隐藏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之中”,因而赢得共鸣,《黄河远上》上市不到一个月,就销出了一千多本。同样,他的评论集《雷达观潮》上市不到一个月,便销售告罄。

《思潮与文化》
从1978年走上文坛,雷达以评论名世,直到2018年才推出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纯粹的散文集,对于雷达来说是一种必然。他的评论,无论涉及什么,最终会落足到人文关怀。他认准一部作品长远与否,与作家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永恒的人文关怀,人的灵魂总是漂浮和挤压在暂时的处境之中,像风中的浮尘一样飘荡无依。他在“对当今文学存在理由的若干思索”中,提出“文学史证明,许多日常化的、无意义的东西,往往最具文学价值。我们是否忽略了私人空间?忽略了某些貌似无意义实乃最具人生意味的空间?日常化记忆与私人化记忆,对文学来说都很重要。”
福柯说,重要的不在于你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你在哪个年代叙述。当雷达在新时代展开他的个人叙述,其笔触指向被遮蔽的历史角落以及情感隐私,大胆地实践“个人化的抗争”,实际也是对于自我评论观点的一种实践,他回到鲁迅的起点,张扬个性,坚持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富有个性地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当前文学症候分析》
雷达的散文写作,受《朝花夕拾》的影响最大。那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后来改为《朝花夕拾》。“朝”意谓早年,“夕”表示中晚年,即早上的花朵晚上来拾采。鲁迅先生回忆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人事,每一篇都是那么沉郁而亲切地展示着世态变迁,人情冷暖、历史沧桑,风俗礼仪,且感情蕴藏得那样深沉,他对社会、人性的深邃洞察和对亲人师友的诚挚感情,只有反复读之才能心有所得。
雷达一直心向往之。他写散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
他的性格率真,不善于遮饰自己,同时也有些叛逆,从小就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意识,没有多少世故和城府。
“我长到22岁时离甘赴京,从西北到了华北,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北方。我发现,我的口味极其顽固,喜欢辣,酸,喜欢牛羊肉,喜欢面食,米饭基本不动。一天不吃面就没着没落的。这绝非我矫情,作秀,实在是一种连我自己也无法解脱的根性。我承认有的人随遇而安,善于应变,但我做不到,我可能属于最顽固的分子。”
在雷达的身上,集中了许多矛盾,他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新旧两个中国,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两条河流关系密切,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他曾奔跑着呼喊着去看黄河“开河”的壮观;他在故乡渭河的臂弯里沉酣地睡去。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经历了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直延至新世纪,像一条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非常密集。在相当的时间里,他只是一个学生,但是,他的眼睛从一个自己的角度看到了许多难忘的往事。弥足珍贵的还因为,他出生并生活到二十多岁的西部,其情调,风俗,生活场景,文化传统,都有丰富的意蕴,到今天,它仍然是神秘的,被遮蔽的,它们的价值有必要得到彰显。
有位哲人说过,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或者多么小的人物,多么尊贵的人物,或者多么卑微的人物,只要他负载的信息有足够的精神含量,那么就具备了使用散文这一形式的条件,把它们记述下来就是宝贵的。灵魂的历史比历史本身更鲜活、更耐久。作为一个跨越了众多剧变年代的人,雷达的内心世界却是丰富的,敏于感受的,惟其单纯,不掺杂质,反而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心灵的历史。
雷达曾在《我的散文观》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首先必须是活文”,而非“呆文”。比如,一度文化散文成风,余秋雨早期的一些文章,雷达认为有开创性,走在前面。但后来忽然很多,有的看上去很渊博,什么都知道,不少是临时从网上书上查的,这未尝不可,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但罗列太多,掉书袋,性灵就不见了,便“呆”了。还有,中国散文的叙事记人,有极深厚传统,弄不好它会变成一种模式的重压,也容易“呆”。“活文”恐怕首先得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包含细腻复杂的人性之困和情感矛盾,这种境界和格局,与作家的知识积累、文学素养有关,更与作家的情怀有关。

《重新发现文学》
“我知道,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活着的尽头是死亡,爱情的终点是灰烬,写作的收场是虚无,不管我们多么珍视自
己的这些作品,这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尽管如此无情,我们依然要尽力地活,尽情地爱,尽心地写……我自知渺小脆弱,难脱定数;我自知人生短暂,如飘尘,如流云,恍然若一梦,却仍想顽强地活出一点意义来。”雷达在《黄河远上》序言中的表达,今天看来似乎是隐约的一种告别。他一直将读者的需要和喜爱、以及心灵难抑的诉求共视为写作的动力。他说,如果自己的文字能让一些读者“在车上,在厕上,在枕边,翻一翻,会心一笑,引起一些共鸣和遐思,那我就没有白写,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舒晋瑜,生于山西霍州,祖籍山东博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自1999年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现为总编辑助理。著有《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