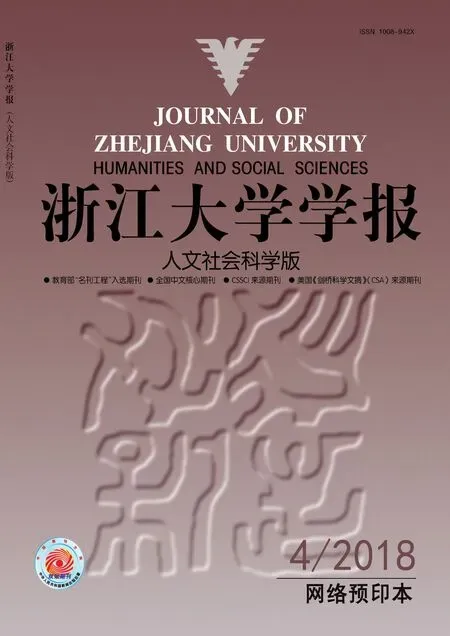司法透明评估的大数据方法研究
康兰平 钱弘道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一、 司法透明指数兴起的背景
量化法治的设计与应用引领了法治研究的实证转型,并在地方层面衍生出多元的实践模式,司法透明指数即司法公开领域的量化评估实践。司法透明指数是一整套量化司法公开的评估指标体系,旨在通过科学量化方式衡量法院司法公开的实施状况和透明程度[1],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提升司法实施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础、智识支持和实践经验[2]。司法透明指数的应运而生既契合了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践行了司法为民的核心理念,也回应了民众对司法工作的新期待、新需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用量化分析技术衡量法治实施成效成为制度层面的共识和实施机制[3];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持续推进司法公开和规范司法权力运行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4];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又将阳光司法机制细化为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11项具体举措;2016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着重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尊重司法规律,促进司法公正,完善对权利的司法保障、对权力的司法监督”;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透明指数即上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实践和现实突破口。
作为量化评估领域的第三方专项评估模式,司法透明指数在实践探索中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从理论维度上看,司法透明指数应国际透明化浪潮和社会指标运动而生,吸纳了实证主义哲学的精髓,实现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互补互惠[5];从实践向度上看,司法透明指数契合了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深度与广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规范司法权力的运行,践行司法为民的核心宗旨[6]。当然囿于量化评估的实证化误区[7],司法透明指数在实践探索中也面临着主客观指标设置随意、调查问卷设计的信度和效度难以验证、量化评估方法论局限等问题。可以说,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评估活动开启了法学研究的数字管理先河[8],在方法论和实践层面重构了法治研究的学术图景。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不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给量化法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评估实践亟待跳脱抽样小样本时代的测量误区,借助大数据技术,探寻司法公开的透明程度、内在规律、运行机理、实施成效、影响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改革的方向。
二、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的证成与回应
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审判实效的有力抓手和有益尝试,司法透明指数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成为倒逼法院改革的有力治理工具[8]。以下将以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为例进行分析,聚焦于测评方式、量化方法以及评估结果的实效等,探究司法透明指数测评在数据筛选与收集、统计分析及结果验证等方面的不足,以此来窥探抽样小数据统计时代量化评估的方法论局限及其应用限度*司法透明指数区别于纯粹思辨研究或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经由数据发现事实而非由理论推演而得出结论。但从当前的应用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缺乏对测量过程和测量方法的应有关注、数据视野过于狭窄、缺乏类型化的数据应用思路、缺乏对数据收集和应用方法的反思等问题,司法透明指数陷入了方法和技术的误区,影响了评估实效的发挥。参见何挺《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应用为中心的探讨》,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98-217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证成与回应,对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实践图景进行前瞻性预测和现实勾勒。
(一) 司法透明指数的实证研究
国内已有的司法透明指数实践主要有阳光司法指数、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司法透明指数、中国司法透明指数等,笔者以浙江大学司法透明评估课题组于2012—2015年在湖州市吴兴区法院所进行的跟踪评估作为分析范例。具体而言,2015年度吴兴区法院司法透明评估体系的测评方式如下:(1)在指标体系设计上采用了总指数与因子指数相结合的模式,细分出行政管理透明指数、司法过程透明指数、民意调查指数,综合考察司法公开的实现程度以及关联机制。(2)在指标设计上实现了对司法公开运行的实时动态监测和操作性过程解释,评估指标体系聚集于行政管理、司法过程两大维度:其中,行政管理维度下设3项一级指标、19项二级指标,涉及人事、财务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司法过程维度下设3项一级指标、28项二级指标,围绕立案、审判和执行等司法公开实施过程和关键因素对司法公开运行状况进行评测。(3)将公众评价纳入司法透明指数测评,从47项二级指标中选取与民众知情权、监督权关系最紧密的10项作为民意调查内容[6]。(4)对系统层指标进行权重分配,其中行政管理透明指数占15%、民意调查指数占30%、司法过程透明指数占55%,通过系统层、因子层、指标层权重进行合理分配,突出司法过程的重要性,注重司法公开的实施效果。其中,行政管理透明指数由人事管理、财务运行、公众交流等因子层和具体指标组成,在具体指标设计上体现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司法过程透明指数包括立案公开、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民意调查部分,分企业、政协、律师、学校以及社区组,从中选取抽样调查对象,通过科学的统计调查方法了解民众对司法公开的舆论导向及内在需求。通过对比分析吴兴司法透明指数各因子指数和总指数历年得分情况的变化趋势可知:2013年吴兴法院各因子指数(民意调查、行政管理、司法过程)得分依次为63.84、56.82、82.14,司法透明总指数为0.729,相较2012年,司法公开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步;此后,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总指数逐年攀升,成绩斐然,到2015年已达到0.864[8]。
运用SPSS20.0软件对2012—2015年吴兴法院司法透明评估的各因子指数进行描述性分析(详见表1),我们发现民意调查指数的数据分布比较集中,稳步上升;行政管理透明指数和司法过程透明指数的数据波动幅度较大,呈现出数据分布不稳定和离散程度高的发展态势。结合吴兴司法透明评估历年的评估报告,司法透明评估面临着价值和技术层面的障碍,一方面是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质疑;另一方面,司法透明评估难以反映司法公开的运行规律和潜在影响因素,面临着评估结果的悬浮化和泡沫化风险。

表1 吴兴区法院司法透明指数评估各因子指数的描述统计量(2012—2015年)
(二) 司法透明指数的实践限度
以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中的数据来源和使用情况为例,其使用的考评数据大都来自法院的内部数据,实践中存在自说自话的嫌疑和数据标准化处理的技术误差,单一的法院内部考评数据容易产生测量偏差,甚至沦为内部考核的幌子[9]。吴兴司法透明实验中的数据处理和运算操作过程中存在着评估数据比较功能缺失、不同来源的数据间可比性差、评估数据间的价值关联度低等缺陷,不利于对司法公开的实施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判断。在量化方法的具体应用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数据测量过程的操作性解释,且缺乏对运算过程的公开和对结果的校验,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均大打折扣,无法为公众所信服[10]。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评估活动缺乏对评估结果的元评估和结果校验机制*Michael Scriven是元评估(meta assessment)的提出者,元评估是以评估本身为研究和规范对象,这实际上是由评估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关系到评估活动的历史发展归宿,也是其逻辑开展的终极归宿,是推动评估科学化的核心论域。参见Scriven M., The Logic of Evaluation, London: Edgepress, 1981;Scriven M.,″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 in Evolutionary Theory,″ Science, Vol.3374, No.130(1959), pp.477-482。,评估结果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司法透明的真实程度仍存在不少疑问。通过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我们发现当前量化评估实践中存在定量研究方法论的局限,在数据收集、数据统计、指数运算以及结果验证等方面均存在操作局限与技术短板。司法透明指数的公众调查问卷也存在主观信息转化为客观数据的操作性技术难题,影响了评估数据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由此造成评估结果公信力和可靠性的不足[11]。为此,有必要重视并开展数据定量分析的方法论研究,让数据发声,既要避免唯数据是从的数据迷信,也要充分发挥数据理性的内在驱动力,在边界可达和理性超越之间实现动态的平衡[12]95-99。
具体而言,检视司法透明指数的各个组成因子指数,我们发现如下缺陷:首先,在司法公开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偏差,影响了评估的实际成效。吴兴区司法透明指数尽管采用了主客观指标结合的方式,但从其客观指标的设计来看,存在指标效度低、收集成本高和真实性备受质疑等问题;而主观指标则受制于调查对象的个体差异和认知偏差,并且容易受到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主观评价波动性大,面临着信度和效度的考验。通过对吴兴区法院2015年民意调查问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在政协委员和学校调查问卷部分存在信度不高以及调查群体的认知差异(详见表2)。对政协委员和学校部分问卷进行克朗巴哈系数的可靠性检验,前者为0.686,后者为0.885。对政协委员组别进行样本偏差和离差系数计算,我们发现其标准差高达1.17,离差系数为30.47%,组间离散程度大,抽样样本的信度和效度有待考量。

表2 民意调查评价分数表
具体来看,调查对象对民意调查10项问题的态度存在较大波动和认知差异,其中对“法官个人收入透明”问题的满意度最低,标准差和方差分别为0.972、0.945,在所有问卷项中最高,显示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也表明公众对法官个人收入透明的高度关注(详见表3)。而通过与行政管理透明指数以及司法过程透明指数的比照分析,我们发现,受制于抽样小样本时代的方法论局限,很难对此进行因果规律研判和关联影响因素分析。因此,司法透明评估始终面临着方法论的技术误区和应用限度,难以有效地挖掘司法公开背后的制度性影响因素以及内在关联机制,从而影响了评估的实效和应用价值。
由表3可知,学校组别的调查对象对法官个人收入透明的需求度高,组间数据离散程度高,数据波动幅度大。对法官个人收入公开透明的强烈司法诉求,反映了民众对司法公开具有多元化需求,更加注重司法公开的实质内容以及对司法权力运行的规范。民众对司法公开的认知逐渐加深,也凸显了既有司法透明评估指标设计和评估方法的局限性,无法深层次洞悉司法公开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及关联机制(详见表4)。
通过对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2015年报告进行内容效度的文本分析[8],我们发现受制于理论预设的先验与悬浮[13],司法透明指数难以有效厘清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造成了评估倾向于制度层面的绩效考核,忽视了对司法公开运行规律的揭示和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面临着评估结果应用限度有限的实施困惑。

表3 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2015年度学校组别问卷调查描述分析

表4 法官个人收入透明的描述性分析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评估活动进行了反思与质疑[14],法治评估实证方法论的应用限度越来越受到关注。从法治评估的实施效果来看,法治评估受制于主体的中立性、问卷调查的抽样误差、评估结果的客观真实性以及难以有效回应司法实施的具体情境和制约性影响因素,导致了实践中法治评估的实效难题。量化法治实际上处于悬浮化状态,难以有效进行真正实践意义上的研判与预测,反而陷入了工具主义的技术泥淖,司法透明指数亟待改变当前困局,洞悉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内在关联机制,进行数据应用的去伪存真,从民众的获得感角度来探究司法公开深度与广度的延伸,提升司法公信力。
(三) 回应: 大数据视野下司法透明指数的精准化转向
从司法透明指数已有的数据分析和应用来看,数据分析作为决策支撑尚未成为气候,驱动力不足,其配套的绩效考核机制也亟须完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司法机关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大数据思维和分析方法有别于传统数据收集和运用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全样本性、混杂性、高速性、价值性[15]。大数据分析颠覆了以往实证研究对因果关系的探寻,而是着眼于挖掘不同数据间的相关关系,同时进行有效预测[16]。相应地,司法透明评估也要进行观念和方法层面的变革,不断更新调查方法,创新调查方式,实现数据的全样本性,不断提升数据治理水平、预测司法运行水平和决策水平[17]。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指出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是顺应大数据时代潮流发展趋势、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期待的重要举措。建设智慧法院,就是要以信息化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全流程审判执行要素依法公开,让司法能够更加契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通过司法审判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辉。伴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司法透明评估亟待进行理论回应与实践转型,亟待由粗放式管理向精准化治理转变。具体而言,从理论架构来看,司法透明评估需要从规范法治观向实效法治观转变[13],应当在理论架构上进行反思与重构,跳出书本法与行动法的规范法治导向,转向探究法治实施成效的实效法治观,关注法治实施的制度文化背景及本土情境。从治理方式上看,司法透明评估需要从宏观层面的经验叙事转向微观验证的社会表征进路。司法透明指数设计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具体实践,表征了司法公开的外生型样态,难以有效回应司法公开的现状和问题,而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从宏观层面的经验叙述转向微观层面的行为分析,厘定司法公开的现状与问题,洞察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内在关联[18]。从技术方法来看,司法透明评估需要从人工判断转变为信息化实时测量[19]。大数据时代,借助互联互通的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实时监测与多元互动,从价值目标来看实现了从程序正义向同理心正义的转变[20]。司法透明评估亟待对司法公开的实施场景进行逻辑诠释和现实解读,通过引入同理心正义,厘清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内在关联和价值导向,探究亲社会性的公共理性培育,形塑民众法治信仰,提升民众法治获得感。
三、 大数据视野下司法透明指数的概念框架设计
(一) 司法透明指数如何适应大数据浪潮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司法评估实践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推进大数据的深度运用,在统一数据标准、深度挖掘信息资源、探寻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减少司法的任意性,提升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增强民众的法治体验和获得感等,是勾勒大数据司法全貌应当关切的具体面相和实践观测点。立足于已有的司法透明指数实践,对大数据司法的认知应当围绕量化评估的数据运用分析过程,即概念化、操作化以及优化设计等方面展开,进行反思与重构。
1.抽样小样本数据的局限性
司法透明指数设计的初衷在于通过量化评估的形式,在抽样小样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数据取样方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动态相对值来诊断和反映法院的司法公开状况。但从历年司法透明指数报告的测评结果来看,传统司法统计模式下小样本研究的弊端制约了司法透明指数实际功用的发挥。以吴兴法院2015年的司法透明指数为例,在民意调查指数测评中,调查问卷设计的信度和效度存在偏差,不同调研对象对司法透明相关信息的获取渠道不同,自身教育水平和专业知识也不同,对司法公开的感受存在主观偏差,如高校非法学专业组别的受访者对司法公开的感受明显低于其他组别;而在社区组受访者中,打分呈现两极分化,其中有受访者出于主观泄愤的情绪化影响,但更多的是对司法透明认识程度不够,对接触的指标打分偏低,对不熟悉的指标反而给出高分。可见,尽管综合采用多种量化分析方法,但受制于抽样小样本的误差、访谈者个体精确性和客观性不足以及因果关系规律难以把握等,司法透明指数容易陷入“实质性隐退”的思维误区,从而造成评估结果的针对性不强和效果较差。
2.司法数据间的价值关联度低
司法透明指数的方法论遵循“假设—实验—证实”的思维模式[1]。首先提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抽样小样本进行实验实证研究,得出司法公开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今后的改进方向。尽管司法透明评估方案设计采用混合的方法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进行深入融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不同司法数据间的价值关联把握不足,陷入了以果寻因的思维胡同。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由民意调查指数和动态监测指数两部分构成,司法透明动态监测聚焦于行政管理与司法过程,权重向司法过程倾斜。其中行政管理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公众交流3项一级指标,司法过程包括立案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3项一级指标;在上述6项一级指标之下设有47项二级指标。但从测评结果来看,不同数据间研究的交互性较低,对数据间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关联度认识不足,难以进行细分类别研究。就得分情况看,吴兴法院执行公开程度相对最高,得分占该项满分的比重为97.38%;立案公开程度次之,得分比重为96.21%;审判公开程度相对最低,得分比重为91.77%。
3.难以有效挖掘数据隐藏的价值
在民意调查指数中,民众对审判公开的满意度>立案公开满意度>执行公开满意度,而司法系统的统计则是执行公开程度>立案公开程度>审判公开程度。司法统计数据和民间调查数据存在评估结果的偏差,公众对司法透明公开状况的整体认知明显有别于官方的司法统计数据结果。司法透明指数的量化评估数据分析缺乏对不同组别数据背后的价值关联探寻,不利于充分发挥量化评估的导向和预测功能,也不利于精准把握民众对司法公开的需求,进行个体需求的精确定位。
(二) 大数据视野下司法透明指数引发的思维变革
理解大数据司法的内涵首先必须对大数据的产生和特征有深刻的认识。大数据又称巨量资料或海量资料[22],其特点可以概括为“4V”,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16],具体表现为全样本性、混杂性、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对大数据的本质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海量数据,要从更高层面关注海量数据背后的价值关联,即海量数据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过程。换言之,大数据即存在价值关联的数据[12]。
以对司法工作影响颇深的司法统计为例,海量数据的处理决定了司法统计工作从传统意义上的抽样时代进入到全样本数据时代,数据采集、数据存储与数据转换等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大数据融入司法统计和审判管理,解决了过去司法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其实时性特点通过数据的及时更新保障了审判管理的高速运转,实现其效能提升;多样性特点决定了司法统计工作应当做好数据分类和信息资料的整合;价值性特点决定了司法统计应当关注海量数据背后的价值关联,关注其价值导向,避免数据孤岛和数据迷信,提升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能力,增进人民群众的法治体验,提升法治获得感。面对大数据,我们必须要明确大数据司法的本质和定义,建立研究和分析大数据司法的正确方法论,从理论、技术和实践层面分析大数据司法的应然图景和实然面向。
大数据司法侧重研究司法制度运行的数据化表达方式和表达手段,以及离散化后的海量数据之间的价值关联,建构在对司法运行规律的预测之上,进而为司法改革提供决策保障和实证支持。具体而言,对大数据司法的内涵认识应当从技术维度和方法论维度展开[16]。(1)技术层面:大数据通过对信息的离散化表达,使信息能够高速、实时地传播,降低获取成本,实现了局部全样本和个体精准,挖掘司法领域数据背后的价值关联对预测司法运行规律和提高决策精确度具有重要价值;(2)方法论层面:首先,大数据司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不对称,司法决策依托于数据不对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信息表达变成了数字表达,信息不对称结构发生了变化,即进入数据不对称状态。其次,大数据司法提升了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成本,对司法统计数据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拓深司法统计职能,提升数据信息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大数据时代司法统计数据面临着从模糊化的经验管理向精准化、科学化的智能管理的转变。大数据司法的核心在于整理、分析、预测和控制,并不是拥有多少数据,而是在数据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其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在认识到数据分析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摆脱对数据的完全依赖,关注司法数据的内在关联。大数据技术不但能够收集和分析信息,也能够对信息背后的逻辑关系做出科学的判断。可见,正确使用司法大数据进行整理、收集、分析,能够为预测司法运行情况、提升司法效能提供决策依据。
司法透明指数受制于传统数据分析模式的局限性,且其量化评估着眼于对司法公开因果关系的探寻。从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来看,仅仅从制度内部建设的角度来树立司法权威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容易陷入司法公开的形式主义,无法捕捉到与司法公开相关联的其他影响因素。司法透明指数从人员公开、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三个维度来测评司法公开的实施状况,目的是合理配置司法职权和规范司法权力运行。但司法公开是一个涉及立案、庭审、执行、审务等方面的实施机制,其实施效果既需要制度内部的管理创新,也需要在情境化制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Sabel、Simon提出了“情境化制度”的概念。情境化制度强调决策过程的透明、多元利益的包容、公平的协商能力,并根据实践情况不断进行评估和修正。在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中,情境化制度针对制度建设内部解释力和践行力不足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和改革方向。司法公开和司法权威的树立需要建立政令畅通、上下一心的制度通道,既要保证决策层的意见能够贯彻,也要保证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能够及时反馈意见和落实政策,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政策本身。破解司法公开的症结,除了需要关键的制度安排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激发司法工作人员的创造力,变倒逼改革为过程监督。建构情境化制度对推进司法公开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发展思路,即在本土视角下探究司法公开运作的独特的组织机制。而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应用有助于深度挖掘司法公开的关联因素,在类型化的思路下探寻司法公开的核心规律和具体要求。参见Sabel C.F.& Simon W.H.,″Contextualizing Regimes: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a Response to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and Policy Engineering,″ Michigan Law Review, Vol.110, No.7(2012), pp.1265-1308。中考量影响司法公开的关联因素。例如,吴兴实验中法院内部数据与民意调查外部数据存在预期差异,司法公开所取得的成效并没有让人民群众产生法治获得感,可见单单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探寻司法公开的运行机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与司法公开相关联的其他外部因素进行深度挖掘,关注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间价值关联的内在逻辑,在遵循数据理性的前提下,厘清边界可达和理性超越的边界,实现内部机制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动态平衡。
(三) 大数据思维下司法透明指数面临的社会变革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内在驱动,正颠覆着传统司法的思维模式,并渗透到司法实施领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具体体现在:第一,夯实司法公开基础,满足民众知情权需求。依托大数据思维,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智慧法院建设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法院的工作模式,给司法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大数据技术的资源整合与传输功能推动了司法在阳光下运行,使民众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到司法信息,其知情权、监督权均得到了保障。第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22],提升办案实效和司法公信力。大数据分析技术与法院审判管理活动的深度融合能够完善法院内部联结机制,加强司法大数据的整合与运用。各地法院相继推出的“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智能审判辅助系统”能够辅助办案人员精准把握案件信息,统一案件裁判标准,确保同案同判的实现[23]。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合理配置法院办案人员和辅助人员的比例,避免既往绩效考核的唯结果论倾向,为法官员额制改革提供精确的决策依据和合理的规划方案。第三,有助于深化司法公开,落实阳光司法机制,促进司法公正早日实现。抽样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所获取的仍旧是片段性、片面性甚至过时的数据,难以有效挖掘数据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变迁及制度性影响因素,难以洞悉司法公开的流变趋势。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本身是对真实世界进行记录的时序性数据,在可信度及研究的时空性上具有延展性,并且不受制于特定研究主题,能够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和价值关联,一方面能够揭示非常重要的司法公开规律与趋势,另一方面也能厘清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内在关联,重塑法院的扁平化管理。最后,践行司法为民的目标,提升民众司法获得感和信任度。以数据驱动为中心的科学计算范式有助于克服现有量化实证分析方法的不足,拓展司法公开的深度与广度,洞悉司法公开的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同时对民众的司法期待和信任感进行积极回应和科学解释,厘清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和信任感,促进司法公正的早日实现。
四、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的方法论变革及其挑战
(一)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的方法论变革
上文已对当前司法透明评估所面临的理念、技术与方法的误区进行解读,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以传统静态数据运用为核心的司法透明指数面临着应用限度和转型的叩问,司法透明指数亟待更新理论范式,推动方法论与范式变革[24]。具体而言:(1)在方法体系方面,大数据时代司法运行的数据应用表征为现实世界中的时序数据和动态数据,体现为民众的真实诉求和行为模式,司法透明评估要重构方法体系,将司法公开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提供更具前瞻性和精准性的评估思路,推动司法公开的理念创新和体制机制完善。(2)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革命,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抽样时代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的计算范式,推动了半/非结构化数据的广泛应用,有助于精准描述、解释和探寻社会发展规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一方面需要对现有评估的数据来源、数据采集以及统计分析模式进行变革与重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更新其测量方式和方法技术,引导司法透明评估进行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3)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推动了跨学科研究与多元方法应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研究者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透明评估需要多元化的评估人才和多学科的合作模式,研究者既要具备专业化、职业化素养,同时也要精通大数据方法与技术,推动司法透明评估的转型升级。(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使司法透明指数的作用机制面临表征与建构的辩难与重构。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要跳出既往对因果关系探寻的诠释进路,注重对相关关系的挖掘,探究司法公开的制度性影响因素和真实情境,进而揭示出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核心在于司法公正,应当适应当前司法改革和大数据的浪潮,结合既有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和测评方法进行求新求变,洞悉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作用机理,为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前瞻性、预测性的成果。(5)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要求对司法公开进行深度探究与追问,既要揭示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也要深度验证相关关系,充分发挥司法透明评估的精准描述、预测和现实观照功能。(6)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应引入系统工程思维,有助于突破既有量化评估的表征与建构的难题,根据评估功效进行类型构造和精准化应用,有助于提升评估的实效,推动司法透明评估的系统工程形态的实现(详见图1)。

图1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的方法论变革
(二)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方法图谱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亟待拓宽方法论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向度,在具体测评方法和技术层面应当围绕数据运用进行司法透明评估方法图谱的构建与设计。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在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数据应用、评估结果分析与应用等方面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数据来源上更为多元化,不仅有传统的民意调查、问卷量表等反映民众主观认知的结构化数据,更有反映现实世界的非结构数据,如文档、视频等,能够呈现出真切而鲜活的发展变迁及未来趋势。(2)在数据采集上体现了从平面向立体转变的思路,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出最具价值的司法公开信息,从而捕捉影响司法公开的关键性影响因素。(3)在数据集成挖掘方面体现了大数据的“4V”特征,即数据体量大、数据类型多、价值密度低、处理速度快,司法透明评估应当探究司法公开的相关关系,洞悉司法公开背后的关联机制及其与司法公正的内在关联,通过数据清洗、转换和获得等去伪存真的过程,在传统统计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互动协作下探究大数据时代司法公开的多维面向和实践图景,提升司法实施效能。(4)在评估结果可视化分析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人机交互技术和数据可视化技术来提升评估结果的科学性、精确性。(5)在评估结果的运用方面,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将打破既有评估模式的表征与建构之争[25],跳出科学与阐释逻辑预设的方法论困局,围绕数据分析模式进一步拓深与形塑,具体可细分为四种类型,将其映射到司法透明评估领域,体现为评估阶段的纵深性和结果应用的多元化:类型一为描述型分析,当前司法透明评估尚停留在数据描述阶段,即通过指标体系对司法公开制度运行和公开状态进行量化评估,揭示了司法公开的实施成效[26];类型二为诊断型分析,围绕司法公开的实施成效,在“发生了什么”维度上进一步拓深,改善供给侧与需求侧层面的关系,进行诊断分析,优化需求侧的响应,即探究“为什么会发生”的实施机制;类型三为预测型分析,结合计算科学、数据科学、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出司法公开领域的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对民众行为模式的预测洞悉司法运行规律;类型四为指令型分析,规划未来需要做什么。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经由描述型分析、诊断型分析、预测型分析的阶段和步骤,指令型分析即体现为规划导向的综合分析,通过持续跟踪能够优化决策分析,提升司法实施效能(详见图2)。

图2 大数据司法透明评估的方法图谱和平台架构* 绘图参考了大数据处理的一般流程以及孟小峰等、刘泽照等对大数据“维稳”评估的概念框架设计,参见孟小峰、慈祥《大数据管理:概念、技术与挑战》,载《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年第1期,第151页;刘泽照、朱正威《大数据平台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前瞻与应用挑战》,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78-85页。
(三)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的方法应用研判
尽管当前学界对大数据法治的探讨已成热潮,但仍需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第一,大数据的全样本性、混杂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如何成为法治研究理论基础的问题。大数据法治要避免陷入数据迷信的思维误区,大数据能够降低随机抽样精确度不足所带来的误差,其应用中自动生成的数据清洗能够剔除错误信息、纠正错误,使数据的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27]。但大数据的应用也要严格遵循应用程序的预先设置,保证运算过程的规范、严谨、科学,杜绝程式污染。对大数据的结果也要进行相应的验证,保证其科学性和实效,同时不能违背社会伦理,遵循法治运行的基本规律。第二,大数据应用于法治的关联和作用机制问题[28]。如何从海量数据中发现隐藏的相关性和作用机制,挖掘法治运行的规律,需要我们在解释和解读的基础上建构出情境化制度分析框架和实验模拟研究。第三,大数据应用于法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大数据法治研究方法应当是多元混合研究方法的融合与互补,在辨析相关关系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因果关系链条的探寻,促成不同研究方法的交互合作。运用大数据进行法治研究时,首先要对大数据有一个清醒的认知,避免唯大数据是从[29]。尽管大数据应用注重相关关系的分析,但对法学研究而言,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同样重要,研究者的经验同样重要,在从相关关系考量大数据的应用之余,还应注重对因果规律的探寻[30]。数据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整体数据中某些指标的相关性,强调对相关关系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因果关系,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融合互补的关系。一方面,相关关系能够改善因果关系的分析,有效剔除具有蒙蔽作用的因果关系;同时,因果关系的普遍性适应于所有情景,而相关关系只适用于相同的状况,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对个案的分析,因果关系的解释能够更好地发现普遍规律、验证理论假设、预测未来和控制进程[29]。可见,大数据应用中的相关性分析只是开始,最终目的仍是因果关系的解释和验证。第四,大数据应用于法治研究可能带来的影响,既要关注大数据对法治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也要避免陷入数据迷信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决策失误。
(四) 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面临的负面效应及其克服之道
上文已对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方法图谱和实践图景进行了勾勒和描绘,然而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发展仍面临着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层面的困惑,并由此引发了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数据滥用、隐私侵犯、危及信息安全等现实风险和负面效应。首先,从认识论上看,大数据视野下司法透明评估通过解释和揭示司法运行规律及影响机制来探究司法公开运行的一般规律,但我们也应当警惕技术逻辑背后所隐藏的情境主义陷阱。其次,从本体论上看,在司法透明的条件下,司法活动所欲实现的正义应当以看得见且及时的方式来获得和实现。大数据视野下司法透明评估亟待厘定司法公开的实质内容和价值目标,洞悉算法和数据驱动下的风险挑战,如跨部门信息数据共享障碍、数据公开与权利保护的矛盾、信息使用和保护的监管机制缺失、碎片化的法律实现机制等新挑战和新问题。最后,从方法论上看,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体现了从因果关系论到相互作用论的技术逻辑转变和关联方向。大数据方法的去因果性尽管能够挖掘出影响司法公开的关联因素和影响机制,但仍面临着理论解释的现实张力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司法透明评估的实效和精准性,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尽管借助大数据的全样本和实时性特点能够推动司法透明评估进行深层次的验证或预测分析,但我们也要思考因数据失真、数据失实以及个人数据利用和保护的失衡所带来的诸多风险,如可能忽略微观层面的细节而更为注重宏观层面的精确度等。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地进行司法大数据与传统小样本的衔接,克服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可能局限。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既需要借助海量数据呈现司法公开运行的全貌和发展趋势,也要结合抽样小样本时代的价值判断和个案分析,洞悉司法公开的真实样态和背后的因果关系,推动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多元融合、方法集成和应用。
五、 结 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必将给法治建设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我们既要避免盲目的数据迷信,也要寻找大数据应用的方法论支撑,对大数据的取舍之道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对法学研究而言,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实践活动使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藩篱被打破,为法学研究带来了方法论的变革与研究空间的拓深;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方法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实践成为助推法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法治建设跳出观念巴别塔的认识误区,坚持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立场,追求法治实效,体现了规范与实效的辩证统一。近年来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作为量化法治评估的践行者和大数据司法的推崇者,其有关量化法治评估的实验模拟研究以及对未来大数据司法时代的前景预测,为司法公开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解释机制,值得深入借鉴[31]。
[参 考 文 献]
[1] 钱弘道: 《司法透明指数的指向与机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4期,第28-30页。[Qian Hongdao,″The Direc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Judicial Transparency Index,″ChineseCadresTribune, No.4(2015), pp.28-30.]
[2] 方桂荣、钱弘道: 《司法透明指数的合理化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5-68页。[Fang Guirong & Qian Hongdao,″Research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Judicial Transparency Index,″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 No.2(2015), pp.65-68.]
[3] 徐汉明、张新平: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内容及其评估》,《法学杂志》2016年第6期,第31-33页。[Xu Hanming & Zhang Xinping,″The Design,Cont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LawScienceMagazine, No.6(2016), pp.31-33.]
[4] 胡铭、自正法: 《司法透明指数:理论、局限与完善——以浙江省的实践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4页。[Hu Ming & Zi Zhengfa,″The Judicial Transparency Index: Theory, Limitations, and Improvement: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No.6(2015), pp.1-4.]
[5] 叶浩生: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对立及其超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9期,第7-8页。[Ye Haosheng,″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Opposition and Transcendence,″StudiesinDialecticsofNature, No.9(2008), pp. 7-8.]
[6] 肖建飞、钱弘道: 《司法透明指数评估指标探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3页。[Xiao Jianfei & Qian Hongdao,″Discussion on Indicators for Judicial Transparency Index Evaluation,″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 No.4(2015), pp.1-3.]
[7] 徐昕: 《司法的实证研究:误区、方法和技术》,《暨南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7-59页。[Xu Xin,″Empirical Judicial Studies: Misunderstandings, Methods and Techniques,″JinanJournal(Humanities&SocialScienceEdition), No.3(2009), pp.57-59.]
[8] 钱弘道: 《中国司法透明指数实验报告——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为样本(2015)》,《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1期,第122-124页。[Qian Hongdao,″Experiment Report on China’s Judicial Transparency Index: A Case Study of Wuxing District Court in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2015),″ChinaAppliedLaw, No.1(2017), pp.122-124.]
[9] 周祖成、杨惠琪: 《法治如何定量——我国法治评估量化方法评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20-24页。[Zhou Zucheng & Yang Huiqi,″How to Quantify the Rule of Law: Analysis of China’s Rule of Law Assessment Method,″ChineseJournalofLaw, No.3(2016), pp.20-24.]
[10] 张德淼、康兰平: 《迈向实证主义的中国法治评估方法论——以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建构方法为镜鉴》,《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6期,第129-130页。[Zhang Demiao & Kang Lanping,″Methodology of China’s Rule of Law Assessment Approaching to Positivism: Using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Rule of Law of the World’s Justice Project as a Mirror,″TheoryandReform, No.6(2015), pp.129-130.]
[11] 孟涛: 《法治的测量: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研究》,《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5期,第15-17页。[Meng Tao,″Measur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 Study of the Rule of Law of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PoliticsandLaw, No.5(2015), pp.15-17.]
[12] 徐晋: 《大数据经济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Xu Jin,BigDataEconomics, Shanghai: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 康兰平: 《法治评估理论的跃升空间:实效法治观与我国法治评估实践机制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第21-24页。[Kang Lanping,″Leap Space for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Assessment: A Study of the Effective Rule of Law and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China’s Rule of Law Assessment,″LawandSocialDevelopment, No.4(2017), pp.21-24.]
[14] 陈林林: 《法治指数中的认真与戏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44-146页。[Chen Linlin,″Seriousness and Playfulness in the Rule of Law Index,″ZhejiangSocialSciences, No.6(2013), pp.144-146.]
[15] Zikopoulos P. & Eaton C.,″Understanding Big Data: Analytics for Enterprise Class Hadoop and Streaming Data,″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2132803, 2017-12-13.
[16] Andrew M. & Erik B.,″Big Data: The Management Revolution,″HarvardBusinessReview, No.10(2012), pp.61-67.
[17] 汪国华: 《司法规律层次论》,《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第5-8页。[Wang Guohua,″The Level of Judicial Law,″ChineseLegalScience, No.1(2016), pp.5-8.]
[18] 罗玮、罗教讲: 《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222-225页。[Luo Wei & Luo Jiaojiang,″New Sociology of Sociology: A Sociological Study in the Age of Big Data,″SociologicalStudies, No.3(2015), pp.222-225.]
[19] 单勇: 《基于犯罪大数据的社会治安精准防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54-56页。[Shan Yong,″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cial Security Based on Big Crime Data,″Studiesonthe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No.6(2016), pp.54-56.]
[20] 杜宴林: 《司法公正与同理心正义》,《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02-105页。[Du Yanlin,″Justice and Empathy Justice,″SocialSciencesinChina, No.6(2017), pp.102-105.]
[21] James M.,Michael C. & Brad B. et al.,″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2017-12-13.
[22] 高岚: 《大数据思维下司法改革之钥》,《人民法院报》2016 年5 月17 日,第2 版。[Gao Lan,″The Key to Judicial Reform under the Big Data Thinking,″People’sCourtNews, 2016-05-17, p.2.]
[23] 殷泓: 《与大数据拥抱的司法改革》,《光明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5版。[Yin Hong,″ The Judicial Reform Embraced with Big Data,″GuangmingDaily, 2017-07-28, p.5.]
[24] 雷鑫洪: 《方法论演进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97-100页。[Lei Xinhong,″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Law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Evolution,″ChineseJournalofLaw, No.4(2017), pp.97-100.]
[25] 孟小峰、李勇、祝建华: 《社会计算: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年第12期,第2483-2486页。[Meng Xiaofeng, Li Yong & Zhu Jianhua,″Social Comput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ComputerResearchandDevelopment, No.12(2013), pp.2483-2486. ]
[26] 康兰平: 《表征与建构:量化法治评估的方法论之争及其实践走向》,《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第152-156页。[Kang Lanping,″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Debate of Methodology and Its Practical Trends in Quantitative Rule of Law Assessment,″TheoryandReform, No.1(2018), pp.152-156.]
[27] Mayer-Schönberger V. & Cukier K.,BigData:ARevolutionThatWillTransformHowWeLive,Work,andThink, Hough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28] 刘晓葳、朱建平: 《大数据内涵的挖掘角度辨析》,《中国统计》2013年第4期,第59-61页。[ Liu Xiaowei & Zhu Jianping,″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Big Data,″ChinaStatistics, No.4(2013), pp.59-61.]
[29] 陈柏峰: 《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44-46页。[Chen Baifeng,″Mechanism Analysis Methodology of Legal Experience Research,″StudiesinLawandBusiness,No.4(2016), pp.44-46.]
[30] 张小天: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它们的关系及它们的差异》,《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97-99页。[Zhang Xiaotian,″Causality and Relevance: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Differences,″SociologicalStudies,No.3(1992), pp.97-99.]
[31] 钱弘道、王梦宇: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9-21页。[Qian Hongdao & Wang Mengyu,″Cultivating Public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chool of Rule of Law in China,″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No.5(2013), p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