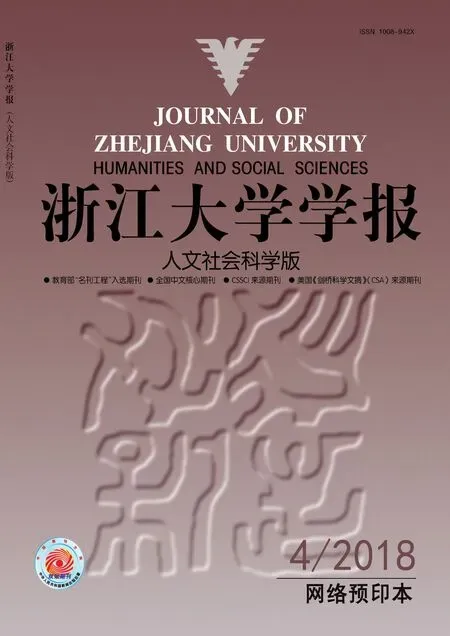论“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
韩 晗
(深圳大学 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互联网+”是近年来一个较为热门的词汇。21世纪以来,一日千里的互联网技术带动了大数据、云计算、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一系列周边技术的迅速发展,进而呈现出“万物互联”的大时代景观,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前提。“互联网+”虽由技术而生,但早已深入地关涉意识形态范畴,这已经为政产学研各界所公认。从内容上看,“互联网+”包括互联网文化、互联网观念以及人类在互联网时代下的联系形式、思维范式与存在方式;从历史来看,它是人类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代语境。
就中国而言,在最近十年,以国家形象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广、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建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互联网+”而得以推进,国家文化建设进入国家文化创新的新时代。不言而喻,“互联网+”对国家文化创新机制、方式与过程的影响很大。
但互联网向来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亦如是。一方面,“互联网+”所赋予的群体协作、信息传播与云端大数据在推动国家文化创新层面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无序、共享、开源与高速化同样为国家文化创新工作制造了安全隐患。因此,探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相当重要。
习近平同志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家文化创新是一个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且具有复杂内涵与重大意义的文化建设工作,非传统安全是它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就相关问题而言,学界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其中以David Lloyd和Paul Thomas的CultureandtheState、Brian Fonseca和Eduardo A.Gamarra编的CultureandNationalSecurityintheAmericas与胡惠林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为代表。但上述研究基本上着力于国家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关系的探讨。事实上,当国家文化建设发展到国家文化创新阶段时,它与国家语言安全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惜的是,截至目前,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相当缺乏。在“互联网+”时代,探讨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之间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与迫切。
由此,本文拟从如下三个部分来阐释此问题:首先,国家文化的概念及国家文化创新的方式是什么?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之间有何种关系?最后,如何在推进国家文化创新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的同时,避免在认识与操作上走入不必要的误区?
一、 国家文化的概念及国家文化创新的方式
要探讨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的关系问题,首先应对国家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沿革流变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国家文化是“二战”以来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重视的一个文化概念,它因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发展,是一个国家国际辨识度的重要依托,更是国家形象的具体表现。学界一般认为,所谓国家文化,即一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之后而形成的总体文化体系,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以民族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文明、核心价值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Lloyd D. & Thomas P., Culture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4; Burke R.J. & Tomlinson E.C.(eds.), Crime and Corruption in Organizations: Why It Occur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London: Routledge, 2016;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自20世纪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只是经济、军事与政治体制的竞争,还有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因此,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提出“国家文化”这一概念;1971年,马来西亚政府在马来亚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国家文化大会,提出马来文化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并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文化政策,走在了亚洲国家的前列。
在国家文化建设这个问题上,我国起步较早,但最开始是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两份颁布于20世纪80年代的决议出现的,其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直至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才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论断,“国家文化”四字正式出现。2009年,文化部设立“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将一系列国家文化建设工作提升到国家文化创新的层面,这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做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以及“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一年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同志又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合当下国情以及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的计划,三次对国家文化进行了重要阐述:“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系列对国家文化的重要阐述为之后国家文化创新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要求国家文化不但要承担国家形象建构的责任,而且还要成为中国融入世界一体化与促进国家内部凝聚力的推动力。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下,国家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都必须超越性地在创新中求发展,从而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归根结底要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则是转换不同的文化资源,从而丰富国家文化体系。笔者浅识,目前国家文化创新工作中转换不同文化资源的方式有三:一是转化与发展并举;二是吸收与扬弃同存;三是继承与辨析兼重。
转化与发展并举主要是指国家文化创新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资源这一问题。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文明古国”一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标志性符号。“互联网+”时代下的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多样化,并日渐成为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传统文化”的格局已经形成,社交软件、自媒体平台为传播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渠道;二是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下形成了受众细分,不同的人群可以通过个人通讯终端、社交软件、游戏软件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传统文化,其中虽然有一部分形成了都市青年亚文化,但“互联网+”时代总体上为传统文化在传播路径上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三是“互联网+”让传统文化通过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互联网渠道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形成了比以往更加有效、多元的传播机制。
因此,国家文化创新,势必要对传统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我们今后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指明了方向。传统文化发生、形成于全球化之前的中国,其部分观念、内容确实与当下中国及世界的主流、核心价值观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国家文化创新工作中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不但要在创造与创新中有所作为,更要认识到转化与发展应当并举而行。
吸收与扬弃同存主要是指如何面对外来文化资源这一问题。人类的文化史本身是一部不同文化互动的历史,对外来文化的摄取是人类文明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1]48。无论是遥远的亚述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中国的秦汉文明,都是与周边甚至更远的其他民族的文明互动、交流的结果。在全球化早期,随着“西学东渐”的兴起,以西方文化(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借势传入中国,当时东西方世界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使得西方文化在传播入华的过程中占据了话语权上的优势地位。但实际上,根植于西方具体语境的西方文化以“拿来主义”的方式移植入华,必定有水土不服的一面,尤其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完全照搬外来文化显然不能满足国家文化创新的需要。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目前世界的新格局:全球化进程已经进入“互联网+”这个新的时代语境,外来文化借助互联网技术并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社交媒体的普及,已经形成了对中国文化从语言到内容的全面干预,这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语言安全是有挑战性的。而且,中国目前进入国家的复兴、崛起期,外来文化之于国家文化创新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任何外来文化都不可能独立承担起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复兴的文化责任,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产生干扰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必须要与扬弃同存。
吸收是指对外来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予以吸纳,譬如日本文化中的敬业守时、美国文化中的尊重创新等,其中有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仍有一些外来文化不适应中国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具体国情,之于国家文化创新而言,只有扬弃。因此,对于外来文化不能笼统地以好坏来评价,只能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
而继承与辨析兼重主要是指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中国是一个有着较长民主革命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文化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文化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指出,要“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历史上看,革命文化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国家文化的重要基石,但革命文化本身具有特殊性、复杂性与多元性,这是我们在继承革命文化、将革命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创新资源时要注意的一点。
革命文化与中国现代革命共生,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曲折前行、筚路蓝缕的历史见证。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曾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701这是关于“革命文化”的经典定义。笔者认为,革命文化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与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对中华民族具有启迪、教化意义的红色精神财富,更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执政理念的历史积淀。故而对于革命文化,首先是继承,但必须与辨析兼重。因为我们需要警惕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和教训也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冠以“革命文化”或“红色文化”的名义,予以刻意放大、宣扬。我们绝不能不加辨析地将革命文化庸俗化、模糊化,从而违背历史决议、基本政治立场与全社会的共识,甚至扭曲革命历史、侵害革命先烈名誉。因此,我们在吸收、继承革命文化的同时,必须谨防被历史虚无主义所蛊惑,要对之进行有效的甄别,并借助“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高速高效,使真正的革命文化不但可以服务于国家文化创新,而且使之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都具备影响力、认同度与传播价值的文化形态。
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革命文化实际上构成了国家文化创新所要面对、利用的三种重要文化资源,并服务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它们在经过转化之后,可成为国家文化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下,对上述三种重要文化资源应如何借鉴、继承与利用,应当受到学界、业界的普遍重视。
二、 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之关系
下面来阐述“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之关系。从形态上看,语言是文化的外衣;而从逻辑上看,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两者因此相辅相成。作为人类文化等级中较为先进的国家文化*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从家庭(早期氏族)、早期国家或联合为民族的各部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变迁。从这个角度来看,因现代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国家文化是目前人类文化的最高形态。参看[德]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它在很大程度上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语言安全与国家文化创新休戚相关。
所谓国家语言安全,主要是指语言范畴内的国家安全,譬如母语(或官方语言)的纯化与国际化传播、语言对国家安全其他领域的介入以及国家语言战略的实施推行等。与其他非传统安全门类相比,国家语言安全是一个近年来被提出的新问题,对国家文化创新工作来说,国家语言安全相当重要。
首先,推动国家文化创新必须注重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语言安全的保证是国家文化创新得以推动的基础。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语言安全问题业已凸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量外来、网络词汇(甚至一些亚文化、低俗词汇)充斥在母语中,导致了互联网语言的出现;二是“互联网+”时代下信息传播速度很快,加剧了外来语言对母语的入侵,使得当下许多年轻人出现了英语比母语好这一不合理现象,甚至外文的学术成果、文艺作品与新闻报道都会被高看一等,造成一种人为的“母语自卑感”,这对国家语言安全百害而无一利;三是全社会对国家语言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国家语言安全因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而愈发突出。上述三点都与国家文化创新息息相关,国家文化创新不只是内容的创新,也包括形式的创新,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当然不能忽视国家语言安全的重要性,如果国家语言安全受到了破坏,国家文化创新就难以真正实现。在目前国家文化创新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对国家语言安全认识不清,对“互联网+”时代下语情、语势掌握不足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文化创新的效果。
在处理推动国家文化创新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的关系上,母语纯化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国家文化创新归根结底是以创新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并提升本国文化的意义、作用与价值,从而使本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辨识度与竞争力。如果不能提升母语的认同感,那么国家文化创新只是空中楼阁。“冷战”时期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行自身国家文化建设时,首要之事便是去除本国文字、语言中的汉字书写与汉语发音,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但对韩国、日本国家文化的建构却有积极意义。
就当下中国国情而言,我们必须正视母语纯化这个严肃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汉语中出现了近两千个外来词汇,它们普遍存在于“互联网+”时代下的日常生活中,并被年轻人所广泛接受,甚至其中不少词汇已经部分取代了日常汉语词汇(如“萌”取代可爱),这实际上反映出“互联网+”时代下中国的民族情绪与社会心理,这些外来词汇客观而现实地塑造了语言使用者及社会现实[3]。因此,母语的纯洁程度很大程度上不但是国家语言安全的核心,更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中之重。因为母语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凝聚力的重要组成,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国家文化的对外传播力。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必须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并举,这样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征在于:信息的高速传播促使许多历时性的行为成为共时性的行为。譬如之前的书信往来,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下,相距万里的信息瞬时可达。国家语言安全的风险也因信息的高速传播迅速加剧,未加甄别、净化的资讯乃至各种有意为之的谣言等一系列危害国家语言安全的信息,都会成为束缚国家文化创新的短板[4],从而影响国家文化创新工作的效能。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文化创新是在“互联网+”时代下,以新观念、新手段、新方式来建构、传播国家文化,从而对内产生凝聚力,对外形成影响力。但这一切必须要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的工作同步开展。从具体措施来看,一方面,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尤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为依托,对互联网语言进行及时的引导、必要的修正与合理的利用,从而推进国家文化创新工作;另一方面促进母语纯化,让服务于国家文化创新的汉语具有国家文化的代表性,这不但可以提升汉语在国际舞台上的认可度,而且有助于国家文化创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目前国家文化创新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国家语言安全的认识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譬如法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法国国家语言研究所,负责制定国家语言战略与有关政策,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编撰“法兰西语库”;美国则在2006年推动包括“星谈”(STARTALK Program)在内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而前文所述的韩国、日本维护国家语言安全的工作也起步较早*1948年10月9日,韩国政府颁布了“第六号法律”《韩文专用法》,将韩文确定为官方文字,逐渐停用汉字。1971年起,在小学教育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因此,推动国家文化创新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要两者并行。
三、 文化自信: 避免文化封闭主义与语言霸权主义的方式
前文阐述了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之关系以及两者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防止在认识与操作上走向两个误区,一是文化封闭主义,二是语言霸权主义。国家文化创新最终目的究竟是将一国文化(或者语言)推向全世界形成新的文化霸权,抑或与当下的文化霸权抗衡,从而为推动文化霸权的消失与人类文化多极化而努力?
文化封闭主义是文化自卑引起的一种文化症候[5],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树立有不小的危害,它广泛出现在具有悠久历史但近代却处于落后地位的亚洲等地区。在中国,与之伴随的则是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暗中破坏、干扰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 Guangqiu Xu,″Anti-Western Nationalism in China, 1989-1999,″ World Affairs, Vol.163, No.4(2001), pp.151-162。,因此,中国要发展,则必须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以杜绝开放的保守姿态来面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这种观点尽管影响不小,社会认可度却较低,也不符合中国未来发展大势[6]。但“互联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封闭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提供了温床,因为文化封闭主义最大的消费土壤是民粹,而互联网很容易将大量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判断力不强的网民聚到一起,形成一种民粹民族主义[7],从而推动文化封闭主义在当下中国的蔓延,甚至会使人误解文化封闭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过激的表达方式。文化封闭主义源于文化自卑,因此树立文化自信是打破文化封闭主义的重要手段,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家文化创新的水平[8]。
就当下而言,国家文化创新工作显然不可能遗世独立,国家文化创新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一个客观的中国,从而促进全球间文化权力的多元化与平衡。文化封闭主义不但会束缚国家文化创新工作的发展,而且还会带动语言霸权主义的出现。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下推进国家文化创新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的同时,我们既要谨防文化封闭主义抬头,还要杜绝语言霸权主义出现。
语言霸权主义本是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在全世界形成霸权的产物,它萌芽于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帝国主义形成期,其根源是文化自大。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近年来,语言霸权主义逐渐成为经济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之后的新一种霸权主义形态。一些经济发达国家认为自己民族优先,利用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多重手段向周边其他弱小民族(国家)强势推行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语言霸权主义由是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参见Phillipson R.,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04; Reagan T., Language Matters: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Charlotte: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9; Blommaert J.,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在“互联网+”时代下,我们既要防止其他国家强行向我国推行他国、他民族语言,也要避免对语言霸权主义持双重标准,将国家文化创新工作教条化、庸俗化与急功近利化,认为要“以霸权制霸权”并提出违背人类文化多元化的“汉语优先论”“世界语言起源中国论”等错误观点,这不但会对汉语的国际传播产生负面作用,而且更不利于国家文化创新工作的开展。
“互联网+”时代为汉语的国际化传播赋予了新的空间,拓展了新的渠道,但极端化、民粹化的思想也很容易形成,从而对国家语言安全构成挑战。在针对民族、种族等议题时尤其明显,会滋生出网络民族主义这类以互联网为渠道宣泄民粹民族主义的文化自大思潮[9]10-11。这一思潮认为,以汉语为核心中国文化理应在宣扬网络民族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并通过社交媒体、论坛与自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与个人博客)等多种渠道,以语言暴力的形式宣扬其优先性,这不利于文化自信的树立[10],因为文化自大势必会忽视创新、包容的必要性。因此,文化封闭主义与语言霸权主义是对国家文化创新工作危害不小的两个误区,它们说到底都是因文化自信缺乏而形成的。
四、 结 语
今日的中国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一方面,我们要推动国家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的多元化而努力;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注重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语言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文化创新的效能。
“互联网+”时代下的国家文化创新要在不同的文化资源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从而凝练出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国家文化体系,这注定了要以创新、包容的开放姿态来推进国家文化创新工作。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新分支,国家语言安全对国家文化创新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国家语言安全是保证是国家文化创新得以推动的基础;另一方面,两者唯有并举,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文化自信应是国家文化创新工作应有的心态。这意味着在面对不同的文化资源取舍以及和不同文化的交流时,我们可以以更为超越的自信心态来进行判断抉择,从而杜绝因为文化自卑或文化自大而走向文化封闭主义或语言霸权主义。可见文化自信在国家文化创新工作中的意义非常重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参 考 文 献]
[1] [日]家永三郎: 《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靳丛林、陈泓、张福贵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Ienaga Saburo,AHistoryofIngestionofForeignCulture, trans. by Jin Conglin, Chen Hong & Zhang Fugui et al.,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17.]
[2]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Mao Zedong,″On New Democracy,″ inSelectedWorksofMaoZedong: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3] 袁周敏、韩璞庚: 《网络语言视域下的网络文化安全研究》,《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第39-43页。[Yuan Zhoumin & Han Pugeng,″A Research on Network Culture Secur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Language,″ForeignLanguageEducation, No.1(2018), pp.39-43.]
[4] Jaeger E. & Levillain O.,″Mind Your Language(s): A Discussion about Languages and Security,″ 2014 IEEE Security and Privacy Workshops,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6957297, 2018-03-20.
[5] 丁立群: 《增强文化自信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19日,第6版。[Ding Liqun,″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ChineseSocialSciencesToday, 2017-05-19, p.6.]
[6] 周少来: 《“激进左派”渐成中国学术界“公害”》,《人民论坛》2018年第6期,第33-35页。[Zhou Shaolai,″Radical Left Have Become the Public Nuisance of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People’sTribune, No.6(2018), pp.33-35.]
[7] 韩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第30-33页。[Han Han,″What Kind of Nationalism Do We Need?″TongzhouGongjin, No.6(2011), pp.30-33.]
[8] 韩晗: 《国家文化创新与民族文化自信》,《中国民族报》2017年7月14日,第5版。[Han Han,″National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ChinaEthnicNews, 2017-07-14, p.5.]
[9] Ying Jiang,Cyber-NationalisminChina:ChallengingWesternMediaPortrayalsofInternetCensorshipinChina, Adelaid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 2010.
[10] Johnston A.I.,″Is Chinese Nationalism Rising?Evidence from Beijing,″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41, No.3(2016/2017), pp.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