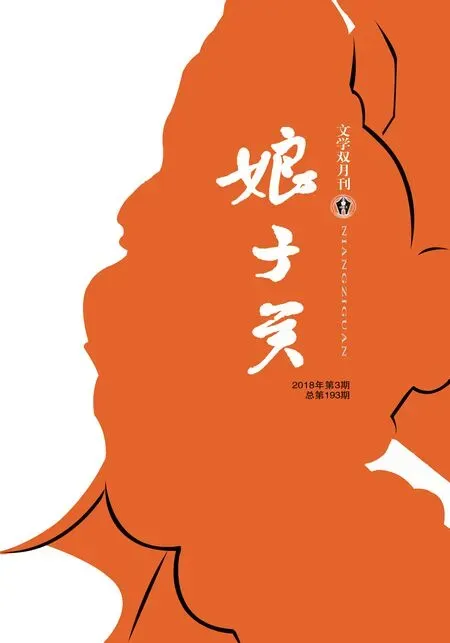镜像与抵达
●指 尖
指尖视角
文学并非放在我们正前方的一面镜子,它不是复制和模仿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它应该是我们身侧的一面镜子,既照见现实,还能映射想象的一面镜子,它能带来阳光的反射,也能映出月光的冷清,因为角度的独特刁钻,才能显示常人所无法得见的某些隐秘,某些暗角。作家显然肩负着将秘密说穿的重任,而创作,就是通途。
当时年少青衫薄
几十年前,人们用的是黑白相机,冲洗出来的,自然也是黑白相片。拥有相机的人,不拘好坏高低,都掌握着冲洗照片这一奇妙技术。冲洗照片的先决条件,需要一间暗房。照相师会根据自己的环境,选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作暗房。有一次我在外婆家住,听说村里有个照相师,他的暗房竟然设在地窨子里,惹得全村人当笑话讲。这也是个好办法。我的暗房,是我的宿舍,窗帘换成双层的,外面一层红,里面一层黑,拉上后,屋子伸手不见五指。
暗房备好后,我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已攀上了成功之肩,不日,我将归属于照相师的队列,走南闯北,得到许多的赞许和羡慕。但当下,却如此令人难堪。我有个黑色的显影罐,还有一个摸起来手感特好的卷片器。将卷片器放到暗袋,把胶卷缠入其中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究其原因,不怪乎几条:自己太缺乏耐心,不懂得刻苦和努力;太着急,不知道停下来喘口气,再继续向前走;最关键的一条是,我刚刚十七岁,尚未得见人世薄凉,以为满世界都跟自己一样,单纯,无遮。事实上,这样的人,不懂得分辨,不懂得缄口,乃至不懂得对错,他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让一张成型的照片最终成像的。
生命中的某些境遇,个体根本无力做出选择,你只能被安排,循着一条你以为的,新的、陌生的、有意义的路,往前。若顺风顺水,便暗自得意。若遇坎坷,又怕人耻笑,掩藏着自己,吞咽着苦水,也要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学了两天,睁眼瞎般,心智愈发愚钝,愈发自卑,找不到捷径,也无窍门。现在想来,或许在胶卷和卷片器之间,有一个非常契合的机关存在,但因我的不认真,不熟悉,心急和敷衍,导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也或许,我的师傅也很清楚这个机关的存在,他因一直遵循着“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的祖训,不去破它。再说,古训中就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种种事例,警戒师傅们,要留一手,以防万一。师傅不无遗憾地注视着我,叹口气说,“自己揣摩吧。如果实在不行,将显影剂按比例跟水混在一起,手拿胶卷,在显影液里不停地来来回晃动。但必须在绝对黑暗中进行,也就是说,暗室里不能有任何一点光亮,包括门缝下。”
师傅教会我数秒表的方法,不能是一、二、三这样,也不是十一、十二、十三这样,必须是一十一,一十二、一十三这样数。这个很容易,我记忆到如今,且数得极其精准。
通往成像的过程,看似容易,实则没有一定的经验和技巧,根本无法做到完美。所以,这是件极其艰难的事。得有某种机缘,电光石火,棒喝或者精心,顿悟等经历,才可能将一张完美的成像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从未有过一卷透亮的底片。在经过显影液——清水——定影液——清水,这样的过程后,将窗帘拉开,底片挂起来。入目的,是灰、暗、厚、硬的底片。这样的底片,成像效果很差,模糊、灰暗。
多年后,我曾将当时的情景写下来:
这样的过程,让我在显影液呛鼻的味道渐渐麻木,我常可以从自己的身上闻出溴化钾的味道,某一刻,我觉得被那些结晶体同化了,或者被水融解掉,也成为成像过程中必然的因素。事实上,作为操作者,我已经是成像过程中必然的因素了,但我又羞于这样的承认,因为,成像的过程,本身就是个失败的过程,而我,不过一个蹩脚的操作手。这样,我会拿一些成型的底片来洗。三个塑料方盒里,分别将溶化了的显影液,定影液,清水放入,然后把底片安置到放大机上。透过镜头,相纸上会出现一个清晰的人。但这是虚影,每次都觉得它的出现,不过在配合我默数的秒表的轨迹。而后用木夹子将它放到显影液里。按理是个值得期待的过程,可惜,因为是照相馆冲洗的胶片,让我的遗憾多过这种期待。我否定着自己,否定着这种日益加重的失落,也否定着身上越来越浓的味道。

在失败的途中蹀躞不止,这是我不遵循秩序和圭臬的结果,也让通往镜像的道路之上,布满荆棘。
遇见阿里萨
你认识阿里萨吗?
这个年轻的电报员,爱上了13岁的女孩,然后,用长达60年时间来苦恋和等待,并最终拥有。可能是天性里的敏感和浪漫作祟,让我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时,无论阿里萨做过怎样过分的事,懦弱,迷乱,乃至在他76岁,终于能和费尔明娜在一起的时候,他的5个日记本里,记录了622条较长恋情,这其中还不包括无数次短暂的艳遇,虽令人憎恨,但依旧对他葆有一种莫名的喜爱,也更向往,一辈子被一个人爱着,从少女,到耄耋,不离不弃,永远保持着纯真而狂热的钟情。
是,阿里萨,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个人,一个生活在艺术镜像中的人。
在这里,我想说的,其实不是阿里萨,而是书里的三个细节。
第一个,当比利时人的照相馆开张时,费尔明娜和布兰达去照相的情节。吸引我的,是在她们去之前,进行了一番极为隆重的打扮,“她们把她的衣柜翻了个底儿朝天,瓜分了那些最耀眼的衣服,阳伞以及节日里穿的鞋帽,把自己打扮得像世纪中叶的贵妇人似的。加拉普拉西迪亚帮她们束紧身胸衣,教她们如何在裙撑的金属丝架中扭动身体,如何戴手套,如何系上高跟靴的扣子。伊尔德布兰达看中一顶宽檐帽,上面插着几根鸵鸟羽毛,一直垂到后背,费尔明娜则戴了一顶样式更新一些,上面装饰着彩色石膏做成的水果和马鬃花。最后,她们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就像银版相片中的祖母一样,互相嘲笑起来。”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因为镜像的存在,而让我们对要进入镜像极为看重,堪比某种庄重的仪式。我拥有记忆后第一次去照相馆,记得穿了过年的新衣,坐在父亲自行车大梁上,走了近20里地到达照相馆。照相前一刻,我的父亲笨拙地用一把绿色的塑料梳子给我梳了梳前面的头发。令人慌张的是,当你进入镜头时,对面的照相师,并未因钻到黑布中而滑稽,相反,他的语气和指挥的气度,仿佛天神降临。那一刻,你的呼吸,你的气味,乃至整个你,在时间的某个点上,全部消失。而当你回归,你确定,你还是你吗?这种疑问,从幼年时期,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轮到她们照相时,“天空已布满乌云,眼看就要下雨了,但两人还是任凭别人在她们脸上涂满淀粉,然后靠在雪花石膏柱上,姿态那么自然,一动不动,甚至超过了所需时间。”最终,这张照片,成为一张永恒的成像。当活到近百岁的布兰达去世后,人们在她卧室衣柜一摞飘着香味的床单中,找到了被藏着的这张照片。而费尔明娜则一直保存在家庭相册的第一页。只是后来莫名其妙不翼而飞。但不可思议的是,这张照片最终竟然到了阿里萨手中。那时,他们都已年过花甲。
另一个情节中,阿里萨某一天在对着镜子梳头时,发现跟父亲极为相似,他们的眼角,他们的鼻梁,他们的嘴角,他们的神情,还有他们的皱纹。镜子,在此时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他一些真相,他终于明白,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变老时,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
类似情形,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有时是镜子,有时出自别人之口。我打小跟母亲有天壤之别,她秀美、矮小,我粗陋,高大。每每出门,别人总会说长得跟母亲一点都不像,他们的神情之中竟然有某种抑郁,似乎为我生出急迫的遗憾。可是,在另外的村庄里,一些陌生人极其准确地说出我的出生,并坚信,我跟母亲一模一样。别人的眼睛,别人的观察,别人的体会,其实就是另一面更加微妙清晰的镜子。近几年,随着年岁的增大,我常常在镜子前发生错觉,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母亲。我们有一样的皱纹和肤色,一样的眼神和疲惫,关键是,我们竟然有一样神情。我不得不跟阿里萨一样,承认自己老了。
历经一年多时间,阿里萨将出至威尼斯工匠之手的精美雕花镜框成功拥有时,他并不因那镜框的精雕细琢而加倍珍爱,相反,他仅仅是因为镜子里的那片天地,他爱恋的费尔明娜曾在那里盘踞了两个小时之久。那里面,那个女人举止自如,优雅地与众人交谈,笑声就像烟火一样。他坐在自己的孤独中,通过镜像所赋予的时间,与她共度人生的片刻。小说的结尾,他们在一条游船上度过,有天夜里,阿里萨借着河水的反光看到费尔明娜,仿佛一个神秘的幽灵,雕塑般的侧影在微微的蓝色光芒下显得柔和甜蜜……
帕慕克曾无比肯定,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有一个分身与你的本尊同时存在的。这个幽灵般的分身,凭借你的第六感而被感知,但会不会,是通过一些东西,比如,记忆、文字、音乐、戏剧、影像而真实存在于世呢?保罗·奥斯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充分的证实:理查德在偶然的机会中,于车库的纸箱里发现一部三维视镜,他带着好奇,找到一个胶卷,放到三维视镜中,于是在刹那间,他生命中的三十年急速被全部抹去,他看到了三十年前的父母,表兄弟,叔叔婶婶们,姐姐,姐姐的朋友们,还有他自己,栩栩如生,充满活力,鲜艳的颜色和入微的细节清楚闪耀,四周的纵深感足以乱真,甚至感觉到幻灯片里的人们的呼吸和体温。
镜像所带来的真实感和空间感,跟现实既是重叠的,同时也是有一定距离的。但不可否认,生活中,的确有一些东西具有映照、重复、模仿和辨认功能,显然,它并非一面天空或大地般阔大无边的镜子。
文学的镜子
莎士比亚认为,戏剧,是反映人生的一面镜子。范围扩大,也就说所有艺术,是反映人生的一面镜子。那么文学,也该为一面镜子,而创作,无疑就是通向镜像的路途。
大约所有的作家,在写作初期,都是从“我”开始写起。特别是散文创作,无虚构,无技巧,全凭本真的自我展示,写到最后,依旧是以“我”为主,我见,我思,我所经历,我所承受,我之喜,我之悲,我之爱欲,我之哀愁,我之思想……只有至我中,才能找见另我,数我,众我。这里,已不是世上一定会有一个另外的我,生活在某处,过着与我一模一样生活这么简单的定义了。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深远而广大的平台,在它之上,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犹疑、局促、虚荣、贪念、麻木和挣扎,被展示的一览无余。文学这面镜子,所呈现出来的镜像,是多姿的,又是单调的,是黑白的,也是彩色的,是小心翼翼的,也是充满野心的。
镜子中的我们,既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也是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文学的镜子,是这世上最清晰,也最真实的镜子,他不单单能照见现实的表象,还能照见明媚阳光下掩藏的阴暗,笑容之下的奸诈,善良包裹的凶恶,看见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也看见神仙鬼怪。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无法逃脱文学的照见,它既是生活的回顾,也是延续和拓展,乃至它能预见。

据说小说作家是极其过瘾的职业。我认识的一位小说家,就特别享受创作的过程,他说,他对这种通过现实基石而虚构的大厦,是如此着迷,在这里,他既看见了真实的“我”的存在,也遇见了虚幻的“我”的存在。他在他人身上,筑建自己的理想和失败,同时,他创造一个既内心阴暗,又葆有善良天性的复杂的面孔,也让他慈悲而可怜。在这里,一个人的分身,已经多达数个,他能游刃有余地将它们融合在一起,通过文学的镜子,呈现给我们。创作的道路如此多姿而艰险,充满诱惑,又时刻具备毁灭的危险,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当然,作为以创作散文为主的我,似乎镜子之中,依旧是小我更多些。但也不尽为然。创作初期,我的《骨头里的花朵》《暗夜柔软》等篇,无论是视野还是思想,都是单薄的,局限的。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的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起初的闲置,被安排到一个有些忙碌的位置上。随着一些不得不的被迫和不得不的熟悉,渐懂得珍惜每一次近距离接触自然和他人的机会。2011年,我写下了《庙堂里的事》《神的故乡》《深处的神》等篇,而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对文学镜子的近距离观察。视觉打开,蓦然醒悟,发觉我之外的我,我们,之后开始写《诸林前》,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山体中的植物、动物和庙宇,它们的存在和灭亡,逝去和新生。另一篇《重生》,评论家黄海曾这样评价:“作者从少女的视角体察到生命被创造、轮回和新生的意义——社会和自然属性给予母性的双重的困顿和责难。在阅读者看来,这一特质可能是微缩的,它甚至可能被轻描淡写,被强大的观念践踏。那些母亲们,她们用身体的重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表达。她们隐忍地承载中国乡土的哀歌,一曲婉转而悠长鸣叫由超载的马车、手扶拖拉机、翻斗车、卡车发出,但无论运载农具如何改变,她们每一次重生却是希望到绝望的开始。”之后,我陆续写下《盖头下的皱纹》《变脸术》《失眠症》《捉迷藏》《暗疾》《爆裂的豆荚》《梨树下》《告别》等长散文,这些文章,凸显了多维度的、隐在的、微缩的,被我们忽略和逃避的真实而隐秘镜像,有无数个我,也有无数个你,无数个我们,无数过去、现在和未来。我觉得,文学并非放在我们正前方的一面镜子,它不是复制和模仿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它应该是我们身侧的一面镜子,既照见现实,还能映射想象的一面镜子,它能带来阳光的反射,也能映出月光的冷清,因为角度的独特刁钻,才能显示常人所无法得见的某些隐秘,某些暗角。作家显然肩负着将秘密说穿的重任,而创作,就是通途。

或道路,或表达
据说,苏轼一生最伤情的作品是《江城子》,“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那种相逢的无奈,揪心的痛意,通过文字延续下来,数百年来,让读者每每惆怅无比,心酸之时生出惋惜的心境。这就是文学镜像的力量。事实上,在此时,苏轼已经拥有了他此生最爱的女子王朝云。一个人,在最幸福的时候,会回忆过往的经历和苦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是,在夜里,他梦到了王弗。他们曾无比相爱,他曾为她的离去痛不欲生,在王弗的孤坟前,种下数万株雪松,为了记得和怀念。而今,他却背离了初心,又将多于一倍的爱,或者比一倍还多的依恋,都献给了朝云。他该是有内疚和愧意的吧?但他当然不能说,只有记下这个似真似假的梦,通过文学镜像,表达出来,才不被人责备,自己也得以解脱。
所有这些后人的猜测和判断,其实都是文学作品赋予我们的想象,是镜像所折射出来的一些细枝末节。真实的样子,无人可见。包括那个叫苏轼的人。苏轼就是运用了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将生活,个人阅历,私人情感,通过叠加、隔离、蒙蔽、分身、空间调度,来顺利抵达镜像般的艺术臻境,让后人通过文字,推测、记忆和看见他时代,及他的个人经历。
这种成功的抵达方式,在另外的艺术作品中,也有极致而具体的表现。比如《百年孤独》中,以勇敢智慧开创世界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塞·阿尔卡蒂奥,另一个叫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就像某种循环,接下来他们的孩子们的名字不是阿尔卡蒂奥,就是奥雷里亚诺·何塞,直到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十几个儿子都回到马孔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居然都叫奥雷里亚诺。这种有意思的情节,其实更像德罗斯特效应,一种递归的视觉形式。当你拿着一面镜子,然后再站在一面镜子前面,让两面镜子相对。你看到镜子里面的情景,是相同的,无限循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人拿着一个相框,相框里他拿着相框,然后相框里拿着相框的他还拿着相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一种错觉。就像奥雷里亚诺一样,他们存在于每个固定的位置和生活轨迹中,他们是独立的,但同时,他们又因为出生于共有的家庭,而维持着一个共有的形象。伟大的马尔克斯通过文字,营造出一个完美的艺术镜像,他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硕大的、黑洞般的、无法弥补、也无法挽救的孤独。这既是作家的孤独,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孤独。孤独得到应和,便成为人性的警觉,这就是通往镜像最直接,也最成功的道路。
电影艺术中,对道路和抵达方式,似乎更加具象。比如《盗梦空间》,随着主人公的梦,被导演通过镜像艺术,带到第一层,第二层……然后产生焦虑,生出若他停留在某层梦境无法醒来怎么办的疑问,心悸,慌张,乃至还会攥紧拳头流泪。1975年,曾拍摄过《伊万的童年》,被誉为“银幕诗人”的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拍摄了带有自传性质的剧情片《镜子》,电影结构采取了“序幕”的形式,类似于歌剧中的序曲、小说中的引子,一段看似跟整部电影毫无关联的序幕中,一个口吃的男孩在接受治疗。于是,整部电影,就在这种结结巴巴表达欲中开始了。说实话,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在魂牵梦绕的童年记忆,和对母亲的爱与负疚感的镜像讲述中,很容易感受到某种气息的氤氲,无奈、苍凉,孤独,渴望温暖,都有,但显然这只是表象的一些东西,暗藏其下,也就是镜子既照见但又照不全的地方,依旧是迷惑而隐秘的。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所接受教育,注定在抵达镜像途中要经受的一切。影片中有个有意思的情节:幼年塔科夫斯基随年轻的母亲踏着泥泞到亲戚家借钱,独自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静默中,他扭身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镜头推近镜子中的脸庞,再推近镜子外的脸庞。幼小的安德烈就那样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镜子前,久久地与镜子里的自己对视……有人这样评价这段镜头:“幼年时的塔科夫斯基通过亲戚家这面陌生的镜子审视着自己;而成人之后的塔科夫斯基通过影片《镜子》,通过记忆进行了自我认知。”在这里,艺术呈现的方式,就是抵达艺术镜像的过程,而抵达过程的顺利与否,或者观众的理解度和接受度,也是抵达镜像,抵达内核的决定性因素。我一直在想,或者《镜子》的小说,要比电影好看得多。文学视觉跟电影视觉是不同的,而文学镜像,因为它的开放度和接纳度,使读者更容易抵达镜像内核。
《KillMeHealMe》中,描述的是一个人格分裂症患者,他竟然能很自如地在生活中交替使用自己的七重人格,当然,该剧并没有期待中那么惊心动魄,不怪乎韩剧惯用的剧情,家族仇恨,兄弟恩怨等等。但很显然,这是一个脑洞大开的剧情,让我们真切并肯定地看到了一个人的另外多面。而生活中,如果你用心体会,是不是常常可以感觉到,在一天,不,在一个小时内,你要换几个“我”,来应付面前的生活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时刻都在制造镜像的圆满?又为抵达生命的镜像而竭尽全力?一直喜欢诗人韩文戈的《另一种时间》,他充满睿智,对生命极其敬畏和热爱,在作品中,他这样表达:
往枯草根上撩着水,
一群野鸭子浮在水面
他或许赖在床上,不愿起来,闭着眼,
听午后的阳光踩过旷野的干草
当我打电话,拨错号码,
听一个陌生人在我耳边说话
此时,第三个我依旧活在前生
他牵着马,陪公子进京赶考
经过一棵开花的苹果树
当我来到燕山,苦菜钻出向阳坡地
童年的影子找到了我,委屈地向我诉说
第四个我,正舒展地活在后世
他刚漂泊归来,天涯路上
细雨把我们变得模糊
在这里,诗人通过营造镜像,带着我们抵达了记忆、梦幻、时间内核,抵达我们原初的对镜像的痴迷和依恋,抵达了南山——那些梅花还在树上冷艳,而看花的人,还在尘世的情谊中挣扎,那个骑马的人,刚刚牵马出来,她尚未坐到镜中,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