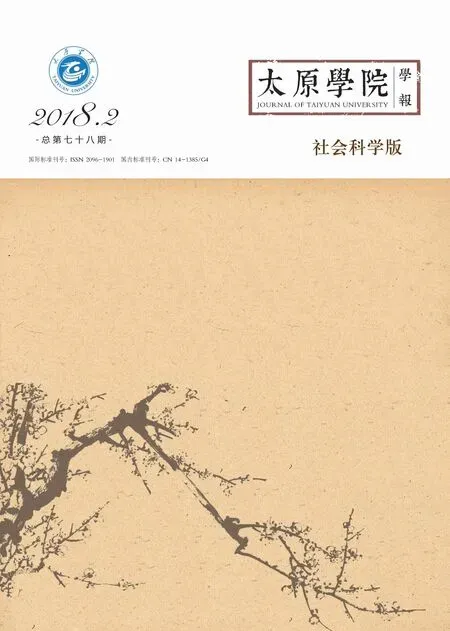《高老夫子》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在鲁迅创作的小说中,《高老夫子》是不大受学界关注的一篇。以“高老夫子”为篇名,经知网检索得到的文献不超过十篇。《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刊登姜彩燕的《自卑与“超越”——鲁迅〈高老夫子〉的心理学解读》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该文首先对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做了综述,然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高老夫子备课时照镜子,不是对自身外貌的自信或自恋,而是因为自卑;这种自卑情结形成的重要原因是高老夫子“童年被家人忽视,进而留下身体上的缺陷”;他课上胆怯与恐惧的来源是“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和额头的瘢痕所导致的自卑感”。该文的结论是:《高老夫子》这篇小说“既是对人生隐秘心理的深刻探索,表现出‘灵魂的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童年期不当教育给人成年后所造成的沉重阴影所进行的反思”。本文则认为包括姜彩燕论文在内的研究成果仍然意犹未尽,并未充分认识到《高老夫子》的艺术匠心,也未能充分挖掘它的思想意蕴。本文将参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这篇小说进行重新分析与评论。
一
小说开始,叙述高老夫子备课,“工夫全费在照镜,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查《袁了凡纲鉴》”: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实在太不将儿女放在心里。他还在孩子的时候,最喜欢爬上桑树去偷桑椹吃,但他们全不管,有一回竟跌下树来磕破了头,又不给好好地医治,至今左边的眉棱上还带着一个永不消灭的尖劈形的瘢痕。他虽然格外留长头发,左右分开,又斜梳下来,可以勉强遮住了,但究竟还看见尖劈的尖,也算得一个缺点,万一给女学生发见,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他放下镜子,怨愤地吁一口气。
据引文来看,父母在高老夫子小时候进行的不是姜彩燕说的“不当教育”,根本就是“不教育”——他偷桑椹,“他们全不管”。父母“全不管”将对儿童人格结构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父亲不管儿子,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儿子将无法以父亲形象为榜样,并与之认同自居,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超我,其道德良心与批判能力不能达到正常水平;母亲不管儿子,意味着母亲溺爱,这将使儿子的力比多固着在母亲身上,以致男性特征不明显(如缺乏男子汉气概),并(可能)导致同性恋倾向。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高老夫子是同性恋,但却有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高老夫子是一个女性化的人物——他喜欢照镜子,备课时照来照去,讲课后回到家里把课本与聘书都塞入了抽屉里,唯独留下那面镜子。高老夫子离不开镜子,因为镜子能够让他发现自己额头上“尖劈形的瘢痕”——偷桑椹时烙下的。一方面,瘢痕是形体上的缺陷,有碍观瞻,所以高老夫子要格外留长头发以掩饰它;另一方面,瘢痕又提示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偷桑椹吃),这又让他感到某种私密性的愿望满足。既要掩饰它的存在,又要照镜子发现它的存在;既要自己偷偷欣赏它的存在,又不想让他人(尤其是女学生)知道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这个“永不消灭的尖劈形的瘢痕”,可视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两者外形上都是裂开的)。
认为瘢痕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这样的解释或许会让人感到不悦。但这不是说高老夫子看到额上瘢痕就想到了性或起了性欲,而是象征性地表达了高老夫子的人格结构缺陷:本我的那些欲望冲动,自我虽觉得羞耻,却又控制不住,因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超我,高老夫子往往把责任推给自身之外的因素,如过去“全不管”的父母,如现在可虑的世风。由此可见,高老夫子的心理控制水平尚未走出儿童期,一直处于小时候最喜欢偷桑椹吃的状态。高老夫子不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成年男性。另有例证:老朋友黄三来找他,“一只手同时从他背后弯过来,一拨他的下巴”,这固然表现了黄三的流氓气,同时也表现了高老夫子某种顺从被动的女性化特质。
这一次,高老夫子特别在意这条“尖劈形的瘢痕”,因为他即将面对的是一群女学生(其实,他在头脑中已经面对着了)。一方面,高老夫子想表现得更男人一些,有例为证:来到贤良女学校,在万瑶圃的聒噪中,他心绪烦乱,涌上了许多“断片的思想: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的瘢痕总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这四条思想断片所表达皆是要保持男性气概与师道尊严;另一方面,高老夫子遮住额前的瘢痕缺陷,也是遮盖他的精神问题与道德缺陷:爬上桑树偷桑葚,跌下来磕破了头,才留下了瘢痕——他是个偷儿,瘢痕就是偷的明证,就是他付出的代价。如果说高老夫子小时候最喜欢偷桑椹吃,成人了则最喜欢偷看女人(“跟女人”)。他这次去做老师,本意并不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为了看女学生;表面上是去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是借此机会看女学生,这亦是“偷”。遮住瘢痕,让女学生看得起,其实是为了偷得顺利、偷得正当,堂而皇之地满足自己“看看女学生”的欲望。
这次进女学校“偷”亦让高老夫子付出了代价。他的讲课很不成功,仓皇逃离教室,跨进植物园,向教员豫备室走去:
他大吃一惊,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他倒退两步,定睛看时,一枝夭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微微发抖。他赶紧弯腰去拾书本,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道:

桑 桑科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于是也就不好意思去抚摩头上已经疼痛起来的皮肤,只一心跑进教员豫备室里去。
高老夫子再次被“桑”击中。“桑”,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在他不提防的时候突然重现,他的心事再次被揭穿。高老夫子小时候偷桑椹,留下了“永不消灭的尖劈形的瘢痕”;这次遭“桑”撞击,则留下了叫他脸红心跳、难以去除的“嘻嘻”。如同他留长头发遮饰瘢痕一样,这次他也装作没事似的,不去“抚摩头上已经疼痛起来的皮肤,只一心跑进教员豫备室里去”,但回家许久之后,依旧受着“嘻嘻”的折磨。
二
“嘻嘻”,是女学生发出的还是自己的幻觉?高老夫子不能确定,但它仿佛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顽固性地发作着。想拔掉它,似乎无能为力;下了辞职的决心,又舍不得鲜红的聘书。为什么如此两难呢?与瘢痕既给高老夫子某种羞耻或罪感又予其欲望满足一样,“嘻嘻”是从“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合的海”发出来的,“嘻嘻”使他“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直言之,“嘻嘻”作为一个症状,意味着他脑子里装的全是女学生;换言之,“嘻嘻”既令他烦躁恼怒,同时又让他回想起课上情景,他忘不掉那些女学生。
高老夫子上课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先是“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后来:
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但当他瞥见时,却又骤然一闪,变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姜彩燕认为,在高老夫子上课的整个过程中,“他几乎一刻也未曾关注过女学生的长相、身材,从未留意过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物,自始至终被隐约听到的笑声所折磨,好像灵魂出窍一般”,这似乎是说,高老夫子的图谋没得逞,因没看到一个“具体的”女学生。这种解释过于注重具体的实指,实际上,性可以不附着于某个具体人物身上,而表现为一种把握不定的情调与流动不居的氛围。对第一次登上讲台的高老夫子来说,他的确感受到了新鲜而浓烈的性欲氛围。
首先,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女学生“蓬蓬松松”的头发就足以唤起了男性新鲜的性感体验。人们向来重视当时剪发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即是如此,它也提到了女子剪发,但关注的是人生出路问题。这大概与鲁迅年入不惑有关,而二十出头、性欲正活跃的沈从文则更关心女人剪发的性感意义。他的小说《岚生同岚生太太》为此留下了佐证。岚生是财政部的二等书记,走路回家的次数多,为的是绕远到墨水胡同的“闺范女子中学”看女学生:
他觉得女人都好看,尤其是把头发剪去后从后面看去,十分有趣。因为是每日要温习这许多头,日子一久,闺范女子中学一些学生的头,差不多完全记熟放在心里了。向侧面,三七分的,平剪的,卷鬓的,起螺旋形的,即或是在冥想时也能记出。且可以从某一种头发式样,记起这人的脸相来……他想着,如果自己太太也肯把发剪了去,凡是一切同太太接近的时候,会更要觉得太太年青美好,那是无疑。
这一天岚生领了工资回来,在餐桌上劝诱太太剪发,“同事中见着,将会说你是什么高等女子闺范的学生哩。”于是,找来相士看定了剪发的日子,又买了德国式剪刀,旗袍料子——剪完头发要配穿旗袍。以后太太的发型便是参照着在市场上见到的年青漂亮的女人头发剪成的。从此以后,岚生先生回家,坐车子的回数就比走路的时候为多了。随着岁月流逝与时代发展,我们已经无从体验“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带给高老夫子的视觉冲击与隐秘兴奋了。
当高老夫子与女学生目光相遇,发现半屋子都是眼睛,眼睛与鼻子构成“小巧的等边三角形”——“小巧”用于描写女性身体时,往往表现了男性的欲望。三角形都生着两个鼻孔,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逼得他连忙收回眼光,再也不敢离开教科书,只能抬起眼来看屋顶。高老夫子愈是有意地抗拒与挣扎,愈是掉进了“海”里不可自拔(症状便是躲不掉的“嘻嘻”)。前文说过,高老夫子备课时,黄三进来拨他的下巴,同时还说了一句话:“哙,你怎么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这句话很突兀,它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高老夫子听了,“板着脸正正经经地”叫黄三“不要胡说!”?原来,高老夫子和黄三在学校外看过女学生,这次高老夫子做教员,进学校里面去看,黄三用的“钻”字既下流又贴切,尽管彼时高老夫子驳斥黄三,可他现在不是真地钻进“深邃的鼻孔的海里”而出不来了吗?
晚上到黄三家打牌时,高老夫子还抱着不平之意,“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但这次总以为世风可虑,实则是女学生的海诱惑了他,使他放不下,直到他快凑成“清一色”的时候,才觉得世风终究好了起来,这固然是因为他要赢牌,亦因骨牌的“清一色”能让人联想到女学堂的清一色光景:半屋子全是蓬蓬松松的头发,半屋子都是眼睛,以及小巧的等边三角形。打牌前,黄三热心地问:“怎么样,可有几个出色的?”高老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却说“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使高老夫子舒适乐观的“清一色”才是对黄三问题的回答:女学生“清一色”、全出色。他的不平之意忘记了,觉得世风好了起来,意味着他还要去教书,去看女学生,去看“海”。
有趣的是,沈从文《八骏图》里的达士先生也掉进了海里不可自拔。达士先生来到青岛给未婚妻写第一封信,称虽然海“真有点迷惑人”,但“若一不小心失足掉到海里去了,我一定还将努力向岸边泅来,因为那时我必想起你,我不会让海把我攫住,却尽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然而,一个女人的一双眼睛把他捕获了,女人的眼光“既代表贞洁,同时也就充满了情欲”,达士先生因此推迟了与未婚妻的相聚,而要在海边多住三天,因海而起的病应该用海来治疗。
现代文学史上最好的两位小说家不约而同地以“海”来写男女情欲,而不去详细描写一个女人具体的身材与长相,这既是洞悉人性,又是艺术高明。
三
谈到《高老夫子》的艺术特色,人们历来重视它的讽刺性:鲁迅善于把人物自身的矛盾“用人物自身的行动暴露出来,让读者看到人物的可笑、可恨、可鄙,就好像并不是作者的描写,而是人物自己的言行暴露了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一样,由此而引出人们的笑声”[1]。从人物言行不一致、里外不协调的角度确实可以揭露高老夫子伪道学、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这从小说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如发表了冠冕堂皇的《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其实他所擅长的不过是野史演义而非真知灼见。但是,对鲁迅《高老夫子》讽刺艺术的论述皆忽略了“桑”的点睛之笔以及“嘻嘻”的重复发作,因为言行不一构成的讽刺性可以暴露人物的矛盾表象,而要想深入挖掘人物“灵魂深处的秘密”却不得不借助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武器。精神分析认为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的心理过程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工作。“灵魂深处的秘密”不在意识层面,而在潜意识之中。那么,我们如何捕捉潜意识本能呢?“在精神生活中,一旦已形成的东西不可能消失,一切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保存下来,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如,当回退到足够的程度)还会再次出现”[2],这就是说,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冲动会借助某个契机重现出来,我们就是要抓住那些重现的事物来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往往那些事物显得琐屑而无足轻重,如前面分析的“桑”和“嘻嘻”,却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原因。
因此,本文认为,《高老夫子》的艺术成就不在讽刺,而在精神分析式的重现。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重现艺术,我们需要对《高老夫子》进行整体上的精神分析学理解。
小说名为《高老夫子》,除了高老夫子,还颇费笔墨写了黄三与万瑶圃。黄三出现在高老夫子备课之时,一礼拜之前他还同黄三打得火热,现在却觉得黄三下流无知了,对之既高傲又冷淡。“黄三”,应视为高老夫子暂时压抑下去了的露骨的本能冲动。与黄三的对话,是高老夫子自我与本我的一场斗争与较量。这时的高老夫子已在《大中日报》上发表大作,得了贤良女学校的聘书,用了新皮包新帽子新名字,“万瑶圃”便是高老夫子的自我形象。与黄三不同,万瑶圃是个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赞同维新,振兴女学,“很能发表什么崇论宏议”。然而,喋喋不休的万瑶圃却弄得高老夫子“烦躁愁苦着”,当堂出丑。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自我是本我的一部分,即通过知觉-意识的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部分,代表着理性,遵循着现实原则,可万瑶圃口头上说顺应世界潮流,实际上却提倡所谓国粹、顽固守旧,又罔顾高老夫子最迫切的现实问题——预备功课;并且对乩坛蕊珠仙子俯首听命,以得之青眼而高兴,以得之“不无可采”的评语而得意,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自我理想(超我)的引导与支配(虚幻的蕊珠仙子绝不是一个正确的自我理想)。总之,“万瑶圃”象征着高老夫子的自我形象既非理性、非现实,又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自我理想(超我)。这似可视为鲁迅对当时知识文化界病症的一个隐喻性表达:“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高老夫子回到家中,“决绝地将《了凡纲鉴》搬开;镜子推在一旁;聘书也合上了。正要坐下,又觉得那聘书实在红得可恨,便抓过来和《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同塞入抽屉里”,这意味着“万瑶圃”已被打回潜意识之中封锁了起来,“桌上只剩下一面镜子,眼界清净得多了。然而还不舒适,仿佛欠缺了半个魂灵,但他当即省悟,戴上红结子的秋帽,径向黄三的家里去了”,于是“黄三”代表的“半个魂灵”及其欲望冲动又被释放出来,以词语重现的方式:
备课时,黄三说:
“你不是亲口对老钵说的么:你要谋一个教员做,去看看女学生?”
“你不要相信老钵的狗屁!”
打牌时:
“来了,尔础高老夫子!”老钵大声说。
“狗屁!”他眉头一皱,在老钵的头顶上打了一下,说。
“狗屁”,或是高老夫子的口头禅,与粗俗的黄三一起出现。前者,“狗屁”意味着高老夫子拒不承认“黄三”的欲望冲动,不承认他做教员的真实动机;后者,“狗屁”则表达了他对“万瑶圃”不情愿的否定。说他“不情愿”,是因为他附加了一个动作“眉头一皱”,他不愿意被人直接说破心机。高老夫子从来没有袒露心曲,而是不断地掩饰(如他费尽心思掩饰额上的瘢痕),但黄三(以及“桑”“嘻嘻”)却总是戳穿他。
备课时,黄三说:
“你不要闹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了!……我们这里有了一个男学堂,风气已经闹得够坏了;他们还要开什么女学堂,将来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才罢。你何苦也去闹,犯不上……”
“我们说正经事罢: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局面。”
打牌时:
“教过了罢?怎么样,可有几个出色的?”黄三热心地问。
“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
“闹”“正经”“犯不上”皆是重现了黄三前面的话。此时的高老夫子活脱就是彼时的黄三。但此时黄三关心的是“怎么样,可有几个出色的”,很平常的一句问话揭露了高老夫子最隐秘的欲念。如前所述,在高老夫子看来,女学生皆出色,口头上虽然说“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但内心深处既恐惧又舍不得那片“流动而深邃的海”。如同“桑”和“嘻嘻”撕开了高老夫子灵魂深处的口子,是他内心隐秘欲望发作的症状,“黄三”的出现与重现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如果仅把黄三看作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而不是视为高老夫子本我的象征,那就无法理解小说字面意义之下的深层含义,无法理解高老夫子打牌时为什么“总还抱着什么不平”,为什么“清一色”使他舒适、使他乐观(黄三“出色”的问题一直盘旋在他心底)。
结语
《高老夫子》是一篇尚未被充分认识与欣赏的小说。借助于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乃有了新的观感与理解。比较《明天》所潜伏着的单四嫂子的性爱本能,《肥皂》所泄露的四铭的性幻想,《高老夫子》对精神分析技术的运用更加自觉与老到,对人物心理过程的揭示更加深刻与复杂。在某种意义上,高老夫子可视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人格不健全、不成熟的象征。虽然没有《狂人日记》《伤逝》《铸剑》那样出名、被重视,但这并不妨碍《高老夫子》是鲁迅所完成的最好的小说之一。
参考文献:
[1]张惠慧.试论《高老夫子》的讽刺艺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1990(1):52-8.
[2]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C]//论文明.徐洋,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