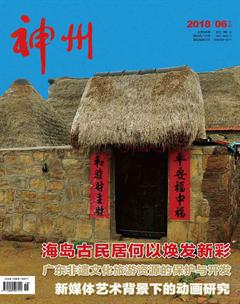青海花儿“盲艺人”的缺类浅析
张英 陈彤 李欣颖 陆弈思
摘要:民歌的历史,离不开《诗经》。由“四始”“六义”构建的《诗经》,“风”可视为我国民歌的源流。继而至汉乐府,南北朝民歌,清晰地呈现了民歌的地域风格。宋词、元小曲、明山歌亦可视为民歌的变形。考察民歌的发展和传承,“瞽”居重要之所,但随着时间流逝,“瞽”这对中国民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群,渐渐退出民歌的舞台。本文拟在从“青海花儿”着眼,通过对其“盲艺人”的缺类分析,追溯“瞽”者身份地位的变化,探讨民歌在社会进程中,形式和内容的变化。
关键词:青海花儿;盲艺人;瞽;民歌
一、从“瞽献曲”至“生活之歌”,民歌功能的变化
《召公谏厉王止谤》中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这儿的瞽未必指“盲人”,但其清楚地指明了早期的乐诗大抵皆为“盲人”,这才使得“瞽”这个词具有“乐师”的所指功能。有关“瞽”的记载,我们可以追溯至《诗经》。《诗经·周颂》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诗经·大雅》云:“鼍鼓逢逢,瞍奏公”。《尚书·夏书》有“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有关瞽瞍之别,《毛诗郑笺》云“无目眸谓之瞽,有目无眸为之瞍”由此可见,瞽瞍所指皆为乐师。
瞽、瞍这类身体方面有残缺的人,在中国古代如何成为乐师的代表,《礼记·正制》给以了回答,“暗、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以器食之,则扬其所长,使其凭其器养活自己。基于此,中国古代瞽瞍是作为一种正式职业出现的。发展到后来,由倡优所取代,瞽者流落民间,仍以“音乐”为职业谋生。宋·陆游《小舟游近村》“负鼓盲翁正作场”;元末明初瞿佑《过汴梁》“陌头盲女无愁恨”明·厉鄂《悼亡姬》“闷凭盲女弹词话”。瞽者从宫廷乐师沦为街头艺人,从谋职到谋生,身份地位,演唱方式、内容;歌曲性质发生质变。
瞽献曲,“采诗”决定了瞽演唱的内容、形式、风格,这时的民歌,功能指向“讽”;之后瞽所演唱的民歌,便是“生活之歌”,有关生活地全面记载。
二、野曲至“乡曲”,青海花儿“盲艺人”的缺类分析
丹纳在《艺术哲学》里面把环境、种族、时代归为影响艺术三个重要因素。本节准备引入此观点,对青海花儿中“盲艺人”的缺类进行分析。
(一)花儿的特色
青海花儿,是爱情生活的记载。作为民歌,保有表达情感的直白大胆,描写内容贴近生活,抒情手法比兴多用、形象意向固定单一的共性之外。作为西北民歌的一种,又以其个性赢得喜爱。
花儿的特性包括:对婚姻的坚守“若要我两的婚姻散,冰冻上开哈个牡丹”(1);爱情的大胆追求“尕妹的跨根里坐半天”;地域性极强的方言:活泛(精神)、心疼(好看)、维(交);贴近生活的起兴“河里的鱼儿一全全”;与劳动生活密切相关的意象:红公鸡、嫩白菜、红樱桃;素朴的比喻“簸箕的湾湾挡来”;使用谚语,野雀儿下蛋土里埋
(二)时代——民歌功能的具体化,“盲艺人”缺失的重要原因
当民歌中独立出来的部分,作为绝对功能的承载,演唱者的身份开始受到限制,某类人群便开始缺席。“瞽”这一类在中国民歌中扮有重要角色的人群,从宫廷乐师转化为街头艺人,皆为扬己之长谋求生活。应运而生的民歌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其承担的主要功能依旧是职业谋生。
作为爱情产物的花儿,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主要功能是传达男女情意。作为爱情的承载物,盲人因其身体缺陷无体悟的对象,缺失男女双方的共鸣,造成了盲艺人的缺席。
(三)环境——地域风俗,“盲艺人”缺席的因素
山歌,作为滇黔影响较大的民歌,大部分是关于爱情的传唱。在对爱情的表达中,“盲人”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同作为爱情歌谣,为什么花儿中会缺少“盲人”,地域风俗原因应该纳入考虑。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获知,古往今来,青海地区因地域优势,一直处于自给自足。同作为祖国边缘地区的滇黔,地表起伏较大且多自然灾害,盲人凭“器”乞生。兼有苗、布依、藏居民风开放,这又为“盲人”歌唱提供了可能。
(四)种族——“野曲”至“乡曲”,“盲艺人”缺席的主要原因
花儿是青海各民族用方言演唱的一种民歌,但主唱者是回族。早期的花儿作为“野曲”,是青年男女言说“私情”的产物。
风俗信仰,回族的青年男女无婚前的自由恋爱,没有“父母之命”的恋爱沦为私情。自由恋爱涉及独身的青年“没拜天地的两口子,它是阳世上有的”、订婚的男女,更甚者,已婚的夫妇“实指望能找个男子汉,享清闲,为娃娃们找个靠山”。私情是自由恋爱,亦是婚外情。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婚外情,“盲人”不是其体验者,因而花儿缺少“盲人”的身影。
作为“私情”产物的花儿,演唱场所和时间上受到的限制非常大,这些客观因素,也导致了花儿中“盲人”的缺席。
三、“盲艺人”的介入,民歌的生活回归
野曲至乡曲,花儿一直是爱情的承载物,细品“野”“乡”两词不难察觉,青海花儿,这一能指的民歌,在功能具体化后,重回生活之歌,回归早期民歌的功能范畴。
演唱的广延,功能的泛化,给“盲人”提供了演唱的契机,出现“先天的盲者”,与模仿“盲人小调演唱”的“假盲人”。表演性、娱乐性、生活性、游戏性、赋予花儿多种可能,加之各民族参与和电子媒介的普及,盲艺人参与演唱。必须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及的花儿特征,对花儿的演唱者同样给以了规定,“盲艺人”只能是珍稀人群,难以进入大众视线,更别提,恢复古代“瞽献曲”的遗风。
四、总结
民歌是大众生活的产物,是人们在劳动之余的游戏。作为生活的反映,本就存在多种可能。纵观民歌的发展,功能从泛化——具体——泛化,即语言的所指——能指——所指之间的转变。演唱人群从单一转为多样又回归单一。演唱方式从随性转向程式化最后到随性。演唱场所则在固定与不固定之间转变。
民歌的魅力所在,在泛化,所指、人群多样、方式随意、场所不固定。因而,要弘扬、发展民歌,就得聚焦其魅力所在。切勿让民歌登上舞台,成为只有表演性的舞台艺术。
注释:
(1)引用的唱词皆出自《老爷山花儿录》
参考文献:
[1]黄焯,《毛诗郑笺平议》,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孔安国,《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赵生民主编,《老爷山花儿集》,西宁四方块印刷有限公司,2015
[4]喇秉德,马小琴《青海回族簡史》,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张英(1994.02)女,汉族,贵州,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
指导老师:何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