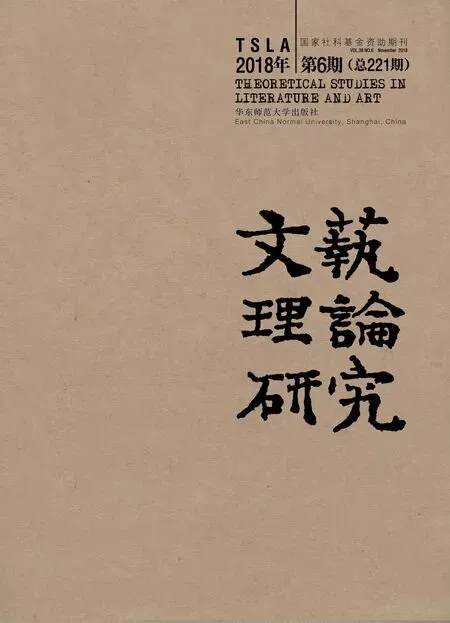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情”“事”互济观念
李桂奎
“诗”因何而生?答案不外乎班固所谓的“缘事”与陆机所谓的“缘情”两种说法。二者虽各有侧重,却并行不悖。“缘情”说虽强调“情”字,但也并不拒绝“缘事”因素;“缘事”说虽突出“事”字,但也没有否定“寄情”意图。多年来,由于人们对“言志”“缘情”等诗学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甚至只把“缘情”奉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再加受西方叙事诗、抒情诗二分观念影响,因而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说一提出就得到较为广泛的追捧,“缘事”诗学观念无形之中遭到遮蔽。近年,随着叙事学的传播与影响,人们开始重新发掘有关诗歌创作的“缘事”传统,并不断地呼吁重视相关诗论问题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实绩。当下,在诗歌叙事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学术背景下,中国诗论中的“感物吟志”“感事遣怀”“述事寄情”“情事合一”等“情”“事”互济观念自成体系,期待予以现代重构。
一、 感事而生情:传统诗歌文本生发观念
从诗论传统看,中国人在突出“言志”“缘情”的同时,也曾不同程度地意识到“感物以抒情”“感事而生情”等问题,从而形成一套关于诗歌生发以及开启诗歌创构的原理。
在古代许多用场中,“物”常常是“事”的同义字,如陆机《文赋》曰 :“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文选》李善注 :“物,事也”(萧统356)。如果把“物”视为包括“事”在内的广义的事物,那么,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所谓的“感物吟志”其实就大体相当于“感事而生情”,足以揭示诗歌生成的普遍规律(童庆炳19-27)。稍后,钟嵘在其《诗品序》中也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指出性情乃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结果,要么是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之四季节候所感;要么是各种人生悲欢离合所激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3)。在历史上,嘉会离群、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之类的人生境遇事件最能诱发当事人或旁观者不吐不快的悲情,也最能成为诗歌叙事抒情的基本素材。稍后,简文帝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严可均3010)
无论是春景秋色,还是浮云明月;无论是旅程光景,还是塞外风景,各种时空里的“物”“事”纷纷纭纭,都可令人触目动情,落笔写心,从而诱发“因事而作”。大千世界里的自然物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物事均可入诗,使得“感事而生情”“因事而作”成为诗歌创作的一条铁的定律。
关于诗歌叙事抒情的原委问题,孟棨《本事诗》之序有云 :“抒怀佳作,讽刺雅言[……]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题,各以其类聚之。”(丁如明1237)。在《本事诗》中,“情感”和“事感”之命题基于述事寄情传统,所记“章台柳”“红叶题诗”“人面桃花”及杜甫诗号为“诗史”等众多逸闻轶事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被后世小说戏曲家改编为妙趣横生的戏剧关目。况且,该书所采取的“以诗系事”“以事明诗”体例,也为后人说诗论文所效仿。至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指出 :“盛唐诸人唯在兴趣,[……]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198)。意思是,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生的情思正是“兴”,从而在标举盛唐诗歌的兴趣时,已将感事叙情的关系讲得比较到位了。在此前后,“感事而生情”这种论调层出不穷,如宋代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说 :“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先焉,而后诗出焉”(杨万里2841),都在强调诗歌总是由事情触动、感动而写出的。元明清时期,人们对“感事而生情”的诗歌创构动因保持广泛的认同。
在“感事以生情”的诗歌生发机制中,乐府诗歌,无论是古乐府,还是新乐府,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西汉《韩诗外传》所谓“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基础上,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六年明确讲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阮元2287)。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认为,乐府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1756)。唐代新乐府的叙事境界又有所开拓。杜甫开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地创作了《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诗。到白居易手里,这种不再依傍前人乐府旧题而自创新题写时事的写法被发扬光大,诗歌的叙事功能被大大激活、发挥。白居易一而再、再而三地倡言“感事”说,其《策林》六十四指出 :“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白居易1364)。《策林》六十九认为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白居易1370)。《与元九书》则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962)。由此可见,乐府诗的叙事性之强是述事寄情相伴而生的必然,无需多言。这些诗论观念既是对以往诗歌叙事经验的总结,又对后世诗歌叙事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创作实践来看,诗歌发生于“感事”现象司空见惯,以至于有不少诗作径直被冠以“感事”之名,如白居易的《感事》《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开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斋居春久,感事遣怀》;许浑的《雍陶下第寓居崇圣寺感事》《骊山(一作望华清宫感事)》《甘露寺感事贻同志》;李商隐的《过故府中武威公交城旧庄感事(武威公王茂元也)》;薛能的《重游德星亭感事》;崔涂的《己亥岁感事》,以及韦庄的《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等等。另外,陆龟蒙、高蟾、吴融、唐求等唐代诗人也都有题名为《感事》的作品存世。宋诗中也不乏像陆游的《乾道之初卜居三山今四十年八十有一感事抒怀》之类的“感事”名篇。除了即事命笔的单篇之作不绝如缕,中国诗歌史上还出现了像明代丘浚的《观时感事诗》一卷这样的感事组诗。也有的诗歌直接以“述事”为题,如唐代薛能《秋夜山中述事》写道 :“初宵门未掩,独坐对霜空。极目故乡月,满溪寒草风。樵声当岭上,僧语在云中。正恨归期晚,萧萧闻塞鸿”(彭定求470)。以诗叙事,时空错落有致,非常得体。
诗而外,宋代以“感事”为题或蕴涵感事之意的词作同样不少,如蔡伸《望江南·感事》写道 :“落花尽,寂寞委残红。蝶帐梦回空晓月,凤楼人去谩东风,春事已成空”(唐圭璋1418)。史达祖《阮郎归·月下感事》写道 :“旧时明月旧时身。旧时梅萼新。旧时月底似梅人。梅春人不春。香入梦,粉成尘。情多多断魂。芙蓉孔雀夜温温。愁痕即泪痕”(唐圭璋3363)。以上二首大约均是感于失恋之事而作,以景衬情,愁怨而伤感。除了流连光景、吟哦儿女情事之外,宋词中也多有面向现实,抚时感事之作。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等无一不是善于借助叙事来抒情的佳作。再如,陈人杰《沁园春·丁酉岁感事》写道:
谁使神州,百年陆沈,青毡未还。怅晨星残月,北州豪杰,西风斜日,东帝江山。刘表坐谈,深源轻进,机会失之弹指间。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风寒。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唐圭璋4261)
该词所感乃元蒙南侵、南宋王朝无力回天之事,故而连用“伤心事”“事犹可做”等语忧国伤时,传达出恢复神州河山的期待和信念。当然,更多诗词虽不以“感事”二字为名,却具“感事”之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诗词作者本人或以后的人在整理诗作时,也常常列出“感事”这一类目。如后人辑录唐代李商隐之诗、宋代朱熹自编其诗,都曾列出“感事诗”一类。宋代阮阅所编的《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四、二十五,也命名为《感事门》。
关于诗歌生发,尽管也会有“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先“情”而后“事”的情况(李梦阳566),但通例却是“感事”在先,“生情”成诗在后。说到底,在中国诗歌创构之初,无论是睹物思人,还是见景生情,其实都属于“感事而生情”,从而成为启动文本创构的理论概括。在中国传统诗论中,基于人们反复传达的物、景、事、情贯通观念,“感事以生情”诗歌生发机制自成体系。
二、 “述事以寄情”:传统诗歌文本生成观念
如前人所指出的,“感事而生情”,尚不等于叙事抒情本身,因为所感之事有的现身于文本,也有的只停留于文本之外,并没能进入文本内部。“述事以寄情”才真正是文本构建的具体行为。
如果梳理“述事以寄情”诗论的来龙去脉,当追溯到被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奉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说。众所周知,这一学说首见于《尚书》,在先秦时期即获得较广的认同。《荀子·儒效》也说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75)。五部经典仿佛各司其职,但皆包含叙事因素。自古以来,志、记、纪三者常常是通用的。可以说,诗与事的原义都包含“记”的意思。《孟子》所谓“以意逆志”之“志”,即赵岐所言 :“志,诗人志所欲之事”(阮元253)。何谓“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 :“事,职也。职,记微也”(116-117)。意思是,“士”的职责是“记微”,记录日常发生的琐事。同时,《史记索隐·五帝本纪第一》说 :“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司马贞1)。郑玄《周礼·保氏》注曰 :“志,古文识。识,记也”(郑玄961)。志,记也,即记录。文言小说集《夷坚志》《聊斋志异》之“志”就是在这意义上使用的。至汉代,人们已经将“诗言志”与“感事为诗”联系起来,如纬书《春秋说·题辞》曾宣称诗歌为事而作,因心动而感发 :“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安居香山856),表明诗歌创作大多会经过由“事”而“谋”,再内化为“心”“志”的过程。基于此,后世“述事以寄情”等说法,既概括出叙事与抒情之于文本建构的功能,也传达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诗言志”之“志”,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一文曾有过一番较为详细的辨析和阐释,他说 :“诗言志有三义:回忆、记录、怀抱,诗乃止于心上。”“无文字时专凭记忆,文字产生以后,则用文字记载以代记忆,故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闻一多186)。在闻先生看来,“诗言志”应该是原始的结绳记事诗性观念的延续,自然离不开叙事。的确,在古代,“志”虽然时而也用以指面向未来、充满展望的志向,但更多地是指回味、感伤或悼昔、忏悔过去,以及记录眼前怀才不遇的遭际。可以说,“诗言志”中的“志”既是指示情感的名词,又是表示言说的动词。就是说,“诗言志”本身兼具叙事、抒情二者化合的意味。“诗”的本质虽在于抒情,但往往要靠“记事”来达成。从原始的猎歌、牧歌、渔歌,到后世面向纷纭世事的各种题材的诗歌,中国诗歌基本坚持叙事、抒情一体。随后,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关于“言志”的解释虽然基于闻一多的见解,但却将其内涵收拢到名词意义上来 :“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朱自清194),从而又舍去了“志”的“记忆”和“记录”义项,只把“志”的内涵限定为“怀抱”。可见,“诗言志”本来兼含“缘事”“缘情”之意,而到了后来,人们通常多属意于“志”的志意、情志、怀抱等内涵,再加为了使“诗言志”与后来的“诗缘情”相匹配,许多学者认为,秦汉之际人们在讨论诗歌时所讲的“情”“志”之涵义实无大的不同,强调“志”就是“情”,从而对其叙事性有所忽略。也许正是沿着这个思路,陈世骧等学人才纷纷将“言志”与“缘情”进行对接,并推演出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无论怎么说,这种思路固然使得中国诗论命脉显得相对集中,且给人以一脉相承感,但却遮蔽了另一个固有的传统——“缘事”传统。
说起来,在中国诗论中,把叙事与抒情关系讲得较为清楚者当数宋代的魏泰,他的《临汉隐居诗话》提出了著名的“述事以寄情”“缘事以审情”创作原则:
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馀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其言止于乌与桑尔,以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之类,皆得诗人之意。至于魏、晋、南北朝乐府,虽未极淳,而亦能隐约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馀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发笑,此曾不足以宣讽。愬之情况,欲使闻者感动而自戒乎?甚者或谲怪,或俚俗,所谓恶诗也,亦何足道哉!(何文焕322)
这段文字以《诗经》中的《卫风·氓》所言“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小雅·正月》所谓“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为例,强调二者表面上是在说桑、乌,实际是意在言外,借事寄情。在魏泰看来,屈原《湘君》《湘夫人》所言“采薜荔兮江(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以及张衡《四愁诗》所说“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都是在借叙事写景传达诗人微妙的情意。虽然魏泰对唐人乐府的评价有失公允,但基本上道出了中国式叙事与抒情相依为命、文本意境相互生发的诗歌创作和接受传统。魏泰还指出,为达“寄情”之目的,必须采取“述事”这一必备的手段,但由于“情贵隐”的缘故,叙事不宜直露周详,而是要借助隐约的意象来达成。读者接受时也要“缘事以审情”,即根据诗语所叙之意象,感知其深藏的意蕴。从发展的态势来看,中国诗歌的“述事以寄情”文本构建也有一个日趋明朗化和具体化的过程。明代袁中郎《雪涛阁集序》指出 :“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辩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郭绍虞205)。意思是,诗歌的本色是不擅长直书其事,晋唐之后已有所改观。
关于叙事与抒情之关系,不同文体有所不同。在汉赋中,抒情是为叙事服务的,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文筌)》曾论汉赋之“抒情”曰 :“抒其真情,以发事端”(王水照1282)。这说明,在赋体中,抒情的目的在于打开故事的头绪。相对而言,在诗歌中,叙事多服务于抒情,抒、叙化合注重的是“钩勒”,即通过顺逆铺展等叙事技巧有效地达成抒情之曲折。既然是借叙事以抒情,较为直观的叙事常常要充当迂回曲折抒情的手段,那么,诗歌叙事只要有利于真情传达,自可不必计较本事的真伪。即使叙事有所杜撰,也似乎无可厚非。对此问题,前人也曾针对不同诗歌文本展开过无数次争论与探讨。如关于白居易创作《琵琶行》“本事”之真伪,人们一度多有质疑。宋代洪迈在《容斋五笔》之《琵琶行·海棠诗》一则说:
白居易《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歌咏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抒写天涯沦落之恨尔。(洪迈508)
洪迈曾怀疑且推论白居易会见琵琶女似乎不合情理,尽管如此,他还是肯定了该诗的写作旨在抒写天涯沦落之恨,而不是就事论事。清人赵翼《欧北诗话》的态度就更明确了 :“《琵琶行》亦是绝作,然身为本郡上佐,送客到船,闻邻船有琵琶女,不问良贱,即呼使奏技,此岂居官者所为?岂唐时法令疏阔若此耶?盖特香山借以为题,发抒其才思耳”(43)。由此可见,为达抒情之目的,诗人尽可借题发挥,甚至“不择手段”。当然,为保证抒情的感人效果,诗歌叙事也不能流于过度失真。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中国诗歌抒情往往会依托于某种叙事,无论假托与否。在中国诗歌史上,自古而今,既不乏多情者,也不缺好事者。即使对那些不够清晰之事,人们也能够按“理”推导或敷衍出“本事”。
“述事以寄情”是中国诗歌本体赖以生成的一道程序,大凡感伤、感遇、怀旧、怀古、悼亡等不同题材的诗歌,几乎无不是先感事而发,而后述事以寄情。尽管有的侧重于叙事,被定性为叙事诗;有的侧重于抒情,被称为抒情诗,但抒情依托于叙事,叙事也会落脚于抒情,叙事与抒情珠联璧合,成为中国诗歌文本创构的基本路数。
三、 “情事之合一”:传统诗歌文本生态观念
关于诗歌文本构成状态,嘉靖间孔天胤在为宋代计有功编订的《唐诗纪事》所作的序言中说 :“夫诗以道性情,畴弗恒言之哉!然而必有事焉。则情之所由起也,辞之所为综也。故观于其诗者,得事则可以识情,得情则可以达辞”“故君子曰:在事为诗。又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夫谓诗为事,以史为诗,其义膴哉!”“至其摛藻命章,逐境纡怀,皆情感事而发,抒辞缘情而绮丽,即情事之合一”(黄宗羲2193-94)。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诗歌重在抒发性情,但必须有事做依托。读者总是由事察情,方得究竟。近年有学者指出 :“人们常说睹物思情,而这个‘物’,可以说包罗万象,可以是物事、情事、人事……不一而足。抒情诗的情感抒发中,往往就免不了涉及‘事’”(谭君强18)。从根本上讲,“情”与“事”是融合为一体的。“情事合一”是唐诗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文本生态。
关于诗歌文本生成的基本手法,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曰 :“叙事议论,绝非诗家所需,以叙事则伤体,议论则费词也。然总贵不烦而至,如《棠棣》不废议论,《公刘》不无叙事。如后人以文体行之,则非也。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过因谗後重,恩合死前酬’,此亦议论之佳者矣”(丁福保1419)。通常说,叙事、议论容易损害诗歌体式、浪费语言,但只要用得巧妙,则可取得好的效果。如此说来,在中国诗歌文本中,抒、叙、议三者经常各显身手。然而,议论却最终并没有取得与抒情、叙事平起平坐的资格。晚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二《论七言歌行流品答陈完夫问》认为 :“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亟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苦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妍钓奇,其品益卑,骎骎乎苏、黄矣!”(王闿运537)。可见,叙事、抒情是中国诗歌文本建构的必需,融情于事获得了举世公认,而议论因缺乏诗性而未能成为必备的诗法。
东汉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引郑众之言云 :“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843)。在比兴链接下,“物”“事”自通。赋的根本是直言其事,即朱熹所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而比兴之于事则是委婉道之。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言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2)。明清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将写景、叙事、述意与赋、比、兴手法进行对接,如清人黄生指出 :“诗有写景,有叙事,有述意,三者即三百篇之所谓赋、比、兴也。事与意,只赋之一字尽之,景则兼兴、比、赋而有之。大较汉魏诗赋体多,唐人诗比兴多。六朝未尝无赋比兴,然非三百篇之所谓赋比兴也。宋人未尝无赋比兴,然只可谓宋人之赋比兴也”(张寅彭101)。赋比兴皆可以服务于写景、叙事、述意,但因时而异,在具体使用上各个时代还是有侧重的。在《诗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中,“情事合一”文本生态已有所体现,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 :“《诗三百》之主要作品‘事’‘情’配合得恰到好处”(闻一多190)。《静女》《硕人》《氓》《采薇》等诗都是“情事合一”的典范,特别是“铺陈其事而直言”的“赋”有利地发挥了叙写事件、人物、场景的作用。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为讲究曲折有致,人们已开始注重用比兴叙事。如庾信的《燕歌行》通过宽泛的叙事和用典写征人思妇,前半写边关战况以及征人思归,后半则写思妇盼望征人归来以及她的寂寞无奈。关于这首诗,清人王夫之的《古诗评选》云 :“句句叙事,句句用兴用比,比中生兴,兴外得比,宛转相生,逢原皆给”(王夫之562)。可见,比兴手法可以服务于句句叙事,且给人以环环相扣、宛转相生之感。
明中叶后,许多有识之士在重新估价诗歌中的“情”与“事”关系时,进而把“述事”当成诗歌创作的重头戏。明代祝允明《姜公尚自别余乐说》曰 :“情从事生,事有向背,而心有爱憎,繇是欣戚形焉。事表而情里也”(祝允明36)。强调情感来自客观事物的刺激与亲身经验,事是表象,而情是内蕴。他的《送蔡子华还关中序》亦云 :“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尸居巩遁之人,虽口泰、华,而目不离檐栋,彼公私之憧憧,则寅燕酉越,川岳盈怀,境之生乎事也”(祝允明33)。认为艺术的境界是自身与外事相碰撞的产物,“境”由“事”而生。那个年代,王世贞也对乐府中情、事的关系给予了特别注意 :“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丁福保1015)。继而,李维桢更直接把事、理、情、景标举为诗文的四大要素 :“诗文大旨有四端,言事、言理、言情、言景,尽之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574)。把“事”列为四端之首。到了明末清初,钱谦益《牧斋初学集》论诗标举灵心、世运、学问,也要求诗歌能“属情藉事”。另外,据西方学者研究,清代王夫之、王士禛、贺贻孙、陈祚明、赵翼、法式善等诗论家也开始关注诗歌中叙事声音、叙事观点、人物刻划(characterization)以及史实(historicity)与虚构(fictionality)等一系列叙事问题。
在以往连绵不断地实践且重视“情事合一”论调的基础上,清代叶燮《原诗》明确提出了“理、事、情”三位一体的诗论思想 :“三者之中,‘事’条以贯之。物是事物,理是事理,情是事情。三者偏一,要么‘为文造情’,要么‘类乏浅切’,要么‘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在他看来,“事”起到了贯穿性的作用 :“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三者缺一,则不成物。”他甚至把“理”与“事”看得比“情”还重要 :“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叶燮20-30)。叶燮的诗论理论是对既往诗论的集大成式总结,也是对既往创作经验的概括。其关于“理”“事”“情”三者之关系及其得以发生的程序的阐发,为中国诗论一锤定音。
四、 意境 :“情”“事”互济诗论之聚焦
我们再从“情事合一”传统这一视角来审视一下“意境”或“境界”等中国最为重要的诗论观念。“意”偏于抒情,“境”偏于叙事,融情于景即为“有意境”,因而“意境”就是叙事抒情化合的结果,自然包含着叙事因素。
明人王世贞说 :“《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丁福保920)。意思是说,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诗歌,其文本形态就是主观抒情与客观叙事有机结合之典范。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曾将情、景、事三者纳入“境界”范畴审视 :“何以谓之有境界?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99)。在中国,直抒胸臆的纯粹抒情诗其实并不多。之所以谓之抒情诗,不过是大旨在借事抒情而已,其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叙情”,即现代意义上的叙事与抒情完美交融。其实,在古今中外诗歌中,叙事与抒情兼而有之是常态。当今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抒情诗的作品也存在值得探讨的叙事问题。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指出 :“叙事诗重述一个事件;而抒情诗则是努力要成为一个事件”(卡勒81)。德国学者彼得·霍恩《抒情诗歌的叙事学分析:16到20世纪英诗研究》已开始致力于探讨抒情诗歌的叙事问题。在中国,人们已经纷纷看到,“即使在许多抒情诗歌中,也存在蕴含的叙事成分”(艾布拉姆斯347)。长此以往,“情事合一”文本构成自成传统。
在中国传统诗歌文本创构中,由“感事而生情”形成的“情事之合一”的文本状态多有不同。有的诗歌属于即时感事,应景顺情,众所周知的代表作是汉魏曹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通过寓意象征,传达骨肉相残之情,事与情互为表里。有的诗歌发自感事伤情,亦含有叙事性。唐代杜牧的《叹花》这首情殇之作也仅四句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既赋物叙事,又比兴寄怀,用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女子过了花季,已结婚生子。在这若即若离、含蓄蕴藉的抒情背后,隐含着一桩伤心事。据晚唐人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载,杜牧早年曾游湖州,遇到一称心如意的美少女,便与其母亲约定十年内来娶。十四年后,杜牧做了湖州刺史,可那女子已嫁人生子。杜牧因逾期而失恋,感叹憾事,写成此诗。(高彦休244)中国传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果说,文化传统主要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实际生活形态的话,那么,文学传统则主要寄寓于文学文本之中,表现为文本形态。在中国传统中,抒情不可能纯粹地独立存在,虚体的情感要进入诗歌化或诗意化,必须依托于某些意象或事象,正所谓“诗者,持也”。中国传统诗歌的文本形态是“情事合一”,是由抒情、叙事化合而成的。抒情的基本策略是“融情于事”或“寓情于事”。中国传统诗歌文本主要是由叙事与抒情构成的,每一首诗歌的叙事与抒情含量比例并不固定,更非独立的存在,而大致处于化合状态。说到底,叙事、抒情均非目的,均为创造文本意义、艺术效果的手段。与抒情一样,诗歌的叙事功用和价值自不可小觑。抒情、叙事之间的博弈消长,情事合一的文本景观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
总体而言,基于叙事与抒情同谋互济创作实践,中国传统诗论由外在的“缘事而发”“感事而生情”诗歌生发,到“述事以寄情”文本生成,再到内在的“情事之合一”诗歌文本生态,形成一套本土化的“情”“事”互济理论体系 :“事”为手段、为前提,“情”为目的、为旨归。
注释[Notes]
① 从本源上讲,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非但没有否定叙事的存在,而且其本身兼含叙事意蕴。
② 韩经太“‘在事为诗’申论——对中国早期政治诗学现象的思想文化分析”,《中国文化研究》3(2000):95-104,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古典诗论研究始终在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框架下进行的,致使诗论被单极化,当下应认真关注“缘事”“在事”等诗学问题。殷学明“缘事诗学纂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2):713-18、“诗缘事辨”《北方论丛》5(2013):12-15、“中国缘事诗学发凡”《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5):143-48、“中国缘事诗评考辨”《文艺评论》4(2015):51-55等系列论文分别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缘事说”进行了发掘,指出“缘事说”的运作方式是缘事生理、缘事生事和缘事生情。周剑之则围绕“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这一课题,推出了《宋诗叙事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专著,以及“自我叙事:中国古代诗歌自传传统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12):113-20、“泛事观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国学学刊》1(2013):131-44等系列论文,也对诗歌叙事问题进行了阐发。
③ 学界关于乐府诗歌“叙事”之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游国恩等人就说 :“汉乐府民歌最大的、最基本的艺术特点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93。到了90年代,袁行霈又提出了新看法 :“‘缘事而发’常被解释为叙事性,这并不确切。‘缘事而发’是指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发为吟咏,是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事’是触发诗情的契机,诗可以把这事叙述出来,也可以不把这事叙述出来。‘缘事’和叙事并不是一回事。”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116。无论如何,乐府之叙事功能是客观存在的。
④ 有关17世纪中国诗论家对叙事的讨论,参见Schmidt,Harmouy Carden, 419-21;以及“袁枚和清代的叙事诗歌”,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37. 1(1999):3-6。⑤ 如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词对天上人间虚实并述,并探讨了人间悲欢离合哲理,就是将“理、事、情”融为一体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