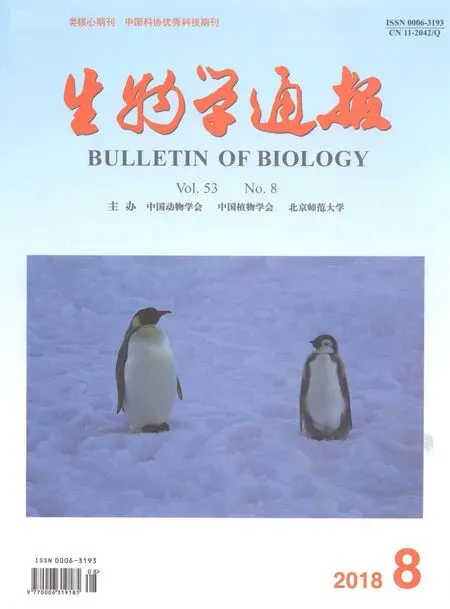毕生践行“手脑并用”的遗传学家李先闻
冯永康 (绵阳第一中学 四川绵阳 621000)

20世纪初期,当孟德尔(G.Mendel)定律被重新发现以后,美国科学家摩尔根(T.H.Morgan)与他的合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开始进行果蝇遗传学的一连串精彩实验。 他们以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揭开了遗传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与此同时,堪与摩尔根并驾齐驱的还有美国科学家埃默森(R.A.Emerson)在康奈尔大学率领的玉米遗传学研究团队,也取得了同样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 2 位遗传学大师携手,共同领跑着遗传学的突飞猛进。
在这期间,一批年轻的中华学人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远涉重洋,踏上了师从国际遗传学大师摩尔根或埃默森的漫漫求学路。 李先闻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1 跋涉求学路,躬行玉米田
1902年10月10日,重庆市江津县(原四川省江津县)登杆坡的一个普通农家降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李家“千里驹”,川人“好儿郎”的李先闻。
1906年,有“神童”之誉的李先闻便开始了求学生涯。 在得到自幼喜好读书、力求上进、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四叔李培癸的大力支持与热心鼓励下,1915年,经过连续2年的复考,在近500名考生参考只录取13 名情况下,他以第9 名的成绩,取得了四川省保送生名额的资格,进入北京清华预备学校继续求学。
1923年,李先闻以和邓叔群(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互争全年级前一二名的成绩,取得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和留美的资格。 随后,他便离开8 载相依的水木清华园,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远洋客轮,赴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园艺系深造。
1926年,李先闻获得普渡大学的学士学位,并考入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国际著名的玉米遗传学大师埃默森,攻读植物细胞遗传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玉米遗传学的创立和发展,集中在埃默森及其学生组成的康乃尔大学研究团队中。 作为埃默森唯一的中国弟子,李先闻与玉米遗传研究团队的10 多位师生,每年夏季都身着田间劳动的服装,满身携带一大堆授粉用的纸袋、小刀等用具,像农民一样活跃在实验田中,进行去雄、授粉、套袋等遗传育种程序的基本操作。
埃默森领导的玉米遗传学研究团队中的不少同行者,都逐渐成为国际上著名的遗传学家。 其中,不仅有与李先闻相处和谐,情谊最深的同学比德尔(G.W.Beadle),后因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学说而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有当时身为细胞遗传学讲师的麦克林托克(B.McClintock),1950年代初首先发现转座子,1983年独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外,还有曾任美国农业部首席玉米育种家的斯勃莱格(G.F.Sprague)等。 李先闻也于1968年列入美国出版的Who′s Who in the World of Science(历代世界科学名人录)之内。
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期间,设备优良的实验室、藏书甚丰的图书馆、 科学研究中的精诚合作及经常对科学问题开展热烈讨论的浓厚学术研究氛围,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中国学子李先闻。这里不仅有作为导师的埃默森,在担任植物育种系系主任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的繁忙事务中,仍然经常整天带着弟子一同下田劳作,从事着“手脑并用”的玉米遗传学研究; 也有当时作为讲师的麦克林托克,在田间实习时用小纸画画给李先闻做特别的讲解,格外关照。 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李先闻立志回国后营造同样的学术研究的智识气氛的信念,也为其之后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长达50年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
2 辗转南北地,潜心育粟禾
1929年,李先闻从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在离美回国前,他专程到加州果蝇实验室,拜访了遗传学大师摩尔根,再一次切身感受到美国遗传学家们勤恳工作的浓厚研究氛围。
当李先闻带着“再会吧,美国! 我要回去救中国了”的抱负回国后,面对着的却是当时国内局势的动荡与权利的倾轧,学界的派系与内讧导致的种种人事纷争,他感到手足无措。
在回国最初的两三年间,李先闻为寻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艰辛地奔波于南北各地。 得到其师长邹秉文、赵连芳、马约翰等人的帮助,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低聘至落聘为蚕桑系讲师,在东北大学被聘为短暂的植物学代理教授,在清华大学被聘为临时的体育教员,在北京大学农学院讲授过植物学课程。
直到1932年,在赵连芳的介绍下,李先闻才找到他当时认为的第1 个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前往河南大学农学院担任主讲遗传学课程的教授。然而短短的3年间,该学校内以无关学术的院长之争引起的人事波澜,小人离间造成的学人之间误解,又面临着分离瓦解的态势。在接到包有子弹的恐吓纸条后,他又不得不迅速逃离这个位于偏僻风沙之地开封的河南大学。
1935年8月,李先闻应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叶雅各之邀,前往参与农学系的筹建。武汉大学因此成为李先闻回国后真正施展遗传学研究才能的理想园地。
当时在学术界和大众眼中,赵连芳已经被誉为“水稻专家”,沈宗翰被誉为“小麦专家”。 作为留美专攻细胞遗传学归来的博士李先闻,却无法从事本行工作。经过几年的颠簸流离,李先闻选择以粟(小米)作为实验材料,开始进行遗传学理论与育种的系统研究。
在河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承担遗传学教学和十分繁忙的行政事务中,他与助手孟及人等一起,首先着手研究粟的开花习性。 白天每隔1 h,晚上每隔2 h,他就要到田间亲自去察看一次。 夜间是用马灯(桅灯)照明,观察计数花朵,并详细做记录。他还常常一个人下田,穿着短裤,水深没胫,冒着酷热气温、蚊子叮咬的困扰,进行水稻遗传育种的田间观察和选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先闻随武汉大学西迁,应聘进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接受杨允奎之约,他前往成都担任四川农业改进所食粮作物组主任,随后担任四川稻麦改良场场长。在长达9年的艰难岁月里,他与杨允奎、赵连芳等一起,头戴斗笠、脚穿草鞋,任劳任怨、合作无间,以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大后方四川省的粮食增产研究,以及水稻作业方面实施检定计划的工作中。
为选育检定稻麦良种,李先闻骑着 “洋马儿”,穿梭在成都静居寺和华西坝之间的小路上;为了向农民推广并种植稻麦良种,李先闻与他的同事,坐着俗称“飞毛腿”的洋车,探访川西北的乡间小镇。
在四川的9年间,李先闻虽主持并承担抗战大后方粮食增产的重任,工作异常艰辛与忙碌,但他仍然忘不了粟类作物进化理论的探索和作物良种的选育。 他以“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之心,尽一个学者的本分,一有时间就到简陋的实验室里指导李竞雄、 鲍文奎等进行粟类遗传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他们师徒多人同力共苦甘,做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仅在1941—1945年的短短几年间,李先闻和李竞雄、鲍文奎等主要用英文撰写多篇有关粟类遗传理论研究论文,大多数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上。
1946—1948年,李先闻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期间,继续进行植物遗传育种的研究。他与助手夏镇澳等先后重点开展了粟、小麦、甘蔗、玉米和有关种属的染色体与性状之间关系的多个课题研究,例如“小麦与狗尾草杂种的染色体变异”“小麦穗型的变化与遗传因子多寡的关系”等。 多年艰辛的研究,他们陆续积累了一整套小麦的单体、缺体和多体染色体的材料,以及粟与狗尾草有性杂种后代的各种株系等,为农作物遗传育种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 这些来之不易的珍贵材料,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然由夏镇澳继续进行一些回交、杂交和细胞学的观察实验,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然而最后终因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而荡然无存了。
1948年以后,李先闻与台湾糖业公司甘蔗研究所协作,开展了关于甘蔗的细胞遗传学和育种、栽培等实践问题的研究。 他经常同工作人员跑农场、下蔗田、看品种,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台湾省。他从区域试验中发现、 试验繁殖并加以推广了从南非引进的N:Co310 甘蔗优良品种,使计穷力竭的台湾糖业获得了新生。 台湾农民也由此称誉李先闻为“甘蔗之神”。
在从事繁忙的甘蔗改良工作之间隙,李先闻还能带着闲情逸致,计数甘蔗属植物中那样繁多(2n=60 及以上)而又很小的染色体,足以体现他对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的深深热爱和坚守执着。
1973年,李先闻因身体健康欠差的原因退休,但仍然不忘对同仁和学生不断地从旁鼓励与督导。1976年7月4日,他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5岁。
3 献身遗传业,学界留美名
从1929年到1949年,在20 余年转战南北的飘荡奔波中,李先闻始终没有澌灭自己的追求和向往。 无论是植物细胞遗传学的课堂教学还是农田的实验操作,他都特别注重将从导师埃默森那里学到的“手脑并用”的优良作风,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要求他的学生和助手们。 他尤其注重通过遗传学实验观察和遗传育种的具体实践,指导培养研究人才。据不完全统计,由李先闻直接培养并推荐出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子就达20 多人以上。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竞雄、鲍文奎及毕生从事农业高等教育的朱立宏等人,都是曾长期跟随李先闻学习并进行合作研究,取得杰出成就的著名遗传育种学家。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李先闻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事业的发生和发展,做了大量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1930—1940年的中国,战乱不息、动荡不宁,科学研究的条件得不到任何保证。李先闻先后到几所高等学校所做的遗传学实验研究工作,常不得不忍痛牺牲,另起炉灶。 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任何作物的改良,就以稻麦为例,最快也要五六年以上,这样时常地变换环境,如何能够出成绩? ”由此,他郑重地提出“守”字对于生物科学工作者的重要性。他以真正的身体力行,乐于担当“粗活”,使得其成功变得实实在在,足可体现出作为一个科学家品质的灼灼其华。
从1933年李先闻在美国的Journal Heredity杂志上发表中国遗传学家第1 篇关于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论文开始,在以后的40 多年间,他和他的助手先后撰写并发表了以粟类作物遗传育种为代表的100 多篇学术研究论文。
正是李先闻在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上所取得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在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第1 届院士选举中,他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共同推荐为院士候选人,并最后当选。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能得到学界推荐、社会推崇的“国士”称号,在当时那样一个政局动荡、派系林立的民国时期,也足以显现出李先闻在科学界中的重要地位。
1948年,国际遗传学会曾专门来函邀请李先闻前往瑞典参加第8 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因当时国内战乱不息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而未成行。 此后,他应邀参加了第9~11 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被当选为第11 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副主席。
李先闻的一生,为人坦诚直率,具有正义感,并乐于助人。 他与其助手、弟子几十年转战南北,融洽相处,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相责,成为终生的良师益友。抗战胜利之后,当李先闻从四川农业改进所,即将至上海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赴任时,所中全体同仁在送给他的签名纪念册中写道:“仓廪之实兮,公著丰功。 方正廉洁兮,两袖清风。 正思请益兮,行色何匆。 德业既展兮,永垂蜀中。 ”这段颂词,正是对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当之无愧的引路人李先闻奋斗人生的一个真实写照。
致谢: 得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夏镇澳研究员的热心指导;得到台湾义守大学张澔教授帮忙查找并邮寄有关李先闻照片、文字等资料,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