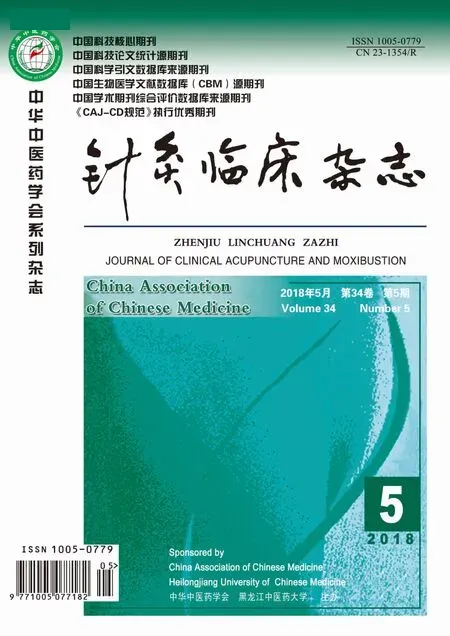经皮穴位电刺激改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踝背屈障碍的疗效观察*
王东岩,何 雷,宋 晶,张 蕊,杨海永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下肢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后遗症之一,1/3以上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3个月内无法进行独立行走,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1]。踝关节是步行的微调枢纽[2],正常的步行需要踝关节的参与。而脑卒中患者,踝关节背屈功能受限,摆动相时足尖离地困难,使患侧下肢膝关节及髋关节代偿性屈曲,降低了患者的步行稳定性,极大增加患者受伤的风险[3]。
目前针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踝背屈功能障碍,针灸、康复支具、手法训练及药物等治疗手段应用广泛[4],本研究采用的经皮穴位电刺激疗法,利用低频电流刺激腧穴周围,患者依从性高,改善脑卒中后踝背屈障碍者的步行能力,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针灸三病房收治的脑卒中后踝背屈障碍患者60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按患者就诊顺序将其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0例。如表1所示,对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病程)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制订的《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4)》[5]和《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14)》[6]。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脑卒中诊断标准的偏瘫患者;②首次发病,病程为2周至3个月,存在踝背屈障碍,且确为卒中所致;③年龄在30~65周岁;④病情稳定,意识清楚,MMSE≥24分;⑤患者能够独立步行10 m以上;⑥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①存在智力、沟通障碍,无法完成动作指令;②存在其他影响患者活动的疾病或状态(严重脏器损害、癌症、病情危重等);③患者存在皮肤破溃、对电刺激过敏、安装起搏器等情况,无法完成本研究的基本疗程;④存在其它影响患者步行的情况,如下肢骨折、周围神经损伤、脊髓疾病等。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针灸科常规治疗,参照我院针灸科中风病恢复期诊疗方案处理,包括针刺治疗、常规康复训练及药物对症治疗等(两组患者均未服用降肌张力药物)。
2.1 治疗组
治疗组用经皮穴位电刺激屈伸肌交替刺激方案,患者取良肢位(健侧卧位),治疗仪器选用本课题组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合作研制的第4代低频穴位电刺激治疗仪,采用规格为φ40×40 mm的导电极片,一组电极片连接患侧足三里(ST36)与阳陵泉(GB34),一组电极片连接患侧飞扬(BL58)与昆仑(BL60),采用50 Hz的断续波电流,两路电流交替发出刺激,使患者踝关节交替出现背屈、外翻及跖屈动作,每次20 min,每日1次,每周治疗6次,共治疗4周。
2.2 对照组
对照组用常规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方案,患者体位和治疗仪器同对照组,一组导电极片连接患侧足三里(ST36)与阳陵泉(GB34),电刺激的仪器、参数、疗程等同治疗组,刺激以患者出现踝关节的背屈、外翻动作为度。
3 疗效观察
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对患者进行1次评价,评价者为同一人,且对本试验设计不知情。
3.1 步态分析系统
本研究采用的步态分析系统为法国RM Informatique公司生产的Lab&Gait步态分析及训练系统,由摄像头、传感器及步行测力板等硬件组成,可在视频下同步观察患者的步行状态,对患者步行的时空参数进行精确而完整的测量。
本研究主要测量以下指标:(1)空间参数:①步速(cm/s):衡量步行能力最常用的指标;②步频(steps/min);反映患者步行的稳定性;③患侧步长(cm):步态最基本的空间描述符。(2)时间参数:①患侧单支撑相时间(%):以其占整个步态周期的百分比表示,能够衡量患肢的负重能力;②双支撑相时间(%):以其占整个步态周期的百分比表示,反映步态的时相分布及稳定性。
3.2 踝关节最大主动背屈角度
踝关节最大主动背屈角度能够反映患者踝背屈的功能[7],患者坐位,踝关节处于中立位,记录患者用力背屈踝关节时的最大角度,参考值为20°。
3.3 Fulg-Meyer运动功能评定量表(下肢)
用于评定下肢运动功能[8],下肢最高分34分,分数越高说明下肢的主动运动能力和分离运动能力越好。
3.4 统计学方法

3.5 治疗结果
3.5.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步行空间参数比较 由表2可见,两组患者治疗前步速、步频、患侧步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步速、步频、患侧步长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组间疗前疗后差值比较,步速、步频、患侧步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3.5.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步行时间参数比较 由表3可见,两组患者治疗前患侧单支撑相时间、双支撑相时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患侧单支撑相时间均较治疗前提高,双支撑相时间均较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组间疗前疗后差值比较,患侧单支撑相时间、双支撑相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表2 两组治疗前后步行空间参数比较

表3 两组治疗前后步行时间参数比较
3.5.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踝关节主动背屈活动度比较 由表4可见,两组患者治疗前踝关节最大主动背屈角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踝关节最大主动背屈角度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组间疗前疗后差值比较,踝关节最大主动背屈角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3.5.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下肢Fulg-Meyer评分比较 由表5可见,两组患者治疗前下肢Fulg-Meye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下肢Fulg-Meyer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组间疗前疗后差值比较,下肢Fulg-Meyer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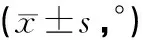
表4 两组踝关节最大主动背屈角度比较

表5 两组下肢Fulg-Meyer评分比较
4 讨论
踝背屈障碍在祖国医学中无明确记载,根据其症状,应属“痿躄”“痿证”的范畴[9]。现代医学认为,踝背屈肌群无力、小腿三头肌张力增高、踝关节的挛缩与疼痛是导致卒中后踝关节背屈障碍的主要原因。由于高级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小腿前外侧肌群麻痹,急性期后,低级中枢原始反射释放,小腿后侧肌群张力增高甚至挛缩,均可导致踝背屈障碍[10]。此外,肌肉、肌腱物理特性变化、制动废用因素也可导致踝关节背屈的受限[11-12]。
祖国医学认为经脉滞涩、筋肉失于濡养是本病的主要病机[13]。本研究治疗主穴为足三里、阳陵泉、昆仑和飞扬。足三里为胃经合穴、下合穴,是强壮要穴,能够濡润宗筋、濡养四肢,常用于下肢痿痹的治疗。阳陵泉为胆经合穴,八会穴之筋会。《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六十六穴治证》云:“阳陵泉为合土,在膝下一寸外廉,……治筋病,中风半身不遂,腰腿膝脚诸病。”其穴处腓骨长肌和腓骨短肌中,刺激该穴能有效对抗卒中后足踝内翻。昆仑、飞扬同属膀胱经,昆仑为本经经穴,飞扬为络穴,《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歌》曰:“昆仑足外踝,……举步行不得……。”《针灸大成》曰:“飞扬……步履不收……足指不能屈伸”。两穴均处跟腱周围,刺激时能够诱发自身抑制效应,降低小腿三头肌的张力。
经皮穴位电刺激在脑卒中后康复领域中应用广泛,通过刺激外周引起相应皮层兴奋,促进大脑重塑性改变,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14]。文献查阅发现,针对卒中偏瘫患者的踝背屈障碍,多针对踝背屈肌肉进行治疗,强调小腿后侧肌群的很少,而这与患者日常生活中对踝关节的需求是相悖的,正常的步行离不开小腿前后肌群的平衡。在本研究中,对照组单纯刺激踝背屈肌群,而治疗组采用屈伸交替的刺激方法,治疗时两路电流交替发出刺激,一组刺激足三里和阳陵泉,激活踝背屈肌腹内部肌梭的交互抑制反应,引起踝背屈肌肉的收缩和小腿后侧肌群的放松;另一组刺激昆仑与飞扬,激活分布于肌腱和肌腹连接处腱梭的自身抑制反应,抑制小腿三头肌的张力。如此交替刺激,不仅能改善踝背屈肌群的力量,还能够缓解小腿三头肌痉挛状态,恢复屈肌与伸肌间的平衡,最终改善患者的步行能力[15]。
本研究利用步态分析系统对患者步行能力进行全面、客观而精确的评估,此外还选取Fulg-Meyer评分(下肢)、踝关节主动活动度等指标,丰富了本研究的评价层次。本研究对脑卒中后踝背屈障碍患者进行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治疗4周后,患者的步行能力获得了明显的提升,步长的改善最为显著;其中,有部分患者步速无明显变化,步频在治疗后反而降低,分析后发现,此部分患者步长显著提升,步行的时相分布更加合理,笔者认为,在治疗前患者步频虽快,但步长小,脚步细碎,稳定性差,在治疗后步长获得明显改善,步频虽然减小,但时相分布趋于正常,行走状态更加稳健;治疗后治疗组各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屈伸肌交替的刺激方法优于常规刺激方法。
本研究的意义在与将屈伸交替刺激的方法应用到卒中后踝背屈障碍的治疗中,在交互抑制、自身抑制机制的参与下,踝关节反复进行背屈-休息-跖屈的过程,其相关的脑区被激活,促进了脑功能重组的过程,患者的步行能力明显改善。为了更加深入探索屈伸肌交替经皮穴位电刺激需要进一步完善试验方法,笔者未来将扩大样本量,力求展开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1] 李哲,范家宏,郭钢花,等.功能性电刺激恢复性治疗踏车对脑卒中早期患者下肢主动运动的影响[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17,32(6):667-672.
[2] 陈岚榕.脑卒中后踝关节功能障碍的临床治疗进展[J].福建中医药,2008,39(3):62-64.
[3] 周朝生,朱玉连.脑卒中患者踝关节运动控制障碍的研究进展[J].中国康复,2014,29(1):61-64.
[4] 荣积峰,吴毅,顾玲,等.脑卒中患者足下垂和足内翻康复研究进展[J].中国康复,2015(1):45-48.
[5]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4)[J].中华神经科杂志,2015,48(4):246-257.
[6]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14)[J].中华神经科杂志,2015,48(6):435-444.
[7] 诸毅晖.康复评定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3-22.
[8] Fugl-Meyer AR,Jääskö L,Leyman I,et al.The post-stroke hemiplegic patient.1.a method for evaluation of physical performance[J].Scand J Rehabil Med,1974,7(1):13-31.
[9] 陈希源,李雪青.巨刺丘墟透照海、昆仑透太溪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足下垂的随机对照研究[J].针灸临床杂志,2017,33(7):41-44.
[10] 祁玉军,沈娟.针刺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足下垂疗效观察[J].中国针灸,2016,36(7):679-682.
[11] 何圣三,张大炯,高世毅.针刺结合中药局部熏洗治疗卒中后足下垂内翻[J].吉林中医药,2017,37(5):524-527.
[12] Carr JH,Shepherd RB.A motor relearning programme for stroke[M].Oxford UK:Heinem ann medical Books,1987.
[13] 杜元灏,董勤.针灸治疗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67-68.
[14] 都天慧,屈云.经皮神经电刺激在脑卒中后患者治疗中的应用[J].华西医学,2016(6):1133-1136.
[15] 李尹娜.电针配合屈伸肌交替低频电剌激改善脑卒中后踝关节功能障碍的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3: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