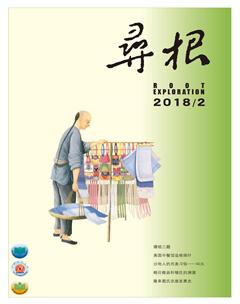《史记》中的『曲笔』
顾春军



班固评价司马迁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代的史学家刘知也说:“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司马迁著史的“实录”精神,历来为人所称道。但考察《史记》一书就会发现,司马迁之著述《史记》,固然多“直书”之笔,在采用“金匮石室”的档案材料,或者摘取已有的古史记载时,均有所选择,也即有“曲笔”之处。“曲笔”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雅驯”的追求。这种“曲笔”写作手法,固然使文本得以洁净,但往往使得一些历史真相被遮蔽,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带来了困难。
被遮蔽的“白登解围”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
这年冬天,刘邦率领的32万汉军被匈奴圍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一连七天七夜,这是汉代外交史上的一次巨大挫折,世称“平城之辱”。关于这次解围,《史记》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为:
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司马迁认为“其计秘,世莫得闻”,所以说不清。另一种解释为:
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
在这里,司马迁给出的解释是“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这就和历史上的“鸡鸣狗盗”有异曲同工之妙:“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史记·孟尝君列传》)其实,以贿赂的办法送上钱财,以和亲的名义送上女人,以缓和与匈奴的紧张关系,这在西汉前期基本就是常态。
从身份来看,司马迁先为掌管“金匮石室”的太史公,后又成为汉武帝近臣的中书令,而“白登之围”相去司马迁所处时代不远,他不可能不知道“其计秘”的具体内容,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西汉的另一位学者桓谭则以为:
或云:“陈平为高帝解平城之围,则言:‘其事,世莫得而闻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隐不传焉。子能权知斯事否?”吾应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刘子骏闻吾言,乃立称善焉。
从桓谭的记载来看,固然有推测的成分在内,但其讲述的内容也必有所本,而且从逻辑推理上来看,甚为符合“其计秘”,因为这种解释更为合理,之后被《白孔六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收入。
在汉高祖之时,国力尚弱,以小伎俩逃脱匈奴的围捕,乃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就手段来说,确实不能登大雅之堂。而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国力大为强盛,昔日的耻辱就演变为积极进攻的动力,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其心态必然发生改变。在司马迁看来,将这样的耻辱录入正史,无疑会损害西汉王朝的形象,所以,司马迁在著录白登之围的时候,就有意使用了“曲笔”,但是,史学家著史的实录精神又使得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不经意间露出了事实的原委。
被隐匿的“书之辱”
“白登之围”后,匈奴处于历史上的强势状态,到了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
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东征西讨,建立匈奴帝国。然而,与匈奴帝国的广阔地域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匈奴国家结构及其稳定性。较之历史上任何草原帝国,匈奴帝国延续的时间更为久远。匈奴帝国在最初的250年中,彻底统治着草原,而匈奴单于在超过5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原边疆事务中的主要政治参与者。
也就是说,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北部边境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但依靠着贿赂及“和亲”措施,西汉王朝统治者不断“示弱”,基本能和睦相处。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去世,3年后,骄横的冒顿单于写信给吕后,《史记》这样记载: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冒顿单于写信给吕太后,司马迁用了“妄言”一词,而将具体内容一笔带过,而“妄言”的内容则被《汉书》记录下来:
孝惠、高后时,冒顿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
在《汉书》中,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偾,仆也,犹言不能自立也。”顾炎武则认为:“《匈奴传》:‘孤偾之君。‘偾如《左传》‘张脉偾兴之‘偾。《仓公传》所谓‘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张脉偾兴”一词源于《左传·僖公十五年》:“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洪亮吉注释以为“血管之涨起者”。“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原文记述了济北王的侍女患病,内寒闭经,仓公诊断后说是“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韩兆琦解释为“想接近男子而不能实现”,钱钟书认为:
顾氏不欲明言,故借《仓公传》语示意,谓冒顿自称“孤偾”,乃“欲女子而不能得”,“有鳏夫见寡妇而欲娶之”耳。“所无”,“所有”亦秽语,指牝牡。
在这封书信中所言“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则是冒顿单于暗示吕太后性饥渴,几乎是赤裸裸的羞辱了。
35岁的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写道:“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受制于物质供给的不足和医学的落后,古人的健康状况远远不如现代人。冒顿单于写这封信的时候,按照中国传统的算法,吕后已是50岁知天命之年了,即使保养得好,吕后至多是“风韵犹在”。冒顿单于不会不知道吕后的“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这样的秽语,完全是有恃无恐的侮辱。
接到书信后,“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这种羞辱就化成一种“愤恨”的符号,直到东汉依旧被汉人念念不忘:
敞上疏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嫚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还忿,舍而不诛。”
對于这起“涉外事件”的“书之辱”,司马迁又一次录之以曲笔,如果没有班固的记载,后人就难以明白冒顿单于“妄言”了什么。
司马迁绍续《春秋》的“秉笔直书”
秦宣太后是秦始皇的高祖母,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秦宣太后秉政四十一年,为秦国统一六国、开土拓边,立下了汗马功劳,近人马非百这样评价说:
宣太后以母后之尊,为国家歼除顽寇,不惜牺牲色相,与义渠戎王私通生子,谋之达三十余年之久,始将此二百年来为秦人腹心大患之敌国巨魁手刃于宫廷之中,衽席之上,然后乘势出兵,一举灭之,收其地为郡县,使秦人得以一意东向,无复后顾之忧。此其功岂在张仪、司马错攻取巴蜀下哉!
但在《史记》中关于秦宣太后的记载只有两条:
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战国策》一书中有很多关于秦宣太后的材料,有一条材料关系到战国时期合纵与连横的走向,而这条重要的材料则没有被《史记》收录: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崤。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崤。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对于这段语涉秽的段子,清朝学者王士评价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战国策》是司马迁著录《史记》的重要的史料来源: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秦汉史是《史记》记述的重头戏,秦宣太后距离司马迁已经久远,秦王朝又是汉人眼中的“伪朝”,这就丝毫没有避讳的必要,而本条材料又很重要,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把秦宣太后的这段话记入呢?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忽略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史学观点,那就是对“雅驯”的追求: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所谓的“不雅驯”,很多学者将其解释为“荒诞、不正经”,其实,就荒诞不经来说,《史记》中的记录可以说比比皆是,后人也多予以批评:
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坠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学者们往往忽视了“雅驯”的另一面,那就是司马迁对秽的“厌恶”。正因为司马迁对史料“雅驯”的自觉追求,也就有了对淫秽史料的自觉“屏蔽”。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所以不能明白指出司马迁对史料取舍的标准所在。
司马迁以孔子“自诩”,自认为来到世上,就是续接孔子,完成孔子未竟的事业: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所以,在《史记》的记述上,司马迁是以孔子著《春秋》为撰写准则的: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孔子撰写《春秋》是以维护“君君、臣臣”的统治秩序为准则,故在书写体例上,就本着惩恶扬善的“实录”精神,从而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所以,即使对于西汉创始者的汉高祖刘邦,司马迁也“不隐恶”,直书其不光彩的一面:
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在逃亡路途,为了活路,刘邦不惜把亲生儿女推下车;为了争夺权力,对项羽则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刘邦无赖流氓的一面尽显,这就体现了司马迁“直书无隐”的实录精神。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刘邦无赖的一面没有记录到其本纪中,而是在《项羽本纪》中记述,既是“直书”,也有“曲笔”的一面,也就是为“尊者讳”,在这个记录上,是采取了折中的手段。
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但有大量的“直书”实录,更有“曲笔”,就司马迁的学习榜样《春秋》一书来说,其“春秋笔法”不但有讓“乱臣贼子惧”的一面,也有为尊者讳的一面,但人们往往强调司马迁直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曲笔的另一面。在理性认识上,司马迁认为: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对隐公、桓公时代的事情述说得详细,对于定公、哀公时代的事情述说得模糊,这是因为时代太靠近,不能如实褒贬,有很多忌讳。而事实也证明了司马迁所言不虚:《史记》成书之后,有10篇或篇目缺失,或文有遗漏,与班固同时的学者就以为这是秉笔直书被“禁毁”所致:
东莱吕氏曰:“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其二曰《武纪》十篇,唯此篇亡。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与班固同时,是时两纪俱亡。今《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纪》终不见者,岂非指切尤其,虽民间亦畏祸,而不敢藏乎?”
无论从现实的政治形势来看,还是从司马迁史学思想来看,落实到著述的实践中,就必然会有遮蔽与忌讳:
又如冒顿遗吕后书至秽亵,《史记》不载,为本朝讳也。班书则缕述之,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其无识更甚。迁之优于固, 岂特在文字间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五)
司马迁使用曲笔记录“言之辱”,而班固则直书其事,在赵翼看来,那就是司马迁比班固更有史识的表现。赵翼没有进一步指出司马迁为什么书以“曲笔”。考校史实,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直书吕太后阴鸷的一面:对戚夫人及刘氏子弟的残害,对孙辈的刻薄无情;再从血统来分析,汉武帝是汉文帝的孙子,而文帝是薄太后所生,薄太后和汉文帝靠着韬光养晦才躲过了吕太后的杀戮,所以说,司马迁没有理由去为吕太后避讳。近人朱东润在其《汉书考索》中从另一个视角分析这个问题,能给人很多启示:
因为中国已经抬头,并且进一步使匈奴对中国称臣。这是一件天翻地覆、值得夸耀的事。在胜利到来的时候,追溯到以往曾经受过如何的屈辱,愈加感到一种欣慰……在那一次战役里,班固身与其事,眼看到敌人的崩溃,所以他感到极大的愉快,更觉得应当把司马迁讳去的史料重新写出。
那么,刘邦贿赂阏氏,而司马迁秉笔不书,也可以找到答案:作为一个受儒学浸染的史学家,司马迁必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用传统的话讲,就是坚持“尊王攘夷”,用“曲笔”把汉民族的屈辱遮掩起来,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找到答案。
(题图:《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