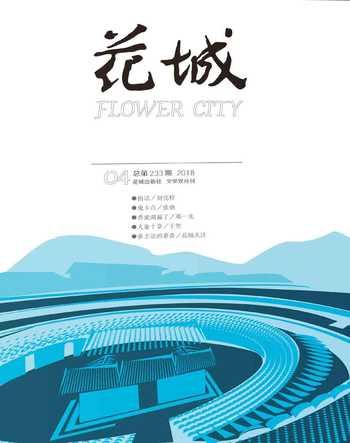萨博·玛格达:能扫描灵魂的人
我——写这本书的人,只要有可能避免,我就不会去读它:我怕它。
——萨博·玛格达
1
小国大文化,这样形容国土和人口都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的匈牙利最为真确。且放下裴多菲、尤若夫·阿蒂拉等大诗人不说,匈牙利当代的世界级作家就很多,保守地讲,不下十位。如果说读书有性别偏向的话,那么我更偏爱匈牙利男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文字里有阴柔的,比如我翻译过的马洛伊、凯尔泰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艾斯特哈兹、纳道什和巴尔提斯,基本都属于这一类;当然,这不等于说没有我喜欢的女作家,只是较少,在匈牙利女作家中我能够不假思索说出的只有两位:写《恶童日记》的克里斯多夫·雅歌塔,再有就是《鹿》这本书的作者萨博·玛格达。为什么喜欢?因为她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字里头有阳刚。前一位主要用法语写作,我无缘翻译,因此后者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对中国读者来说,萨博·玛格达,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在国际书坛,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享盛誉,不要说西方,日语、越南语和蒙古语的译本也早就问世。就在三年前,她八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门》在美国再版,再度引发关注,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说明读者的阅读热情至今未减。几十年来,她在匈牙利作家里始终是作品翻译版本最多的一位,如列名单,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和马洛伊都排在她之后。
那么,我该怎么介绍这样一位对中国读者来说陌生的女作家?我想打个简单、大概的比方帮读者定位:萨博·玛格达,有点像女版的马洛伊。当然,我指的“像”并非在作品主题、思想和深度上,毕竟两位作家的家族历史、性别视角、生长环境和个人阅历都截然不同;但即便这样,从两人作品的怀旧情调、文字的细腻程度、结构的复杂精致、对主人公心理的深潜、处理冲突的戏剧化手法以及作品的多样与多产来看,仍有很多的可比之处。马洛伊生于一九○○年,比萨博年长十七岁,基本属于同时代人,马洛伊八十九岁自杀,萨博九十岁病逝,他俩经历了同样大的动荡和同样久的坎坷,而且两位作家都是活到老,写到老,追求艺术层面的文学。再有,就是两个人骨子里的自由、孤傲和坚强,尽管由于活在两个被铁幕分割的世界里,表现的方式互不相同。具体到《鹿》这本书,它在萨博诸多作品中的地位,相当于马洛伊作品中的《烛烬》,这两本书都属于各自的早期作品,都写得深情,入骨,炫技。
有一次,萨博在采访中这样说:“我——写这本书的人,只要有可能避免,我就不会去读它:我怕它。”为什么怕?她怕什么?我想,是因为写得太狠了。
《鹿》里的女主人公恩契·艾丝特生长在帝国瓦解后的平原小城,家境从中产向无产滑落,她拥有一个那样艰涩、痛楚的青少年时代,家族遗传给她的尊严、贫穷导致的自卑和强烈自尊心磨砺出的争强好胜,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内心矛盾地搅缠,她对原属阶层的背叛和被渴望加入的阶层的残酷拒绝打磨出她深埋的敌意,战争的恐怖和社会变迁的无常都在她的记忆深处投下阴影,即使成功和爱情也无法拯救,怀疑和嫉恨的黑色旋涡不断将她朝毁灭的方向冲卷。
2
萨博·玛格达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五日出生在匈牙利东部大平原上的德布勒森市,父亲萨博·艾莱克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市政府官员,母亲雅布伦采伊·兰凯是一名普普通通女教师。按照匈牙利人“姓在先,名在后”的习惯,萨博是她的家姓。萨博是典型的匈牙利姓氏,匈牙利人姓萨博的很多,匈牙利语是“裁缝”的意思,估计他们很早的祖先从事过裁缝职业。
萨博·玛格达很爱自己的父母,这种爱和尊崇持续她的一生。后来她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她说:“小的时候,我被父母教养成一个意志极强、心性自由的孩子。我是两个被培养成了囚徒之人的女儿。我父亲从来不能做任何实现自己欲求的事。他从一个理想的家庭进到一个现实的家庭。早在他的第一次婚姻里他就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父母这样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让孩子自由。她可以说不,可以反抗,可以自己选择。让她决定。那是她的生活。那是她不可重復的生活。”
她的母亲虽命运坎坷,但情感丰富,挚爱文学,女人在琐碎而艰难的日常生活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秘密、敏感的情感世界,写了许多从未发表过的文学作品,没有读者,她会把自己写的故事读给女儿听。父亲喜欢拉丁语,钟爱古典世界,喜欢给女儿讲神话故事。“我是两个天使的女儿。”萨博还说。父母的修养和文学情结对玛格达的影响非常大,后来,她不仅也学了拉丁语,还致力于建造自己的文学世界,并在作品里让过去,让家乡、家庭、前辈和记忆,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她的成名作《鹿》里,自身家庭背景的浸透尤为明显:女主人公恩契·艾丝特的父亲身为律师,却与世无争,沉溺于自己的花草世界,母亲撑起持家的重担,但用钢琴、音乐为自己打造出一个精神避难所。艾丝特的拉丁语很好,而且也会弹钢琴,心性自由、倔强,对世界充满自己的怀疑、判断和抵抗,艾丝特深爱父母,但又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感觉自己像个孤儿。当然,小说不是传记,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摸到创作的基石。
萨博·玛格达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德布勒森度过的,毕业于当地新教的寄宿学校——杜茨中学,之后在德布勒森大学攻读拉丁语和匈牙利语专业,学习勤奋,成绩优秀;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女子学校教书,同时攻读教育与文学博士学位。所以,她的早期重要记忆都与德布勒森有关,这座城市为她后来的多部作品提供了背景或舞台。德布勒森虽然是十三世纪就有史料记载的城市,十六世纪已发展成重要的商业城镇,十七世纪被利奥波德一世定为“帝国自由城市”,但是相对首都布达佩斯来讲,它还是一个“外地小城”。一九四四年八月,城市在二战末遭受空袭轰炸,大半座城市沦为废墟,这些在《鹿》里都有描写,想来女作家亲历了这些恐怖和苦难。玛格达在晚年的时候经常返回家乡,有时候,她一年里在家乡和在布达佩斯居住的时间对半平分。
一九四五年,拿到博士学位后的萨博离开了家乡,搬到首都布达佩斯,受聘于政府的宗教与公共教育部,在负责电影、文学领域的管理部门做公务员。由于她聪颖能干,而且显露出文学的天赋,很快受到时任国务秘书的作家、诗人博考·拉斯洛的赏识,请她任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萨博·玛格达最初的文学梦想是当一位诗人,她的早期诗作大多发表在《匈牙利人》和追随西欧文学步伐的《新月》杂志上。一九四七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羊羔》,并与诗人、作家、史学家索伯特卡·迪波尔结婚,那年她四十岁;一九四九年,她的第二部诗集《回到人》刚一问世,就获得好评,被授予当时匈牙利最重要的文学奖——鲍姆伽滕奖。
一九五七年,萨博·玛格达像试水一样地先出了一本给孩子看的童话诗《谁住在哪儿》,随后写了一本青少年小说《告诉若菲卡吧》。之后的两年,是她文学生涯的重要年份,她在继续出版儿童读物的同时,先后推出两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壁画》(1958)和《鹿》(1959),可以说一鸣惊人。从那之后,她辞掉了工作,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谋生。
3
《壁画》是萨博·玛格达的长篇处女作,标志着她由诗人向小说家的转型;《鹿》则是她命运的重要作品,它的问世,对于当时喑哑了多年的匈牙利文坛来说,用“炸弹”来形容也不夸张。对女作家来说尤其幸运的是,德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偶然读到了《鹿》,极为赞赏,大概在一九六○年,黑塞将这位对西方来说全然陌生的匈牙利女作家推荐给了因赛尔出版社,由此迅速传到了西方,译成多种语言。我说她幸运,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时黑塞已经搁笔十几年,就在推荐了萨博之后不到两年,就死于脑溢血。假如萨博被晚解禁两年或这本书晚写两年,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命运。
《鹿》为女作家打开了世界的大门,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鹿》已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在之后的半个世纪,无论冷战中还是冷战后,“萨博·玛格达”都是匈牙利文学的一张国际名片。《鹿》让国际媒体一下子记住了她这个地道的匈牙利名字和卓尔不群的知性美貌,当年有西方媒体是这样推介《鹿》的:“……在故事中的凶手们和受害者们继续他们的生活的同时,令人同情的冷暖激情熊熊燃烧。”
在当时,《鹿》是一部文学实验性很强的先锋作品,以第一人称叙事;不仅叙事,更叙内心。她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讲述一个女人的特殊命运,最重要的是,她把个体的命运放到了社会大命运之中(注意,不是背景下!)无情地剖解,难怪有评论家称之为“社会心理小说”。当然,在萨博·玛格达之前,乔伊斯和马洛伊都是运用现代意识流的内心独白写作的大师,马洛伊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就是一个出色的范本,用四重奏的内心独白讲述大历史下个体的精神生存,但萨博另辟蹊径,一是发挥女性作家的特殊视角,二是结合了多种小说的元素。我读《鹿》,既感觉在读一部女性成长小说、爱情小说、家族小说,更感觉像读一部犯罪小说、推理小说,整个阅读过程撕心裂肺,心惊肉跳。很过瘾,而且,这种过瘾不受阅读者性别经验的影响,因为作家透视到了人的灵魂深处,不仅透视到了,而且像核磁共振检查一样从横断面、矢状面、冠状面和各种斜面,精准地将灵魂扫描了下来,记录了下来。
小说中的庞大独白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不是日记,而是在很短的时间从女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喷涌出来的。我并不想剧透,只将原书的匈牙利语内容简介翻译过来贴在这里,吊一下胃口:“《鹿》是一部凶手与受害者的小说。三个轻骑兵小酒馆的老板尤若行凶了,故事主人公、女演员恩契·艾丝特行凶了:各自都以自己的手段。但在两个凶手背后还潜伏着第三个最危险的凶手: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女演员出生并度过了令她窒息的青少年时代,那个时代将埃米尔送到了雷区,将她没有工作能力、养花爱草的父亲过早送到了坟墓里,永远毁灭了恩契·艾丝特的信仰、信心和快乐的能力。她从生活手中得到的一切都来得太晚:无论金钱,还是爱情,都无法让她摆脱那个令人生厌的可怕自我。恩契·艾丝特从她所生活的并受之教养的社会里学到了杀人:杀了唯一爱她的人,从而也为自己宣判了死刑。”
文学批评家扎裴·拉斯洛这样评论:“不管谁说什么,作品都无疑涉及了作家本人,这是萨博·玛格达的小说。《鹿》讲的是关于嫉妒的故事。但那不是简单、日常、普通人的嫉妒,而是浓缩了的、升级了的、发展到极致了的嫉妒,可以这么讲,是艺术化的嫉妒,所以极其灼烫,在这个故事里,更准确地说是地狱的炼火……毫无疑问,《鹿》是一部极度渲染、极度工细、极度缜密、极度设计的作品,其艺术性显而易见。”
4
萨博·玛格达是一位创作力旺盛的作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总共出版了作品五十多部,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广播剧、随想、自传体小说、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体裁,她有十一部小说被改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中有多部电影的剧本由她亲自撰写。在她的众多作品里,除了《壁画》和《鹿》这两部成名作之外,还值得推介另一部代表作——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门》。
《门》通过一位女作家的眼睛讲述了一位善良、古怪的——用现在的话说,有“反社会人格”的——女邻居艾梅兰茨不幸的遭遇,再次表现出作者对女人命运的深度关注与理解。据萨博自己讲,这部小说是有生活原型的。或许在萨博的小说里,《门》是读者人性的冲击力最大的一部作品,也是讲人与人关系最深刻的一部,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二○○三年获得法国著名的费米娜外国小说奖;《门》先后两次被译成英文,第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在美国出版,第二次是二○○五年在英国出版,第二个译本获得二○○六年度的牛津-韦登菲尔德翻译奖,又过了十年,这个译本在美国再版,很快成为当年的畅销小说,《纽约时报》发现了一枚被遗忘的珍珠,将《门》评为二○一五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美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克莱尔·梅苏德在《纽约时报》经典书评中撰文说:“假如你自信你对文学的风景十分了解,那么《門》将促使你重新思考……萨博小说的人物命运和场景突然地占据我的脑海,萦回不散,带着他们强烈的情感。它改变了我对我所拥有的生命的理解。”二○一二年,匈牙利导演、奥斯卡奖得主萨博·伊什特万将《门》改拍成同名电影,《门》还被搬上过戏剧舞台。
另外,女作家的三部自传体小说《古井》(1970)、《旧事》(1977)和《致爱丽丝》(2002)也很值得读,不仅用工细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和父母的童年时代,还再现了二十世纪初的德布勒森,就像马洛伊·山多尔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描述他的家乡考绍和家族过去一样,她也用文字将逝去的“过去”变成恒在的“经典”。虽然多产,但据她自己说,她的写作并不容易,有的书写了七遍。无论多么成功,她都不放弃勤奋。
有一次,玛格达又回忆起母亲说:“我想非常简单地告诉你们,当时我从我母亲那里学到了什么:那是一个星期一,从那天或这天开始,我就毁灭了。我母亲看着我,只是看着我,说:我的小闺女,今天是星期一,之后是星期二。但你不会认为,星期二跟星期一有什么关系吧?风也会转向。一个人总会有一点忧伤。如果不为自己,也会为别人。但你要相信生活。你不会没有缘由地得到什么。”她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依靠自己,不依靠任何人,学到了应该自信、自由地主动掌握命运,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秘诀就是:勤奋。她即使快九十岁了,也常爱说一句狠话:“我诅咒所有妨碍我工作的人!”
萨博·玛格达获奖很多,从鲍姆伽滕奖(1949),两届尤若夫·阿蒂拉奖(1959,1972),到实至名归的国家最高奖——科舒特奖(1978),之后还有布达佩斯城市贡献奖(1983),戴利·迪波尔奖(1996),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1997),塞朴·埃尔诺奖金(1998),匈牙利科尔文金链(2003),贡德尔艺术奖、最佳艺术奖和法国费米娜文学奖(2003),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获得了祖国奖和匈牙利共和国大十字勋章(2007)。此外,她还是德布勒森和布达佩斯两市的荣誉市民,德布勒森新教神学大学和米什科尔茨大学的荣誉博士。九十年代,她还是匈牙利塞切尼文学与艺术学院和电子文学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九十岁高龄的女作家在家中逝去。据家人讲,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看书。死后,她终于在墓穴里跟比她先走了二十年的丈夫重又厮守。
我想,花城出版社的“蓝色东欧”系列能够首次推出萨博·玛格达,是送给中国读者的又一份厚礼。前面讲了,女作家曾说过自己“怕读”自己写的这本书,那句话里隐藏了许多层次的意味。我在读完又译完这本书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译者郑重推荐:每位有缘拿起这本书或听说了这本书的文学朋友,都应该一口气把它读完。
巴拉顿弗莱德,匈牙利翻译之家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本文是长篇小说《鹿》的中译本前言,收入书中时有删节。《鹿》(萨博·玛格达著,余泽民译),花城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