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少年班:像天才的普通人
王珊

中国科大即将毕业的学生
开学时的告诫:拒绝媒体采访
第一次见周天翼和张载熙,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第一教学楼门口的马路上。张载熙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短袖,背着一个灰绿色的书包,鼻子上搭着一副板板正正的黑框眼镜,反而凸显了他的稚气。他的旁边站着周天翼,比张载熙矮一些瘦一些,眼睛细长明亮,看得出来是个有灵气的小伙子。他有些瘦,灰色的上衣在他身上晃晃荡荡的。两人都是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大三的学生,今年都是20岁。
见他俩前,我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少年班的学生到底有哪些特质,是外界说的全部是天才吗?我觉得说服不了自己。作为一个跟他们就读于同样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我跟少年班的孩子也有过许多交集,一起踢过球、做过暑期实践,除了觉得他们聪明和有韧劲外,我没觉得他们长了三头六臂啊!但我也会想,会不会因为我在学校的环境下待了太久,所以很多东西都理所当然了呢。我的观察就从周天翼和张载熙开始了。
那天刚刚下过雨,地面上有些潮湿,空气里也弥漫着淡淡的水汽。两旁高高的法国梧桐树舒展着长长的枝干,将整条道路包裹起来,光线从缝隙中一打一打地冲出来,可以看到它们柔和的棱角。正是上课的时间,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周天翼和张载熙安静地站在一棵树下,像是环境里天成的一部分,说话都是慢条斯理、声音小小的。第一眼看下来,他们和我认识的学校其他学生,并无两样。
面对我这个陌生人,两人有些拘谨腼腆,但很坦诚。我问他们:“你们觉得少年班的学生跟学校学生有什么不同吗?”周天翼挠了下头,只想到了一点,“可能(学校给的)资源更好一些,你看新寝室建好后,我们少年班学院2015级就搬了进来,但其他院系只有一年级搬到新校区。我们少年班的楼有基金会捐赠。”
这点是比较明显的。在学校,少年班学生基础好,学校为了满足这些精英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更优越的教育资源。比如,全国教学名师向守平几十年來一直承担少年班大一基础物理教学。向守平的理论是,不能只给孩子传授知识,要帮学生仔细梳理科学体系的源流。一定要他们知道科学的源头在哪里,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在科学的源头上。此外,中国科大的传统是,大一一整年,学校全部要进行通识教育,所有学生都要学习物理、数学,如果是非物理、数学专业的学生,在教材难度上一般会低于物理、数学专业的难度,但少年班学生要与这两个专业学生保持同样的学习难度。
摄影记者打起了灯,跟两人聊拍照的要求,并商量选景。他俩并不是十分清楚我们的意图。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想做一个关于少年班的报道,希望展现少年班平常生活和学习的模样。听完,张载熙说:“那我们能否站在自行车前拍?我们平常就是这么去上课的。”他随手拉过旁边的一辆自行车,倚在车旁,他有些紧张,看起来像只等待摄影记者摆布的小木偶一样。他不喜欢拍照,平常家人聚会拍照、同学合影,他都会悄悄站在角落里,“当然,也不会躲到看不见的地方”。
对于二人来说,这是班主任交代下来的任务,所以要尽量配合我们。这是他们第一次与媒体打交道,入学的时候,从少年班学院院长到班主任都告诉他们,在大四之前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都听了进去。刚入学做开学教育时,院里既给他们介绍了张亚勤、庄小威、郭元林等一些在科学界、企业界耳熟能详的校友,也向他们讲述了极少数人被媒体“捧杀”的故事,希望他们能够引以为戒。

宁铂(右一)和同学在下围棋
不准私自接受采访的规定是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院长陈旸确立的,就连院楼的门卫保安都知道这个事情。每次,当有陌生的面孔试图穿过大门进入少年班学院,都会被他们截住详细询问。所以,每次走进少年班学院的大楼,我都会老老实实跑到门卫那去登记。陈旸告诉我:“少年班的学生都是孩子,承受不起这种吹捧,这个年龄的小孩,一旦抬起来,他们会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很难沉得下去,所谓的‘捧杀就是这个意思。”
一直以来,宁铂被外界视作“捧杀”的典型。中国科大少年班成立于1978年,它的背后是整个国家被压抑十几年的科学热忱。当时,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人才奇缺。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1974年,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被国家主席毛泽东接见的时候,当面建议毛泽东参考中国体育对运动员从小培养的模式成立大学少年班,对中国的少年天才进行科学培养。此时,国际上也早有对智力超常少年培养的先例。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专门设立了“特科学校”,对天赋异秉的青少年施以特殊训练;美国1973年通过的《天才教育法》,目的也正是为天才教育提供物力、人力和法律保障。
1977年,邓小平发表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号召要“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最终促使了这项实践。宁铂的一个长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从广播中完整地收听了邓小平讲话,他心想,“宁铂不就是国家要找的人嘛?”在他的眼中,宁铂就是“天才”二字的具体呈现:2岁就能背诵30首现代诗词,4岁识别400个汉字,5岁读小学,8岁已经会开中药药方,不到13岁就通过了1977年的高考。
倪霖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推荐了宁铂。方毅将此信转给中科院的下属单位中国科大,上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信才寄出去10天,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老师就抵达江西,到宁铂就读的学校面试。通过对宁铂的文学、数学、中医甚至围棋等方面的全面考查,他们得出结论,“宁铂的确很优秀”。随后,宁铂被中科大破格录取。宁铂被录取后,开始有人不断地效仿倪霖给中科院和中国科技大学写信,向他们推荐更多早慧的儿童。中国科大少年班由此成立。
整个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和渴求使得少年班的關注度达到了高峰,少年班成了“天才”和“神童”的代名词。宁铂当时的同学王永现在是中国科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他还记得,在他面试的时候,除了有科大的老师外,还有两名新华社的记者在场。他告诉我,曾经有个记者采访时问他和同学,“你们班同学都是班级前几名吧?”“我们中没有哪个人不是年级第一名的。”王永说。同学里从山西过来的几个人,囊括了山西省数学竞赛的前三名,而他自己,也一直是年级第一,第二名的同学因为一直无法超越他而被永远称为“二将”。
宁铂的同班同学张亚勤现在是百度总裁,他就是看了宁铂的宣传,下了去读少年班的决心。他还记得入学后校园里到处都是记者。他告诉我,当时他与母亲说起过这个情况。母亲听了后,反复告诫张亚勤,要婉言谢绝记者的采访。“你只是个普通的孩子,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神童。被记者过多报道,别人谈论,只会给你带来压力,不利于你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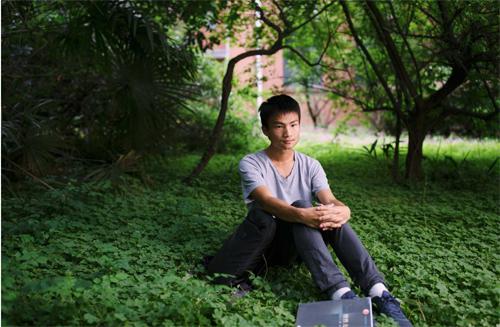
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学生周天翼
张亚勤母亲的话在宁铂身上应验了。宁铂开始变得自大。一名当初教过宁铂的老师向我回忆了一件往事。当时,数学大师张广厚到学校来做报告,跟少年班的孩子见面,“其他的小孩都跑去找张广厚签名,只有宁铂没去。他对张广厚不认识他很气愤,我说了一句‘宁铂别这样,但他根本听不下去”。
“当时外界也都认为我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没有人说你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孩子,你应该做个正常的人。”2016年,我曾在杭州见到宁铂,他自学了心理学,还考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他对自己进行了剖析,他说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对他的要求是“七步成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觉得自己是“不同于常人的”。他甚至开始克制自己的想法去迎合“神童”的定位。有不少媒体在采访的时候,说个病症,要求宁铂开个中药方子,他也照做了。
这一切,最终使宁铂觉得痛苦,后来,为了继续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在选专业的时候,他放弃了感兴趣的天文学,选了被认为智商高的人才能学习的物理专业。他写信告诉父母自己的纠结,回信却让他万分失望。父母并告诉他“不要随便猜疑他人”“不要感情用事”“国家和学校对你都是负责任的”。“他们也更愿意接受媒体所塑造的那个宁铂,不接受也不允许我身上出现什么与那个榜样看起来不相同的地方。”
宁铂的同学也慢慢发现,他的脾气开始变得很怪。比如,他把自己理成了光头,拍合影的时候总是最后一个出现,喜欢站在最角落里,脑袋还要躲在别人的后面。他也不喜欢打桥牌了。曾有同学问他原因,他的解释是:“这样我就不用被送到北京去陪人打桥牌了。”宁铂还曾经对一个爱好围棋的同学评论过与其下棋的人:“那些棋技并不高超的人要求和我下,他们不在乎我的技术,只在乎我的名声。”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压抑许久的宁铂开始公开批评中国的“神童”教育。他不断地向媒体和世人反复强调:“我不是什么‘神童,媒体上关于我的说法都是胡编出来的。”在一期广为流传的《评说神童》的电视对话栏目里,身着蓝色上衣的宁铂坐在嘉宾席的最右边,情绪激动,不时打断主持人和其他嘉宾的讲话,插入自己的观点:“那会害死人的!”“这不是做生意!”“不能拿他们做实验!”……不过,嘉宾和观众并不在意宁铂说了什么,他们眼神里对这个“伤仲永”般的人物充满了同情和戏谑。
2002年,宁铂出家,这次,少年班集聚的镜头并不比高峰时少,媒体们更加确定了“宁铂是‘神童教育失败的典型”“落魄到要出家”,而少年班更是“神童集中营”。40年内,讨论一波波地袭来,且似乎没有终止的苗头。到现在,还有人将少年班的教育称之为“拔苗计划”。
多年后,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也在反思整件事情。“那时不停地有媒体找来,孩子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念书。那时的精神就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你不可能对抗中央的精神吧。”一名退休的负责教学任务的教师告诉我,“对少年班的宣传已经变成了一股潮流,潮流来了,挡也挡不住。”
后来,他们想了很多方法拒绝媒体,但总是有人能想方设法找到少年班的学生,寻找一些“穿毛衣弄错了前后”“回答不上同学的问题哭上半天”的谈资,发在报纸或者杂志上。“每个时代都有偶像和榜样。以前有人质疑少年班的价值,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就是我们鼓舞了一代人,成为‘树雄心立壮志,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典型。”中国科大生命学院教授周逸峰在回忆时如此表示。

张载熙(右一)和同学在寝室娱乐,他很喜欢弹吉他
认可努力,不夸聪明
“你是不是那个中国少年科技大学的?”2009年,陈旸出任少年班学院院长,任职近10年,每当他介绍自己身份时,都会被问上这么一句。“对,我就是那个少年科技大学的。”对于已经存在了40年的少年班,人们依然是试图将她和神秘结合起来。
截止到2016年,中国科大少年班一共培养了3167人,18%~20%左右在留在学术界,其中包括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在国内外做教授的超过250人,哈佛就有5人,清华有6人;6位少年班校友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此外,还有商业金融领域的张亚勤、郭去疾……这些数据,都印在陈旸的脑子里,无需准备即可脱口而出。“用事实说话,可能会更简单直接地让大家了解少年班。”
事实上,少年班的孩子已经不是最初创办时那么低龄。少年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兰荣告诉我,少年班的年龄普遍在14岁或者15岁左右。“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孩子年龄太小的话,可能不太容易适应系统的教育。另一方面,整个义务教育的改革,比如说跳级越来越难,孩子的年龄也就相对不会太低,只是比同龄人小一两岁。”
没任院长前,对于这些孩子,陈旸就不陌生。2003年的時候,他曾出任少年班学导,为学生选专业提供辅导。那时,他就发现,少年班的孩子特别聪明。他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在读一本关于条形码的书,看完后,学生过来找他,问能不能将条形码做成立体的。那时,二维码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我有一点很佩服少年班的孩子,就是他们遇到新鲜事物,总是能很快抓住事物的核心,洞察和学习能力很强。”兰荣告诉我。
这样聪明的孩子,少年班并不少见。朱源曾在少年班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他还记得有名叫尹希的学生,出生于1983年,13岁考入少年班,31岁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一个学生要想到少年班就读,必须在高二通过高考,然后才能进入少年班组织的复试。朱源说,当时尹希在北京八中就读,高考只考了570多分,并没有达到中科大少年班的录取线。当时,北京八中的校长给朱源打了个电话,“尹希是北京八中超常教育班创立十几年来,我见到的最聪明的学生,你们能否给他一个进入复试的机会?”
朱源有些犹豫,但还是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校领导,最终决定让尹希参加复试。少年班复试时,会请中国科大有经验的教授来讲一堂数学课、一堂物理课,讲课的内容会是学生没有学过的。讲完课后,教授会当场出题让学生做。“这是少年班筛选学生的重要步骤,高考成绩是可以靠刷题训练出来的,现学现考更能考察一个学生的理解和学习能力。”朱源当时在考场负责监考。数学考试的时间为120分钟,刚过了45分钟,尹希就过来交卷了。朱源告诉他“不能交卷,要回去检查一下”,但尹希说已经检查过了。后来,考卷改出来,尹希是全场的最高分。“我们并不是揠苗助长,你说苗出来了,不能一直放着不管吧,总得找块儿地给它种下去吧。”陈旸告诉我。
在少年班,不管是朱源还是陈旸,没有人当着少年班学生的面夸过他们聪明。“我们觉得一个人聪明与否,是父母给的,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但我们会认可他们努力和奋斗的过程。而且,能考进科大的孩子,没有一个是笨的,这是共性,没啥好夸的。”
兰荣已经在少年班工作了9年,带过两届少年班。她的谨慎更多的是源于对外界的担心。即使是她身边相熟的朋友也会过来跟她说:“你当那群聪明孩子的头,你带得下来吗?”“外界对少年班总是有各种的想象,他们这种联想多是来自一些负面的报道,我们也怕孩子被夸赞多了骄傲。”兰荣曾经带过一个孩子,喜欢数学,但数学有很多分支,这个学生就很犹疑,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方向,最终他找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数学系所有的课程都修了一遍,最终确定了一个方向。“对于数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一个方向都很吃力,他全部学完了,但我也没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只是肯定他的努力。”在与我的交谈中,兰荣避讳提任何与聪慧相关的字眼,“你看有些孩子,虽然没有花费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但他们效率是很高的。”
尽管如此,作为少年班的学生,刚一开始,还是很容易被光环笼罩。徐平平记得,当她复试从少年班学院出来时,有很多媒体守在学院外的台阶上,追着问他们的年龄、以前获奖的经历。军训时,少年班自成一个方阵,尽管学校设置了门禁查岗,但仍有不少媒体潜入进来,围着少年班各种拍照。徐平平说,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今年多大啊?”“你们班最小的是谁呀?”“你这么小,会洗衣服吗?”徐平平班级最小的同学只有13岁,被媒体围追堵截了好几天。“当时觉得被关注挺开心,现在觉得他好可怜。他还是很独立的,什么事情都自己做,我们大家都叫他小弟弟。”
徐平平来自吉林,今年上大二,还不到18岁。她长得清清秀秀,讲起话来有条有理,逻辑很是清晰。她从小就是被人仰望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初中的时还跳了级。2016年,她考了666分,超过科大在吉林省的录取线30多分。考上少年班后,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学还专门联系她,惊呼道“原来我身边一直有个天才”。徐平平所在的班级总共有40多个同学,几乎每个孩子都有类似的经历。刚开始,班里同学谁也不服气谁。第一天军训,徐平平和同学就互相熟悉了彼此的底细,基本都是名校过来,高中排名名列前茅,高考成绩均超录取线几十分,“最牛的是那个小弟弟,考了699分”。“那时,你会觉得待在少年班,自己也是天才。”徐平平说,她体育课去练瑜伽,当同学知道她是少年班的学生时,都会很崇拜地看着她,自己练习也忍不住更加有模有样起来。
不过,这样的自信或者光环很快在一个月后的数学分析考试后瞬间被抹去。徐平平只考了60多分。她觉得很难相信,“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自己都学会了啊!”徐平平回忆了自己学习的过程,老师讲的都听懂了,自己复习时也背了很多概念,课后练习题也看了。她很崩溃,给父母打了电话。父母安慰她不要着急,多找师兄师姐请教经验,多做练习题。“后来,我想了下,我觉得自己学懂了,但只是懂了那个含义,但并不会利用这个知识点去发散,并运用在习题中。”整个大一上学期,她都觉得自己生活在黑暗中,就连上体育课,头脑里想的也是“题目不会做”。“我当时最怕听见的就是数分又要月考了,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希望;早上连5分钟都不敢多睡,觉得必须要起床去做题。”
张载熙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他的数分月考成绩是不及格。班主任老师找他谈话,第一句问的就是:“你以后是打算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呢?”他一下懵了,小声地回答说:“深造。”“他那段时间很迷茫,不知道成绩怎么下来的,总是给我打电话,但整个人比较消沉。”张载熙的父亲告诉我。张载熙事后想了想,他觉得尽管自己也按时完成老师作业,但除此之外,他多数的时间都用在看小说了,并没有好好地去预习和主动学习。周天翼还记得张载熙当时抱着一本《红楼梦》,在寝室里一坐就是好久。
对于这样的情况,兰荣已经能够应对自如。这其实很容易理解:第一,学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脱离了高中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学习方面会放松;第二,高中是老师带着学习,一遍遍重复讲解,而大学则是不断地学习新知识的过程,学生一时会有些不适应。“所以进入少年班后,学生都会有一个重建自信的过程。比如说,你在高中是尖子,但在少年班所有的尖子生都聚到一起了,在这个平台上,你必须要用平常心来对待,将过去清零,重建自我自信,这需要付出足够的努力。”
兰荣告诉我,为了帮助少年班学生过渡,在大一第一学期,他们会安排学生集中上晚自习。大一第一年,是兰荣最忙的时候,她每天的工作有规律地分为三个时间段: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晚上7点到9点。孩子生病、学习、成绩下降乃至谈恋爱,她都要一一注意。现在她已经能够根据学生的病情迅速地判断出该去哪个医院,也知道派出所在哪里,教学以及学生管理涉及的各个部门她也了如指掌。“头一年是任务最重的,主要给孩子们建立规则意识。”这之后,他们会默默退到背后做个“隐形人”,给他们更多自我成长的空间。少年班的一个理念是:“老师家长都做个‘隐形人,看到孩子路走弯的时候,出来拨一拨就好。”

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薛天
不過,也有学生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比如说有的孩子玩游戏,不去上课,成绩很快降了下来。兰荣和其他班主任就会和学生协商共同制定一份时间规划,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出现在哪里,都会清清楚楚地写在规划上,班主任会随时去抽查。“有时候你去了会发现他们不在,他也会找理由搪塞你,但一般都能够完成70%~80%。”兰荣说,“少年班的孩子真诚而单纯,一般答应的事都会做到。他们会跟班主任老师很亲密,会找你讲最近的学习情况,跟同学的矛盾、家长的摩擦等,他们有什么事都会选择直接的表达方式。你跟他交谈,会觉得很舒服。”
教学改革试验田
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薛天入学的时候跟张载熙是同样的年龄。薛天1995年入读少年班教学改革试点班(以下简称“教改班”)就读,他们同少年班一样,在入学两年后可以在校内自由选择专业。这是中国科大自1985年的一次尝试。他们试图做一次对照研究,看这批学生是否能适应少年班的节奏,结果很不错,这种班级模式一直得以保留到现在,并成为少年班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少年班已经演变成由三类班级构成的少年班学院:成立于1978年最早针对早慧儿童设立的少年班;1985年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的“教学改革试点班”;以及成立于2010年,通过先面试后高考录取的创新试点班。“我们不提倡学生年纪越小越好,现在的少年班学院,绝大多数是16到18岁的学生。”陈旸说。为学院起名字时,陈旸等人想了很多名字,最终还是决定叫“少年班学院”,“少年班”三个字保留了原来的草书,学院则是“正楷体”,“少年班是我们这么多年精心打造的招牌,要好好珍惜和保留”。
薛天讲话很快,别人说一分钟的话,他10秒钟就能讲完。他选择教改班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那里一方面会学很难的教材,另一方面两年后可以在学校自由选择专业,“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薛天还记得当时他们线性代数课本“超级厚”,跟数学系使用一样的课本,被称为全亚洲最难的教材。“这个很大程度上培养了我逻辑思维的能力。”即使当年的教改班不像现在自成班级,是跟少年班混成两个班级,一半少年班的学生,一半教改班学生,薛天从来不承认自己来自少年班。“只要一提少年班,就觉得别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就觉得你是天才。”张亚勤也表达过类似的疑惑,“大家一提少年班就认为我们是天才,感觉被否定了所有的努力”。
少年班自由选专业的举动2002年在全校推广开来——学校允许学生100%自主选择专业,这在所有高校中是首创。本科生在校期间拥有三次自主选专业的机会:入学一年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范围内选择学院或学科类;大二结束后可在学院或学科内选择专业;三年级后还可以进行专业调整或按个性化修课计划学习。“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很重要的是呵护、引导、提升学生的兴趣爱好、好奇心和求知欲,自主选择专业也是国际一流名校的通行做法。”中国科大副校长陈初升告诉我,很多学生由于高考填报志愿时对学校、专业不太了解,或受家长、社会的影响,不能恰当地填报专业,所以很有必要在大学期间帮助他们逐步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潜能,并给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周天翼和张载熙都是选的生物力学专业。两个人自小对航空航天和机械加工感兴趣。后来,他们发现,力学不仅可以运用在火箭发射这样的大器件上,还可以用在细胞这样小的存在上。“通过调整力学信号去调控细胞的生长变化,你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奇妙和有意思的事情。”寝室的另外一位同学则是数学统计方向,会做一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的研究,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就会在寝室互相讨论彼此的方向,寝室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小课堂。周天翼说,这在他跟导师沟通保研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导师希望将人工智能模型应用到生物力学中来,两人一拍即合。张载熙则打算出国,两个人都有很明确的志向,也比同龄的孩子思考得更多。
“学校给少年班的定位是整个中国科大教学改革的试验田。少年班其实相当于一个校中校,各种专业的学生编在一起,很容易发现教学管理和科学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寻找解决方式,先在少年班小范围内尝试,试后觉得挺好,就推广。”兰荣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科大实行的弹性学制,也是从少年班开始的。兰荣说,有的孩子三年就能学完160个学分,且论文做完了,那么就可以申请毕业,也可以去选修研究生的课程;但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慢,要学个五六年,那样也可以。“学校给学生的宽容度还是很高的。我们不对学生规定统一的知识结构和学业课程要求,而是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设计个性化培养方案。”陈旸说,“少年班学院的学生,毕业时,100个人应有100份不同的成绩单。”

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院长陈旸
除了要应对学生的不适应,陈旸和少年班学院的学生管理队伍还需要与对孩子期待过高、不理性的家长进行沟通。经常有人来找少年班的老师,说自己没有机会读博士,希望孩子将来读个博士。“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孩子是孩子,家长是家长,你自己当年都没能力读,你凭什么要你儿子来完成你的理想?”陈旸劝诫家长,要给孩子自由的空间,但并不总能奏效。
兰荣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数学成绩很差,入校以来《数学分析》这门课就没有及格过一次。但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却选了数学,理由是“父母认为数学就业前景好”。兰荣觉得不妥当,就和孩子的父母沟通。谈了几个回合,也没有能说服家长,最后只得退一步说,“下个学期做个尝试看吧”。结果第二学期,孩子的数学全挂科,只好改学化学,多耽搁了一年才毕业,但最终也拿到美国一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很多家长的思维是固化的,他们不知道孩子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一旦孩子成绩下降,就会过来说:‘为什么我的孩子高中那么优秀。到了大学就不行了?他们其实是拿高中的尺子在量大学的孩子。他们没想过,在初高中阶段,家长代劳了学生很多事情,所以很多孩子的习惯并没有养成。所以,你会看到孩子很快适应了,但外围的家长依然在焦虑。”

中国科大教师和同学们共同研究弹头爆炸半径问题
相比于张载熙的名列前茅,周天翼的成绩在班里处于中等位置,但他并不觉得过于焦虑。“我性格好啊,愿意帮助同学啊,这是我的长处呀。”周天翼的优点显然不止这些。这两天,我发现,他很善于观察,也有很好的感知力,他喜欢一款叫刺客信条的游戏,“这里面对秩序自由的思考,以及中世纪欧洲中东人文的描述,都是电影或者书本很难直观沉浸地展现给你的”。但他很佩服另外一个学数学的同学,会将各种计算用到游戏中去,“一般我们觉得要输了就泄气了,但他会利用手中的装备算获各种随即组合的成功率。”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其实我打游戏很挑的,做得差的、剧情不好的、操作反人类的,我都不玩的。外人可能覺得我们是天才,但我觉得大家是像天才的普通人。”
这也是陈旸一直追求的。“我们要把孩子的长处告诉他们,鼓励他们。个人的成长是全方位的,他比你长得高,那你比他壮也是优势啊。学校给学生的宽容度还是很高的。我们不对学生规定统一的知识结构和学业课程要求,而是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设计个性化培养方案。”陈旸说,“少年班学院的学生,毕业时,100个人应有100份不同的成绩单。”(本文徐平平为化名)
——郭沫若的中国科大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