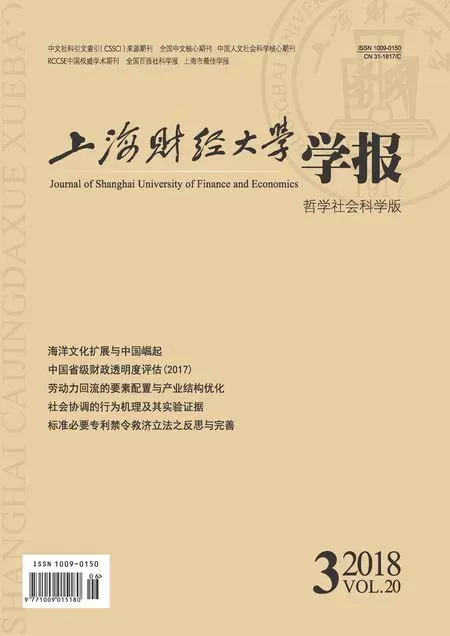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立法之反思与完善
袁 波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一、前 言
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EP)是实施标准所必不可少的专利。近些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禁令救济(injunctive relief)①所谓禁令救济,是指法院或者有关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严格说来,禁令救济是英美法系衡平法上的一项救济措施,大陆法系与之对应的概念是停止侵害救济。依据颁发阶段和效力期间的不同,禁令分为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ts)、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和永久禁令(permanent injunction)。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称“禁令”仅指永久禁令,也即大陆法系上的停止侵害,而不包含临时禁令和初步禁令,后两种禁令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为假处分或者行为保全。纠纷席卷全球②例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结的“橙皮书案”(2009年)、荷兰海牙地区法院审结的“飞利浦诉SK-Kassetten案”(2010年)、我国广东高院审结的“华为诉IDC案”(2013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结的“苹果诉摩托罗拉案”(2014年)、日本东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审结的“三星诉苹果案”(2014年)、欧盟法院作出先行裁决的“华为诉中兴案”(2015年)、英国高等法院新近作出判决的“UPI诉华为案”(2017年)。,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禁令救济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为了适时回应并消解此类纷争的现实需求,《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提出“完善标准必要专利的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政策和停止侵权的适用规则”。③参见《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2/22/content_10468.htm,2017年8月3日访问。当前,我国各级立法和司法机关正在通过修订专利法、颁布司法解释等立法举措来创设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这些规则可见于:《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修订稿)》(以下简称《深圳规定》)第28条,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指南》)第149–152段。
然而,如果用批判的、系统的眼光对初具雏形的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加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新近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无论是在其规则的明确性、妥适性、协调性甚或条文表述的精细化方面均有所欠缺。例如,上述规范性文件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成立要件的规定普遍较为原则和粗疏,缺乏可操作性;《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http://www.gov.cn/xinwen/2015-12/03/content_5019664.htm,2017年7月19日访问。和《专利法司法解释(二)》就国家标准中的必要专利是否采取默示许可分持不同立场;《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二款关于颁发禁令条件的规定欠缺对公共利益的考量,等等。以上规范所存在的罅隙或不足致其难以为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救济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和秩序保障,相应的民事司法实践恐怕也会陷入迷途。
略感遗憾的是,国内学界虽然已经开始关注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滥用与规制问题,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反垄断法视角展开,或是集中于对德国、欧盟典型案例和具体制度的梳理、介绍及评述,而从专利法角度讨论是否应当以及如何给予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禁令救济的论述并不多见,②笔者于2017年9月10日登录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以“标准必要专利禁令”和“标准必要专利停止侵权”作为篇名共计检索到期刊论文20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不足5篇。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丁亚琦:《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反垄断的法律规制》,《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2期;韩伟、徐美玲:《标准必要专利禁令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探析》,《知识产权》2016年第1期;魏立舟:《标准必要专利情形下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法规制——从“橘皮书标准”到“华为诉中兴”》,《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赵启杉:《竞争法与专利法的交错:德国涉及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禁令救济规则演变研究》,《竞争政策研究》2015年第2期;史少华:《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引发的思考——FRAND原则与禁令》,《电子知识产权》2014年第1期。以至于让人误以为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滥用只是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严格说来,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首先是专利法的议题,然后才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话题。试想,倘若专利法完全剥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禁令救济请求权,滥用禁令救济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法介入将丧失基础。因此,对该问题的探讨首先需要回归到专利法视域。再者,如前文所述,相关立法实践主要集中于专利法,加之有关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诉讼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③根据笔者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截至目前,我国法院现已审结或者正在审理的与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禁令救济纠纷案件包括:深圳中院主持调解结案的“中兴和华为互诉案”(2015年),正在审理的“华为和三星互诉案”及其“美国GPNE公司诉苹果、诺基亚、中国电信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新近审结的“西电捷通诉索尼案”(2017年)以及已经受理的“高通诉苹果案”;北京三中院正在审理的“新岸线诉金立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西电捷通诉苹果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四环制药诉齐鲁制药案”(2017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华为诉三星案”(2017年)。,因此从专利法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拥有更多的本土素材,而且更加契合当前的立法动向和实务中的理论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发生的“美国制裁中兴事件”④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戒信,并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两份函件中对此做了虚假陈述为由,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和中兴康讯公司拒绝令的决定。美国商务部下令拒绝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的出口特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电讯零部件产品,期限为7年。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还对中兴通讯处以3亿美元罚款。折射出我国通信产业“缺芯少魂”的尴尬处境,就此而言,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直接关涉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创造、推广和运用,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规则可以为我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领域“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提供法治保障。
时值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以及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制度初创的关键时期,鉴于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重心的偏离以及尚未就此给予学理上的分析和回应,本文将从专利法视角对此略作探讨,以期推动该问题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为实务部门破解这一疑难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在此过程中,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三:一是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选取反垄断法或者比较法作为研究视角,本文聚焦国内相关立法,力图在专利法制度框架内探寻预防和制止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被滥用的解决方案。二是对国内外相关典型案例和立法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确保最终成果能够客观反映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并对接实务界需求。三是使用列表和作图的方式更为全面和直观地呈现相关立法的基本概况、有关案件的裁判思路以及本文所提出的改进方案,增强有关对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遵循如下研究思路:首先,结合标准必要专利的技术和经济特征,探究专利法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进行限制的缘由和理据。其次,梳理现有的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立法,剖析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最后,提出完善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立法的基本进路以及补正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的具体维度。
二、专利法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主要动因
我们提出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进行限制,实际上是相对于禁令救济无限制适用的理论基础和裁判方式而言的。大陆法系国家目前的通说是将知识产权视为准物权,认为它是一种绝对权。根据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的区分理论,如果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或者面临侵害之虞,专利权人自然可以要求侵权行为人停止侵害。①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有学者将这种传统的类物权化处理模式称为“停止侵害当然论”。②参见李扬、许清:《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法学家》2012年第6期。我国现行专利法和民事法中并无法律条文规定向专利权人签发禁令的条件,如何适用禁令救济往往由法院基于个案自由裁量。因循大陆法系传统,我国法院在以往的实践中多加大保护力度,只要认定知识产权侵权的事实,鲜有不适用或者限制性适用禁令救济的判决。③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4月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报告中写道:“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在认定侵权成立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判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也可参见孔祥俊:《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思维——知识产权司法前沿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在此背景下,作为研究的前提,首先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回应的一个问题是:专利法何须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施加限制?
作为专利和标准相互融合的特殊产物,标准必要专利在法律性质上仍旧属于知识产权,但是相比于一般专利,不管是其具体内涵还是实施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标准的开放性使得标准必要专利携有公共产品特征,标准必要专利实施通常采取“先实施、后许可”的模式,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中更容易证明被控侵权行为成立等。若是依然遵循“有侵权行为发生即颁发禁令”的思维定势,将可能破坏专利法蕴含的利益平衡,致使许可双方的谈判力量严重失衡,出现“专利劫持(patent holdup)”、“许可费叠加(royalty stacking)”等诸多问题。如此既与专利法的宗旨和FRAND(公平、合理和无歧视,fair,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许可的要求相背离,也无益于相关行业的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甚至会阻碍社会创新。④参见魏立舟:《标准必要专利情形下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法规制——从“橘皮书标准”到“华为诉中兴”》,《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详而论之,主要缘由如下:
(一)无限制适用禁令将导致专利劫持发生
当专利被纳入标准,不同技术之间原先存在的竞争将被削弱或者排除,标准实施者为实施标准必须使用该标准中所包含的必要专利,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议价能力大增。鉴于专利权人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后续创新的跟进和标准的升级换代①Spulber,Daniel F. Innovation economics:The interplay among technology standards,competitive conduct,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2013,(9):779.,标准必要专利并不必然赋予其权利人绝对的垄断力量。②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是:每个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都必然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无需基于个案认定。实际上,鉴于每个标准必要专利并不都构成独立的相关市场,不同标准之间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替代性以及技术和标准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这一推论并不成立。详细内容可参阅袁波:《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兼议“推定说”和“认定说”之争》,《法学》2017年第3期。但是,在一项标准被广泛采用并且转向另一项替代标准需要大量额外成本时,该标准中的必要专利权人往往胁迫使用人在如下选项中做出抉择:“或者不实施标准,或者接受其‘勒索’”。③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April 2007,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tr/antitrust-enforcement-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visited on Aug.7,2017.不少学者称之为“专利劫持”。④See Daniel G. Swanson & William J. Baumol.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RAND) royalties,standards selection,and control of market power,73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05:1; Mark A. Lemley &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85 Texas Law Review. 2007:1991; Joseph S. Miller. Standard Setting,Patents,and Access Lock-In:RAND Licens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40 Indiana Law Review. 2007:351.实际上,专利劫持的发生与高悬于专利使用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禁令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旦执行禁令,就意味着被控侵权人必须立即停止实施专利乃至标准,标准化产品被迫退出市场,即便这仅仅维系一段时间,对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使用人而言仍是难以承受之重。此际,即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仅仅是以寻求或者实施禁令相要挟,潜在被许可人也只能被迫接受其提出的不合理许可条件。美国学者马克•莱姆利(Mark A. Lemley)和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甚至直言,“禁令的实施和潜在的威胁是诱发专利劫持和许可费叠加的‘罪魁祸首’”。⑤Mark A. Lemley &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85 Texas Law Review. 2007:2009.
从现已审结的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垄断案件和诉讼纠纷看,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无一例外地都寻求过或者实施过禁令⑥例如,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结的“苹果诉摩托罗拉案”、日本东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审结的“三星诉苹果案”、欧盟委员会查处的“三星和摩托罗拉标准必要专利垄断案”、中国法院审结的“华为诉IDC案”。,该事实恰好印证:禁令救济与专利劫持的发生有着毋庸置疑的紧密关联。⑦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其实,类似的判断在诸多法域的政策声明和法律实践中亦有所体现。例如,美国司法部(DOJ)与专利和商标局(PTO)2013年发布的《负担F/RAND许可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救济政策声明》指出,“禁令救济正在逐步偏离正轨,沦为专利权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而这有违FRAND许可的要求和专利法激励创新的宗旨。”⑧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January 2013,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about/offices/ogc/Final_DOJPTO_Policy_Statement_on_FRAND_SEPs_1-8-13.pdf,visited on JUL.12,2017.又如,欧盟委员会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竞争政策简报》中提到,“通过查处摩托罗拉和三星两起标准必要专利垄断案件,委员会发现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将扭曲许可谈判,衍生出不公平许可条件。”⑨See EU. Competition policy brief: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June 2014,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cpb/2014/008_en.pdf,visited on JUL.12,2017.再如,我国法院在华为诉IDC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认为,IDC向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提起禁令之诉表面上是在维权,但实则是藉此逼迫华为接受不合理许可条件。由此不难看出,为避免禁令救济异化为专利劫持的实施手段,须摒弃无限制适用禁令的惯常做法,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施以必要的限制。
(二)FRAND许可要求对禁令救济予以限制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通常会向标准化组织做出FRAND许可承诺。然而,禁令救济与FRAND许可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即执行禁令意味着被控侵权人必须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乃至标准,而这与FRAND许可的核心要求——确保标准必要专利可开放性这一根本目标相抵触。通常而言,专利权人做出FRAND许可承诺就表明放弃自主独占实施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它们的专利得以进入标准并可以通过FRAND许可获得收益。①See J. Gregory Sidak. The Meaning of Frand,Part Ii:Injunctions,11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015:212.由此推演开去,只要潜在被许可人有意愿也有能力以FRAND条件实施标准必要专利,就足以表明专利权人能够通过许可费或者损害赔偿获得激励性回报,此时再无必要给予其禁令救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苹果诉摩托罗拉案”②Apple,lnc. v. Motorola,lnc.,757 F.3d 1286(Fed.Cir.2014).中指出,“专利权人提交FRAND许可声明,就默认金钱赔偿可以弥补任何侵权行为给其带来的损失。除非被控侵权人拒绝支付FRAND许可费或者故意拖延谈判进程,否则就不应当颁发禁令。”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6年在eBay案中明确了禁令救济在衡平法框架内适用“四要素检验法”。法院在决定是否颁发禁令时,需要结合案件基本事实审查是否满足颁发禁令的四个要件:一是原告是否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二是损害赔偿是否能够实现充分救济;三是权衡颁发禁令给原被告造成的困难和带来的收益;四是考虑公共利益。See eBay Inc. v. MercExchange,L.L.C.,547 U.S. 388(2006).此外,在“微软诉摩托罗拉案”④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Inc.,696 F.3d 872,878(9th Cir. 2012).、“爱立信诉D-Link案”⑤Ericsson,Inc. v. D-Link Systems,Inc.,773 F.3d 1201(Fed. Cir. 2014).、“UPI诉华为案”⑥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 Anor [2017]EWHC 1304(Pat)(07 June 2017).等案件中,美英法院一致认为,FRAND许可承诺是专利权人和标准化组织之间的合同,使用人作为该合同第三方受益人享有独立请求权,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径直寻求禁令救济将可能构成违约。
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调和FRAND许可与禁令救济冲突的途径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具有可行性。首先,与英美法系国家把禁令当做损害赔偿的补充救济手段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将其视为侵权行为发生后必然引发的结果,⑦参见施高翔:《中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8页。难以摆脱“禁令救济当然论”的桎梏;其次,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大陆法系国家对FRAND许可承诺法律性质的认识莫衷一是,但是都拒绝承认它构成所谓的第三方利益合同,合同法规制进路窒碍难行。⑧根据法国法律,FRAND许可承诺是邀请进行协商的标志,并不是一种缔约的强制要求,也不构成第三方利益合同;See Brooks,Roger Geradin & Damien. Interpreting and Enforcing the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T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2011:23. 德国法院认为,FRAND许可承诺既不构成专利权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合同,也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方利益合同。参阅叶若思、祝建军、陈文全、叶艳:《关于标准必要专利中反垄断及FRAND原则司法适用的调研》,《知识产权法研究》2013年第2期;我国法院在华为诉IDC案中援引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法律原则解释FRAND的含义,并指出该承诺一经作出就意味着专利权人负有FRAND许可的义务,而非由此构成合同。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值得一提的是,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2016年修订的专利政策指出:“专利权人做出FRAND许可承诺后不得寻求禁令,也不得执行禁令……除非使用人不愿意将纠纷提交法院审判或者拒绝遵守司法裁决”⑨See IEEE-SA Standards Board Bylaws,December 2016,available at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policies/bylaws/sb_bylaws.pdf,visited on JUL.12,2017.。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滥用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行为。但是,考虑到标准化组织并非公共利益的代表,以协商作为组建基础的标准化组织首先必须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在制定专利政策时需妥善平衡标准制定和实施各方的利益诉求,①参见张平、赵启杉:《冲突与共赢:技术标准中的私权保护——信息产业技术标准的知识产权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故而很难希冀别的标准化组织也争相效仿该专利政策。②诺基亚和爱立信作为IEEE的重要成员已经公开表示,它们不会遵守IEEE最新修订的专利政策。See Richard Lloyd,Ericsson and Nokia the latest to confirm that they will not license under the new IEEE patent policy,available at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policies/bylaws/sb_bylaws.pdf,visited on Aug.12,2017.事实上,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和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已经指出,它们不会像IEEE一样通过修订专利政策来阐述FRAND许可与禁令救济的关系。③Pentheroudakis,Chryssoula & Baron,Justus,Licensing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ases,January 2017,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4068/jrc104068%20online.pdf,visited on JUL.14,2017.可见,为确保FRAND许可得以实现,针对标准必要专利设立特殊的禁令救济规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意义重大且势在必行。
(三)标准必要专利实施关涉社会公共利益
禁令救济制度诞生于早期工业时代,当时专利权所保护的客体形态比较单一,很少出现单个产品中包含多项互补专利的情况。④参见仲春:《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滥用的规制安全港原则及其他》,《电子知识产权》2014年第5期。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标准化产品动辄包含成千上万项必要专利,如单个智能手机包含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就高达25万件。⑤See RPX Corp. Amendment No. 3 to Form S-1,59,available at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509432/00011931 2511240287/ds1.htm,visited on JUL.17,2017.此时,只要针对任何一项标准必要专利颁发禁令,就将导致整个标准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迫中止,这对使用人是极其不公平的。再有,如果一个标准得到广泛应用而成为行业标准或者国家强制性标准,达不到标准的产品或者服务就不能进入市场,这个标准对相关企业就是强制性的要求。⑥参见王晓晔:《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诉讼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这种情况下,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仍可毫无限制地提起禁令之诉,并轻易地获得支持,那么无异于排除了标准实施者对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的使用,这既与技术标准化的目的背道而驰,又将妨碍社会公众分享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各种益处。可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不止是标准化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合同关系,牵涉技术标准化各方的合作和协调,而且关乎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⑦参见王晓晔、丁亚琦:《标准必要专利卷入反垄断案件的原因》,《法学杂志》2017年第6期。,颁发禁令时需要考虑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
在有些法域,公共利益已然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能否获颁禁令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在针对苹果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337调查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认为苹果进口和在境内销售的上述产品侵犯了三星在美标准必要专利,对这些产品颁发了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⑧See In the matter of Certain electronic devices,Includin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devices,Portable music and data Processing devices,and tablet Computers,Inv. No. 337-TA-794,available at https://www.usitc.gov/secretary/fed_reg_notices/337/337-794_notice06042013sgl.pdf,visited on JUL.12,2017.紧随其后,奥巴马政府就以该决定有损美国市场的自由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为由否定了该裁决,并要求ITC日后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务必全面细致地评估颁发禁令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的损害。⑨See Obama administration stops ban on sale,import of older Apple devices,available a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08032013%20Letter_1.PDF,visited on JUL.12,2017.在苹果和Next诉摩托罗拉案中,理查德•A.波斯纳法官指出:“容许专利权人收取许可费的强制性许可有可能是代替禁令救济的理想办法,因为当所涉的发明创造仅仅覆盖专利产品中的某一个小部件时,给予权利人以禁令救济不仅会造成原被告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而且还将导致消费者不能再购买被禁止销售的专利产品,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①See Apple,Inc. And Next Software,Inc. v. Motorola Mobility,Inc.,Nos. 2012-1548,2012-1549.DOJ和USPTO明确指出,在决定是否针对负担FRAND许可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颁发禁令时,必须审慎评估由此对公共健康和福利、市场竞争环境及消费者利益的潜在影响。②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January 2013,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about/offices/ogc/Final_DOJPTO_Policy_Statement_on_FRAND_SEPs_1-8-13.pdf,visited on JUL.12,2017.
三、规范性文件梳理和解析:对于现行立法的反思
在探明专利法为何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进行限制之后,反思现行立法也就有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指向。现阶段,有关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规定散见于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和法院内部审判指引四个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中,③严格说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公开征求意见稿)》第26条也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作了限制性规定,但是考虑到本文是以专利法作为研究视角,因而未将其纳入论述范围。即前文所提到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④《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规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不披露其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的,视为其许可该标准的实施者使用其专利技术”。、《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⑤《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被诉侵权人以实施该标准无需专利权人许可为由抗辩不侵犯该专利权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且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明显过错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深圳规定》第28条⑥《深圳规定》第28条规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应当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条件进行专利许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适当履行本条第一款所述义务的要求包括:……标准实施人适当履行本条第一款所述义务的要求包括:……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适当履行了本条第一款所述义务,仍无法达成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许可协议且已经给专利权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而主张标准实施人停止侵权的,在侵权成立且不影响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标准实施人适当履行了本条第一款所述义务,仍无法达成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许可协议,而主张不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里仅仅列举部分相关内容,详细内容可参见http://www.szsti.gov.cn/notices/2017/3/24/1,2017年7月19日访问。以及《北京高院指南》第149–152段⑦《北京高院指南》:149. ……虽非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但属于国际标准组织或其他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标准,且专利权人按照该标准组织章程明示且做出了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亦做同样处理……152. 没有证据证明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且被诉侵权人在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许可协商中也没有明显过错的……对于专利权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一般不予支持。有下列情况之一,可以认定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153. 专利权人未履行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许可义务,但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也存在明显过错的,应在分析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并判断许可协商中断的承担主要责任一方之后,再确定是否应支持专利权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商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这里仅仅列举部分相关内容,详细内容可参见http://bjg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4/id/2820737.shtml,2017年7月19日访问。。省思这些规范不难发现,它们虽然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均作了限制,却存在着适用范围局限、可操作性存疑、利益平衡失当等诸多缺陷,凡此种种无疑会令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堪忧。
(一)现有规范适用范围较窄和内容不统一
纵览现有规范即可发现,相关规定适用范围局限,具体条文内容差异显著。一方面,相关规定适用门槛很高,未触及目前备受争议的问题。《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仅仅适用于没有披露的国家标准中的必要专利,这意味着,不管是已经披露的国家标准中的必要专利,还是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中所包含的必要专利,均不能适用该条款;①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6条的规定,按照实施范围的大小,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只是针对推荐性标准中明示的必要专利,而不涉及推荐性标准中未明示的和强制性标准中所包含的必要专利;②根据《标准化法》第7条的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深圳规定》和《北京高院指南》所针对的标准类型稍有扩展(详见表1中的“所针对的标准类型”一栏),无奈效力位阶过低。对于国内外禁令救济纠纷集中指向的国际标准及其国内采用问题,除了《北京高院指南》作出规定外,别的规范性文件皆未提及。另外,在“所针对的标准类型”、“FRAND许可义务的来源”、“有无考虑公共利益”、“是否规定许可双方义务”、“是否采取默示许可”等方面,现有规范在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详见表1),这使得相关规定杂乱无序、不成体系,很可能导致裁判者、守法者在规范的理解、适用和遵循上无所适从。

表1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现有规范之比较
(二)相关规定模糊不清并暗含着潜在冲突
如表1中的“考察指标”一栏所示,相比于《深圳规定》和《北京高院指南》,《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和《专利法司法解释(二)》所作的规定相对原则和粗疏,这使得有关条文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其一,《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规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不披露其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的,视为其许可该标准的实施者使用其专利技术”。若仔细考究,这里存在不少有待释明之处。比如,“披露必要专利”是一项法定义务还是标准制定组织的硬性要求?如果专利权人作了披露,但是披露不充分或者不准确,是否构成“不披露”?再进一步,假使不披露是因疏忽大意所致,而非有意为之,是否需要区别对待?其二,依据《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做出的FRAND许可承诺导致许可协议无法达成,且被控侵权人没有明显的过错,即不适用禁令救济。但是,何谓“故意违反FRAND许可义务”?如何判定“被控侵权人没有明显的过错”?此处的“明显”又该作何理解?该条款未作阐释。另外,该条款没有说明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③参见赵启杉:《竞争法与专利法的交错:德国涉及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禁令救济规则演变研究》,《竞争政策研究》2015年第2期。更为严重的是,《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和《专利法司法解释(二)》存在着紧张关系,考虑到二者同属国家层级的规范性文件,这有可能危及法制统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例如,《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针对纳入国家标准却未披露的专利适用默示许可,而《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一款则背离了该进路。诚然,二者适用对象稍有区别,但是鉴于取向上的截然对立,日后不无发生冲突的可能。①参见朱理:《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问题:专利法、合同法、竞争法的交错》,《竞争政策研究》2016年第2期。
(三)对许可所涉各方利益的平衡有所偏失
如前文所述,防止专利劫持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专利法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两大动因,反映到规则设计中,这就要求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三方的利益进行妥善平衡。然而,立法者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一是在平衡许可双方利益方面,过度偏向使用人(被许可方)。主要表现有二:一方面,《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规定标准必要专利采取默示许可,即“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不披露其拥有的必要专利的,视为其许可该使用人使用该专利,无权起诉使用人侵犯其标准必要专利”②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http://www.sipo.gov.cn/zcfg/zcjd/201504/t20150402_1096196.html,2017年8月13日访问。。这在遏制专利劫持的同时,剥夺了该等专利权人的禁令救济请求权,甚至隐含着任何人都可以未经授权实施标准必要专利,无须与专利权人达成许可使用费协议,留待行政机关或者法院日后裁决就行。③参见张伟君:《默示许可抑或法定许可——论《专利法》修订草案有关标准必要专利披露制度的完善》,《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另一方面,现有规范将专利许可条件与禁令颁发联系起来,即根据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使用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的大小决定是否适用禁令救济。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新增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但是,这只是着眼于潜在被许可人主观善意程度,而欠缺对其履约能力的考察,忽略了标准必要专利人获得正当收益的合理诉求。二是在确定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成立条件时存有疏漏,缺乏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如表1中的“有无考虑公共利益”一栏所示,除了《深圳规定》第28条第四款明确将公共利益纳入颁发禁令的考量因素外,别的规范性文件均未提及,并且该条文仅仅是一笔带过。
四、完善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的进路及维度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禁令救济属于跨界违法行为,有可能违反专利法或者反垄断法,在创设规则时,首先需要明确专利法和反垄断法的不同定位和分工,谨防突破不同法律的功能界限。另外,针对标准必要专利采取默示许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仅无助于争议的解决,反而会造成利益关系的二次失衡,更为妥适的做法是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采取限制性适用,从如下三个维度着手完善现有规范:列举颁发和阻却禁令的条件要求、明确FRAND许可的私法属性和考量颁发禁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
(一)厘清专利法和反垄断法的角色分工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滥用与规制属于专利法和反垄断法交叉问题。一方面,凡权利皆有界限,禁令救济请求权亦然。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行使该权利超出正当范围,以此牟取超出激励创新所必需的经济回报或者获取了其他不正当利益,就将构成专利法所禁止的专利权滥用;另一方面,标准必要专利是制造标准化产品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相比于一般专利权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更有动机和能力利用禁令救济排除、限制竞争,如此原本正当的行权行为即异化为反垄断法所制止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在实践中,主要法域皆是通过专利法或者反垄断法约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例如,美国法院依据e-bay案确立了四要素检测法来严格控制禁令颁发,并在“微软诉摩托罗拉案”和“爱立信诉D-Link案”中进行了运用;又如,在欧洲范围内,两者兼而有之。德国法院在专利法框架内引入反垄断抗辩规则阻却禁令颁发,如“橙皮书案”①See German Federal Supreme Court,KZR 39/06(6 May 2009).。欧盟委员会通过反垄断法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禁令救济排除、限制竞争,如“三星标准必要专利垄断案”②See Case At.39939 - Samsung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available at .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39/39939_1301_5.pdf,visited on JUL.18,2017.和“摩托罗拉标准必要专利垄断案”③See Case AT.39985 - Motorola - 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85/39985_928_16.pdf,visited on JUL.18,2017.。再如,我国采取双管齐下的做法。除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在“IDC垄断案”④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美国IDC公司涉嫌价格垄断案中止调查》,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405/t20140522_612465.html,2017年7月23日访问。中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的正当性提出过质疑外,我国法院现已审结或者正在审理多起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禁令救济纠纷。
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专利法和反垄断法都可以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予以制衡。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究竟应当诉诸于哪一个部门法化解这类纷争?对此,有观点认为,“当知识产权法和竞争法出现竞合的时候,特别是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情况下,竞争法往往可以得到优先适用的地位。”⑤参见王晓晔:《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诉讼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但是在笔者看来,专利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各自的价值本位和适用逻辑,二者定位和分工各不相同,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究竟选用何种法律需要依据个案所处的具体情形而定,至少在规则适用层面不存在孰先孰后一说。展开来说,两法角色分工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专利法角色分工。知识产权法律最基本功能在于调整权利人行使“专有权利”与促进知识、技术广泛传播的矛盾,协调知识财产所有人、传播人与使用人各方利益的关系。⑥吴汉东:《试论知识产权限制的法理基础》,《法学杂志》2012年第6期。如前文所述,专利法之所以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禁令救济请求权作出限制,主要动因是防止专利劫持、实现FRAND许可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若从深层次看,这些缘由皆可归结为矫正专利和标准相互结合所造成的各相关方利益失衡。可以说,利益平衡是专利法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进行限制性适用的起点和终点,而专利法的定位和分工在于:妥善配置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确保专利权人获得正当收益的同时,避免专利权的行使妨碍专利和标准的实施及推广,协调好专利权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三方的利益关系。
第二,反垄断法角色分工。对滥用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进行反垄断法规制不同于采用专利法的规制,更侧重于以经济效率和自由竞争为原则来分析该行为是否正当合理。⑦参见丁亚琦:《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反垄断的法律规制》,《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2期。两者最大的分野在于规制基点存有差异:反垄断法以反竞争效果作为规制基点,适用前提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或者实施禁令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⑧参见韩伟、徐美玲:《标准必要专利禁令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探析》,《知识产权》2016年第1期。而专利法主要限制那些虽然尚未损害竞争,但是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已然超出法律允许的正当范围的行为。通常来说,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有关的垄断行为集中体现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制定有关反垄断规则时,相关条文将主要围绕滥用行为的分析步骤展开,即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竞争效果分析和正当性抗辩。
总体上,专利法着眼于平衡许可所涉各方的利益,而反垄断法旨在规制损害自由竞争的行为。在构建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时,需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异同,意识到所处的部门法场域,避免“张冠李戴”。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已然出现。如前文所述,现有规范都是依据许可双方善意程度决定是否适用禁令救济。在笔者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欧盟法院2015年就“华为诉中兴案”①See Huawei v. ZTE,CJEU,Case C-170/13,关于此案的中文介绍可参阅魏立舟:《标准必要专利情形下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法规制——从“橘皮书标准”到“华为诉中兴”》,《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所做的先行裁决。该判决的核心要旨是考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大小,据此判定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行为。确切地说,与之对应的是滥用行为分析中的正当性抗辩这一环节。然而,这些内容却被完全照搬地复制移植到我国专利法中,并被当做判断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成立与否的法律依据。正因为如此,已有规定仅仅关注行为人的主观要件,而欠缺对社会公共利益和潜在被许可人履约能力的考察。可见,准确把握专利法和反垄断法角色分工对于妥善制定规则极其重要。
(二)默示许可之否定与附条件限制之提倡
如表1中的“是否采取默示许可”一栏所示,现有规范对标准必要专利是否采取默示许可存有分歧。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学界早已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支持者②参见李文江:《我国专利默示许可制度探析——兼论《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知识产权》2015年第12期;袁真富:《标准涉及的专利默示许可问题研究》,《知识产权》2016年第9期;朱雪忠、李闯豪:《论默示许可原则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规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年第23期。和反对者③参见张伟君:《默示许可抑或法定许可——论〈专利法〉修订草案有关标准必要专利披露制度的完善》,《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祝建军:《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成立条件》,《人民司法》2016年第1期。兼而有之。那么,是否应当针对标准必要专利设立默示许可?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默示许可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专利权人丧失禁令救济请求权,这非但不能彻底消除禁令救济纠纷,而且会招致更加严重的问题,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难以获得合理的经济补偿,致使专利法创新机制遭受破坏和技术标准化受到阻滞。此外,基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和参考国际通行做法,也不宜作出这般规定。具而言之,反对理由如下:
首先,禁令和损害赔偿是专利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为重要的救济措施。假使剥夺专利权人禁令救济请求权,就意味着其只能诉诸损害赔偿,这将使之陷入程序冗长繁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如此一来,有可能导致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无法或者未能及时地获得正当收益,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其从事发明创造和参与技术标准化的积极性。再有,相较于美欧发达国家高额的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往往偏低,加之法院并不审理专利的有效性问题,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程序可随时中止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这使得此类案件常常久拖不决。④王斌:《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思考》,《电子知识产权》2014年第11期。
其次,不管是基于标准化组织专利政策,还是依据主要法域对该问题抱持的立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都有权寻求禁令救济,只不过这一权利的行使将受到必要的限制。如前文所述,纵使IEEE对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作了严格的限制,它在专利政策中依然强调,如果使用人不愿意将纠纷提交司法裁判或者遵守该裁决结果,专利权人就可以寻求禁令救济。据笔者考证,包括德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在内的诸个法域仅仅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作了限制,而未采取“剥夺专利权人禁令救济请求权”这样一刀切式的做法。美欧在有关政策文件中还表示,若是使用人缺乏谈判诚意或者履约能力,专利权人即可寻求禁令救济。⑤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January 2013,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about/offices/ogc/Final_DOJPTO_Policy_Statement_on_FRAND_SEPs_1-8-13.pdf,visited on JUL.12,2017; EU.,Competition policy brief: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June 2014,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cpb/2014/008_en.pdf,visited on JUL.12,2017.
最后,不少学者之所以主张对标准必要专利采取默示许可,其主要关切是避免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禁令救济。笔者认为,解困之策不在于“剥夺权利”,而在于“制约权利”。实际上,有学者采用博弈论方法对“一律拒绝适用禁令”、“不限制适用禁令”和“有条件适用禁令”三种情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最为理想的制度安排是“有条件适用禁令”,这既容易促成谈判,也有利于达成公平合理的许可条件。相较之下,另外两种策略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弊端。①详细内容可参阅丁文联:《标准必要专利禁令适用与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竞争政策研究》2017年第1期。可见,化解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纠纷的最优方案是附加限制性条件适用禁令救济,而采用默示许可既无必要,也不妥当。
值得重视的是,依据《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的规定,默示许可仅仅适用于国家标准中未披露的专利,这意味着其只能约束国家标准,无法涵摄现阶段各类争议集中指向的国际标准及其国内采用问题。另外,由于国内标准化组织的主要成员单位通常来自于国内,而国外企业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故而该条款的适用对象一定程度上仅仅限于国内企业,国外企业有可能不受此约束。对此,国内产业界人士甚至直言,“该规定只是单方面缴了国内公司的械,使国内公司在解决全球市场知识产权问题时失去重要武器,实质性损害了中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②宋柳平:《标准必要专利的若干重要问题》,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年12月18日第008版。毋庸讳言,面对各方争议,规则制定者亟须审慎处之,全面细致地评估有无必要作此规定及该规定是否合理。笔者的基本态度是:删除该条文。这样既可以克服前文所述及的其自身存在的模糊不清问题,也能够消弭现有规范之间暗含的潜在冲突。
(三)补正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的三重维度
厘清专利法和反垄断法角色分工与否定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这仅仅是从宏观层面廓清和解决重塑规则的前置性和原则性问题,而对于现有规范的完善,笔者认为除了亟须扩张其适用范围,一律延伸至各个类型的标准。且标准类型只作为参考因素外,还需契合专利法利益平衡之精神意蕴对已有规定加以统一、匡正和细化,具体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 列举颁发和阻却禁令的条件要求
由表1中的“是否规定许可双方义务”一栏可以看出,就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使用人的利益平衡而言,现行立法的缺失和不足可以概括为:具体规则不明和判断标准缺失。前者是指国家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就如何判断许可双方过错作出规定,而这恰恰是认定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是否成立以及指引当事人遵循FRAND许可进行谈判的重要依据;后者是指《北京高院指南》和《深圳规定》虽然明确了许可双方义务,但从主要内容看,只是依据当事人在许可谈判中的表现确定其有无过错和过错大小,没有关注到使用人的履约能力。对此,笔者认为,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③See Huawei v. ZTE,CJEU,Case C-170/13.先行裁决中所提出的谈判框架(如图1所示)可资借鉴。诚然,前文指出该裁决无法直接嫁接到专利法中作为颁发禁令的依据,但是鉴于该谈判框架是为了促成当事人诚信和高效率的谈判,以便达成FRAND许可条件,若是能够辅以考量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因素,它就不失为在专利法框架内平衡许可双方利益的可行办法。由此推演开去,一种衡平私益的改进方案即是:以促成许可谈判为目的,从专利权人和使用人两个方向分别列举颁发禁令和阻却禁令的条件要求,以此取代关于许可双方义务的规定。表2给出了初步的设想。这样一来,既可以增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明晰禁令救济的成立条件,也能够为当事人的许可谈判提供一定的指引,促使其通过自主协商达成彼此满意的许可条件。另外,出于简化分析流程和提高办案效率之考量,增设专利权人获颁禁令和使用人阻却禁令的推定要件,同时规定前述推论均可以被另一方通过举证予以推翻。在实践中,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有关部门可以逐一筛查当事人是否满足表2中所列举的认定要件或者推定要件,以此作为颁发禁令的参考依据之一。

图1 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中提出的许可谈判框架

表2 专利权人获颁禁令和使用人阻却禁令的条件要求
2. 明确FRAND许可的私法属性
如表1中的“FRAND许可义务的来源”一栏所示,FRAND许可义务究竟是来源于专利权人所做出的FRAND许可承诺,还是一种类似于法律原则所附随的义务,现有规范存有分歧。对此,笔者认为FRAND许可义务是一种基于专利权人意思表示形成的具有私法属性的义务,而非带有公法色彩的强制性义务,其原因在于:综观国际上主要标准化组织专利政策,FRAND许可义务的产生皆是基于专利权人向标准化组织提交的自愿声明,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化组织强制要求专利权人必须做出此类承诺。①参见史少华:《披露与许可——困扰标准化工作的两大难题》,《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07年第1–2期。例如,IEEE最新修订的专利政策就指出,“它不会强制要求必要专利持有人提交FRAND许可保证函,不过,在决定是否批准包含该专利的标准草案时会考虑这一情况。”②See IEEE-SA Standards Board Bylaws,December 2016,available at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policies/bylaws/sb_bylaws.pdf,visited on JUL.12,2017.在我国,《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第9条规定:“国家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涉及专利的……应当及时要求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在以下三项内容中选择一项作出专利实施许可声明。”③参见《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第9条。可见,我国知识产权和标准化主管部门同样主张FRAND许可义务来源于专利权人的自愿声明,并非法律的强制性义务。
另外,从主要法域处理的此类纠纷或者颁布的有关政策文件看,往往只有在专利权人做出FRAND许可承诺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才在专利法框架内对禁令救济进行限制性适用。假使专利权人没有做出FRAND许可承诺,将会适用截然不同的规则。例如,在“橙皮书案”中,飞利浦持有制造CD-R标准光盘所必需实施的必要专利,但是该标准属于事实标准,专利权人没有做出过FRAND许可承诺,在确立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抗辩要件④其一,在缔结许可协议时,被许可方必须主动向专利权人发出一个无条件的许可要约,该许可要约不得以专利的有效性、侵权行为确有发生为前提条件,且应当含有其提出的经法院审查合理的许可费报价等相关条款;其二,如果被许可人已经事先使用所涉专利,则其应当向专利权人支付许可费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包括向其提供相关的账务清单、将许可费存放于托管账户等。See German Federal Supreme Court,KZR 39/06(6 May 2009).时,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更加注重保护专利权人利益,施以使用人较为繁重的义务;在《关于朝阳兴诺公司按照建设部颁发的行业标准〈复合载体夯扩桩设计规程〉设计、施工而实施标准中专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专利权问题的函》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指出没有负担FRAND许可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适用默示许可。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朝阳兴诺公司按照建设部颁发的行业标准〈复合载体夯扩桩设计规程〉设计、施工而实施标准中专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专利权问题的函(〔2008〕民三他字第4号)》,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gid=110288&c50997bacdbe-4fa5-bc10-a3b0f5988860=1448012820484,2017年8月6日访问。
综上,由于标准化组织未曾要求专利权人必须做出FRAND许可承诺,而该许可承诺通常又被当做专利法限制禁令救济适用的基础,并决定了不同禁令救济规则的选取和适用,因此亟须在现行立法中澄清FRAND许可的私法属性。申言之,即修改《深圳规定》第28条第一款之规定,明晰FRAND许可要求来源于专利权人所做出的FRAND许可承诺,与《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二款保持一致。
3. 考量颁发禁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
正如表1中的“有无考量公共利益”一栏所呈现的,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有关的规定或者没有提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就只是一带而过,因而有必要在各个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中增加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具体而言,除了规定“引发公共安全事件、危及公共卫生、造成重大环境保护事件、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①参见《北京高院指南》第148段。此类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情形外,为了更好地识别该因素,还可以将所涉标准类型规定为判断颁发禁令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无影响或者影响大小的参考依据。举例而言,相比于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影响更大、程度更深,在决定是否向这类标准中的必要专利的权利人颁发禁令时,就需要格外关注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情况下,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对社会公众生活的影响力大小依次下降,在确定是否向该等标准中的必要专利的权利人颁发禁令时,社会公共利益在衡平中所占的比重将随之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给予禁令是原则,拒绝禁令为例外”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制传统,但是法院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拒绝颁发禁令的案例并不罕见。在“白云机场专利侵权案”②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91号民事判决书。、“武汉晶源‘烟气脱硫’方法专利案”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等案件中,我国法院就强调颁发禁令可能对社会公众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没有判令停止侵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Klaus Grabinski法官也曾指出,“在禁令救济的适用将严重危及第三人的生活和健康,或者将导致被告破产等情形下,法院将不会强制适用此类救济。”④杨涛:《比较法视野下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方式的完善路径——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二)〉第26条》,《知识产权》2016年第4期。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适用的依据有先例可循。
五、结 语
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情形下,标准的开放性和强制性使得许可双方谈判力量严重失衡,若是依然固守传统的“禁令救济当然论”,就有可能导致禁令救济请求权沦为专利劫持的实施手段,从而背离FRAND许可的宗旨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鉴于此,主要法域纷纷在专利法制度框架内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予以制衡。可惜的是,审视我国各级立法和司法机关创设的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其存在着适用范围过窄、内容不尽统一、可操作性存疑、规则不成体系等缺憾,如此将可能导致该制度难以达致立法预期。为进一步明晰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成立条件,指引当事人遵循FRAND许可要求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许可谈判,并尽可能平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三方的利益,首先需要把握两个原则性问题:一是厘清专利法和反垄断法角色分工,防止立法实践中出现规则混杂、误置和颠倒;二是否定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避免因矫枉过正衍生出反向劫持问题。其次,还须从列举颁发禁令和阻却禁令的条件要求、明确FRAND许可的私法属性和考量颁发禁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这三重维度弥合有关立法缺陷。令人欣喜的是,新近颁布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再次提出“积极开展对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前沿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⑤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chl&Gid=293510&keyword=%E6%A0%87%E5%87%86%E5%BF%85%E8%A6%81%E4%B8%93%E5%88%A9&EncodingName=&Search_Mode=accurate,2017年9月6日访问。。
此外,在新近作出判决的“西电捷通诉索尼”⑥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1194号民事判决书。、“华为诉三星”⑦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初840号民事判决书。等标准必要专利侵权诉讼中,我国法院已就如何适用禁令救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这表明,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制度的构建并没有就此划上休止符,依然处于不断摸索和完善之中,现有规范将有望被逐步修正和补全。
[1]Anderman S D.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mpetition policy[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38.
[2]Geradin,Damien. Pricing Abuses by Essential Patent Holders in a Standard-Setting Context:A View from Europe[J]. Antitrust Law Journal,2009,76(1):329–358.
[3]Hovenkamp E,Cotter T F. Anticompetitive Patent Injunctions[J]. Minnesota Law Review,2016,100(3):873–901.
[4]Lee J A. Implementing the FRAND Standard in China[J].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 Technology Law,2016,19(1):37–86.
[5]Lemley M A,Shapiro C.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J]. Texas Law Review,2007,85(7):1993–2021.
[6]Maldonado,Kassandra. Breaching RAND and Reaching for Reasonable:Microsoft v. Motorola and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Litigation[J].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2014,29(1):419–464.
[7]Miller J S. Standard Setting,Patents,and Access Lock-In:RAND Licens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Indiana Law Review,2007,40(2):351–378.
[8]Sidak J G. The Meaning of Frand,Part II:Injunctions[J].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2015,11(1):212–228.
[9]Spulber D F. Innovation Economics:The Interplay among Technology Standards,Competitive Conduct,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2013,9(4):779–790.
[10]Swanson D G,Baumol W J.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ND) Royalties,Standards Selection,and Control of Market Power[J]. Antitrust Law Journal,2005,73(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