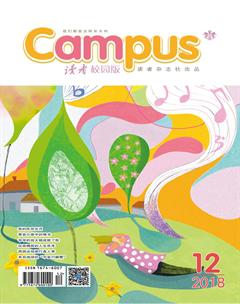记住一些植物的名字
蛇不过
小时候,我分辨野草优劣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吃还是不能吃。有一种草,长着奇怪的三角形叶子,蓝色果实,比绿豆还要小,像一串小葡萄。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知道它的叶子可以吃。五六月里,摘下那些嫩绿的三角形叶子,像邻家爷爷卷烟叶一样一片一片卷起来吃,微微的酸。要是运气好,还能遇上酸里带甜的。有一天,我给它取名叫“酸叶儿”,然后郑重其事地向小伙伴们宣告,但没想到他们早就叫它“酸叶儿”了。
母亲在屋旁新开垦了一块菜地。为了挡住贪吃的鸡和牛羊,母亲又花了好几天时间,用木桩、竹竿、铁丝和旧渔网,做了一道结结实实的篱笆。
春天的菜地里没什么可生吃的。萝卜开了花,变成空心,不好吃。幸好,酸叶儿爬满了篱笆。它们长得特别肥大,绿得好像能掐出水来。我经常趁母亲不注意,钻进菜地摘酸叶儿。也许母亲是知道的,没什么零食可吃的年代,她默许了我对酸叶儿的贪婪。
母亲讨厌菜地里所有的野草。哪怕只是冒出一点点草芽,只要被她发现,她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从土里揪出来。奇怪的是,她对篱笆上的酸叶儿竟然视若无睹。有些不小心爬到菜畦上,她还会拎起细细的藤蔓,挽在篱笆上。后来,因为她的偏心,篱笆上的渔网几乎看不见了,密密麻麻的酸叶儿藤,成了实际上的篱笆。一直到深秋,酸叶儿枯萎了,藤蔓也干瘪了,可怜的渔网才露出来。我对母亲的举动不理解。后来,她告诉我,因为酸叶儿的藤蔓上有刺,连蛇都害怕,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蛇不过”。
有一年夏天,村里有个女人生了疮,在镇上的卫生院打针吃药,就是不见好转。有人说,她长的是烂蛇疮。听说这种疮可怕得很,围着腰长,像一条腰带,如果长得首尾相连了,什么灵丹妙药都治不好,只能等死了。
母亲听说这个消息后,带着我去了那个女人家,母亲说,罐头叶可以治这个病,劝她不妨试一试。
我插了一句嘴:“罐头叶是什么呀?”
母亲说:“就是你经常嚼的那酸叶儿啊。”
罐头叶——母亲所说的“罐头”,并不是可以吃的罐头,而是耕田用的犁铧。酸叶儿长得还真有点像犁铧。
不久以后,那个女人痊愈了。一个下雨天,她拎着一包红糖来到我家。她说是“蛇不过”救了她。
巴辣子
山村里的野草,几乎都是为人而生的:有的可以入药治病,有的可以喂猪,有的可以做牛羊的食物,再不济的草,也可以铲了烧成草木灰当肥料。
而巴辣子,生来就是让人讨厌的。
巴辣子是苍耳的俗名。
我是先知道巴辣子,后知道苍耳的。上小学时,有一篇课文《植物妈妈有办法》,介绍了几种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课文有插图,我一眼就认出了巴辣子——苍耳。
小时候上学有秋收农忙假,学校号召学生勤工俭学,去田野里捡稻穗。那时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假借捡稻穗的名义,和伙伴们在田野上奔跑。秋天的山村是一首欢快的诗。秋风渐凉,阳光还暖,桂花香若有若无,野菊花像星星一样遍地开放。
跑得累了,找一块草地坐下来休息或者做游戏。男孩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打仗,分作两派,在他们想象中的战场上喊打喊杀,互相追逐。他们摘下成熟的巴辣子果实,攥在手里,扔过来,扔过去。巴辣子的果实俨然成为战场上的子弹。
有时候,巴辣子会飞到我们女孩头上。我虽然留着短发,但摘巴辣子时也会扯得头皮发痛。英子留着长发,扎着马尾。有一回,不记得为了什么,我们几个女孩和男孩们吵架了,他们竟然把巴辣子扔在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天哪,可怜的我们,一个个散了头发,你帮我,我帮你,一直忙到太阳偏西。英子被扯得眼泪直流,才把头发上的巴辣子摘干净。
从那以后,我见了巴辣子都会绕道走,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这种麻烦的植物,黏在头发上和衣服上,是一件很闹心的事。
还有一次,母亲去一个亲戚家,她不愿带我去。我死活不干,紧紧拽着她的裤腿哭得天昏地暗。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拉开,还说了一句:“你怎么像个巴辣子?”
我马上停止了哭泣。我可不能做让人讨厌的巴辣子。
地鼓呐儿
认识“地鼓呐儿”这种植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它究竟是草还是花?
田埂上、山林里、河边、地头,甚至什么也没种的荒地上,到处都是地鼓呐儿。村里有户人家修了新房子,村子里的野草好像也得知了消息,老房子的地基上很快就有了它们的影子。四五月里,地鼓呐儿混在一群野草之中,影影绰绰地摇曳。它们的叶子很小,却是一副倔强的模样,像好斗的小牛角。淡紫色的小花很听话,长得整整齐齐的,有点像麦穗。
围绕“地鼓呐儿是花还是草”这个问题,我和伙伴们经常争论不休。她们说是草,矮矮的,散在野草丛里,花儿小,不起眼,也没有香味,和野草没什么区别。我却认为它们是花。淡紫色的小花穗,娇小玲珑的花朵,开得热烈奔放。伙伴们当然是不会认同我的,有时候还嘲笑我把粗俗常见不好看的野草当成宝贝。我很委屈,又找不出辩驳的理由,時间长了,我也动摇了,开始怀疑地鼓呐儿的身世。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是杞人忧天。地鼓呐儿就是一种植物,花也好,草也罢,都是世间的生命,是平等的。
母亲常常扯回来各种野草,洗干净了扔在窗台上,任凭风吹日晒。家里人有什么小病小痛的,选几样熬水喝。地鼓呐儿晒干了,我也能认出它的样子,曾经漂亮的紫色小花穗,失去了颜色和水分,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
我有个毛病,容易上火,经常嗓子疼,嘴角生疮,痛得吃不下饭。母亲抓一把地鼓呐儿,放在茶壶里,熬成又苦又涩的汤汁,逼着我喝。我捧着药碗,眼泪汪汪地暗暗发誓,再也不喜欢地鼓呐儿了。
春风吹起,地鼓呐儿开花的时节,我忘了自己的誓言。
上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学校号召勤工俭学。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一种叫夏枯草的中药,滔滔不绝地讲它的好处。
“什么是夏枯草?”有人提出了疑问。
老师跑到操场边上,扯回一种草,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这不是地鼓呐儿吗?”
那一年老师规定的采摘数量我早就忘了,只记得和同学们提着口袋漫山遍野找地鼓呐儿的快乐。一个星期之后,教室里堆满了地鼓呐儿,像一座小山,也像一座坟——地鼓呐儿的坟。我心里忽然有一股不能描述的忧伤,山野田间,夏天刚刚来到,绿正浓,花正开,稻子将要成熟,这小小的地鼓呐儿,竟撇下热热闹闹的山村,离开了。
随着春雨来,又追着春风离去,地鼓呐儿,你怎么能叫夏枯草,你应该是春天最忠实的情人。
冬果儿刺
第一次随父亲去给祖父母上坟,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看什么都新鲜。四月的江南山林,用“青翠欲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林间草地上到处是各色赶趟儿似的山花,就连坟头上,也插着清明祭奠用的纸花。
我看到一种白色的花,攀附在油茶树上,开得格外努力,露出黄色的花蕊,雪白的花瓣像绸缎。我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漂亮的花,喜欢它们毫不扭捏、盛装开放的姿态,好像一群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山林里仿佛都回荡着她们清脆如鸟鸣的笑声。
父亲说,这是冬果儿花。
我伸手去摘,痛。冬果儿花茎上有刺,扎手。花托上也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细刺,我无从下手。
得不到的,最让人眼馋。我突然发现,村子里有不少冬果儿花。地头、堰塘边、路旁,还有不少人家屋后的芭茅丛中,也有冬果儿花,一朵比一朵开得好看。我忍着痛,摘了好几朵,一朵插在头发上,剩下的捧回家,用一个玻璃瓶子装了水养着。白花、黄蕊、绿叶,清新雅致,在陈旧的写字台上亭亭玉立,简陋低矮的屋子也变敞亮了。
可我的手指被刺扎得又麻又痛。晚上,母亲不得不就着煤油灯给我挑刺。那时候农村虽然有了电灯,但是不够亮,母亲晚上做针线活,仍然点着煤油灯。
瓶子里的冬果儿花没几天就枯萎了,我也慢慢把它忘了。童年的山村里好玩的东西很多,我不会记得已渐渐枯萎的几朵野花。
与花开遍野的春天相比,我们更喜欢秋天的山林。我们可以追在大孩子们的屁股后面,去山上寻找各种野果子。有一天,他们把一蓬刺丛指给我们看,说那是可以吃的,叫冬果儿刺。
这不就是冬果儿花的果实吗?
刺藤上的绿叶和白花已经凋零,露出狰狞的刺。密集的芒刺从茎上一直长到果实上,肆无忌惮,让人望而却步。
大孩子们摘下橘红色的果子,扔在地上,用鞋底搓几下,刺没了。捡起来,在衣服上擦几下,咬开。只有外面的果皮能吃。
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茎上的刺,摘了两个。尽管我一再小心,还是被扎到了,裤子被刺挂住,一个手指也被刺中,渗出了小血珠。果子没吃到,我先吸了自己的血。
学着大孩子的樣子,用鞋底板搓去芒刺,擦几下,再吃。没有想象中甜,有点甜,也有点涩,干干的,毛毛糙糙,没什么水分。嚼了几口,我不敢咽下,又吐了出来。
那天晚上,母亲又在煤油灯下给我挑刺,看到母亲满脸心疼的样子,我忽然觉得不痛了。
后来,我不敢再吃冬果儿刺了。上中学后,我才知道冬果儿刺的大名叫金樱子。
金樱子,这名字就像一户金姓人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却厉害得很,不好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