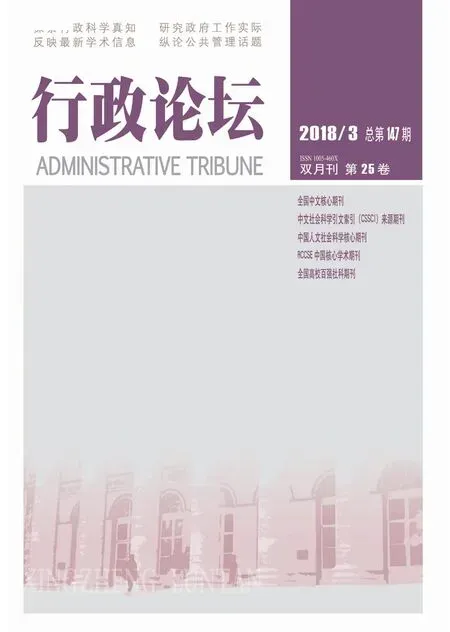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于君博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时代的政治危机常常与学术危机彼此交织,两方面的严肃工作互相渗透”[1]。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共同揭开了西方“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的序幕。由此,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反思也在社会科学研究者间展开。其中既有偏重经验层面的政治危机成因解释,如全球化加剧贫富悬殊、知识经济的“幂律”固化赢家通吃的不平等格局、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推动舆论极化、“循证决策”(Evidence Based Decision-making)的专家治国模式制造公众与政府间隔膜等,也有偏重规范层面的价值批判,如对新自由主义蔓延的担忧、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警惕、对精英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对民主制度前景的重构等。在这场反思中,现代政府所采用的治理手段,无论是实践工具还是价值理念,几乎无一例外地招致批评,甚至连一些前后相继、互为修正的措施也不能幸免。比如,在公共领域坚持循证决策被认为是奉行科学至上和精英主义,但更加开放和直接的决策模式又被诟病为对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想的放纵;在公共事业的运行中倡导市场化、公司伙伴关系和绩效管理被认为是偏离了政府应有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可是基于公民身份、以平等为取向的福利制度又被批评为是孕育种族歧视和社会原子化的温床……
从上述危机的反思与批判中全身而退的是依旧方兴未艾的数字政府治理运动。以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政府治理运动,在过去十年间替代“新公共管理运动”成为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新宠”: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把打造、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当作是改善政府绩效、提升社会对于政府信任的“万灵药”[2-3]。但令人惊奇的,这剂“万灵药”的“药材”之中,像强调对政府绩效的量化与公开、主张利用大数据思维进行循证决策、倡导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开放和公众参与等,恰恰是危机反思与批判的焦点。更加吊诡的是,这剂“万灵药”宣称包治传统政府治理无法有效应对互联网社会变革之症。然而开药方的“医生”——英、美两国政府及其政治精英,却恰恰是在互联网民意的争夺中失利,从而引发这场全球政治危机。数字政府治理能深涉其中却又置身事外的魅力何在?祛魅之后,又该如何看待数字化政府治理运动过去十年间的得失?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4]的要求,我国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变革应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的数字政府治理危机?本文试图沿着“技术—组织—权威”等三个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现实诠释,进而提出对上述问题的初步分析和解答。
一、数字政府治理之“魅”
2006年,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Patrick Dunleavy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在全球公共管理研究顶尖学术刊物《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上刊发了《新公共管理已死,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万岁》[5]一文(以下简称《万岁》)。尽管作者在命名论文时略有哗众取宠之嫌,文章的影响力倒是没有辜负作者的苦心——根据谷歌学术截止2017年5月的统计,《万岁》一文累计被引1531次,位列当年所有公共管理研究论文之首。可以说,作者不仅基于跨越欧洲和北美的大型案例比较研究,赋予数字政府治理“万岁”般的魅力,还使得发现这种“魅力”成为过去十年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而由于同《万岁》一起位列影响力排行榜前十位的论文中,还有多达四篇是以数字治理和电子政府为研究对象的,所以,推动数字政府治理俨然已是过去一个时代里公共管理最核心的议题。我们不妨以《万岁》一文为例,剖析一下“数字政府治理”的魅力之源。
在综述过去二十年间实务界与学术界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评后,《万岁》概括指出,新公共管理在治理改革中的核心思想是推动分权(Disaggregation)、绩效激励(Incentivization)和通过私有化引入竞争并改善效率(Competition)[5]。这套“组合拳”最大的弊病在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设置与政策设计日趋复杂化,越来越超出公众的理解能力。结果,公众依靠自身的集体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断弱化;而没有了社会的呼应,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果和效率也陷于停滞甚至衰退[5]。相形之下,作者认为,在《万岁》一文发表时渐渐兴起的数字政府治理(作者在文中的表述是“数字时代的治理”,即“Digital-Era Governance”,其所指应等同于本文所用的“数字政府治理”)则体现出新的改革思维:反碎片化的集权(Reintegration)、直面需求而非效率的整体视角(Needs-Based Holism)、全数字化的政策流程(Digitization Processes)。顾名思义,由此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将基于信息系统的支持,解决政府和政策的碎片化问题,精准、灵活地回应公众需求来提供公共物品,显著降低政府—社会间信息流动的成本、促进信息公开。
至此,《万岁》终于顺理成章地提出两个重要结论来倡导由新公共管理转向数字政府治理:一是如果政治精英们继续沉迷于新公共管理思维,因滞后于整个社会的学习曲线而错失向数字政府治理转型的时机,那么政府部门将变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滞后环节,在庞大的社会信息网络中日渐边缘化,由此深陷资源匮乏而无法治理[5]。二是只有依靠数字政府治理思维,数字时代的政府机器才能让内部变革跟上公民社会自组织能力不断提升的步伐。公共管理者所能做的,就是接纳这一思维,让变革与追赶的过程更加顺利[5]。
作为点睛之笔,《万岁》一文的作者在两个简短结论中突出了数字政府治理集“技术”“组织”“权威”于一身的复合特征——作为“技术”,数字政府治理能实现对线下传统政府的升级;作为“组织”,数字政府治理可以撬动政府向内的力量整合以及向外的资源获取;作为“权威”,数字政府治理使政府继续在信息网络中成为关键节点,以此维持其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这种复合特征的界定方式,直击决策者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中一些基本要素的关切——必须找到特定技术来维系组织内部的集体行动,唯此,政府相对于其他组织(市场和社会)的权威才能得到巩固。更加巧妙的是,作者以一种递进语气的措辞警告决策者,忽视数字政府治理的复合特征,将造成政府“学习曲线”的滞后、内部变革的滞后和最终的边缘化。这成功利用了全球决策者们潜在的心理恐惧——因为面对变迁,决策者最恐惧的莫过于组织管理技术代沟的出现:这不仅使政府向内的动员能力落后于其他组织,继而在围绕“权威”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而且,即便政府希望通过共享权威来缓解它和市场、社会间的竞争,技术代沟的存在也会让信息的沟通和信任的建立困难重重,大大压缩政治回旋的空间。众所周知,没有比恐惧在促成人们搁置异议、采取行动时更有效的工具了[6]。
所以,同类似主题的研究不同,《万岁》并不拘泥于“善治”的框架——不再单纯从“效率”“效能”“透明”“问责”“回应性”“整体性”等耳熟能详的维度论证数字政府治理的优越性,并据此推论数字政府治理可以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7]。它另辟蹊径地赋予数字政府治理一种无可替代的地位,警示那些试图拖延、抗拒这一模式的政府,必将面临技术脱节、组织孤立和权威崩溃。相比于在“善治”框架下锦上添花般的增量收益,这种在“技术—组织—权威”路径下力挽狂澜式的存量贡献,似乎更能让决策者感受到数字政府治理难以抗拒的魅力。
二、后真相时代的真相
十年之后,《万岁》一语成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让两国政府在公众中显得前所未有的孤立,也暴露出其政治精英们的权威已是摇摇欲坠。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失控,恐惧而羞愤的精英指责那些加入对立阵营的公众“对从政者是否在讲真话毫不介意”,把政府和政治拖进了“后真相时代”的泥潭[8]。本文无意赘述已有文献关于公众为何会支持“谎言”的分析,但必须指出,这些分析共同的逻辑起点在于构建利益冲突来解释部分公众对事实带有选择性的接纳[9]——如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草根和精英、乡村和城市、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传统产业和互联网产业、本土化和全球化间的利益冲突等。与此不同,本文试图提出两种新的分析路径。目的不仅限于更好地解释“后真相时代”的成因,还希望可以借此引发有关数字政府治理的深刻反思。
(一)注重引入对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的分析,而不是单纯分析利益冲突本身
尽管“治理”的需求和起点通常在于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失序”,但它的微观基础和核心内涵则在于提供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来重新协调利益,缓解冲突并促成合作[10-13]。利益冲突是人类群居并构成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无法幸免,然而政治危机却只发生于特定的时期。所以,一个社会的政治危机的源头不可能仅仅是利益冲突,而应是利益冲突同它的解决机制(治理)这一对复合结构之间的错配。要求解“后真相时代”开启的“真相”,我们需要超越利益冲突,重新审视此前时代中治理模式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的利益冲突主要源于基本生活物资和服务稀缺所导致的零和博弈。传统国家和政府为这种零和博弈提供的协调机制,更多依赖对利益和程序中立的保障来获得权威以及公众的遵从。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昌明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化解了人类基本物资和服务的匮乏。随之而来的,是基于相关领域的科学知识而形成的专业性晋升为现代国家利益冲突协调机制中的新要素。而且,伴随着“科学至上主义”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断弥散,“专业性”越来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各国政治精英都倾向于借助技术精英的“专家意见”和“科学结论”来统一公众因为利益冲突而分化的意见。
后真相时代开启了上述“专家治国”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危机时刻——正如英国保守党党魁迈克尔·戈乌(Michael Gove)在分析英国脱欧的原因时所说:“我想人民已经受够了那些专家了!”[14]在摩登时代被专业化分工和科层理性所“异化”的公众,激情与异见更容易为科学和专家的权威所驯服。再加之政治精英对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控制,即便有不满于“科学和理性”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群体,他们也很难在公众面前发声,无力同专家和精英进行争辩。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社交媒体的盛行,不仅能便捷地为公众提供用以挑战专家科学判断的“反例”——基于搜索引擎进行带有选择性的证据收集,还能通过所谓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有效屏蔽专家和政治精英们借助“官媒”(传统主流媒体加上官方社交媒体)来进行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依赖“专家治国”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必然陷入同英国“脱欧”相类似的权威及话语困境[8]。
(二)注重分析利益集团间在价值层面的观念差异,从而解释利益格局的形成和利益冲突的出现
诚如韦伯所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15]由于冲突的行为是即时的、可见的,所以左右它的通常是人们短期的、局部的利益;如果人们更善于用长期的和整体的视角来界定自身利益,那么短期、局部的零和博弈就可能被转化为正和博弈,冲突就更容易化解。为此,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注意到价值观对人们界定利益方式的影响,达成基于观念变迁来解释利益格局及冲突演变的理论共识。
政府治理尽管可以在“增量”改革中借助科学和专家的权威来赢得公众的支持与遵从,但在涉及社会政策的“存量”改革中,道德与价值判断的影响不断增大,科学与理性的角色变得模糊不清。比如,罗尔斯的“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16]的表述,常常被用来强调正义观念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追问——一个追求正义的社会体制究竟能否同一个追求真理的思想体系相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似乎表明,对“正义”与“真理”能否相融的关心简直是杞人忧天。因为“历史的终结”已经证明,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真理”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同一个持有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社会体制不但可以相容,而且可以完美相容,再无改进的可能。然而,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到反移民、反全球化情绪的抬头,直至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的发生,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在短短八年间就从凝聚社会的观念共识,变成了精英与公众对峙的焦点[17-18]。时过境迁,谁还敢说专家宣扬真理能为民粹伸张的正义所容?
必须指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所营造出的“回音室效应”在前述正义观念的快速分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精英掌控教育和传媒体系的格局下,一种竞争性的公正观念通常是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公众虽然可能早已对精英所推崇的正义观念及其实施方式心存不满,但由于竞争性的公正观念缺少被感知的渠道,公众只好被动地选择向精英进行“呼吁”,寄希望于精英能够进行改革来平息公众的不满。但是,“回音室效应”的出现,让竞争性的正义观念可以在“官方”体系之外被感知、被放大。公众可以断然“退出”精英主导的正义观念系统,另起炉灶来分庭抗礼。最终,观念的差异,让利益的分歧变得难以调和,让官民间随之而来的行为对抗触发了政治危机[19-20]。
三、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后真相时代的政治危机毫不留情地表明,过去十年间席卷全球的数字政府治理运动,并没有如预期般帮助现代政府赢得争取民意、巩固权威的“互联网战役”。可出人意料的是,数字政府治理非但没有因此走下神坛,反而由于和政治危机同期出现的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为什么数字政府治理的思维方式会在危机过后的社会科学反思中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免疫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万岁》一文中倡导数字政府治理的基本逻辑:技术—组织—权威,即如果不能及时升级政府的技术能力,那么作为组织的政府就会被边缘化和孤立化,政府在整个治理活动中的权威也会遭到削弱。这一基本逻辑下隐含的命题是,技术能力升级是维系政府权威的必要条件。将数字政府治理构建为巩固政府治理权威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可以借助技术进步频发的时代特征,让深陷“权威恐慌”的政府争先恐后地拥抱这种新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则机智地为数字政府治理开具了一份“免责声明”——既然是必要条件,没有它就必然危及权威,可有了它也不能保证政府权威高枕无忧。面对来势汹汹的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在不断延长的问责清单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曾将自己标榜为“万灵药”的“自由市场”“竞争性民主”“全球化”,而非仅作为必要条件的数字政府治理。但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又迫使身处信息风暴中心的政府必须当机立断,抓住身边最容易抓到的东西,把它作为挽救自身权威的希望。既然“可能”是技术变革引发了危机,那么利用同样建构于技术变革基础上的数字政府治理来应对危机,似乎正是对症下药了。在危机的重压之下,将数字政府治理作为对策,既可以避开批评的焦点,又可以树立起“对症下药”的形象,也就无怪乎它具有对反思免疫的魅力了。
本文无意争辩在数字政府治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谁更应该为后真相时代的政治危机负责,但是前文对这场政治危机真相的探讨表明,塑造利益格局的观念和协调利益冲突的机制可能是触发危机的更深层原因。那么,在明确技术变革同观念分歧和利益冲突失调的关系之前,鼓动以数字政府治理来应对后真相时代的逻辑就显得“模糊而乐观”[10],是在沿用“必要条件”的魅力。本文余下部分的工作,就是要“对症下药”地检视技术—组织—权威这一数字政府治理基本逻辑在解决观念分歧和利益冲突失调问题时的作用与局限,在明确数字政府治理“不能做什么”的过程中,完成对其的“祛魅”。这种“祛魅”绝非意在让数字政府治理的前景变得消极、悲观,而是希望人们可以对它在后真相时代的价值形成更加“清晰而现实”的预期,见图1。

图1 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逻辑
(一)技术的祛魅
1.已有的数字政府治理文献非常热衷于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论证互联网技术对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官民互动并最终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的作用[7]。作为数字政府治理最被广泛认同的魅力,前述乐观的判断建立于互联网能显著降低数据传输成本的技术特征之上,其对策价值看似无可争辩。但冷静分析后不难发现其中同样隐含“必要条件”的逻辑陷阱——数据的充分共享,只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必要条件。如果数据共享要成为充要条件,至少还需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数据呈现的形式能够充分为公众所理解,只有数据中揭示的趋势和特征能够为使用者所理解,数据才完成向信息的转化;第二,由数据转化成的信息还必须为公众所信任,即从信息转化成公众头脑中的真相。第一个条件的满足,有赖于数据提供者对数据使用者认知能力和模式的“服从”;第二个条件的满足则是对第一个条件的进阶要求,意味着数据提供者将面临竞争,他对数据的呈现方式必须更加符合数据使用者的认知能力和模式。
一经采用这种“充要条件”的逻辑来检视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魅力,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为数字政府治理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提供经验证据的研究,普遍存在样本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即选择了缺乏竞争性的数据供给情景来凸显线上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这种做法的弊端在英国脱欧的案例中得以充分暴露——在“脱欧”方(Leave)与“留欧”方(Stay)进入为公投而大肆造势的阶段之前,执政的“留欧”方长期坚持例行公开其精心选取的社会经济指标,寄希望于借此提升公众对于政府“留欧”政策的信任和信心。然而,当“脱欧”方推出他们的证据和口号,并利用互联网、传统媒体、甚至公交汽车来进行铺天盖地地宣传时,更多原本持中立态度的选民,最终采信了“脱欧”方而非官方的数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脱欧”方提供的数据被官方和专家们抨击为是片面的、误导的,但在采信这些数据的公众看来,它们传递的信息比官方数据更加简洁、易懂。身为数字政府治理先驱的英国尚且如此,数字政府治理要真正做到可以借助信息公开来赢得公众的信任与信心,依然任重而道远。
2.同样基于互联网降低数据交流成本的特征,数字政府治理被认为可以大大方便官民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寻求到更加有效的冲突协调机制。众所周知,互动的效果取决于双方对对方信息的准确解读,信息传播中的实际沟通发生于信源与信宿经验范围内的共同领域[21]。恰如前文所述,当前数字政府治理的官方话语体系普遍是精英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的,所以它对数据的呈现方式很难顾及普通公众的认知能力和模式[22]。这样一来,所谓的网上官民互动、公众参与,其实更多是政府在以点对点的方式反复对公众进行科学和理性地说教。“技术与变革并不是同义词”[23]。如此下去,数字政府治理徒有“数据传输技术”上的升级,却没有“信息传播技术”上的革新,自然难以推出新的冲突协调机制和观念共识来化解后真相时代的政治危机。
(二)组织的祛魅
数字政府治理的倡导者提出,由线下政府到线上政府的技术升级,不仅具有由内向外扩散信息、再由外向内获取反馈的意义,还具有由内向外整合资源、再由外向内积聚社会注意力的价值。在后一个维度上,传统政府因为科层制运作而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可以得到克服,信息孤岛间的隔膜更容易突破;同时,更具整体性的政府也可以在同企业及社会组织争夺互联网资源和网民注意力时形成更强的竞争力,避免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于科层制管理技术形成的条块分割的部门主义(Departmentalism)权利观念同基于信息管理技术所形成的整体论(Holism)观念形成尖锐的对立。由于长期笼罩在科层制下的组织内部利益格局已经高度固化,新兴的信息技术往往不能改变组织,反而会为组织所吸纳[24],被用来巩固原来的组织结构,而不是打开传播渠道[25]。其结果是,数字政府虽然能够在数据意义上建立起整合与共享的平台,但加工数据、提供信息的工作仍然由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割进行。这种“前厂后店”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数据孤岛,但并没有打破信息孤岛,无法将数据转化为经过系统优化的信息,也就难以实现由内向外的政府效能与效率提升。
受制于部门主义的权利观念以及政治精英的主流政治观念,数字政府治理由外向内的资源与注意力吸纳过程同样不可避免地为条条块块所分割和主导,为“政治正确”的观念所束缚。以美国为例,政府同互联网企业的密切合作依然只能在国土安全、教育、能源等传统领域借助传统职能部门的推动得以开展。但对来势汹汹、社会破坏性极强的社交媒体谣言及阴谋论,由于部门职责不明,居然只能依靠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企业社会责任自律来予以应对;由于忌惮对自由主义政治信念的触犯,国家权力机关的信息平台更是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地坐视政治危机的蔓延[26]。所以,仅仅在数据层面进行整体化包装的政府,还是难以同要求信息整体化的市场和社会相对接。而没有通畅连接的信息网络,又何谈从企业和公众那里去吸纳资源和注意力呢?[27]
至此,我们发现,今天的数字政府治理其实是一个新兴的管理技术为更强大的传统管理技术以及建构其上的传统组织所吸纳后的产物。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封闭而非开放的权利观念,是零和而非正和的利益格局,是机械而非人本的行为模式。由这样一个组织所提供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和正义观念及原则,是否能够为观念—利益—行为系统在互联网影响下深刻变革的市场和社会组织所接受,答案并不令人乐观,至少充满不确定性。
(三)权威的祛魅
数字政府治理的倡导者非常敏锐地预见到,伴随后工业化进程中利益的日趋多元化和社会网络的密殖,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专家作为复杂冲突仲裁权威的公信力不断为“民间高手”所蚕食。而在未来,希望像传统社会那样,找到利益不相关的主体或者是冲突各方都认可的公正程序,并据此确立冲突仲裁的权威,可能性微乎其微。为此,数字政府治理应该借助互联网努力改变政府的“铁面”形象,建立一种关联型的权威(Relational Authority)——能够“聆听”公众的诉求并做出积极的回应,在决策过程中采纳公众的意见,善于和公民组织互动、合作并分享权威。社会冲突理论发现,这种关联型权威容易被冲突方当作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更有希望在专业的、中立的权威或程序缺失时,引导冲突方为了自己信任的利益共同体做出暂时的妥协和让步[28],从而化解激烈的冲突。
然而,关联型权威的建立,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化的信任建立过程。要求被以去人格化为特征的科层制所控制的政府,采用去人格化的信息技术,来建立一种人格化的冲突仲裁权威,这显然是一个悖论[29]。而实施这种缘木求鱼的权威构建策略,结果是数字政府治理普遍追求程序的标准化、绩效的数量化和互动的智能化①智能化的含义是在给定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寻求算法的优化。由于价值标准的给定是外生的,因此智能化本身是一个去人格化的过程。。相较于科层制所推动的去人格化,数字政府治理的去人格化范围更广、深度更甚。
更广、更深的去人格化,意味着对科学、理性以及代表它们的专家角色的更大依赖,也意味着科层制下支配政府治理的精英价值观依然盛行。所以,过去十年的数字政府治理运动,既不能提供专家治国以外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也难以在观念层面促成精英与公众的和解与共识。当社会中的利益冲突迟迟得不到缓解,就会逐渐蔓延成为观念的对立;而当观念的对立缺少对话与和解的平台,社会就容易从分裂走向极化,使得原有的秩序变得岌岌可危。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政府治理构建关联型权威策略的失误,对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的形成难辞其咎。
四、结语
科学主义和现代化的观念在全球政治精英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宁愿相信问题出在技术使用得不充分,而不是技术本身不足以解决问题[23]。过去十年间,数字政府治理运动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中独领风骚,它所经历的严肃批评同它受到的追捧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而这种失衡能在后真相时代的政治危机后依然延续更是令人惊愕。
当政府和它后面的政治精英发现互联网和它后面的社会正在脱离自己的控制时,指导政府和政治精英应对互联网社会的数字政府治理运动理应经历深刻的反思。考虑到数字政府治理在危机前后无法撼动的明星地位,笔者认为对它的批评、反思也同样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提炼出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组织—权威”魅力要素,分析了这些魅力要素对于身处技术与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精英的心理作用。然后,我们转向对于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成因的讨论: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失灵和正义观念在精英与大众间的冲突,被我们列为是利益冲突之外更具解释力的变量。而这两个变量所反映的,正是互联网时代大众对于政治精英基于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建立的权威的抵制。最后,在揭示了数字政府治理内含的必要条件逻辑后,我们逐一分析了其魅力要素在利益冲突协调机制重建与观念冲突化解中的理想作用和局限性,完成对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必须再次强调,本文的祛魅并不是要使数字政府治理的前景变得消极、暗淡。毕竟,在一个技术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面临其影响和后果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必须去接纳技术。以中国的“网络问政”平台发展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级党政机关踊跃将以微博、微信和手机客户端为代表的“两微一端”建设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升政府回应性的新平台、新机制。这种“互联网+”思维在群众路线中的创造性应用,已经将中国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水平推向国际前沿。但是,提倡接纳技术的数字政府治理运动不应成为哈耶克笔下“知识的僭越”,因为对于如何在后真相时代重建治理的权威和秩序,除了技术,人们还所知甚少[30]。所以,我国的“网络问政”,不能重复西方国家追求“回复率”“回复时效性”“问题解决率”的片面做法,要避免因为追求行政体系内的问政“绩效”而落入脱离群众的陷阱——不能只回应群众明确的要求,而忽视群众建设性的意见;不能只照章办事、自说自话,而错失借官民互动来更新服务思维的机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4]。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数字政府治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一场创造性的反思正当其时。
[1]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
[2]OECD/ITU.M-government:Mobile Technologies for Responsive Governments and Connected Societies[R].Paris:OECD Publishing/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2011:70.
[3]UN.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16:E-government in Suppor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New York:United Nations,2016:14.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 10月 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5]DUNLEAVY P,MARGETTS H, BASTOW S,&TINKLER J.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Long Live Digital-Era Governance [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6,16(3):467-494.
[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北京:新视界出版社,2010:2.
[7]TOLBERT C J&MOSSBERGER K.The Effects of E-Government on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3):354-369.
[8]FUREDI F.A Revolt Against Deference[EB/OL].(2017-03-31)[2017-04-06].http://www.spiked-online.com/spiked-review/article/a-revolt-against-deference/19611#.Wf-ysIZx3-Y.
[8]Furedi F.A Revolt Against Deference [EB/OL]. (2017-03-31)[2017-04-06].http://www.spiked-online.com/spiked-review/article/a-revolt-against-deference/19611#.Wf-ysIZx3-Y.
[9]王礼鑫,莫勇波.基于知识视角的政策制定基本问题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7,(6):90-96.
[10]菲利普·施密特.“治理”的概念:定义、诠释与使用[J].赫宁,译.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6,(1):1-26.
[11]于君博.治理的微观基础——一个基于“合作”的概念框架[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5,(2):78-95.
[12]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J].社会科学研究,2012,(3):35-42.
[13]李文钊.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6):47-57.
[14]MORRIS H.Dangerously blinded by science[EB/OL].(2017-09-17)[2018-02-16].http://www.chinadaily.com.cn/kindle/2017-09/17/content_32114144.htm.
[15]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6.
[16]RAWLS J.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3.
[17]WALT S M.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EB/OL].(2016-06-26)[2018-02-10].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6/26/the-collapse-of-theliberal-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
[18]ALBERT O.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9.
[19]HIRSCHMAN A O.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9.
[20]RODRIK D.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4,28(1):189-208.
[21]沃纳·赛福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
[22]梁春晓.互联网革命对知识与治理体系的重塑[J].文化纵横,2017,(4):98-102.
[23]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2.
[24]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技术与制度的辩证法[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2):4-11.
[25]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
[26]D’ANCONA M.Post Truth:The New War on Truth and How to Fight Back [M].London,UK:Ebury Press,2017:45.
[27]何包钢,吴进进.社会矛盾与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兴起[J].开放时代,2017,(3):101-124.
[28]TYLER T R.Justic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J].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12,25(4):355-375.
[29]孔繁斌.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知识扩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31-38.
[30]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