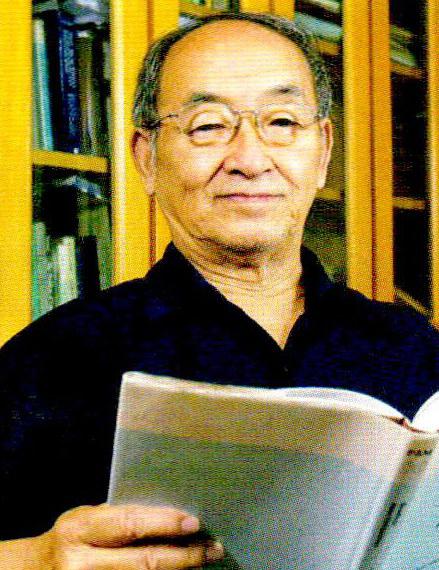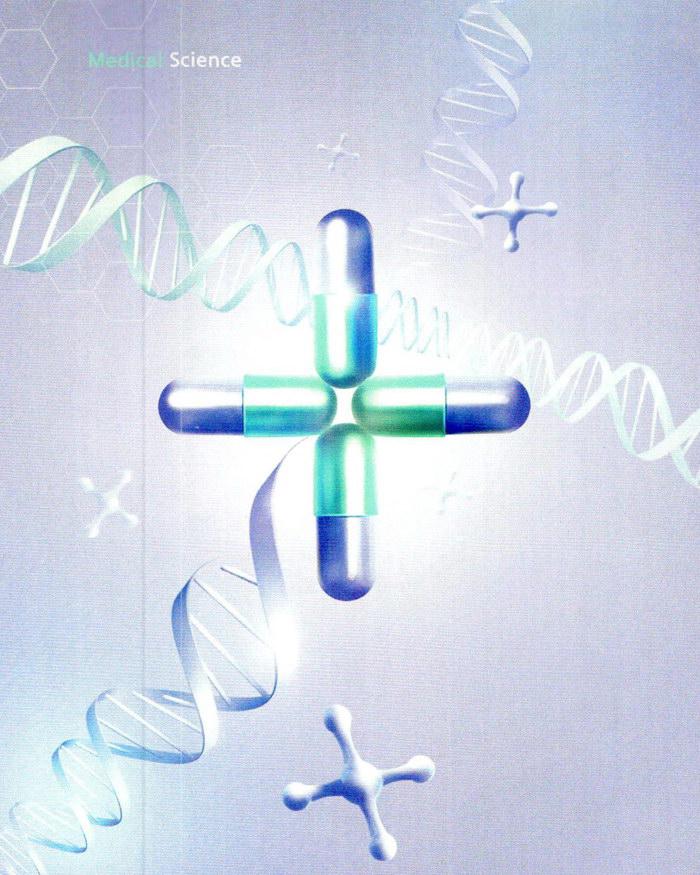这样的“你”,还是不是你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所所长,国际哲学院院士,著有《生命伦理学》《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等,并在中国、法国、德国、日本、罗马尼亚、西班牙、美国等国的杂志和书籍中发表有关生命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论文400余篇,撰写和编辑书籍25册。
对疾病治疗的迫切要求,使得现在很多新技术只关注能治疗什么病,很少有人关注它们是否会影响到个人的身份认同。而实际上,对人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在医学上,我们可以发现有少数人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这是一种病态,被称为多重身份障碍。英国牛津大学已故哲学家凯瑟琳·威尔克斯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讨论多重身份障碍问题,其中谈到一个案例。这个人有三重人格或身份,她会从一种身份转换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俨然是三个不同的人,但她却不自觉,并不知道自己有三重身份。此病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这种身份认同的改变并非由技术引起。如今,不断翻新的生物技术的应用,则可能真的会对人的身份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
另一个星球的“你”,还是不是你
在“换头术”热炒之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生命伦理学界就已经讨论过裂脑(split-brain)人的问题。正常人在两个大脑半球之间,有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胼胝体,因此虽然两个大脑半球各有分工,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其身份是统一的。后来为了治疗癫痫的发作,医生发现将胼胝体切断,可减缓癫痫发病,但这样一来,病人就变成了“裂脑人”。裂脑人的特点是,他似乎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大脑左半球显示的身份,另一个则是大腦右半球显示的身份。
例如有一位48岁的老兵约翰,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医生无奈之下为他做了裂脑手术,结果癫痫病是控制住了,但其行为方式却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吃饭时,他一只手把碗推开,另一只手又把碗往回拉。他有时一手推开亲人,另一只手又把亲人拉回来。更有甚者,有一天早上起床,他一只手把裤子提上来,另一只手又把裤子拼命往下拉,直到把裤子撕扯成两半为止。如果将一张年轻女子照片的左半部和一个小男孩照片的右半部拼成一张照片给他看,他会用手指着年轻女子,口中却说:“一个小孩。”
那么,切断胼胝体的手术是否改变了病人的身份呢?有人认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两个人,有两个身份。这一论断的实质是,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决定于大脑半球的功能。一般来说,人的右脑与想象、整体思维、直觉、艺术、韵律、非言语信息处理有关,而人的左脑与逻辑、排序、线性思维、数学、言语信息处理有关。不同的人,处于优先地位的是不同的半球,因而显示他处于优先地位的半球的身份。然而,英国哲学家德里克·帕森斯则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人的身份问题。如果发明一种先进的技术,将你分子结构上的所有信息全部传送到另一个星球。那个星球接受有关你的全部信息后,复制出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么,你与另一个星球上的“你”是不是一个人?是否有着完全相同的身份呢?德里克-帕森斯认为不是。那个星球上的人不是你,他拥有他的身份,因为他的生活、他与那个星球上环境的互动,与你的生活、你与地球上环境的互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如果一个裂脑人快要去世了,我们把他大脑的右半球移植到甲身上,把他大脑的左半球移植到乙身上,然后再将甲大脑的右半球和乙大脑的左半球一起移植到丙的身体内。那么,甲、乙、丙应该各有各的身份,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他们与各自特有的环境发生着互动。这也就是否定了将基因组作为人身份的论点,甲、乙、丙的基因组是相同的,但他们的身份互不相同。
现实世界里,同卵双生子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基因组是相同的,但自他们出生后,他们的脑与他们各自的身体以及环境的互动是不同的,而脑中神经结构的建立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具有不同的身份,因而需要发给他们不同的身份证,即使他们的基因组相同。
甲的头安在乙的身上,便有了丙
与这些研究并行的,是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的思维、认知或智能是什么?它们是否能够被归结为计算?老式的人工智能是按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提出“思维就是计算”的命题进行的。然而,人的思维不仅仅是计算或信息处理,智能必须被赋予身体、嵌入环境。唯有这样,才能够完成智能作业。这是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一次革命。这一革命对人的身份研究十分重要。
在器官移植的应用过程中,身份改变的问题也曾被一再提出。例如人们声称,换了心脏的病人,其心情、脾性、情态也改变了。但我们尚未见到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种改变已经到达身份改变的程度。也有人设想,如果一个病人的内脏器官全部换掉,可能就改变了他的身份,但这也没有科学的证据来证明。恐怕最有可能改变病人身份的,就是头颅移植或脑移植。
就拿我们最近两年讨论得比较多的头颅移植为例。当然,现在要做头颅移植,科学上不可能、伦理上不允许、法律上犯禁。但撇开这些不谈,假设有个绝顶聪明的病人甲,患有英国大科学家霍金那样的肌肉萎缩疾病,苦不堪言,希望能将他的脑袋移植到出了车祸、处于脑死亡状态、身体健康的乙身上。我们还要假设头颅移植手术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成熟,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做手术的移植外科医生是否就能救治病人甲呢?结果可能不是。
当医生把甲的头颅安在乙的身体上时,假设手术成功了,那么形成的可能是另一个人丙,而不是原来的甲。这个新形成的丙是一个同种嵌合体,是甲的身份与乙的身份的混合,因为甲的大脑已经不能与甲的身体互动,而是在与乙的身体互动。丙拥有了一个独特的身份,甲和乙都死了。他不能持有甲的身份证,应该去派出所另外申请一个新的身份证。
在此还有必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异种移植会不会改变病人的身份呢?由于供移植的器官严重短缺,科学家设法将猪的器官移植到病人體内,因为猪的有些器官与人的大小差不多。然而,猪与人的组织极不匹配,猪器官一旦移植到人体,就会发生急性免疫排斥。现在设法将人体干细胞注入猪胚胎内,希望等猪长大后生长出具有人体细胞的器官,以避免免疫排斥。另外就是猪器官内有类似艾滋病病毒那样的逆转录病毒,科学家正在设法采用基因编辑的办法将病毒剪除。如果这些都取得了成功,将猪器官移植到人体内,会不会使病人的身份发生改变呢?我想,这可能与人体器官移植一样,首先,个别器官的置换,对人整体的影响不大;其次,对人身份影响最大的是脑,如果仅仅是将人肾换成猪肾,身份应该不会有很大变化。
类似人,性状和能力却“超人”
那么,还有哪些技术会改变人的身份呢?
首先就是变性术。一个人接受变性手术后,他或她的身体发生了改变,脑还是原来的脑,但这个脑要与变了性的身体发生互动,也要与不同的环境互动。因此,他或她的身份会发生改变,其中当然也包括性别的改变,他或她不能沿用原来的身份证,必须另外申请一张新的身份证。
基因编辑可能会影响人的身份,但这取决于编辑哪些基因。目前基因编辑的主要目标是致病基因,这里讲的致病基因是引起人的身体疾病的基因。如果科学家发现了决定人的心理状态或引起精神病的基因,那么在用基因编辑进行改变人的心理状态或治疗精神疾病时,就有可能改变人的身份。当然,现在距离做到这一点还比较远。
基因编辑如果用于增强人的性状或能力,那也有可能改变人的身份。这里讲的增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善、改进或加强,而是指将人的性状或能力增强到超过我们的智人物种固有的性状或能力的范围。例如,人没有夜视的能力,如果我们通过基因编辑将猫科动物的夜视基因连接到某个人身上,使他具备夜视能力,这就是增强。未来学家认为,如果充分利用各种技术使人的性状或能力得到增强,甚至人可拥有48条染色体,那么那时的人就变成“后人”(posthumans)了。在逐步增强人的性状和能力的过程中,或在人与“后人”之间的过渡时间内存在的人,就被称为“过渡人”(transhumans)。那时他在大多数方面类似一个人,但拥有超越标准的人具备的能力。也就是说,作为人的身份已经开始改变了。
还有可能改变人身份的,是人与非人动物的混合体技术,包括杂合体和嵌合体。像动物学家将马与驴、狮与虎进行杂交那样,将人与任何动物杂交目前都是不允许的。以前曾有科学家建议,将人与猿杂交,形成半人半猿的动物,让它们去做人类不愿意做的工作,如排雷、打扫厕所等,这种建议被否定了。现在允许做的是细胞质杂合体,即将某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到某种动物的去核卵细胞内,形成具有动物细胞质的杂合体。但这类研究仅允许在体外进行,而且这种细胞质杂合体的研究仅允许在其14天的存活时间内进行,因为这段时间这种胚胎不存在身份问题。但如果允许将这种混合体胚胎植入子宫,并将其生出来,那么这种人一非人动物混合体的婴儿是否会改变人的身份,就成为问题了。
“技术智人”更少有人的要素
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有些妇女患有线粒体病,她的线粒体基因有缺陷。线粒体在细胞质内。线粒体基因有缺陷就会影响线粒体为细胞提供能量或动力的功能,这会影响到人体细胞的正常功能,尤其像心肌细胞,每天要搏动许多次,心肌细胞缺乏能量,不能使心肌发挥正常功能。
目前没有治疗这些线粒体病的办法,但可以预防这些妇女生出的孩子患这种病。那就是将她卵细胞内的细胞核取出,移植到另一位线粒体正常的妇女的去核卵细胞内,然后设法使这个含有另一位妇女正常线粒体的卵与这位妇女丈夫的精子受精,这样生出的孩子就不会患线粒体病。
那么,这种线粒体置换技术对未来孩子的身份影响会很大吗?不会。因为影响一个人身份的因素主要在细胞核的基因组内,不在线粒体的基因组内。线粒体基因组的数量很小,大约只有13条基因,而细胞核内的基因则有2万多条。
最后一项可能影响人身份的技术,是脑机接口(brain-machineinterface)。简单的脑机接口,就像将一个帮助我们记忆或加速我们信息处理的芯片植入我们体内。当我们对外来的信息进行处理时,是这个芯片在处理信息,还是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信息,还是脑和芯片联合起来一起处理信息?复杂一些的,是将我们与计算机连接起来。例如我们将肌肉麻痹的病人与计算机连接起来,可以帮助肌肉麻痹的病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操作假肢。
在这里,那位肌肉麻痹的病人与计算机进行了互动。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脑与计算机的接口只是一个工具,还是病人“自己”的一部分?脑机接口的使用者是否会成为一个“电子人”?甚至会影响我们的人性、人的身份呢?
有人认为影响不大,而有人认为这类技术发展下去,我们身体有更多的机器人(robot)要素,而更少有人(human)的要素了,我们就有失去使我们成为人的东西的风险,甚至令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智人物种的一员,而成为“功能性人机杂合体”(functionalman-machinehyhrid)或“技术智人”(Homo sapiens technologicus)。这样,我们原来作为人(智人物种一员)的身份就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