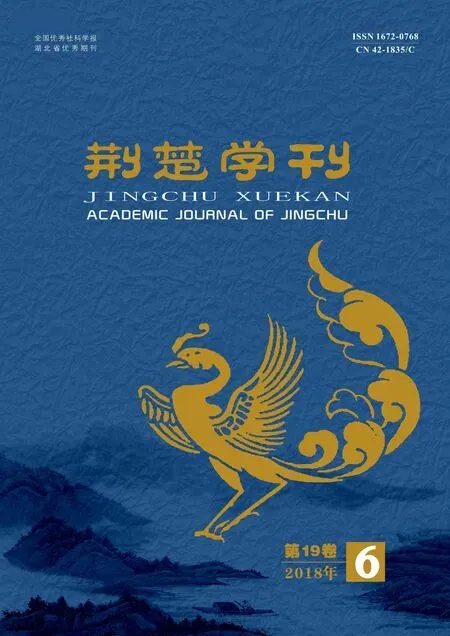明清时期湖北文学批评中的楚文化创新影响论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楚文化是中华文化之中非常有特色和活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湖北是楚国的核心区,研究楚文化对后世文学发生的影响,从明清时期的湖北入手,自有其典型性。
历史上的楚国,枢要之地在湖北。但直至明代以前,行政上的湖北治域尚未形成,所以楚文化在湖北人的心中还是很平淡的。洪武九年(1376),明朝设立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基本囊括两湖地域,其中洞庭湖以北即湖北,将湖北今境除了英山、建始二县之外的所有区域,首次纳入同一高层政区。湖广虽为一统一政区,但八百里洞庭事实上将之分隔为湖北湖南两个区域,统一施政,多有不便,所以,某些业务的有限分治,时有发生。尤其是正德五年(1510),“以大湖(洞庭湖)中分南北”,设置南北巡按御史二人,分按湖北、湖南。(参《明武宗实录》卷59“正德五年正月癸亥”)这个官职是省级配置,湖北与湖南分省已显苗头。虽然基本独立的湖北政区要到康熙三年设置,然而,期间有关行政、司法、科举、粮政、民族、军政等方面南北分理之策,多有出台。这些就使得湖北成为了一个机能文化区,具有文化发生学的作用。大量文献显示,此后的湖北文人乐道楚文化,以楚文化自豪;楚文化在湖北文人身上形成浓郁的区域文化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明清时期湖北文学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在王齐洲、王泽龙所著《湖北文学史》和湖北作协组编的《湖北文学通史》中,有所体现,但限于体例,明显缺乏专门性、系统性、鲜明性。因此,从明清时期的湖北入手,研究楚文化对后世文学发生的影响,颇具学术意义。
有关楚文化对后世文学发生的影响,中外研究成果甚夥,其中有两部集大成的著作:郭维森的《屈原评传》和蔡靖泉的《楚文化流变史》。前著集中论述了屈骚对后世文学发生的影响。后著论述了楚文化在以后各个朝代文化中的流变,其中就包含楚文化对各个时期文学的影响。纵观这些成果,总体上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探索楚文化的影响,至于楚文化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本文所关注的正是楚文化对明清时期湖北文学批评的影响。
文学发展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情形复杂,这就往往导致学界在探讨某种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时出现抽象的武断。如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道家精神等,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中都包含着它们的源泉,如果探讨楚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时,每逢这些精神便属诸楚文化的影响,就难免武断。事实上,现在的楚学界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楚文化影响论的泛化倾向。鉴于此,本文拟以明清时期湖北文人自身的言论为依据,论述楚文化对湖北文学的影响,看看作为受楚文化影响的亲身经历者,他们究竟意识到楚文化怎样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别有其学术意义。
明清时期的湖北文学批评,包含大量有关楚文化影响的言论,涉及到的楚文化因素有楚国的立国史,楚人多忧、多怨、贵真、气直大激昂、才气踔厉、无门户之见、能自树立的文化性格,惟楚有才和楚地悠久的文化文学创新传统,等等。经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核心,那便是楚文化的创新精神,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指向这个核心。本文拟抓住这个核心,考察楚文化对明清时期湖北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楚文化培育湖北文人创新精神的要素论
(一)楚国的兴族立国史和地理优势是培育湖北文人创新精神的基础

就地理位置来看,正如光绪时钟祥黄振鋐所言“楚居天下之中,当水陆之冲”,因此楚国有着极强的文化交汇力、融合力,胸怀宽广,视野开阔,有利于文学的创新。康熙时孝感夏力恕在《湖北诗佩序》中云:“天下名山大川,其环拱于外而络绎于中者莫如楚,楚固四方风气之所通,岂仅娖娖焉守一家言,与海内执牛耳诸公若熏莸冰炭之不相入哉!有明一代,曰竟陵,曰公安,竟陵、公安尚矣。竟陵一家也,公安又一家也,楚地之不为竟陵、公安而自为一家者,岂系无人?”[5]
这位夏力恕目光敏锐,看出了楚国是一个中央大国,四方风气之所通,文化包容,文学上善于与不同流派之间融合生长,显示出一派文学创新的生气,创造出了“公安”、“竟陵”诸派的辉煌。正如万历时蕲水郭士望所说:“楚人无门户,此楚人之得也。”
(二)楚人的性情气质培育了湖北文人创新精神的主体特征
明清时期湖北文人对楚人的性情气质多有评价,比较集中的观点有:楚人多忧、多怨、贵真,气直大激昂,才气踔厉,无门户之见,能自树立等等。从这些评论的逻辑来看,他们要强调的核心是不傍门户,能自树立。多忧体现改变现状的责任,多怨是对现状的批评,贵真是创新的人性依据,直大激昂是创新的气魄,才气踔厉是创新的力量。明清时期的湖北文人清醒意识到,楚人的这些性情气质培育了他们文学创新精神的主体特征。
贵真是创新的人性依据,同样也是文学创新的人性依据。中国文学自来就有修辞立其诚的古训,从来文章传真不传伪。明清湖北文人看到了楚人有着鲜明的保真性格特点,正因为如此,才创造了文学的辉煌。万历时蕲水郭士望在《蕲上社初集序》中云:“宇内博士家,无不高楚人才分者。”接着,郭氏指出楚人才分高妙的性情根据:“夫文,与人不相远也。幼清有言:为文而欲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为文;为人而欲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为人。故人不破绽,定非真人;文不破绽,定非真文。”[6]指明了真文源自真人,而不是完人(不破绽)。所谓完人,全合道德准则,故为文亦汲汲于法度,“十指渐欲缩”,“必不能有所发明”。那么,真人为什么会写出真文呢?万历时夷陵雷思霈云:“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并且将袁宏道作为一面大纛昭示这番道理:“(石公)但任吾真率而已。…石公之文,石公之自为文也,明文也;石公之诗,石公之自为诗也,明诗也。……或古人所有,石公不必有;或古人所无,石公不必无…则石公独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也。石公,楚人也。”[7]作为楚人的袁宏道(石公),但任情真率,故能与古人抗首,自铸伟词,成就了楚人在明代文坛上的辉煌。这种看法也是袁石公的自道,他曾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8]可以看出,这些立论,同时也是对于明代文坛拟古之风的有力批判。
多忧善怨也是楚人的气质。明清湖北文人看到了楚人多忧善怨。明末清初景陵邹枚在《雅笑编自序》中云:“邹荻翁曰:‘楚人始为骚经。’余楚人,多忧,固近之矣。”[9]嘉靖时兴国吴国伦云:“予读《楚辞》,而知楚之人善怨,其天性哉。”“夫《离骚》,自怨生也。”[10]袁宏道云:“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斎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乎?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11]他们认为楚人本性多忧善怨,文学上的典型便是《离骚》。其实,说多忧善怨是楚人的天性,并不过分。楚族的文化自来就与儒家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中原文化有所不同,儒家道德对感情的抑制相对较轻;同时在儒家文化之外,非常重视道家文化,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因此,楚人的天性之中主体精神格外鲜明。体现在文学上,便是文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情感抒发,即所谓的多忧善怨。
楚人这种性格特征,内含着文学创新的力量。嘉靖时沔阳陈文烛在《少泉集序》中云:“夫骚,楚辞也。三闾大夫,憔悴湘潭,忠而抱愤,溢为苦言。凄婉忉怛,不能泽以中和。孟、杜两襄阳,睹时艰而遭隐沦,其诗穷而后工。余每读‘哀郢’、‘怀沙’之章,‘垂老’、‘无家’之叹,‘不才’、‘多病’之咏,千载而下,使人沾襟。倘所谓楚人之深于怨乎!”认为屈原“忠而抱愤,溢为苦言”而成《离骚》,也就是说《离骚》是忧怨之声;并总体解释了这种文学创造感人至深的原因,即“凄婉忉怛,不能泽以中和”,认为这种深于怨的情感,冲破了儒家中正平和的抒情界域,勃发出了“使人沾襟”的动人力量;还援引孟浩然和杜甫印证。接着通过当时京山太仆少卿王少泉的诗作,具体探讨了这种原因:“(王少泉抱器而濩落终身,其诗)情属景生,神在象外,如元造播物,色相种种。一物之中,生意俱足。其文丽而则,正而不迂。苕发颖竖,离众绝志,而奇气横逸,不可控驭。”认为王少泉怀忧怨之深情,则奇气横逸,不可控驭;托诸景,故神行于化境之中;这种文学上的任情挥洒,很像“元造播物”,任凭“色相种种”,每一种都“生意俱足”。所以陈文烛云:“若先生者,其张楚乎。”[12]认为王少泉的诗风,与《离骚》一道,彰显了楚国文学的创新精神。
明清湖北文人还看到了楚人直大激昂的性格特点,这正是创新所需要的气魄。咸丰、同治时黄梅吴铎云:“楚人气悍,能自树立。”[13]楚人的文气充沛激荡,故能创立成就。气本来是一个哲学范畴,转用于文论之后成了一个基本的文论范畴,这里的气,是指文人的精神生命力。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韩愈提出“气盛言宜”,方东树提出“诗文者生气也”,都主张气本言末,诗文的根本在于生气流贯。所谓楚人气悍,是指楚地文人的精神生命力充沛饱满,放逸奔涌。明末嘉鱼尹民兴在《姚天逋诗序》中云:“艾轩曰:‘诗芽茁,自楚国。’盖以风始江汉,骚肇三闾也。楚人以直大激昂之气泄诸诗歌,故能内贡丹心,外仪峻表,静言哦之,穆然怀矣。”[14]指出楚人气悍,所以风骚皆于楚地发其端。尹民兴在《某小吏学诗序》中解释这种原因,认为以直大激昂之气泄诸诗歌,能破除和平温厚,能“广心肆志”,“自酣自唱”,“自颠自狂”,故能自造门户。[15]乾隆时汉阳彭湘怀历数有明以来,楚地文人尚气性所激发的诗歌创造:“声诗之盛,三百年来莫楚若矣。盖楚风直质,尚气性,能不傍门户。若兴国、黄冈(谓王稚钦、伯固两公)、公安、景陵(钟、谭前有鲁公振之),皆是也。杜茶村推为楚风之极盛。”[16]其中特别是公安派主将袁宏道,史载其“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17]不仅年少才情富赡,更具有非同一般的勇气与胆略,可谓“气悍”。
才气踔厉是实现文学创新的力量。楚人,因得江山之助,又得丰富而瑰丽的文化滋养,还得舒展的精神滋养,因而文才骏发踔厉,这恰恰是楚人在文学方面除旧布新的实力。吴铎在《龙冈山人诗钞序》中云:“明季公安、竟陵,为世所诟病,然并能以其力易天下者。说者曰‘楚人气悍’则然,夫非徒气也,唯其能自树立也。右臣(洪良品——引者)不求悦于里耳,而日以金钟大镛,铿鍧于折杨、皇荂之间,其不谓之能自树立者与!”[18]认为文学创新,固然离不开悍气,但又不能止于悍气,还须有才气。明季公安“三袁”、竟陵“钟、谭”,清季龙冈山人洪良品,都不徒“气悍”,更重要的是“并能以其力易天下”,能自树立。
(三)楚地悠久的文化创新传统是养成湖北文人创新自信的资本
1.这种创新自信来自屈原的伟大人格和文学成就。
自《诗经》以后,屈原所创造的楚辞成为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这一点,湖北文人有着强烈的认同。崇祯时蕲水官抚辰在《霜轮上人诗序》中云:“自《诗》亡,楚固诗之祖也。”[19]同治、光绪间孝感龙登甲在《楚辞原本六艺论》中云:“粤自风雅不作,文体屡迁,屈宋继兴,爰创骚体,撷六艺之精华,为艺文之准臬,信乎辞赋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20]都指出《诗》之后,骚体是诗赋之宗祖,艺文之准臬。而且,屈骚包含的是一种行廉志洁的伟大精神,正如道光时蕲水范德炜所说的那样:“(屈原)匪直文章著述称盛一时,其志洁行廉,竭忠事主,尤足垂世教而励末俗。”[21]这样一来,屈原的文学成就便超越了“艺文之准臬”,而具有了文化神像的意义。顺治时孝感黄文星云:“诗变为骚,自吾楚屈大夫始,今昭然与日月争光。”[22]明末黄冈杜岕云:“屈宋以骚继经称,与日月争光。楚之振于古以此。”[23]湖北文士们皆笃信司马迁“推此志(志洁行廉)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崇高评价;而且断言,正是凭屈原的成就,楚国才在古代的文坛上振拔起来。
屈原的成就给湖北文人带来高度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激励着湖北文学的创新。明末景陵邹枚在《郢中白雪记叙》中云:“吾郢自三皇以迄战国千万年,而屈原为一人。夫以灵均为千古一人可乎?缘其事,考其心,察其著述,而灵均之品地乃见,则楚之所共尊,而天下万世所共尊也。……至性之人,无所效述,惟楚有之,至今不绝。”[24]指出屈原为千古一人,堪称至性之人,无所效述,只有我楚地之人,被屈原遗芳余韵,代生异人。康熙时夷陵王言惠认为,正是在屈原的激励下,湖北形成了唐诗“独标先进”和明诗“迭主夏盟”的光辉成就。
2.这种自信也来自楚文化悠久的创新传统。

这种自信心激励着楚地后人的文学创新。如雍正时孝感程光炬在《厀啸集宋序》中评价汉阳张叔珽的诗学主张云:“吾楚夙号多材……江永汉广,贤哲挺生。……先生(汉阳张叔珽——引者)之诗,久已雄三户矣。……天门、公安之后,又为诗场立一坛坫矣。(先生)搜罗往籍,爰集宋诗。言诗者每高谈盛唐,睥睨中晚,递至于宋几乎靡曼视之矣。夫宋岂无诗哉?……(宋诗)与开元大历诸君子并驾齐驱耶!”[27]这段评论体现了湖北文人文学批评的一种常见心态,先铺排楚地多才,贤哲挺生的传统,旋即力称作者的开拓之功。张叔珽,康熙时汉阳文人,从他评论时人程松门诗文“语必惊人,论忌谐俗” (张叔珽《程松门集序》)看,他的文学创作是追求创新的。从程光炬评论他的诗“季鹰鲈脍,托兴秋风;林泉啸傲,静对古人”看,在当时诗坛上,他很可能是得了王士祯神韵说的风气。从对待诗歌传统的态度来看,康熙时宗唐派依然势盛,慢视宋诗,而张氏认为宋诗堪与开元大历诸君子并驾齐驱。这也可以说为诗坛尚宋派的风头助了鼓吹之力。因此,程光炬充分评价了张氏在“天门、公安之后,又为诗场立一坛坫”的开拓之功。
(四)湖北文人从楚地悠久的文化创新传统中觉悟到创新的责任
楚文化悠久的创新传统也给湖北文人以高度的创新责任感。光绪时松滋雷以震在《拟集湖北诗征序例》中云:“荆楚之地,方广千里,江汉炳灵,代产人杰。”他列举一长串在文学和文化上具有创造之功的湖北人,如屈原、宋玉、景差、王逸王延寿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杜甫(按祖籍襄阳)、孟浩然、岑参、薛据、戎昱、卫象、潘大临、林敏功林敏修兄弟、“三袁”、钟惺、张仁熙、杜于皇、李云田,等等,真所谓“汇千古之骚雅,聚一时之坛坫”;然后申述编辑湖北乡贤诗作的意图:“不有表章,何昭来许?一旦殒落,允替陵蔑。姓名沦于荒榛,文字磨乎洛劫。风流精爽,沈翳厚地。后之君子,与有责焉。”[28]表示如果自己不辑录和传承楚地乡贤成果,如何激励后生?如果乡贤文献在我辈手中湮没沉埋,我们就成了后辈的罪人。无独有偶,光绪时沔阳卢靖在《湖北先正遗书序》中亦云:“乡人读此,当知吾鄂数千年之灏气英光,流风余韵……于以张吾楚帜,发扬光大,跻于不朽之林。非所重赖于后贤者乎!”[29]可以看出,楚地悠久的文化和文学创造传统,在湖北文人身上渗入了顽强的统系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以统系的延续者和光大者自许或许人。
正因如此,他们常常能从历史的使命高度定位自身的文学活动,评价湖北文学史上的每一个进步。如明末孝感夏炜在《沈大悟青云堂稿序》中评价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进步:(面对“后七子”传响趋声之徒),“公安出而救之以自然,竟陵出而救之以简远。不阶尺土,狎主齐盟。此以三户复楚者也。”[30]认为公安派和竟陵派以其文学创造复兴了楚文学。然而,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弊病却授人口实,作为楚人的汉阳李以笃遂忧心如焚,遂担起维新的使命。因此,他在《江北七子(非指前后七子——引者)诗选自序》中说:“(后七子)其弊也缛绘而无风骨。公安袁氏起而乘之,独赏清迥,钟、谭扬其波而逐其流,其弊也佻巧而无声韵。夫数君子又皆吾楚人,于是海内率以楚为口实。余与友人程子鳃忧焉,思有以正之。……(江北七子诗)于以息两家之异同,正群言之淆乱,将使王李钟谭异趋而同归,鸣我清一代之盛。”[31]明末,属于“后七子”残余力量的兴国吴国伦、京山李维桢基本维持王世贞、李攀龙的后“七子”派重格调的主张,其羽翼末流对于汉魏盛唐诗徒袭形貌,遗落真力,“缛绘而无风骨”。公安派及竟陵派相继起而排之,重视诗歌才情,但其末流又分别陷入率易失范及幽渺褊狭,“佻巧而无声韵”。因为两个阵营的干将都是楚地人,于是时人对这些文学问题的批评遂转化成了对楚人的批评。此情此景,李以笃作为楚人后生,忧心如焚,以“鸣我清一代之盛”为己任,纠偏补弊,以选江北七子之诗示法。他的诗论既重格调,亦重性情,“将使王李钟谭异趋而同归”。正如邵长蘅所说:“明季诗学榛芜, 历下、竟陵争焰互熸, 浸淫五六十年。国初犹沿余习, 江北七子出, 然后诗道寖昌。”[32]可见当时李以笃所选的《江北七子诗选》在矫诗坛六十年之偏弊,给诗坛注入活力方面,产生了很大的效益。
二、楚文化培育的湖北文人创新精神在明清时期湖北文学评论中的体现
由楚文化培育出的这种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湖北文人对明清时期湖北文学创作发展进程的评论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明前期文坛,被台阁体笼罩,暮气沉沉,亟待变革,遂出现“七子”的复古风潮。乾隆时汉阳彭湘怀云:“声诗之盛,三百年来莫楚若矣。盖楚风直质,尚气性,能不傍门户。若兴国、黄冈(谓王稚钦、伯固两公)……皆是也。”[33]认为明代楚地诗歌是发展得最好的,因为尚气性,善创造,便出现了兴国吴国伦、黄冈王稚钦等人的新成就。事实上,在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过程中,湖北有一大批才士投身这一文学改良运动,其中之尤者,与前“七子”一道的有黄冈王稚钦,嘉鱼“二李”(李承芳、李承箕),与后“七子”一道的有兴国吴国伦,京山王格、李维桢,沔南陈文烛等。他们一方面以古诗文高古宏壮的格调,矫“台阁体”平庸萎靡之积弊,另一方面,又保持清醒头脑,不走极端,在习古的同时不忘师心。王稚钦的观点偏向何景明,拟古诗颇能得古诗神髓,创作成就侔于“七子”上乘,实乃复古运动中的一大干将,朱彝尊称其“盖在正嘉之间,何景明最为俊逸,廷陈(即王稚钦——引者)之天骨雄秀,抑亦骖乘矣。”(《四库全书》别集类·《梦泽集》提要)惜其过早归田,妨了名位。吴国伦是后“七子”的干将,提倡“诗道性情”,“闳襟宇而发其才情”,强调性情。这些才士们,在明代前、中期现实难以给文学提供活力的时候,从古诗文那里寻求养分,给萎靡不振的文坛“补钙”,另一方面,又不忘重视性情,启迪着诗文发展的新方向,为公安派的挺生蓄积力量。
“七子”的复古运动,其注重古诗文法度格调的思路并没有为文学的发展指明真正的出路,久之,陷入了拟古的窠臼而难以自拔。此时,提倡性灵的公安派,以其“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干”的气概,以其回天的才力和“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创作成果,给诗文打开了一条充满生机的道路,恰如钱谦益所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34]因此,光绪时应山进士左绍佐在《荻训堂诗钞序》中云:“吾楚诗人能以气力斡回一世者,明有公安袁氏。”[35]袁氏气力宏大,一扫模拟之习,以真实的性灵代替矫饰的道德,以自然的文风代替陈言套语,廓清之功甚巨。
然而,公安派提出的主要口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本身也有缺陷,导致该派末流出现了率易鄙俗的反文学倾向,于是竟陵派起而补偏救弊。嘉庆时汉阳邱树棠云:“至明末而又有楚派者行,则竟陵钟退谷先生为之也。”[36]竟陵钟惺论诗,刻意求新。他曾说:“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或以为着论驳之者,自袁石公始。与李氏首难者,楚人也。”“(人人效于鳞),世岂复有于鳞哉?石公恶世之群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有复见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是岂石公意哉?”[37]当初后“七子”的李攀龙(于鳞)执诗坛牛耳,人人争效之。如今处在性灵派时代,人们谈诗,无不排击李攀龙而称颂袁宏道。钟氏认为这种表面的趋新恰恰是从众、守旧。其实创新正是来自批判。当初袁氏批判李氏,正是为了保持李氏的创造光辉,是保护李氏的功臣。现在自己对袁氏予以救弊,也是为了保持袁氏创造的光辉。这段话显示钟惺有着强烈的文学创新意识。邱树棠评钟惺诗云:“若其清幽峭逸,则固楚人骚怨之遗,亦自成其为楚声而已。”因为翕集在“三袁”周围的文士中,平庸之辈凑的是表面上的热闹,邱树棠认为钟惺提倡的书写独幽之感遇,探寻诗歌幽怨的真情,确实可让他们警醒,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得了骚人之旨。在这里,钟惺强调当初对李攀龙发起首难的袁宏道是楚人;邱树棠强调给袁氏发难的钟惺也是楚人。都突出了楚人的创新精神推进了湖北的文学创作。
然而,竟陵派提倡的幽情单绪又陷入幽僻、褊狭之中,将文学引入旁门,于是湖北文人们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清中期汉阳王元起借王士祯之言称许乃祖王孟谷云:“楚才踔厉,横绝古今。百年来公安浅俚,竟陵蒙昧,为世口实。得吾侄(王孟谷——引者)大才,令三湘七泽别开面目。”“衔华佩实,自名一家。”[38]认为王孟谷才大,横绝公安、竟陵之上,引导诗歌华实兼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咸丰、同治间孝感沈用增在《程维周先生诗抄序》中所言更为深刻:“当明神宗时,诗学榛芜,吾楚钟、谭二子特标性灵之旨拯其弊,说固本诸沧浪也,顾不主性情而专性灵,久之遂入于幽僻。于是登骚坛执牛耳者,以沉雄博大相矜尚而集矢竟陵,至谓楚人为厉阶,不亦太过矣乎。杜茶村山人胜国移民……诗以理性情,性情之发为忠孝,犹天之有经纬,地之有泰华也……然则诗有山人,可识性情之正;黄冈有山人,足称张楚也已。”[39]指出自明后期以来,公安派、竟陵派专主性灵,忽视性情,只关注心性情趣,忽略了胸怀和社会责任。于是杜茶村等人起而矫之。杜茶村即黄冈杜濬,清初遗民诗人,倜傥有高才,历经易代大乱,功名濩落,困居他乡,以不羁之才,写亡国之痛、兴亡之感,以及自身的忧愤,唤醒了沉埋已久的风骚精神。
清代中期,文坛风云变幻,派系迭起,如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这些派别,各走偏锋。吴铎在《龙冈山人诗钞序》中云:“自袁简斋以性灵之说倡率后进,海内靡然从风,其陋者往往束书高阁,不解风格为何语。而矫其失者,则又巑岏面目,屏黜性灵。两家率龃龉而不合。自右臣为之,庶几无所偏徇与。自来天下风气,微楚人不能开先。”[40]指出袁枚倡性灵说之后,海内风从,末流则只见性灵,忽视诗歌风格的丰富性。另一边翁方纲的肌理说则引起许多文人对学问义理的重视,却忽视了诗歌的性灵。两派执偏相攻。吴铎认为黄冈洪良品气势超越,合两家之长以成己;认为这体现了楚人开天下风气之先的优良传统。
总之,在明清时期的湖北文人看来,当时湖北甚至全国的文学发展,几乎每一步都伴随着楚文化在湖北文人身上培育出的创新精神的支持,这里不再费笔。
余论
楚文化的创新精神,不仅培育了明清时期的湖北文人,被当时的湖北文学批评界共同关注,而且一直贯通影响到现当代湖北文学。这里不妨摘录王先霈先生评论湖北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段话:“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屡屡有人敢于提出新异见解,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这类相关)文章和发言在发表的当时,都因为言人之所未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而引起强烈反响,遭遇到猛烈的批判。更加敢于提出理论异见的是胡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阵营内部,他长期发出独特的声音,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见解。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一种‘狂者’之风?”[41]这里的‘狂者’之风,就是楚文化中勇于开创的精神。
同时,我们可以由此发生引申,楚文化在湖北文学中培育出的这种创新精神,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思想领域的李贽童心说的挺出,社会发展领域的张之洞督鄂先得欧风美雨之实,政治界的辛亥首义的横空出世,等等,都应该是呼应的,相通的。特别是清末,当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的存亡危机之中的时候,楚文化所培育的这种创新精神,又一次激发湖北人勇于开拓,勇于担当。如1903年由留日湖北同乡会主办的报纸《湖北学生界》,其《叙论》云:“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今日之楚,乃因各国竞争之局势,而重其价值者也”;湖北是“吾国最重要之地, 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 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 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42]434该报又云:“中国之内, 有位置如武汉之足重者乎, 无有也。其所居者为竞争之中心点, 故其所任者为世界之重心。”该报《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云:“(湖北)无人不思有所以效其力于中国者在。夫岂有捐弃,偏视故乡, 甘使天下人士谓吾楚人皆沐猴而冠带者乎!”[42]443湖北居天下之中心,将引领民族的文明;武汉为竞争之中心,将任世界之重心;楚人纷纷踊跃报效国家,勇肩使命,绝不愿抽身事外,辱没楚人的优良传统。这些言论与后来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并取得成功,合若符契。这样看来,中华民族能从近代苦难中走出,有一份大功劳该归诸楚文化的创新精神。吴铎云:“自来天下风气,微楚人不能开先。”这话说得有勇气,也有底气。从这样的高度去看,明清时期湖北文学批评中所凸现的楚文化创新精神,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便具有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