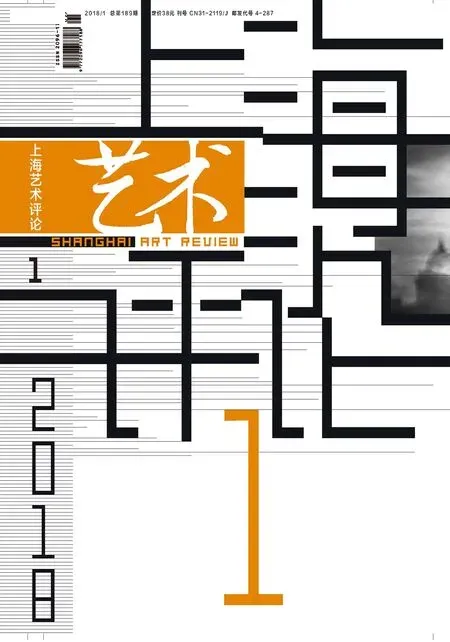《家客》呼唤家国情怀
当“知识分子尊严”“精致的利己主义”“产能过剩”“青春无悔、认知失调”等理性的语言自然而然通过角色之口蹦出来时,你不但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感同身受,并开始触发了更为深广的思考……
在所有的艺术样式里,最能打动我心灵的,话剧当先。
发此感言,乃因又一部话剧打动了我,这就是“上话”张先衡、宋忆宁、许承先三位老戏骨演绎的话剧《家客》。它讲了什么?好像没讲什么。剧情非常简单,戏剧冲突不强烈,人物关系不复杂,没有大悲大喜的桥段,只是一地鸡毛的唠唠叨叨。然而,正是在那些极其细腻甚至戏谑的对话和表演中,有一种让人刻骨铭心的沉思和温暖,渐渐融入观者心中。
由于“剧情”较弱,“说话”就尤显重要。三个老人能说出什么不同寻常的话?这个就要考验剧作家的思想和文学功底了。
试想一下,老年人的生活有什么“可写”的呢?正如剧中许承先饰演的夏满天所说,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上公园、吃饭、睡觉、发呆、吃饭、睡觉……周而复始。但是平静的生活因为“家客”的闯入而陡起波澜—当大学教授莫桑晚和丈夫夏满天正享受着如上所述的退休生活时,一位神秘人物降临到他们的生活中,他正是莫教授失去音信40年的丈夫马时途。这40年来,他一直悄悄关注着他们的人生,但始终不来打扰。直到如今得了癌症、临近晚年,才想到“缅怀故旧”,突然走入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真相并不复杂:唐山大地震时马时途在那儿出差身负重伤,随身携带的公款也因之失踪,如果当时回上海,等待他的必然是牢狱之灾;加之他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仙女”莫桑晚,所以做了一个“因公殉职”的抉择,以牺牲自己来成全莫桑晚的幸福人生……这些“情节”,都是在人物对话过程中慢慢揭示的,而不是该剧的主要结构,编剧的着力点显然不在“戏剧性”上,而在“思想性”上—通过对主人公那一代人心路历程的描述,引发观众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对事业、对爱情的思考。当“知识分子尊严”“精致的利己主义”“产能过剩”“青春无悔、认知失调”等理性的语言自然而然通过角色之口蹦出来时,你不但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感同身受,并开始触发了更为深广的思考……
一个大学资深美女教授,和她有心脏病的局长级歌唱家丈夫,以及从天而降的身患肺癌的副总经理前夫,在曾经属于前夫先辈的花园式旧居中,彼此掐架、调侃、嘲讽、和解、感悟……假如没有精彩的台词,没有极富思想力的表达,这三个走向暮年的老人很难演绎一台“老少通吃”的好戏。可是编导将话剧艺术“话”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不是简单地做一台“老年题材戏”,而是通过老人角色,承载了更多的思想命题—其思想火花,频频闪现在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对话中。当马时途鼓励夏满天放下架子,到公园教普罗大众唱歌,当马时途激发莫桑晚尽到一个社会学教授的社会责任,当马时途面临夏满天猝然离世而拒绝了“破镜重圆”的可能……你会充分体会到什么是人格和人性的力量。他们老了,被边缘化了,似乎“对社会无用了”,可是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勿忘一份清醒的责任。尽管台词不乏调侃戏谑,但其核心是非常严肃的。
编剧喻荣军说:“《家客》这部戏的构思由来已久,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戏,尤其是我父辈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命运一直是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却又精致而利已;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或是弄潮儿,却又在经济大潮中浮浮沉沉。跨入21世纪,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已步入暮年,却把自己当做了国家的客人,他们或远离政治和社会;或蛰伏陋室、冷眼旁观。在他们身上似乎已看不到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都是国家的主人,可是当他们老了,却赫然把自己当客了?他们这代人都太识相了。”
这代知识分子为何会从“主”到“客”?为何会变得“太识相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背后又是什么原因?这些问号其实是很沉重的。诚如喻荣军所说:“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从家国情怀到天地情怀,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有所启迪。”—这就是他写这部戏的初衷。由此可知,三个老人絮絮叨叨,仿佛说得不着边际,但作者正是要用这种貌似“言不及义”的方式,透露出“士大夫精神”在当代的缺失状况;同时又通过主人公的口,委婉呼唤知识分子应重拾人文传统,在任何时候都勿忘“天下为公、担当道义”的初心情怀。
天下者,人民的天下,知识分子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更是责无旁贷。“国家的主人”哪有“退休”的道理?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家国情怀永不过时。当揶揄、反讽、牢骚、失望乃至“识相”敷衍成日常景观时,这个社会一定是出问题了—知识分子不再主动关心国家命运,识相地退缩到行尸走肉,未来会好么?
我一直看重话剧艺术的思想性和启蒙性。陈独秀先生早在 1904年就有过名言:“剧场者,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戏曲者,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他的主张为整个20世纪中国话剧的启蒙和教化功能做了规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戏剧家。对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蒙,是需要借助“工具”的,话剧无疑是极佳的“工具”,它的“说话为主”的表现方式,能够最直接而有效地直击灵魂。“剧院就是教堂”(俄罗斯著名戏剧家扎哈罗夫名言)的比喻是非常贴切的。当然,启蒙也好,教化也罢,在话剧艺术中,它绝非耳提面命的说教,而是“从剧情生长出来的”。
我观看了两轮的演出。相对于第一轮的演出,为了使该剧更为紧凑好看,后一轮将“三种不同生活状态”的对比更加清晰,个别细节也做了适当的变动。我的理解,可能编导出于“好看”与“票房”考虑,使之变得更养眼、更有时代气息。不过我有一点个人见解,认为此剧未来有打造成“保留剧目”甚至“经典剧目”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此话怎讲?就是不妨滤去“不同生活状态的可能”,滤去说明与过渡的加唱,做成纯粹的“三个老戏骨一台戏”。哪怕是在小剧场里常演,也未尝不可。真正的好剧目,可能就是呈现“最简单的样子”。当然目前的版本也是不错的,总体来看,第一轮的“原汁原味”并无改变。至于后面部分的“对比”演绎,我则持保留看法:审美一旦满足,无需画蛇添足,“多余的演绎”,可能会破坏连贯的心情。
还有,此剧被称为“荒诞喜剧”也有点名不副实。作为促进票房的包装策略,似可理解,大体上也不算太离谱。其实“荒诞”的只是“时空倒转”的假设部分,而在具体演绎时,完全是正剧的格局和风格,尚算不上喜剧。不过话又说回来,称它什么是次要的,要紧的是它向观众传达了什么。
瑕不掩瑜,这是一部佳剧,至少它极大地打动了我。本文一开头,我就说,在所有的艺术样式里,最能打动我心灵的,话剧当先。这是因为,走进剧场,有时就像走进教堂,在浓浓的艺术氛围里,你屏住呼吸,与台上的主人公呼吸与共、命运相随,然后在清晰的台词里,你的心与之共振,你收获了启蒙,得到了启悟,受到了感染。这才是话剧艺术,而不是简单的娱乐!
感谢夜色迷蒙中有这样一部《家客》滋润业已干涸的心田,让我重新检视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理应背负的责任。感谢编剧和老戏骨们用一句句台词激荡了我的心,让我蓦然觉得,人生不再那么乏味,似有某种意义在召唤……感谢话剧!

话剧《家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