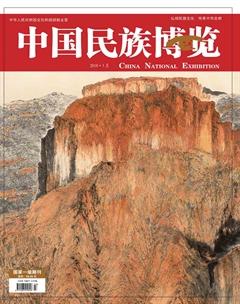浅谈中西方艺术真实观的发展必然
任紫菡
【摘要】艺术真实性问题一直是中西文论史的贯穿性问题。中西方早期艺术真实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人文观念的改变,中西方艺术真实观的壁垒限制被打破并开始融合,走向必然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西方;艺术真实观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法国19世纪伟大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说:“获得全世界文明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1],真实历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生命,而艺术的真实性一直是贯穿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几千年来,针对这一问题,中西方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古希腊时代的人们是充分信赖与认同艺术真实性的,尽管作为文学起源的神话在叙述中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和虚幻的形象,但“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2]。在神话叙述者自己看来,他们是在揭示客观世界的真相,而这也为西方文论最早的艺术观和艺术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最先为我们概括出艺术真实性问题全部内涵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肯定了艺术的本质是摹仿(现实),将客观自然作为了艺术真实的参照系统。这不仅打破了柏拉图的“理式世界”,肯定了现象世界的真实,也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此外,他还注意到了文学真实与虚构、创造、想象之间的关系,“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3]换言之,这种“摹仿”并不一定要与真人真事相吻合,艺术需要摹仿者在选择、加工、集中、概括,甚至虚构的创造过程中实现。摹仿决不仅是现实的外形,而且反映世界本身具有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才是更高的真实性。
与西方文学理论的系统性相较,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观则呈现出杂语共生的特点。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在三位一体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先秦时代对文艺本质的一个基本认识——“诗言志”,朱自清先生曾在《诗言志辨》中称之为“开山的纲领”,这也为古典文论艺术真实观奠定了基础。
“诗言志”这个命题最早出现于《左传》和《尚书》,先秦诸子也有类似的提法,《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荀子·乐论》篇云“君子以钟鼓道志”,普遍认为,诗歌表现作者的思想、志向、抱负等;魏晋南北朝时,陆机在《文赋》中又进一步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直接强调情感的抒发;到了唐代,孔颖达明确地把情、志统一起来,“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4]也就是说,“诗”产生于情感的抒发,情感产生于人心对外物的感动,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抒情。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一直被视为是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其朴素的语言、优美和谐的韵律,以及高超的写景抒情艺术手法创造了抒情诗歌的最佳典范。其中的《蒹葭》篇又历来为人所称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朔洄从之,道阻且长。朔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委婉、含蓄的意境为后来的中国文学奠定了基调。这种侧重于抒发主观情感,把文艺看作人心灵表现的真实论,就与西方古代把文艺看作是对客观现实的摹仿和再现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艺术真实观虽一致地反映出人们的理想与追求,但基本上一个侧重叙事,一个偏重抒情;一个强调客观再现,一个坦诚主观描绘;一个系统理性,一个杂言直观……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雄霸了二千余年”[5],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在“摹仿说”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镜子说”,形象地概括了艺术必须反映现实的普遍规律,这也得到了莎士比亚的赞同。莎翁认为戏剧创作必须正视现实,面向人生,就像他借笔下人物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的那樣:“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因此,18世纪英国著名评论家约翰逊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真实镜子的诗人”[6]。莎士比亚的这种创作理论,从忠实反映自然开始转向了忠实反映社会和世道生活。
这种发展趋势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发生变化,人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随西方启蒙主义运动而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等因素,成为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发动的巨大动因。18世纪后期,一位诗人兼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在剑桥大学讲学时将《毛诗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名句,翻译为“诗歌产生于人的内心情感的流露”,之后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在其《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发出浪漫主义宣言:“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样,西方真实观开始注入主观真实因素。
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这种反传统的自由精神体现得更为彻底,文学表现的对象由外在真实全面进入内在真实,文学反映观彻底突破了模仿自然和现实的观点,真实性发展出了一套主观性的标准,真实成为一种感觉、认识和表达的真实。英国表现主义美学家科林伍德在他的《艺术原理》中说:“艺术家所尝试去做的,是要表达一种他所体会过的感情。”美国现代美学家苏姗·朗格也认为:“所谓艺术品,说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现”,“艺术品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欣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7]
从侧重客观真实走向侧重主观真实,这就是西方真实观的发展过程,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艺术真实观也适时地走出了一条完全相逆的发展之路——从重主观真实走向重客观真实。“言志缘情”的艺术真实观在不断的传承和发展中,逐渐脱离了诗歌范畴走向更广阔的艺术体裁领域,如西汉前期的“愤于中而形于外”,《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唐代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北宋郭熙的“身即山川而取之”……尽管仍是各抒己见的体会和争辩,但基本未脱真实表达情感的轨迹。到明清时,艺术真实性的讨论在小说和戏曲领域达到高潮,明清美学家把真实性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强调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性,艺术的传奇性必须寓于真实性中,脂砚斋就明确提出,艺术真实性的含义就是“毕真”[8],“有情有理”[9],写出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真实情状和内在的必然性、规律性,这已经开始体现出了西方重客观真实的特点。
可以说,清末民初的小说真实观在框架上虽然承袭此前的中国古典小说真实观,但在概念上则渐染西风,这种概念的转换实际上已使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异,西方的小说真实观已经嵌入中国固有的小说真实观中,并且逐渐取而代之。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开放性思想的发展,也是缘于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强制交流。到“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来临时,传统真实观念的话语模式被彻底打破,于是,中西方艺术真实观就像两股波浪一样,不时地碰撞、交汇、融合。鲁迅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就大量运用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大量采用象征、内心独白手法来展示内心的矛盾冲突等;典型的又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蝴蝶》,一方面引用中国古老寓言“庄周梦蝶”,一方面又借重西方内心对白、幻觉、情绪、闪念等主体意识表现手法,深刻揭示主人公张思远灵魂的搏斗,这种将中西方理论结合运用的手法,使得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一言以蔽之,中西方艺术真实观就主流倾向而言,各有其特点,各有其长短。随着东西方文化话语的碰撞与交流,艺术真实观正在走向世界性的沟通与交汇,统一之下个性而开放的真实观念势必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时代的必然,更是文学真实观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557.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3]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60-61.
[4]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9:51.
[5][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缪灵珠,译.美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29.
[6]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27.
[7][美]苏姗·朗格,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21,24.
[8][9]《红楼梦》第十九回、第三十九回批语(庚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