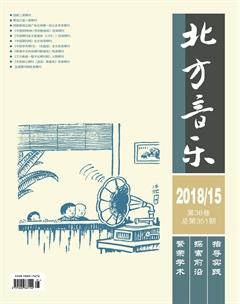论音乐中的再现性
【摘要】本文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结合音乐示例,首先分析了再现、指谓在音乐符号方面的表现,从表现手段上证明再现应用于时间艺术的抽象性;其次,探讨音乐再现性现实主义的认识误区,并借助再现性体裁与表现性体裁的比较研究,进一步阐释再现性现实主义的实际内涵;由于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间的类似,最后本文对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分析,以揭示音乐再现的独特艺术地位与审美内涵。
【关键词】再现;抽象;现实主义;语言描述
【中图分类号】G229.2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再现”一词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经围绕“再现”这一概念进行过深入探讨,诸多争论持续至今。其中,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从反映事物的主客观特征方面为再现和表现做出了判断依据,强调再现着重反映客观性特征,而表现着重反映主观性特征;程金城先生则因为再现派现实主义过度强化客观事实,曾一再解释现实主义文学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原因等。艺术再现性研究似乎是一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问,没有客观标准而言。一部艺术作品再现或不再现也许并不重要,但若从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的角度来看,对再现做出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据“中国知网”主题字“再现”搜索,可查出相关论文一万六千多篇,其中有五千六百多篇分布在语言文字、美学、哲学等文学学科,而音乐类仅有600篇。关于音乐再现性,研究者们的焦点主要聚集在两方面:一是把再现理解为作曲家的一种创作手法,是关于调式调性、音型、和声、主题等具体客观反映的研究,旨在探索再现在曲式结构层面的重要意义。如大量奏鸣曲、叙事曲体裁类作品的曲式结构分析,又如杨儒怀在研究再现之于音乐发展的积极表现过程中,得出再现为大多数曲式结构成形、演变和变化基石的结论;二是基于作品演奏,以乐谱文本——音响文本的转化过程为研究对象,把从风格、情绪、音量、音色到情感等方面的演奏最大程度上忠于原作的“音响文本”视为再现。如“再现意味著对符号化乐谱转为动态音响结构的绝对忠实”(杜晶2015年)。
不同于以往研究,笔者结合实践分析法与理论研究法,把视角转移到符号学意义上的再现,即研究音乐符号对对象的再现,客体对主体的再现。文中先后对再现的含义、音乐再现的抽象理论展开阐释,为有关音乐再现性现实主义的几个误区做出区分,并将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音乐再现的内涵及艺术价值,以期为今后音乐符号研究提供努力新方向。
一、何为再现
(一)何为再现
“在任何对符号在艺术之中或之外起作用的方式的哲学考察中,都需要先来研究再现的本质。”[1]再现比之于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然其在音乐艺术研究领域却并未获得足够多的关注度。音乐中究竟有没有再现?若有,那么再现又在音乐艺术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并将结果整理如下。当然,首先是关于再现评判标准的讨论。
1.再现不是相似
相似具有对称性和自反性,即若A与B相似,则B也相似于A,就像我们看到的一对双胞胎兄弟间的相似,一条生产线上的汽车的互为相似。但再现不是对称的,也不是自反的。一幅苏里科夫的画作《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再现了兵变失败的近卫军在莫斯科红场临刑前的悲壮画面,但临刑现场并不再现这幅画;舒伯特的《魔王》再现了黑夜中父亲带着被魔王引诱的儿子在森林中疾驰的场景,但无论从父亲、儿子还是森林来看,都无法再现这段音乐。因此,无论相似程度有多深,都不构成再现的必要条件。
2.再现不是复制
两个关于模仿的训喻误区是“要制作一幅符合实际的图画,就是尽可能地将那个对象复制的如其所是”“复制的东西是对象存在或看上去的一个方面、一种方式”。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个人,是法学家,是布里安莱沙托军校被人嘲笑的学生,是细胞联合体;达维特的画作《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山》塑造出现世英雄之形象,但看不到拿破仑对务实主义的信奉与否;披头士乐队用摇滚唱着所生活的世界,但不是全方位的世界;肖斯塔科维奇写下了《第二钢琴协奏曲》,回忆与孩童时期的儿子玩儿玩具兵的童趣画面,但钢琴的音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玩具兵的发声。你无法真正刻画出一个事实的全部方面,你如何去看待事实和你所看到的事实都受到耳鼻口舌、大脑、过去等的制约,而倘若你真的做出了一个如此这般的事实,那也不过如出售礼物一般,并非艺术。
3.再现是主动获得说明或解释,是对对象的一种刻画
艺术的模仿理论正方兴未艾,艺术创作中对于对象的再现过程无外乎是通过模仿获得某种说明和解释而不是复制一种说明或解释,而这种获得即成为艺术作品的艺术创新、艺术价值所在。在主动获得解释的再现过程中,摄影师刘易斯·海因在社会纪实照片《10岁的纺织长工,北卡罗来纳棉纺厂》中显示出自己的艺术成就;保加利亚“夜莺式”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成为了世界合唱领域的一朵娇艳奇葩。
(二)何为指谓
指谓是再现的核心。就像是对一个对象进行描述的段落,一个作品若再现了对象,那么它就指谓这个对象。指谓有单个指谓、复合指谓:文学作品中讲“狗”是真诚的朋友,既不是哈士奇狗,也不是比熊狗,既不是白色皮毛的狗,也不是棕色皮毛的狗,当然也不是从整体上指示狗这一类别,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狗——有四条腿,会汪汪叫,有尾巴;《成语词典》上的插图“蛇”,既不指谓某只蛇,也不总体指谓蛇这一类别,它是一般意义上的蛇。指谓还可以是零指谓:中国当代华人音乐家谭盾为弦乐四重奏和琵琶所作的《鬼戏》就是零指谓再现。在驱魅和复魅的反复中,听到鬼的哭泣、鬼的呼吸,然而却从来没有真正的鬼。
人们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求知”的,绘画雕塑作品也好,音乐作品也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感性的冲击,但是也总会伴随着人类的理性思考。所谓的理性思考,就是不断地去“求知”,求有所得便转化为一种快感 。什么是求知?这幅画指谓这个事物,这部音乐指谓这个对象,正如高小康在《人与故事》一书中所说:“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某一事物是某一事物”。[2]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艺术终归是与审美需求相伴的。因此,图像的种类不应以作品的指谓决定,而应视图像本身的种类决定它的指谓;音乐更应视其本身所具有的这样或那样的审美特征为类别划分标准。
(三)音乐再现的抽象理论
上文在何为再现的讨论中提到,再现是对对象的一种刻画与分类,是获得解释与说明。艺术价值产生于创作,创作需要有影响力的再现,而有影响力的再现又需要发明——对原型的所有存在方式和所有属性不停地删减、遗弃、组合,获得新表达。这一过程表明了再现过程中的主动性。毕竟所有未被再现或即将被再现的对象绝不会顺从地待在那里,露出其锋芒,而艺术者们既不会再现出对象存在的所有方式,也做不到让其所有存在属性都不显现。音乐艺术当然也不例外。音乐是有再现性的,如舒伯特《魔王》的例子,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例子,但是音乐作为一种时间维度艺术,又是如何再现四维空间的呢?再现在音乐中的地位较之于绘画、雕塑等是否还是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上述疑问,笔者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说明。
1.抽象化的再现性手段
余建章、叶舒宪曾在《符号:语言与艺术》一书中对艺术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四维空间的形体类艺术,如舞蹈、仪式表演等。这一类艺术因为有空间和时间的四维展示,因此对对象(即原型)的删减,或者说抽象的方面较少。因此,从人类的感官和思维上来讲,是更容易联想和还原对象的。第二类是舍弃时间维度的空间造型艺术,如雕塑、陶器、建筑、绘画等。这一类艺术虽说没有了“时间”的“叙述”,但还是有物理维度支撑你去想象。第三类是则是时间维度艺术,如音乐、诗歌、民间文学等。至此,所有再现仅能依靠你的内心表象去建立,如果诗歌还是有眼睛参与的话,音乐则仅能依靠耳朵去听见声音、 “看见”画面和“读出”故事。从四维空间艺术再到时间艺术,音乐中的再现手段无疑是最抽象的。
2.抽象化的再现性表达
表达之抽象,一方面体现在音乐符号表征对象的一般性上。叔本华说:“(音乐)在某种程度内可以说是抽象地、一般地表示这些情感的本质上的东西。”[3]意思就是说,音乐要表达的所有的情绪既不是这样的快乐,也不是那样的痛苦,而是从无数种快乐和痛苦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快乐和痛苦本身。音乐要表述的情况也不是具体上或这样或那样的情况,而是从各种情况中抽象出来的激发最原生感觉的表述。列维·斯特劳斯对此也发出过“音乐不依赖于任何模仿却使人欢喜”[4]的言论。再现性表达之抽象一方面还体现在音乐表征对象的“不准确”上。斯美塔娜《我的祖国之沃尔塔瓦河》中,作者用长笛、单簧管分别指代沃尔塔瓦河的两条源流,用圆号再现狩猎号角的回音,用木管象征城堡等。可是如果没有标题,你能确定音乐中的河流是沃尔塔瓦河的源流吗?又或者你能判断这是溪流的歌唱吗?同理,你又能否仅从木管主题得出所再现的城堡是红砖建筑还是白砖建筑的结论?这些自然是无法准确识别的。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音乐在再现表达上的巨大抽象性,才给耳朵的独立发展带来了可能性,让音乐摆脱了理性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大意义上的自由与音乐审美体验。
二、音乐再现的现实主义
(一)再现性现实主义的认识误区
关于再现的现实主义标准,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认为再现现实主义由作品的欺骗性所决定;另一种则认为由作品发出的信息数量所决定。欺骗性观点的持有者认为,作品只要能产生成功的幻象就是现实主义,即只要能够让欣赏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它所再现的东西或所再现东西的特征就是再现的现实主义。其实,反驳这一观点并不困难。以谭盾的《鬼戏》为例,音樂再现了鬼之哭泣与哀嚎,然实质是情感需求的完全解放,重在自我感受,是表现主义音乐而非现实主义。毕竟只要场景设计充分,就足以让非现实主义音乐具有欺骗性。就像用炸油条的声音充当淅淅沥沥的雨声完成一段电影配乐,这段配乐目的在于渲染内心的静谧却并不是再现雨天。另一种信息量决定再现现实主义的观点,同样有充分的理由给予否定。联系信息传达的编码和解码理论,一部分已被公认的现实主义音乐,如能重新建立符号系统,让新的编码与旧的编码一一对应,比如让大调(即明亮)代替小调(即阴暗)、让高音表示浅吟而不是低音等,只要这一编码成为解码者的常规习惯,那么非现实主义的音乐也就与现实主义音乐产生了同样的信息。可能你会说上述的例子绝不可能发生,但谁又能否定这是你长久以来养成的解码习惯的结果呢?
(二)再现的现实主义标准
再现的现实主义标准既不是欺骗性也不为信息量所决定,而在于成功解码的难易程度。这与再现模式的固定性及解码系统如何通行是紧密联系的。对这一标准进行解释实则并不容易,因此,笔者要再一次重申符号学的编码和解码理论。人类信息传达的过程就是表达者编码、理解者解码的过程。表达者的编码需要经历制码和发码。“制码是使讯息符号化……发码是符号形式的呈现。”[5]作曲家贝多芬想传达“告别”这一信息,于是把这一信息在大调式体系中按照大三度、纯五度、小六度的下行音程排列,组合成号角的声音用以表达告别,完成制码;当贝多芬完成《降E大调奏鸣曲》(Op.81a)这一作品,进行演奏时,发码成功。接下来就是接收者的解码过程,即理解符号信息的过程。接收者从贝多芬的音程下行进行感受到了结尾,从音程度数的变化中听出了“狩猎号角”,并联想到宫廷贵族生活,于是最终将这段音乐指谓高贵浪漫的告别。至此,解码结束,一条浪漫的告别信息得以传播。这当然是一条理想的交际传播链,编码者贝多芬掌握了大家习惯和认可的编码规则,解码者的联想、推理与编码者刚好一致。然而,在更多交际过程中,编码者对信息符号化之后,解码者却未必得到相等的信息,也就是说会产生误解。受到生活方式、专业修养、地区文化、时代特点的影响,编码者形成了与其一一对应的编码规则,而解码者却只能按照人们早已约定俗成的解码习惯,即“根据编码的符号能指形式进行一定的联想和推理,从而获得关于该能指形式的所知讯息”,当表达者与理解者符号规则不统一时,误解便也产生了。
现在,再回头看再现的现实主义标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再现的现实主义不受欺骗性和产生信息量的影响,在于解码过程的容易程度,即表达者的编码规则为众人熟知和习惯,理解者可以轻松地用已知的解码规则对作品进行解码。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讲:再现是关于编码规则选择方面的问题,准确性是关于解码信息的问题,而现实主义是关于习惯性的问题。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但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变化也会发生改变并重新养成。从这一点来看,现实主义是相对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迁移也是非常迅速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现在看来当然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音乐符号的意义,但是在当时却一度为长期习惯古典主义符号解读的世人所不解。19世纪美国人眼里的爵士音乐不同于现代的美国人,也不同于20世纪的英国人,乡村音乐、布鲁斯音乐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任何永恒的现实主义。
(三)音乐中再现的现实主义体裁
1.再现性现实主义的体裁及其来源
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再现性现实主义体裁当属叙事曲,叙事曲又分为声乐叙事曲和钢琴叙事曲两种。传统的叙事曲主要指欧洲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的叙事曲,这四国的叙事曲虽然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但都以分节歌的形式或叙述英雄史诗、或讲述民间爱情、或讲述古代神话。声乐叙事曲、钢琴叙事曲建应在传统叙事曲的创作方式之上,再现出亦幻亦真的内容,并在作曲家手里得以发展壮大。不过,说起叙事曲就必须谈及叙事诗。叙事诗是一种集民族性、戏剧性为一体的诗节式结构的对话叙述艺术,以民间故事为原型,诗作者注重刻画人物性格、人物对话和动作,故事的陈述相对客观。作曲家以这种叙事诗为载体创作了声乐叙事曲,又以声乐叙事曲和叙事诗为原型创作出钢琴叙事曲,其原型叙事诗的客观再现性决定了叙事曲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了再现性。典型的声乐叙事曲——舒伯特的《魔王》就是这样一部再现性现实主义作品。舒伯特在该叙事曲中用到了不同的音区音调、柱式和弦、快速并贯穿全曲的三连音节奏型等多种手法(也就是符号学意义上的编码),再现父亲为了拯救被魔王引诱的儿子在黑夜里骑着马疾驰,最终儿子还是不幸死亡的故事。简言之,叙事曲这种再现的现实主义体裁在民间故事-叙事曲-叙事诗-声乐叙事曲-钢琴叙事曲的过程中产生。不过,在音乐巫术说方面,也对叙事曲的体裁来源有一定解释:“接触巫术-转喻功能-象征意义-音乐的叙事性。”[6]正如我们在多部故事传说中所听,接触巫术往往借助于人的头发、衣物、指甲等对人施行巫术,这是因为接触巫术暗含着部分代替整体的规则,认为相近事物间有着相对强烈的影响作用。在这样的原则下,接触巫术对原始符号实现了转喻功能性的操作,以部分象征整体。在接触巫术之后是雨后春笋般林立的神话传说,一个个关于祖先、神灵的英勇事迹成为部落文化的象征,化身为艺术创作之典型,构成叙事曲再现性现实主义的原型。
2.再现性体裁与表现性体裁的区别
与再现性音乐体裁的来源不同,表现性体裁如幻想曲、狂想曲等,来源于模拟巫术,发挥隐喻的功能作用,以意向间的相似性实现意向转化,以音乐表达作曲家内心情感;与再现性音乐体裁的规整结构及内容上的陈述性相区别,表现性体裁以抒发情感为主,结构多以片段化存在;与再现性音乐体裁的单一动机不同,表现性体裁往往发展多个主题,形成意向的组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再现性体裁重在富有逻辑意义地讲述事情的原委,而表现性体裁依赖多种创作手法将事件加工,完成音响意向的组合。
三、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
从表达模式的含义来讲,“音乐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的复杂的听觉符号系统”,[7]既相似于语言符号,又与语言符号相区别。
(一)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的共通之处
音乐再现需要让音乐符号和对象这二者间具有指谓关系(第一章已论述),指谓一个对象,就要描述这个对象;语言对对象的描述同样要指谓这个对象。音乐再现和语言描述共同归结于指谓之下,因此,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就产生了极大的关联。
1.音乐再现与语言描绘都要经历选择、变形的抽象过程,完成对对象的解释和说明,并彼此间相互影响
没有经历选择和迁移,音乐与语言就不能被称为艺术。同理,音乐再现和语言描绘作为人类艺术表达的重要手法,就必须经过剥丝抽茧,对被表征客体的某些特点进行诠释。在此进程中,若艺术家们通过惯有的符号体系去再现事物未被发现的新方面,或者将事物早已被认知的一面用非传统的符号去组织和展现,那么此时的音乐再现或语言描绘便成为了富有艺术价值的创新性艺术。毕加索采用新奇而不被习惯的“土著面具式”象征符号为美国文学家、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所作的肖像,曾一度被人评价为最不像斯泰因本人的画像,其与女主人气质之高度相似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为业界所正名;贝多芬在序曲《艾格蒙特》中用激烈的和弦再现西班牙朝廷的阴险;“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诗人白居易寥寥几句就写出莺歌燕舞、繁花似锦的早春景象,从“渐欲”和“才能”二词之中,我们更是看出此番春景是诗人主观选择的结果,是诗人個人对所见之春的解释说明;同样是描写春日,宋朝晏殊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却深深道出诗人惆怅之情。无论是毕加索的变形、贝多芬的迁移,还是白居易、晏殊的选择,它们都是作者用来对对象进行解释说明的手法,并在此之后成为当之无愧的永恒艺术之作。
2.音乐与语言大多时候通过表征客体本身进行分类,偶尔又可以根据客体与对象间的指谓关系,即单一指谓模式、复合指谓模式或零指谓模式进行分类
表征客体即将事物艺术性再现的载体符号,按此标准执行划分后,音乐中的可分类别有叙事曲、革命曲等,语言中的可分类别如诗歌、散文、小说等。而按照指谓关系进行划分的实例如下。吴祖强、杜鸣心先生创作的《水草舞》,在引子部分再现了纤细柔软的水草在水中微微摆动的场景,而这水草既不是指生长在云南的水草,也不是长或短的水草,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水草,是一种复合指谓;三国时期的曹植用“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再现虚拟人物——体态婀娜的洛神,是一种零指谓;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是一种单一指谓,仿佛描绘出了多瑙河河面上的跃然灵动。
3.每一种音乐再现和语言描述的应用或分类,都有与其相对应的符号系统——编码、解码系统,而符号系统的选择是相对自由的
各个时代的艺术家们运用自己所熟悉的艺术符号,将情感或真实的世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完成个人的编码,并最终在人们的欣赏与求知中获得普通的解码,这一点毋庸多言。
(二)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的差别
符号体系同时包含了符号本身及其对对象的释义,音乐再现、语言描述二者之间,除了符号体系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音乐再现是一种经过自我选择的再现,倾向审美性功能;语言的具体与确切使得语言描述不得不承担再现客观世界的任务。以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与歌德《艾格蒙特》戏剧的比较为例,贝多芬在众赞歌响起,再现英雄艾格蒙特之死之后,并没有结束整段音乐,而是加入颂歌,象征真正的英雄永垂不朽,继续活在世人面前;而在歌德的戏剧中,艾格蒙特伯爵最终因反抗压迫被处以死刑,离开了现实世界。“原始人类或许用过前音乐声音,可能是一种准音符的形式出现的,用以表达情感;还或许用过周期性的声音结构,用以在各式各样的身体动作之中确保同步性。但是,只有在这些声音之结构被赋予了抽象的、无涉的意义之时,这些声音结构方才成为音乐。”[8]汉森所讲正可以说明,音乐再现在经历高度抽象之后便产生因无序而高度凝华的审美性。然而,尽管语言符号一样需要抽象,但传达结果终归是具体的,也因此语言符号需要更多地承担描述客观世界的任务。
以上是笔者对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所作的区分,当然,当前也有不少学者因音乐再现过程中对语言描述的依赖(音乐再现最终还是要以语言为“媒介的媒介”来解释与传播),认为音乐再现的本质就是语言描述,意即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不过,就像音乐再现需要音乐符号而语言描述依赖语言符号一样,音乐再现与语言描述一定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才造成二者在一般意义上的不同,不过其本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语
再现在艺术领域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从舞蹈形体、哑剧等四维艺术,再到雕塑、建筑、绘画的空间艺术,从诗歌、文学再到音乐,再现总是伴随着艺术的成长与变迁。人们在寻找再现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在对符号与对象指谓关系的求知中,获得快感。音乐信息大多时候无法直接告诉人们任何具体的形象,其再现也无疑是最复杂的、最抽象的。本文运用符号学相关原理,在音乐实例的基础上,对包括再现、指谓、现实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概念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研究,找出了现实主义体裁的来源及其特点,并对再现与语言描述的联系及区别做了初探,以便为今后的音乐符号研究提供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美]纳尔逊·古德曼,彭峰.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6).
[2][美]高小康.人与故事——文学文化批判[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42).
[3][德]叔本华,石冲白.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2:361.
[4][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顾嘉琛.看·听·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85).
[5]黄华新.符号学导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36).
[6]李小诺.音樂表述中的表现性——以幻想曲、随想曲、狂想曲为例[J].音乐艺术,2010(04).
[7]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105).
[8] Finn Egeland Hansen. Layers of Musical Meaning[M].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06(28).
作者简介:江俊叶(1995—),女,深圳大学音乐与舞蹈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音乐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