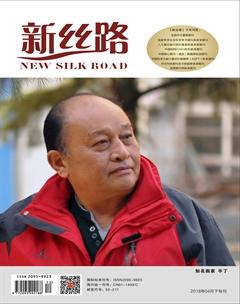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麦克尤恩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谢一榕 刘一静
摘 要:麦克尤恩在他的处女作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他通过压抑的环境、扭曲的人性、两性的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割裂来表现出一种“末世”般的荒凉感。这些元素的挖掘与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不谋而合,通过后者可以更容易的解读这部小说怪诞黑暗外壳下的某种核心内涵与价值倡导。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麦克尤恩;性别
生态女性主义正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脱胎于“生态主义”中。工业化后,社会的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但与之而来的生态破坏也随之加剧。马克思曾经这样预言19世纪的景象:我们的一切发展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主义”研究的火热也不足为奇。“生态批评的活力还在于它虽然立足于文学但决不拘泥于文学, 而是把批评的触角伸向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 比如环境伦理问题的提出。 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把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与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等联系起来, 特别是将女性与动物进行类比 , 将二者同视为父权制下的牺牲品。”【2】女性生态主义批评的崛起,也为我们研读文本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在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从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性别间的冲突,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子。
一、男权话语下对生态的破坏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和环境的关系变成“征服—被征服”的二元对立,人们不是将自然作为一个平等的客体相处,而是作为索取资源的对象,变本加厉的加以掠夺和改造。不仅原有的自然风貌被破坏的千疮百孔,被工厂和烟囱占据的城市中也呈现出一种“水泥荒原”的景象,人类这种对自然的支配如同男权话语下男性对女性的强权压迫,在麦克尤恩的小说里,这中冲突通过对肮脏颓败的都市景观的直接描写而表现出来。他在《家庭制造》里描多次使用“广袤荒凉”、“工厂”与“高压电缆”等意象,从环境上就带给人一种对工业的排斥感和恐慌感。这样的破败的景观是主人公的工人父辈们年年月月疲惫穿梭的,也是年少的他和朋友玩闹游荡的场所。正是在这里,白天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重复生产线上的枯燥,下班后去黑暗肮脏的酒馆讲“下三滥”的笑话与的恶俗的传闻,孩子们穿梭在这冷漠低俗的环境中自然也成长成一个个人性沦丧的“小野兽”。
在《蝴蝶》中,更有大段的文字来描写肮脏的运河:“运河是这附近唯一的一条蜿蜒水道。走在水边总能给人不同感受,哪怕是工厂区背后这条又黑又臭的水道。俯瞰运河的工厂大部分已经废弃,没有窗户。你沿着纤道可以走上一里半,通常一个人也碰不到。途中会经过一处年头久远的废品站。”,“久而久之,周围的篱笆全都被当地的孩子糟蹋殆尽,如今只剩下大门还没倒。废品站是这一里半路上唯一的景致,其余路段全都紧挨着工厂后墙。”【3】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性变得暧昧不明,主人公为了一己私欲残忍的诱拐、杀害女孩,而路上一群少年的也以无比残忍的手段虐杀了一只猫:“有一群男孩围立在一堆点燃的火边。他们像是一伙的,都穿同样的蓝上衣,剃平头。据我判断,他们正准备活烤一头猫。烟在他们头上凝固的空气中悬浮,在他们身后废品层层堆积像座山。他们把猫的脖子绑在过去拴狗的那根木杆上,猫的前肢和后腿也被捆在一起。他们用几块铁丝网做了个笼子架在火上。我们走过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扯着猫脖子上的绳子把它往火里拽。”【4】冒着黑烟的烟囱和肮脏的运河是人类对自然的亵渎,毫无人性的滥杀无辜则是对人性的背弃,自然风貌的破坏和人性道德的沉沦在麦克尤恩的笔下都通过末日式的描写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除了《家庭制造》和《蝴蝶》,这种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带来的恐怖氛围在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有出现,比如《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蜗居在码头上方的青年男女,春末微风和空气让他们觉得放松,而當夏季闷热的空气混合着腥臭的气温从码头下涌上来时,他们都变得烦躁不安。麦克尤恩正是通过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来批判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恶劣的生态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从而引发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崩塌。
二、女性话语下和自然的亲近
苏珊·格里芬说过:“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 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 我们就是自然。 ”【5】女性和自然生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因为自然孕育人类,而女性则承担着繁衍生息的任务。在许多文学文本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女性对自然的亲近和对生命的尊重,这和男性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极强的反差,也是女性生态主义所指出的“性别与生态的联系”。
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麦克尤恩除了描写压抑衰败的生态环境,还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但是相较于他笔下的变态和杀人犯男性,他把带有希望和光芒的描写都给了女性。在《立体几何》中敏感又渴望爱的梅茜,《家庭制造》和《蝴蝶》中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夏日里的最后一天》温柔善良的珍妮以及《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充满母爱光辉的西瑟儿……她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立体几何》中的梅茜因为丈夫的冷落而敏感烦躁,当她彻底放松下来,充满爱意的时候,想到的是“人行道上的山毛榉、接骨木”、“果汁饱满的黑莓”和“河边遍布落叶、蝴蝶飞舞的小天地”……《蝴蝶》里小女孩被诱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想突破灰暗环境的束缚去运河边上看一看主人公口中编造出来的蝴蝶,《夏日里的最后一天》乐于助人但因为肥胖和自闭被排挤的珍妮,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带着婴儿艾丽斯和“我”穿过树林,到河里的木船上无忧无虑的谈天说地……在这部小说里,自然的美只有女性和孩子能顾欣赏,而人性中好的一面也自然的被放置在她们身上。甚至她们会对万物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保护欲与责任感。
在《短篇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当发现那个给“我们”带来无限恐慌的老鼠怀着一胞孩子时,“西瑟尔跪在老鼠旁边,阿德里安和我像保镖一样站在她身后,那情形似乎她拥有某种特权,她蹲在那儿,长长的红裙子铺满四周。她用拇指和食指分开老鼠妈妈的伤口,把袋子塞进去,合上血肉模糊的皮毛。她继续跪了一会儿,我们默默地站在后面。然后她把几个碟子从水槽移开好洗手。现在我们都想到外面去,于是西瑟尔用报纸把老鼠包起来,我们裹着它下楼。西瑟尔掀开垃圾桶的盖子,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去。”【6】这种对生命的平等与尊重正是源自女性和自然天然的联系,她们既是自然之美的发现者也是生命的守护者。如果将这种联系割裂开,女性的灵动与独特也就不复存在。还是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当西瑟儿找到一份工厂的工作时,原本惬意自然的描述改变了:“那是河对岸其中一所没有窗户的工厂,生产罐装水果和蔬菜。每天十小时,她要坐在机器轰隆的传送带边,不能交谈,抢在罐装之前把腐烂的胡萝卜捡出来。”【7】工厂像一个巨兽,将性格与生命力在流水线上吞噬殆尽,而原本美丽洒脱的西瑟儿变成“她的罩衣被机油和泥巴玷污,散发出异味。”【8】,所有的美都在工业中被变成了废料。麦克尤恩也借此来表现出自然和女性同生一体,工业化的压榨和污染,给两者带来的只有“美的毁灭”。
三、两性关系与环境的冲突
女性生态主义的范畴中不仅探讨了生态问题,同时也提到了性别问题,女性主义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文本分析的角度。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有性别与生态的联系与冲突,还有性别本身的冲突。在男权话语中,环境在和人类交锋的时候处于弱势环节,女性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除了正面描写生态被人类支配和破坏的景象,他还通过女性被敌对和侵害的无助来展现“男性中心主义”对自然界和女性的强权压迫。
在《立体几何》中,丈夫只醉心于祖父留下的日记,除此之外既不关心外部环境也很厌倦妻子梅茜。梅茜试图将丈夫拉出逼仄的世界,但所有的交流和接触的尝试都被一一拒绝,甚至在矛盾激化后丈夫不仅没有反思,还诱骗妻子进入他设下的陷阱,彻底从现实中消失。 《家庭制造》中妹妹对哥哥不设防备,哥哥却一直厌恶妹妹“干瘪”的长相,并在性欲来临时毫无愧疚感的“诱奸”了她。更尖锐的是,在麦克尤恩的笔下,受压迫的一方能够做出的反抗是极为有限的,无论是夫妻间尝试沟通的举动,还是女孩们对施暴者的哀求统统都是徒然,就像生态环境在工业的时代只能接受钢筋水泥的侵害和破坏。
但或许人类与自然的割裂、男性与女性的对峙也并不是那么无解,尽管麦克尤恩在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绝望和恐怖,但提供了一种途径来弥补,就是重拾“平等与尊重”。在《夏日的最后一天》中,珍妮和“我”有一种无形的牵绊,尽管她胖的连“我”也惧之三分,但“我”并不排斥她反而尝试着接纳,并和她渡过了相当愉快的一段时光,这种“平等与尊重”的友谊最后虽然因为可能的死亡添上一抹灰色,但并不妨碍两个孤独心灵之间的碰撞带来的感动。在短篇《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文中,因为那只怀孕的死老鼠,西瑟儿和“我”终于选择了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西瑟儿决定辞去工厂麻木枯燥的流水线工作,而我也放掉了那只奄奄一息的“鳗鱼”。或许那只死去的母鼠代表着他们过去的生活,决心释放鰻鱼的那一个瞬间,就象征了他们对生活的重新拥抱,西瑟儿和“我”不再是和别人相同的,在工业化背景下被异化的人,而是重新找回了自我,踏上了新的生活。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荒诞恐怖的外壳里实则包含着多层次的反思,对“人与生态关系的反思”,“对异化的人的反思”以及对“人类前途的反思”。他尖锐的指向男权话语下生态与性别的对立冲突,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反思工业化带来的人的生存危机,以及性别对立中女性的弱势地位。但在这看似绝望的背景下,麦克尤恩仍给我们讲述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是女性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与尊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2]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2年03期;
[3][4]伊恩·麦克尤恩:《蝴蝶》,《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09月;
[5]苏珊·格里芬:《女性与生态:男权语境下的压迫》,New York:Harper&Row,1978;
[6][7][8]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09月。
作者介绍:
谢一榕,女,西安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刘一静,女,硕士,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